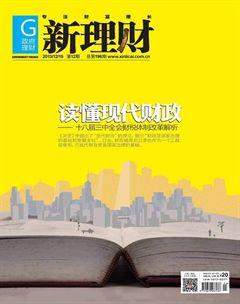古代分稅制嘗試
史衛

1994年開始啟動的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迄今運行已近20年。新一輪財政改革已如箭在弦,大家紀念分稅制改革20年,贊嘆其成就,總結經驗教訓,探索如何進一步深化和完善分稅制財政體制。毋庸諱言,當年的分稅制改革主要借鑒西方,我們這里想試著追溯一下分稅制的本土資源,希望對今天的財政體制改革也能有一定借鑒意義。
秦漢:皇室與國家的雙元架構
如果探索西方現代分稅制的源頭,可以追溯到中世紀。當時歐洲列國處于封建時代,國王之下還有各級領主,他們經過各種博弈,形成按照稅種將國家財源在各級政府間劃分的體制,并用法律的形式規范各自的權利、義務與責任,此后在封建體制解體之后,又經過近代文明的沖擊,逐步和市場經濟體制結合而形成現代分稅制。
同樣,中國最早的分稅制也可以追溯到西周時代的封建制度。在封建體制下,財政必然表現為某種分稅形式。當時周王的治權只及于直屬領地的王畿地區,而對廣大的封國并不直接管理。周天子的財政設太府管理,表現出家計財政的特點,支出主要限于王室穿用、周王宴請賓客、制造宮室車輦器具、賞賜臣工、祭祀天地祖先山川、飼養牲畜、王室玩好等王室費用,其收入主要包括王室擁有土地的田租、關稅、商業稅、產業稅、山林川澤收入,各封國的貢品等。對于國家財政支出最大項的官俸和軍費,是通過封建的方式來解決,也就是分封各官員一定量的土地,以其田租為俸祿,而受封者也要承擔一定的軍事義務,用當時的話說就是“分田制祿”和“軍賦出井田”。
到了戰國時代,各國內部逐步形成專制集權制度,土地不再分封,而由君主直接管理,征收田租來支付官員薪水和軍費,也就是“賦祿以粟,案田而稅”。這也就出現了一個新的國家財政管理機構,由原來負責記錄和保管分封文書的“內史”管理,成為“治粟內史”。原來的財政機構太府,逐步演化為王室財政的管理機構“少府”。
秦漢一統,整理制度,形成了國家財政與皇室財政的雙元架構,將國家的全部稅收按照稅種在國家和皇室之間進行劃分,各自承擔一定的支出責任,即“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于天下之經費”。劃給國家財政的稅收主要有農業稅和人頭稅,劃分給皇室財政的和各級封君主要包括王室和封君土地的地租和各類工商雜稅。其劃分標準是對此前封建體制的延續,并不科學,所以皇室財政的收入遠遠高于國家財政的收入,還要經常補貼國家財政使用。東漢時進行改革,統一了國家財政,少府收入除部分皇室產業收入外,由國家財政劃撥,支出僅限于皇室自身生活所需。
南北朝:南北不同的分稅制
東漢末年,天下三分,西晉短期統一,南北再度分裂,形成南北朝。由于東漢末年的長期混戰,原有的財政體制完全崩潰,南北朝都在戰亂中,開始重建國家財政體制,也出現了不同的分稅制嘗試。
南朝由于世家大族勢力強大,政府在與北朝對峙中,不得不對世族勢力有所讓步,在財政體制上,就表現為某種形式的分稅制。其特點有三:一是分稅。中央稅主要是田租、戶調,以及市稅等。地方稅除了供應地方官員俸祿的“祿米”、“祿絹”之征外,還有各種工商雜稅和傳屯邸冶專利收入等。雖然在中央稅和地方稅中都有商稅,但是商稅不是共享稅,中央是統一征收的市稅,地方是在此外征收的其他名目的商稅或附加稅。二是分機構。為了保證中央稅收,劉宋政府開始在各地方設臺傳,派出臺傳御史控制。州郡臺傳各有倉庫,儲備國家稅收收入部分。三是分權。地方建設費用,如教育辦學、水利興修、救濟流民基本都由地方負責支出。有些時候,地方長官可向中央政府提請資助,也可以由國庫調撥一部分,然后地方再配套一部分經費。
當時戰亂主要集中在北方,經濟破壞特別嚴重,到北魏統一北方時,政府所能依靠的還主要是田賦,主要征收糧食絹帛等實物,工商雜稅很少。所以北朝雖然對南朝制度多所模仿,但卻不可能實行像南朝那樣的分稅制。北朝當時實行了一種統收分成制,就是統一征收田賦后,再在中央和地方間按照一定比率進行分配。其分配不是按特定比例進行分配,而是按照戶等進行分配,“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當時人民按照財產的多少分為三等九品。用戶等作為分配比率,主要是從運輸角度考慮,讓不同戶等承擔不同距離的運費,也是利用稅收杠桿調劑貧富的措施。這個分配比率因各地情況不同,可能各有差異,但總體上是中央拿大頭,地方拿小頭。
唐朝:“分天下之賦以為三”
唐朝建立后,又繼承北朝稅收三分之法,給予地方一定分權。唐前期史料有限,幸有許福謙先生在吐魯番文書中找到2件收支法律文書,進行了闕字填補、考證的工作,把當時租庸調三分制清晰的展示在我們面前。唐中期租庸調制瓦解,實行兩稅法,三分財政體制還繼續延續。唐憲宗時的宰相裴洎在議論兩稅之前的三分制時說:“先是,天下百姓輸賦于州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元稹的《錢貨議狀》說:“自國家制兩稅以來,天下之財限為三品,一曰上供,二曰留使,三曰留州。”前后的繼承性很明顯。
“上供”是指上供中央財政的部分;“送使”是送歸所屬的節度使和觀察使的部分;“留州”是留存本州的部分,以供地方開支之用。唐代三分比率和北朝不同,是按照對中央地方支出所需進行分配。戶部司根據計帳折算來年收入,金部司根據各地上報都帳核實所需支出,度支司綜合收支數據編制預算。地方所需支出包括官員工資(官祿、料錢、衣糧食等)、行政費用、公共建設費用、交通運輸費用、宗教費用、禮儀費用等。
根據《通典》記錄,我們可以知道兩稅法之前的三分比率大體是:粟歲入2500余萬石,上供1000萬,占40%,留州500萬,占20%,送使及留州儲備1000萬,占40%;布絹綿2700余萬,上供1400余萬,占52%,送使留州合計1300余萬,占48%。兩稅法實行初期的三分比率是:收錢3000余萬貫,上供950余萬貫,占32%,送使留州2050萬貫,占68%;收米麥1600萬石,上供200萬石,占13%,送使留州1400萬石,占87%。
古為今用
這些制度創新不僅對當時的社會經濟產生重大影響,而且對今天財政體制改革的深化也具有借鑒意義。
一是不同時期的分稅制雖然背景、目標都不相同,但都在歷史上產生了積極作用,促進了地方經濟的發展,在傳統中國高度集權的財政體制中做出了可貴的嘗試。
二是分稅制不僅是各級政府之間的分稅,而應和相應的責、權、利相結合。由于古代事權缺乏明確的劃分和問責,常出現缺位和越位現象。很多公共事務都得依靠地方官的自我道德約束。如東晉時規定地方每千戶就得建一小學。庾亮任職武昌,從地方經費中撥付興辦了,但他離職后,繼任者不再撥款,學校也就只能廢棄。
三是面對未來進一步的分權改革,一定要建立強有力的監督約束機制。南朝給予了地方較大的財權,但是由于約束監督力量有限,一些地方政府濫用職權,產生不少腐敗案件。由于有了一定征稅權,一些貪官更是無限加稅,各種名目的稅層出不窮。梁竟陵太守魚弘曾宣稱:“我為郡,所謂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谷盡,村里百姓盡。”
四是唐代將分稅比率納入國家預算,根據科學測算進行調整,也是一個可供借鑒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