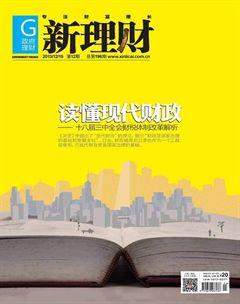執行力雙面觀
史可
政府與市場,一個是“有形的手”、一個是“無形的手”。
備受矚目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再次理順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而早在9月30日,國務院公布了《關于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的指導意見》,這被外界解讀為中央政府簡政放權思路的延伸,即“市場能辦的,多放給市場。社會可以做好的,就交給社會”。只有市場和社會組織做不了或做不好的,政府才應插手。
決策層對于政府和市場關系的頂層設計已經非常明晰,但是頂層設計的另一端——政府和市場的執行力如何,尚且未知。不管怎樣說,“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樣的頂層設計不失為是對于地方政府執行力的考驗,也是對于市場力量的一種檢驗。
拷問地方政府執行力
改革改什么?改革就是改革政府自己,把錯裝在政府上的手還給市場,強化政府的公共服務的職能,打破行政性壟斷,對權力運行進行有效的監督,減少政府直接干預微觀經濟活動的行為。
李克強總理不久前在地方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要求,地方政府要重點抓好“接、放、管” 的職能轉變。
接,就是接好中央下放的審批事項。中央明令取消的,要不折不扣地放給市場、社會,不得截留。
放,就是把地方本級該放的權力切實放下去、放到位,特別是對不符合法律規定、利用“紅頭文件”設定的管理、收費、罰款項目應一律取消,決不能打“小算盤”、搞“小九九”,防止“上動下不動、頭轉身不轉”。
管,就是把該管的管起來、管到位。在減少事前審批的同時,加強事中事后監管,規范監管行為,克服隨意性,著力構建統一開放、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讓創業“火”起來。
地方政府的權力自上個世紀80年代中央向地方放權讓利集中擴大,地方的積極性得到提高,然而經過二三十年的發展卻似乎走向了個極端。
近幾年,中央的一些事關國計民生的大政方針難以在地方落實。盡管中央反復強調加強各級政府的執行力建設,但是政令不暢、陽奉陰違的現象仍然大量存在。
具體表現在,地方政府諸侯經濟越來越嚴重、插手市場經營土地、盲目依靠投資拉動為主的經濟增長方式、節能減排落實不力、食品安全問題百出、過度干預經濟造成地方債務難以扭轉等等問題。
RET睿意德沈陽公司總經理梁煒驊對記者表示,地方政府的改革是重中之重,確保某些資源有效的回歸市場就一定要減少地方政府的權力干預。
近幾年,地方政府高度依賴土地收入來經營城市的模式推高了地價和房價。很多地方政府都得上了“土地病”,導致房地產發展綁架了城市建設,也綁架了地方政府。
2013年初,中信建投研發部曾針對九大城市2012年1-11月的數據,做了一個土地出讓金與財政收入的統計。數據顯示,在土地出讓金與財政收入的占比中,6個城市超過了40%。據了解,一個年財政收入為200多億元的西部城市,其年經營土地的收入竟超過了100億元。
就連2013年上半年最嚴厲的調控政策落地之后,土地市場也絲毫未見冷卻的跡象。根據我愛我家的統計數據,2013年前6月,全國306個城市共交易土地15493宗,土地出讓金達1.13萬億元,同比大幅增長60%。其中北、上、廣三地經營性土地出讓金已超1739億元,接近去年全年1934.92億元的水平。
如此情況下,又如何寄希望于地方政府能夠有效執行中央政府的房地產調控政策呢?
梁煒驊認為,“房價越調越高,地方政府應該承擔重要責任。但是不能完全把當前房地產的責任都歸咎于地方政府,妖魔化地方政府不能解決實際問題,畢竟地方政府自己也承擔著維系一方生存的重任。”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貨幣金融系助理教授俞平康認為,破解當前地方政府依賴土地政策的沉疴痼疾最主要的是財稅改革要跟上。短期內地方政府的改革執行情況不可能有大的突破,依然有可能依賴土地財政,因為中央和地方的財稅體制重新分配是需要時間的。“財稅改革不僅僅是觸動各方面的利益,也觸動了中央的利益,可以說中央的斷腕改革,這對于新一屆政府的執行力也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地方政府的職能既是一種權力,更是一種責任,執行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職責。作為頂層設計執行中的最基礎、最直接的環節,地方政府一旦某一環節執行不力,勢必宣告中央政策落敗。
著名財經作家、藍獅子財經圖書出版人吳曉波在近期的一次公開活動中表示,“《決定》中的60條能實現一半甚至是三分之一的話,對于中國都將是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
市場本身就是一種力量
對于很多期冀改革的人士來說,十八屆三中全會無疑是鼓舞人心的。“市場在配置資源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全新提法,可謂是一個深刻的理論突破。我們不禁要問的是:如何保障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政府放權讓利、減少直接干預,加大市場準入之后,市場這只手會不會變得有執行力?
俞平康預計金融市場的執行力會很強,因為利率市場化等金融市場各項改革理念是為大家所共識,應該能把過去十年“落下的課”給補上了。
在近期的一些活動中,很多專家學者、企業家都對市場自身的“力量”給予了肯定和樂觀的預期。
吳曉波在近期的公開活動中發言稱,市場的力量都是被人民激發出來的。他認為有兩個客觀的力量推動了今天的改革,一個是技術的力量,另一個是危機的力量,中國的改革有一個重大的特點,就是被動的改革,每一個改變的時間點都是國民經濟到了一個很不堪的地步。
另外吳曉波表示,也應該看到35年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力量,好多地方的經濟發展都是在地方政府的容忍下推出來的。以溫州為例,“90年代我去溫州調研,那時候溫州所有的東西都搞股份制企業,搞地下錢莊,搞民營參與資金,搞城鎮化建設,每件事都是違反國家法律的,一切的改革都是從違法開始。”
對于市場的力量有多大,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在近期的某論壇中感慨道,在市場化改革開始之前,國家沒有放開糧食政策、糧票異常緊俏的情況下,我們都有能力去發展飼料企業。“那時候我們冒著非法的危險用鵪鶉蛋和雞蛋去換飼料糧票。”
劉永好認為市場化改革開始之后,市場化運作的企業的巨大力量立刻凸顯出來。據他介紹,在1992年到1994年,市場化啟幕之后,那些手握糧票的國有飼料企業都倒閉了,而我們卻蒸蒸日上。我們收購了三十多家國有企業,是當時收購國有企業最多的一家。目前這30多家飼料廠全部都健在,而且發展得都很好。其余七八十家沒有與我們合作的,全部都倒閉了。
另外,建設一個充滿活力的市場,政府為市場參與主體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法治市場環境是為必要。
對于當前的國企和民企地位不平等的問題,在劉永好看來,這是地方執行不力造成的。“實際上我們幾乎所有的民營企業都遇到同樣的問題,當公司出現問題的時候,比如外面有什么資產流失到法院告狀的時候,往往被受理的幾率小很多,而國有企業被受理的幾率就大很多,而這就是不平等。”
著名法學家江平分析稱,國營企業和民營企業確實是處在不平等的地位,不僅不平等,有些地方還很不平等。比如在資源方面,國有企業使用國有劃撥土地,無需自己出資,而民營企業的土地由國家出讓才能夠取得。“三中全會提出了要開放,很多的領域允許民營企業進入,關鍵在于怎么落實?過去國務院通過了幾次的決議都沒有落實,那么通過三中全會的決議能不能夠改變這個不平等的局面,只能拭目以待了。”
俞平康總結稱,改革是一盤棋,同時改革也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目前中央改革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深化改革小組的成立也可見中央改革的決心之堅決,但是具體如何落實各項改革,落實得效果如何,需要一步一步來,這其中當然少不了和既得利益集團的協商和溝通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