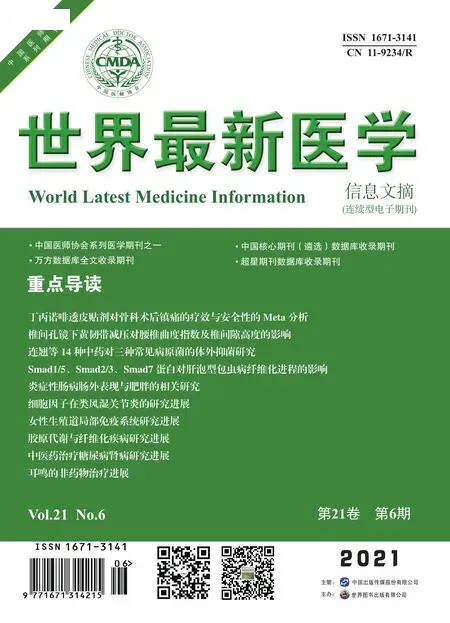iNKT 細胞在腫瘤免疫調節中的作用及機制研究
李婕,王俊秋,王彤敏
(1.昆明理工大學醫學院,云南 昆明 650000; 2.昆明理工大學附屬醫院/云南省第一人民醫院 普外二科,云南 昆明650000)
1 iNKT 細胞
自然殺傷T細胞(natural killer T,NKT)因其兼具NK細胞(natural killer cell,NK)特征和T細胞特征而得名。NKT細胞可以被分為Type I NKT細胞和Type II NKT細胞兩個亞群,其中Type I NKT細胞也叫做恒定自然殺傷T(invariant natural killer T,iNKT)細胞,可識別主要組織相容性復合體I類分子CD1d 1呈遞的脂質抗原,是經典的NKT細胞[1]。
作為經典的NKT細胞,iNKT細胞具有明顯的NK細胞特征和T細胞特征。iNKT細胞的T細胞特征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同T細胞一樣,iNKT細胞也由CD4+CD8+胸腺細胞發育而來[2];另一方面,iNKT細胞表達T細胞譜系經典分子,包括CD3、T細胞受體(T cellreceptor, TCR)以及部分iNKT細胞表達CD4、CD8等,所以NKT細胞屬于T細胞亞群[3]。在小鼠中已經鑒定出iNKT細胞的三個主要細胞群:NKT1,NKT2和NKT17細胞,可以通過它們的表型,轉錄因子和產生的細胞因子來區分。在體外刺激時,胸腺NKT1,NKT2和NKT17細胞產生干擾素γ(IFN-γ),白細胞介素4(IL-4)和IL-17[4]。與傳統T細胞表達高度多樣性的TCR不同,iNKT表達的TCR具有高度保守性。在小鼠中,iNKT細胞的TCR由Vα14-Jα18與Vβ8.2、Vβ7或Vβ2組 成;在 人 類中,iNKT細胞的TCR則由Vα24-Jα18和Vβ11配對組成,CD3+Vα24+Vβ11+細 胞 為 人 類iNKT細 胞[5]。正 是 由 于iNKT細胞表達的TCRα鏈具有恒定不變的特征而被命名為恒定自然殺傷T細胞。此外,與傳統T細胞通過TCR識別由MHCI和MHCII提呈的肽類抗原不同,iNKT細胞識別由MHCI樣分子—CD1d提呈的脂類抗原,CD1d主要表達在抗原提呈細胞上。α-半乳糖酰基鞘氨醇(α-Galcer)是人工合成的iNKT細胞的經典抗原,iNKT細胞的內源性抗原現在還不夠清楚,而且熒光素標記的CD1d-α-GalCer四聚體也被廣泛用流式來鑒定iNKT細胞[6,7]。
iNKT細胞具有經典的NK細胞特征。比如,部分iNKT細胞表達NK細胞譜系分子CD56、CD161、NKG2D、DNAM1、2B4等[3,8]。此外,與NK細胞相似,iNKT細胞在發育成熟過程中就獲得組成性表達細胞因子,如IL-4、IFNγ的能力并且iNKT細胞在受到抗原刺激的情況下能夠快速激活作出免疫反應[9],所以iNKT細胞和NK細胞一樣也屬于固有免疫細胞,并且被激活的iNKT細胞具有殺傷作用,發揮類似NK細胞的功能[10]。綜上所述,iNKT細胞與其命名相契合,是一群自然殺傷樣T細胞亞群。
與iNKT細胞不同,Type II NKT細胞表達的TCR具有一定的多樣性,并且Type II NKT細胞并不識別α-Galcer,sulfatide被發現是部分Type II NKT細胞的抗原。有文章報道,與iNKT細胞發揮抗腫瘤作用不同,Type II NKT細胞通過表達TGF-β、IL-13等發揮抑制腫瘤免疫的作用[11]。本篇綜述主要對具有抗腫瘤作用的iNKT細胞及其作用的機制進行介紹。
2 iNKT 細胞的抗腫瘤機制
iNKT在胸腺中發育并以記憶樣表型出現,在抗原刺激后,它們可以迅速產生大量的Th1和Th2細胞因子,并介導幾個免疫細胞的激活。因此,iNKT細胞在多種疾病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12]。在小鼠多種腫瘤模型中注射特異性激活iNKT細胞的抗原—α-GalCer,觀察到了顯著的抑制腫瘤轉移或生長的作用[13-15]。對腫瘤病人研究發現,前列腺癌病人、多種造血系統惡性腫瘤病人、肺癌病人以及一些其它實體瘤病人的外周血中,iNKT細胞的數目發生了顯著降低[16-19],并在經過治療病情得到緩解的前列腺癌病人的外周血中iNKT細胞數目會有所恢復[16],提示了iNKT細胞對人類惡性腫瘤可能也會起到抑制作用。iNKT細胞被報道可以通過直接殺傷腫瘤細胞、促進其它效應細胞的殺傷作用以及抑制腫瘤微環境中的免疫抑制細胞這三種途徑發揮抗腫瘤功能。
2.1 iNKT 細胞直接殺傷腫瘤細胞
2.1.1 CD1d 依賴的 iNKT 細胞直接殺傷機制
小鼠肝臟來源的iNKT細胞與EL4淋巴瘤細胞共培養不會直接發揮殺傷作用,但若在共培養體系中加入α-GalCer會誘導iNKT細胞殺傷EL4,并且該過程非常依賴于EL4表達的CD1d。通過敲除FASL、穿孔素和TRAIL等分子的方法,證明iNKT細胞通過表達FASL和穿孔素殺傷T淋巴瘤細胞。而且也通過將iNKT細胞與EL4細胞注射入NSG小鼠中的方法,證明了iNKT細胞在體內也可以殺傷EL4細胞。但與體外實驗不同的是,在體內注射或不注射α-GalCer ,iNKT細胞對腫瘤細胞的殺傷作用沒有明顯影響,體內殺傷作用仍然依賴于EL4表達的CD1d,可能在體內環境中,EL4可以通過提呈內源性脂類抗原激活iNKT細胞,使iNKT細胞發揮細胞殺傷作用[20]。與小鼠中的研究結果相似,人外周血iNKT細胞與表達CD1d的U937和Jukart這兩種淋巴腫瘤細胞共培養僅具有微弱殺傷作用,對CD1d-的神經母細胞瘤細胞系LAN-1和CHLA-20完全沒有殺傷作用,而在共培養體系中加α-GalCer可以顯著增強iNKT細胞對U937細胞和Jukart細胞的殺傷作用,對LA-N-1和CHLA-20仍然沒有殺傷作用,但若在LA-N-1和CHLA-20腫瘤細胞中過表達CD1d,iNKT就可以發揮殺傷作用[21]。對來自人臍帶血的CD4+ iNKT細胞對多種腫瘤細胞,如C1R細胞、U-937細胞、Molt-4細胞、Jurkat細胞、Hela細胞等的殺傷作用分析發現,α-GalCer激活的人CD4+ iNKT在短期內同樣只對表達CD1d的腫瘤細胞有殺傷作用。機制研究發現,體外擴增培養的CD4+ iNKT細胞具有表達FASL、TNFα、IFNγ、perforin等多種促進細胞死亡因子的能力,通過加阻斷抗體的方法,發現CD4+ iNKT細胞表達的FASL、TNFα、perforin都具有殺傷作用,但對于不同的腫瘤細胞,發揮主要殺傷功能的分子不同,這可能與不同腫瘤細胞對不同致細胞死亡分子敏感性不同有關[22]。總之,在iNKT細胞體外腫瘤殺傷實驗中,表達CD1d的腫瘤細胞通過提呈抗原激活iNKT細胞,促進iNKT細胞表達穿孔素、溶菌酶、FASL以及TNFα等誘導細胞凋亡的分子,特異性殺傷CD1d+腫瘤細胞,而CD1d-腫瘤細胞由于無法呈遞抗原,不能激活iNKT細胞,導致iNKT細胞不能有效發揮直接細胞殺傷作用。
2.1.2 細胞因子激活的iNKT細胞直接殺傷作用
M C Leite-De-Moraes等人研究發現,在沒有TCR信號活化的情況下,IL-12可以協同IL-18促進iNKT細胞增殖,并促進iNKT細胞表達FASL,作用于腫瘤細胞表達的FAS,起到直接殺傷作用[23]。
2.1.3 NKR 激活的 iNKT 細胞直接殺傷作用
iNKT細胞還被發現可以由NKR配體激活而發揮直接腫瘤殺傷作用。對人外周血iNKT分析發現,NK細胞受體如2B4、NKG2D、CD94以 及NKG2A主 要 在CD4- iNKT細胞中表達,并且細胞殺傷分子perforin和Granzyme B主要在NKG2D+的iNKT細胞中表達,經由IL-2和α-Galcer刺激擴增的iNKT細胞可以直接殺傷表達NKG2D配體但不表達CD1d的K562腫瘤細胞。直接從人外周血中分選iNKT細胞用于腫瘤殺傷實驗,發現新分離出的iNKT細胞對K562細胞也具有直接殺傷作用,證明了NKR依賴的CD1d不依賴的iNKT細胞殺傷途徑的存在[8]。
2.2 iNKT 細胞間接殺傷腫瘤細胞
雖然在體外共培養條件下,iNKT細胞僅對具有相應抗原提呈功能的CD1d+腫瘤細胞具有殺傷作用,但在體內注射條件下,α-GalCer對CD1d-或CD1d+的腫瘤具有普遍抑制潛力,提示iNKT細胞在體內可以通過間接作用抑制腫瘤[24]。研究發現,體內注射α-Galcer可以抑制B16黑色素瘤肺轉移,并通過缺失iNKT細胞的Jα18敲除小鼠證明了該作用完全依賴于iNKT細胞,進一步研究發現,α- Galcer對腫瘤轉移的抑制作用不僅依賴于iNKT細胞,還非常依賴于NK細胞和IL-12[15]。眾所周知,IL-12是促進NK細胞殺傷功能的經典細胞因子,而且樹突細胞、巨噬細胞是IL-12的主要細胞來源,這些細胞作用于組織和粘膜,以維持組織的穩態和免疫監視。并且體外實驗已經證明了樹突細胞呈遞α-GalCer不僅促進NKT細胞增殖和表達細胞因子,也會促進NKT細胞表達CD40L,而NKT細胞會通過CD40L反作用于DC細胞表達的CD40,促進DC細胞表達IL-12[25],所以體內注射α-GalCer導致iNKT細胞和DC細胞發生相互作用,促進DC細胞表達IL-12,進一步促進NK細胞表達IFNγ起到間接抑制腫瘤的作用。α-GalCer激活的人肝臟來源的iNKT細胞也被發現通過促進NK細胞的殺傷作用間接殺傷K562和Colo201腫瘤細胞[26]。此外,體內注射α- Galcer通過iNKT細胞促進樹突細胞表達的IL-12也可以促進CD8+T細胞的殺傷能力,起到抑制腫瘤轉移的作用[27]。總之,激活的iNKT細胞可以通過促進NK細胞和CD8+T細胞的殺傷能力起到間接殺傷腫瘤的作用。
2.3 iNKT 細胞抑制腫瘤微環境中的免疫抑制細胞
腫瘤相關巨噬細胞(tumor associated macrophage, TAM)和髓系來源的抑制細胞(Myeloid derived suppressor cell,MDSC)可以通過抑制效應T細胞增殖、促進效應T細胞死亡以及促進Treg細胞分化等途徑抑制免疫系統對腫瘤細胞的攻擊作用[28]。TAM表達CD1d,iNKT細胞被指出可以通過殺傷荷載腫瘤細胞抗原的TAM細胞起到抗腫瘤作用[29]。iNKT也被發現可以抑制MDSC的作用。在體外實驗中,小鼠和人來源的iNKT細胞都可以解除MDSC對效應T細胞的抑制作用,暗示了這可能也是iNKT在體內抑制腫瘤的途徑之一[30]。
3 總結與討論
綜上所述,iNKT細胞是兼具NK細胞和T細胞特征的特殊T細胞亞群,被激活的iNKT細胞具有腫瘤殺傷作用,其中iNKT細胞的直接殺傷作用主要針對具有α-GalCer抗原提呈能力的CD1d+的腫瘤細胞,不依賴于TCR信號的細胞因子或NKR激活的iNKT細胞也可以發揮直接殺傷作用,但相關報道較少。體內注射α-GalCer或直接注射荷載α-GalCer的樹突細胞在小鼠中都觀察到了較好的抑制腫瘤效果,并且在機制上依賴于iNKT細胞在體內對NK細胞和CD8+ T細胞的促進作用[31]。但這兩種方法是否可用于治療人類惡性腫瘤還需進一步研究。在與樹突細胞共培養條件下,再加入IL-2和α-GalCer可以實現小鼠和人類iNKT細胞的體外擴增培養[32]。聯合注射α-GalCer和iNKT細胞是否可以起到更好的治療效果也需要深入研究。靶向iNKT細胞用于人類惡性腫瘤治療,特別是實體瘤治療時,iNKT細胞是否能有效地進入腫瘤部位,iNKT細胞數量是否能有效維持以及iNKT細胞是否也會像CD8+T細胞那樣在腫瘤免疫抑制微環境下,殺傷能力被減弱甚至丟失等,都是需要考慮和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