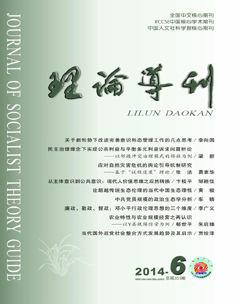產業組織模式轉型的路徑探討——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視角
劉 健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工商管理學院,北京 100070)
一、引言
《經濟學人》在2012 年4 月發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制造業與創新》專題報道中描述了目前正在發生的由技術引領的制造業的深刻變化。同年6 月美國著名未來學學者杰里米·里夫金的著作《第三次工業革命——新經濟模式如何改變世界》中文版的面世,使得“第三次工業革命”成為年度最炙手可熱的詞匯之一。毋庸置疑,無論視角或語境有何不同,對于人類正在迎來一場劃時代的技術和經濟大變革這一判斷,人們越來越趨于共識。新一代信息技術、移動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新能源等已成為描述和討論這場變革基本特征的“關鍵詞”。
在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背景下,制造業生產方式將由大規模標準化生產向大規模個性化定制轉變,這一轉變將型塑全新的產業組織模式,垂直結構、中央集權、自上而下、企業巨頭的組織模式將向扁平化結構、分散分布式、社會化、競合化的網絡狀的組織模式轉變。作為產業運營的組織載體,產業組織的形成和發展在影響著企業績效和產業結構的同時,也決定著一個國家產業競爭力的大小和國家競爭優勢的強弱。對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背景與內涵及其對產業組織所產生的影響進行深入研究,分析第三次工業革命背景下產業組織模式轉型的發展趨勢與特征表現,科學設計產業組織模式轉型的模式與路徑,在此基礎上做好前瞻性的戰略部署和政策準備,是實現中國制造業產業升級與轉型、提升制造業產業競爭力的根本要求,也是實現中國經濟轉型、保證中國經濟長期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二、第三次工業革命背景下產業組織模式的特征
在第三次工業革命背景下,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飛速發展,消費者需求日益多樣化,技術創新的步伐日益加速,市場趨向于不斷波動,產品的生命周期縮短、復雜性加劇,企業面臨著巨大的壓力。為應對這一壓力,縱向一體化大企業開始實施“歸核化戰略”與“集約化戰略”,逐步將企業的非核心業務外包出去,產業組織呈現出內部規模經濟逐步弱化,生產池效應逐步顯現、產業集中度和規模起點逐步下降、市場進入壁壘逐步下降、中小企業的創新與生產優勢逐步顯現,可競爭市場結構逐步形成等趨勢。然而,縱向一體化大企業的垂直解體并不是從一體化的科層組織簡單地回歸到原子型市場,而是形成了一種產業組織模塊化的趨勢,企業之間為達到雙贏而開展了大量交易和合作,并逐步形成模塊化的生產網絡。
首先,模塊化生產網絡具有適用性更好、抗風險能力更強的特點。模塊化生產網絡無須像縱向一體化企業一樣將價值鏈中所有的業務活動全部集中在企業內部,模塊化生產網絡中的系統集成商①可以采取外包、靈活的雇傭制、企業聯盟等形式,將市場風險分散和轉移到組織內的其他企業。這樣,系統集成商無須自己花費成本承擔風險來組建和維持龐大的企業組織,他通過利用外部生產網絡,可以專注于產品創新、市場開發、品牌管理等核心業務,并在全球范圍內實施新產品的開發、制造和推廣,而模塊供應商基于專業化分工,可以有效地獲得專業化優勢,化解風險并獲得市場份額和利潤。
其次,模塊化生產網絡可以獲得更高的生產和組織柔性。從某種意義上說,模塊化生產網絡是基于企業核心能力的專業化分工的結果,系統集成商集中于創新和新產品的推廣,而模塊供應商集中于生產和制造能力的提供,這樣的一種生產與創新相分離的產業組織模式,使得系統集成商可以在市場需求旺盛時期快速增加產品產量,而在市場疲軟時又可以快速地減少生產,同時,在新產品推出的情況下,模塊供應商可以快速地從生產老產品轉換為生產新產品,從而獲得系統內生產的柔性。
第三,模塊化生產網絡體現了一種新興的既競爭又合作的競合關系。為適應多變的市場需求和快速發展的技術創新,一家企業的創新成本和代價往往過高,這就需要網絡內的所有企業的相互合作與交流,從而降低創新成本,加速技術和知識的流動,進一步推動技術創新、知識創新和價值創新,而創新的加速又進一步地加劇了市場的波動,企業之間為獲得更多的市場份額和市場利潤,競爭亦隨著加劇。
第四,模塊化生產網絡可以產生協同效應。系統集成商和模塊供應商根據自身的核心能力差異,形成差異化的但又是互補的高度專業化的分工體系,并通過二者之間的合作、創新和競爭以及資源、服務、品牌和文化等的整合,將各種能力要素協同在一個產業網絡之中,產生“1 +1 >2”的協同效應。每個企業都只做自己最擅長的業務,僅專注于“長板”,系統內企業之間基于“長板”的合作與競爭,構造出一個“更大的木桶”,獲得“新木桶效應”(李海艦,2004)。
第五,模塊化生產網絡擴大了創新空間,降低了創新成本,增強了創新能力。模塊化生產網絡的創新活動通過分散與集中、合作與競爭,形成了與市場型和企業型不同的創新體系,系統集成商通過集中于產品創新的業務,可以實現生產與創新的分離,從而有效地降低了創新的整體成本,拓展了產品創新的空間。而編碼化知識在企業之間的交流更為順暢,傳遞與擴散更為便捷,有利于知識的創新與創造。
三、產業組織模式轉型的總體思路
產業組織模式是隨著產業所處的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化而變化的,外部經濟環境可以驅動產業組織模式朝某個特定的方向和狀態演進,從而形成不同型構的企業間關系的產業組織模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產業組織模式與第三次工業革命之間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協同演進的。
一方面,在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背景下,制造業技術經濟范式的轉變催生了生產方式的變革,生產方式的變革又重構了企業與企業之間、產業與產業之間的關系,經濟系統的創新性變革迫使產業組織模式進行有效轉型以應對經濟環境的變化,通過產業組織內部企業間競爭與合作關系的重新界定與優化調整,產業組織由工業經濟時代的縱向一體化大企業模式逐漸演變成網絡經濟時代的生產網絡模式,產業組織可以獲得更大的系統柔性和更高的組織效率,從而增強產業組織與第三次工業革命所型塑的經濟環境之間的適應性。在全球化個性化的大規模定制生產方式下,產業組織要在以合作、社會網絡和行業專家、技術勞動力為特征的經濟環境中生存和發展,就必須選擇與經濟環境特征相適應的產業組織模式,也就是說,新通信技術與新能源體系的有機結合形成了產業組織模式轉型的倒逼機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產業組織模式的轉型在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背景下具有自我演化的特征和趨勢。
另一方面,正如生物組織的變異、自選擇、存續的演化往往需要數代百年的傳承一樣,產業組織的變革與創新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既不是可以鏟除社會病毒的靈丹妙藥,也不是能帶我們進入極樂世界的鴉片,在現實的經濟實踐中,新通信技術與新能源的有機結合是一個長期的動態的過程,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進程涵蓋技術范式的轉型、機制體制的創新、市場體系的構建等諸多因素,涉及到企業、協會、社會組織、政府機構、消費者等眾多的市場主體,因而以全球化個性化的大規模定制為基礎的全球化生產網絡的形成和演進是一項系統工程。與此同時,即使是在經濟環境快速變化的條件下,產業組織也會因其自身的僵化而抵制變革,往往必須經歷長時期的摸索和實驗才能有效地實現產業組織模式的創新。而且產業組織應對環境變化的適應性能力的形成也是需要時間和成本的,復雜生物和社會系統所內含的“沖突性妥協”特征決定了系統往往無法處于適應性最優的狀態(Kauffman,1993,1995),而科學的局限性決定了產業組織往往無法獲得最優的技術解決方案。因此,第三次工業革命背景下的產業組織模式轉型的過程注定是緩慢而曲折的。
綜上所述,我們將經濟環境、市場主體與產業組織之間的動態關系圖繪制如下。
如上圖所示,經濟環境的變化驅動市場主體的適應性變革和調整行為達致產業組織的形成,而市場主體在應對經濟環境變化的同時,也將反作用于其所處的經濟環境,通過強化或維護經濟環境要素條件,維護其特定產業組織形態的一貫性和連續性。產業組織模式的轉型是經濟環境與市場主體之間相互作用協同演進的結果,是經濟環境與市場主體之間作用與反作用的長期動態博弈的結果。產業組織模式的轉型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經濟環境、政治環境、社會環境、技術環境等眾多外部約束條件,環境要素、主體行為以及產業組織之間是相互作用、協同演進的。
應該指出的是,第三次工業革命并不會憑空而來,經濟革命并不會從創造者和企業家的組合中不可阻擋地迸發,我們不能想當然地認為一旦有了新的技術、產品或服務,市場就會及時有效地做出反應。新通信技術和新能源的融合也需要政府的積極推動,需要政府通過建立新的規章制度和標準對新興經濟活動進行管理,并通過不同的稅收激勵機制和補貼確保新經濟秩序的發展與穩定。
四、產業組織模式轉型的路徑設計
在第三次工業革命背景下產業組織模式轉型的具體路徑設計上,我們應該以制造業所處的經濟環境與制度條件為基礎,以制造業產業組織模式發展的特征、現狀和問題為出發點,以系統論思想為指導,從經濟環境和市場主體兩個層面入手,推動產業組織模式的轉型。(參見圖2)
如上圖所示,第三次工業革命背景下產業組織模式轉型涉及到市場經濟機制的完善、社會服務體系的建設、相關輔助產業的支持以及政府政策體系的扶持,這是經濟環境系統層面的優化,是產業組織模塊化發展的前提基礎和必要條件。產業組織模式的轉型還需要制造業企業在多樣化的需求條件和復雜多變的市場波動情況下,積極主動地開展技術創新、設立與完善產業標準、強化市場競爭,形成產業組織模式轉型的技術驅動力、標準驅動力與競爭驅動力,這是市場主體微觀層面的行為,是提升產業競爭力和推進產業組織模塊化發展的手段和過程。在產業組織模式轉型的過程中,政府、企業、行業協會、中介組織等各個市場主體之間形成良性互動,大、中、小企業共生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與傳統產業之間協調發展,通過深化壟斷行業改革,優化產業結構,實現產業融合,最終推動制造業產業組織模式的轉型,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模塊化生產網絡,在真正意義上實現制造業國際競爭力的提升。
應該指出的是,在現實的經濟實踐中,產業組織模式的轉型是一個長期的動態的過程,產業組織不是總能對經濟環境的變化作出最優反應的。遵循“經濟環境驅動主體行為,主體行為型塑產業組織”這一基本思路,我們嘗試性地提出第三次工業革命背景下產業組織模式的轉型的“三階段”路徑,具體如圖3 所示。
在產業組織模式轉型的第一階段,我們必須從市場經濟機制、社會服務體系、政府政策體系以及輔助產業支持四個方面入手,優化制造業發展所處的經濟環境,健全相應的制度機制,這是產業組織模式轉型不可逾越的最基礎一環,是產業組織模式轉型的前提基礎和必要條件,更是制造業有效提升國際競爭力的出路所在。在市場經濟機制方面,應協調區域經濟統籌發展,積極培育和發展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技術市場、信息市場、產權市場以及土地市場,進而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促進高層次要素的自由流動。同時應進一步深化壟斷行業和國有企業改革,打破區域壟斷和行政壟斷,強化市場競爭機制,營造公平有序的市場競爭環境。在社會服務體系方面,各個行業協會、中介機構以及政府組織應通力配合,為制造業企業提供全方位的信息咨詢、技術支持、市場拓展、籌資融資、創業輔導、人力資源等服務,建立起“多層次、多渠道、多方位”的社會化服務體系,優化產業組織模式轉型的社會網絡。在輔助產業支持方面,應促進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的協調發展,引導生產制造網絡成員企業的生產性服務需求,促進成員企業間生產性服務業的資源和信息共享,從技術的學習與創新、人力資本與技術經濟、知識經濟的融合發展等方面著力提升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水平,為產業組織模式的轉型提供產業支持。在政府政策體系方面,應明確政府的職能定位,加強服務意識,提供高效服務,優化政策供給,引導和推動產業組織模式轉型的良性發展。
在產業組織模式轉型的第二階段,制造業企業之間在經濟環境和制度條件的驅動下展開充分有效的競爭與合作,推動大、中、小企業協調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與傳統產業之間的融合發展,實現制造業價值鏈的垂直解體和扁平化發展,形成系統集成商與模塊制造商的專業化分工體系。制造業企業是制造業產業組織模式轉型的最重要市場主體,制造業產業發展的核心是產業競爭力的提升,而產業競爭力具體表現為企業核心能力的構建與企業競爭能力的提升,這是產業組織模式轉型的本質要求和根本目的,是產業組織模式轉型最為關鍵也是最為重要的一環。一方面,制造業價值鏈在縱向上垂直解體,實現技術的歸核化,形成具有自主創新能力的系統集成商。技術實力強、掌握核心技術和市場渠道及標準制定能力的制造業企業逐步將生產制造等非核心業務剝離,外包給其他專業的生產制造商,自身專注于技術創新、標準設定、市場營銷、品牌建設等核心業務環節。為實現企業大而強的目標,這些企業之間為獲得技術領先地位、掌握標準制定的話語權而展開創新、標準和服務的競爭,不斷強化技術創新的機制和動力。與此同時,為實現技術的創新與發展,制定出適合產業發展的標準,企業之間將在競爭的基礎上加強合作與聯合,共同推動整個制造業產業技術水平的提升和自主創新能力的構建。另一方面,傳統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具有生產制造的比較優勢,為獲得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效益,這些企業之間也開展直接而有效的質量與價格競爭,降低生產與制造成本,通過自由競爭的優勝劣汰,專業化的模塊制造商逐漸形成,制造業生產集約化的目標得以實現。
在產業組織模式轉型的第三階段,制造業產業中的系統集成商與模塊制造供應商同生產性服務企業、各個行業協會、中介組織、科研院所、政府機構等共同組成模塊化的產業網絡。生產性服務產業為模塊化產業網絡的構建提供輔助產業支持,社會服務體系為模塊化產業網絡的形成提供社會保障。各個市場主體之間相互合作、協同發展、整體推進,共同形成具有強大生命力和競爭力的產業網絡,獲得網絡經濟效益和整體競爭優勢。應該指出的是,產業組織模式轉型后所形成的具體的生產網絡形式可以是控制型生產網絡、關系型生產網絡或者模塊化生產網絡中的一種或其混合形式。經濟環境與產業組織之間是否具備適用性、是否有利于獲得規模經濟、范圍經濟、網絡經濟效益、是否能顯著提高組織效率和提升制造業的產業競爭力,是選擇具體的生產網絡形式的標準和出發點。
五、第三次工業革命背景下促進產業組織模式轉型的政策建議
首先,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構建產業組織模式轉型的市場體系。中國經濟區域發展的不均衡性以及條條塊塊的市場分割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人才、技術、信息等高層次生產要素在全國范圍內的流動,地方保護主義與部門保護主義所形成的行政壟斷則進一步阻礙了市場競爭,而基于歸核化戰略與集約化戰略的生產網絡的構建需要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專業化分工和資源配置,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離開了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立,產業組織模式的轉型無異于空中樓閣。因此,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解決中國經濟目前存在的市場分割、區域和行業壟斷、缺乏競爭等現實問題,是推動產業組織模式轉型必不可少的制度基礎。我們應轉變將資源過多投入到大中城市、沿海城市的發展思路,在“十二五”時期進一步深化壟斷行業和國有企業改革,從制度體制上創造公平公正的市場競爭環境,協調區域經濟統籌發展,完善區域間交通網絡,疏導體制弊端,減少企業物流成本,促進市場經濟中物流、信息流和價值流的自由流動。通過積極培育和發展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技術市場、信息市場、產權市場以及土地市場,建立起全國統一的市場體系。
其次,強化市場競爭機制,營造產業組織模式轉型的競爭環境。只有在激烈和有效競爭的市場格局下,效率高的企業才能脫穎而出,效率低的企業最終將被市場所淘汰,也唯有此,由有效率、有競爭力的企業所組成的產業網絡才會具備生命力,才是形成產業競爭力的有效組織載體。中國制造業企業目前存在的“大而不強”、“小而不專”的現實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是源于制造業企業的國有行政壟斷以及條條塊塊的地方市場分割所形成的區域壟斷,基于此,應該強化市場競爭機制,深化壟斷行業改革,打破行政壟斷與區域壟斷,構建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戚聿東,2008),以有效競爭的市場體系,推動產業組織模式的轉型。
第三,加強社會服務體系的建設,優化產業組織模式轉型的社會網絡。第三次工業革命背景下所型塑的產業組織模式是涉及眾多市場主體的模塊化產業網絡,其組織效率的有效發揮依賴于眾多的中介組織、行業協會、政府機構等提供的全方位社會服務。完善的社會服務體系是產業網絡賴以形成和發展的社會保障,可以促進產業網絡與社會各界之間的聯系與交流,降低產業網絡與其他市場主體間的協調成本,提升產業網絡的運營效率。在構建信息服務體系、技術服務體系、籌融資服務體系、人才服務體系的基礎上,建立起“多層次、多渠道、多方位”的社會化服務體系,促進產業組織模式的成功轉型。
第四,促進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提供產業組織模式轉型的產業支持。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可以深化社會的專業化分工、延長產品的生產鏈、降低社會經濟運行的交易成本,是提高制造業生產率的前提和基礎(顧乃華等,2006),也是制造業產業組織模式轉型的產業保障。從中國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現狀來看,物流、融資、信息、商務、科技等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較為滯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制造業產業組織競爭力的提升,影響了制造業產業組織模式的轉型。因此,在產業組織模式轉型的過程中,一定要注重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的協調與聯動發展。一方面制造業要通過“歸核化”與“集約化”的戰略實施,進一步促進制造業產業的專業化分工,形成模塊供應商與系統集成商協同發展的生產制造網絡;另一方面,要從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角度充分認識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重要地位,優化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環境,放寬市場準入,強化生產性服務產業市場競爭,為加快生產性服務產業的發展創造必要的制度條件。
最后,明確政府職能定位,優化政府政策供給,為產業組織模式的轉型保駕護航。林毅夫(1989)曾指出:“為了一個經濟的發展,有必要冒超一般化的風險去建立一種鼓勵個人生動活潑地尋求并創造新的可獲利的生產收入流的系統,和一種允許用時間、努力和金錢進行投資并讓個人收獲他應得好處的系統……沒有政府一心一意的支持,社會上不會存在這樣的制度安排。”產業組織模式轉型可以說是產業組織層面的制度創新與制度安排,離不開政府力量的推動。市場競爭機制的完善、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立、社會服務體系的建設、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等都離不開政府政策的支持。需要強調的是,一方面,在產業組織模式轉型的過程中,應十分注重政府的服務、引導和推動作用,但也必須防止政府行政權力過大的問題,要明確政府的職能定位,提高政府的服務效率,避免出現政府直接干預和主導企業運營、行業發展等市場微觀經濟事務的情形,倡導“小政府、大社會”的管理模式;另一方面,政府對制造業產業組織模式轉型的推動作用主要表現在經濟運行環境的優化與政府政策的供給上。政府要通過完善相應的法規法律體系,營造公平公正的法制環境來促進制造業企業間的有序競爭,維護市場經濟的正常秩序。通過制定相應的產業政策,扭轉市場失靈,優化資源配置,引導制造業產業組織模式的順利轉型,實現產業競爭力的提升。
六、結論
在第三次工業革命背景下,新通信技術與新能源技術的有效結合將最大程度地釋放合作性權力的效用,打破垂直、自上而下、中央集權的組織模式,向分散化、民主化、社會化的合作模式轉變。它對制造業產生的最深遠影響便是生產方式的轉變,即由大規模標準化制造向個性化大規模定制轉變,這一變化將驅動產業組織模式的轉型,由縱向一體化大企業轉向全球化的生產網絡。
產業組織模式轉型不會是一蹴而就的,即使是在第三次工業革命經濟環境快速變化的條件下,產業組織也因其自身的僵化而抵制變革,產業組織模式轉型所內涵的應對環境變化的適應性能力的形成也是需要時間和成本的,環境要素、主體行為以及產業組織之間必然是相互作用、協同演進的。尤其應該指出的是,目前中國的壟斷行業包括傳統能源、電力、電信等行業的改革遠未破題,傳統壟斷行業所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已成為一股可以與國家就公共利益進行博弈的勢力,具有干預和把持改革的能量,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第三次工業革命背景下產業組織模式轉型的進程。基于此,我們必須通過發揮出政府在促進產業組織模式轉型中的積極作用,從深化壟斷行業改革、構建市場體系、營造競爭環境、優化社會網絡、提供產業支持等各個層面入手,推進產業組織模式在我國的順利轉型。
當下,美國和歐盟“再工業化”、“重振制造業”戰略正如火如荼地開展,它們意欲牢牢掌控制造業的高端環節,而中國周邊一些發展中國家正在制造領域的低端環節搶占市場。在兩頭擠壓的國際競爭舞臺上,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順應歷史發展的趨勢和潮流,把握好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歷史機遇,以新通信技術和可再生新能源技術為支點,推動產業組織模式的轉型,進而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升級,才是實現中國經濟走向可持續發展之路的根本。
注釋:
①模塊化生產網絡中的系統集成商具有很強的創新能力,是非垂直一體化的領導企業,負責創新和市場開發,推動新產品的開發和營銷。而模塊供應商則具有高度功能專業化的特點,又可稱為交鑰匙供應商(Sturgeon,2002),負責提供包括物流、工藝流程、零部件采購、制造、組裝、包裝、分銷、乃至售后服務等全方位的生產服務。
[1]Chandler.A.Scale and Scope[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2]World Bank.Reforming Infrastructure——Privatization,Regulation,and Competition [R].World Bank Report,2004.
[3]Schilling,M.A.Toward a General Modular Systems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to Interfirm Product Modularity[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0,25(2).
[4]Sturgeon,T.and R.Lester.Upgrading East Asian Industries:New Challenges for Local Suppliers[R].Prepared for the World Bank's Project on East Asia's Economic Future,Industrial Performance Center,2002.
[5]Kauffman,S.A.At Home in the Universe[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6]Kauffman,S.A.The Origins of Order[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7]賈根良.第三次工業革命與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新思維——來自演化經濟學和經濟史的視角[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3,(2).
[8][美]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業革命:新經濟模式如何改變世界[M].張體偉,孫豫寧,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9]李海艦,聶輝華.論企業與市場的相互融合[J].中國工業經濟,2004,(8).
[10][法]保爾·芒圖.十八世紀產業革命[M].楊人楩,陳希秦,吳緒,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11]黃群慧,賀俊.“第三次工業革命”與中國經濟發展戰略調整——技術經濟范式轉變的視角[J].中國工業經濟,2013,(1).
[12]戚聿東,柳學信.深化壟斷行業改革的模式與路徑:整體漸進改革觀[J].中國工業經濟,2008,(6).
[13]顧乃華,畢斗斗,任旺兵.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互動發展:文獻綜述[J].經濟學家,2006,(6).
[14]劉健.中國生產性服務產業與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基于1978-2007 年數據的分析[J].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10,(3).
[15]林毅夫.誘致性制度變遷與強制性制度變遷[J].卡托雜志(美),1989(春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