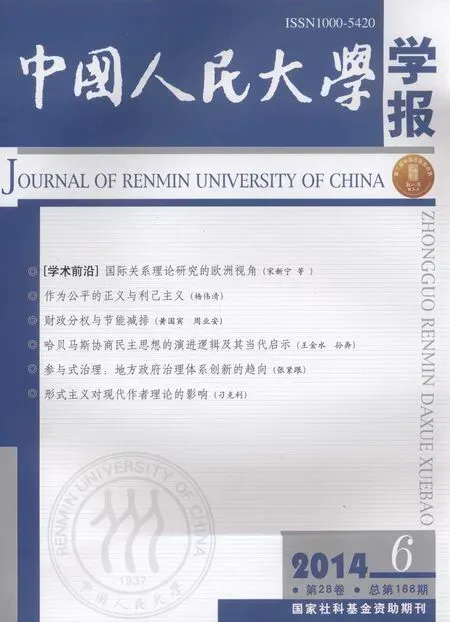清代宗教與國家關系簡論
祁美琴
清代宗教與國家關系簡論
祁美琴
清朝開啟了真正融合北方游牧文化與中原農耕文化的時代,同時又是中國傳統統治思想與近代西方基督教文明產生激烈碰撞的時期。清朝國家的這一特性,決定了清朝宗教政策的特征是:以儒家文化和藏傳佛教為主導,兼顧傳統釋道和伊斯蘭教,排斥新“入侵”的基督教。有清一代,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各自的境遇雖然不同,但均對清朝國家產生了影響,尤其是藏傳佛教對蒙藏地區的影響更加深遠。總體來看,清廷對各類宗教基本采取一種政治功利化的態度,有利有用則推舉,無利無用則抑制,這也是清代統治者始終沒有為后來的某一宗教所控制、各教派的興衰基本限制在皇權之下的根本原因。
清代;宗教;國家
在中國多民族國家的歷史上,沒有一個朝代的宗教對民族關系的影響超過清代,從努爾哈赤利用喇嘛教建立滿族與蒙古族的同盟關系開始到逐步統一蒙古與西藏地區,宗教都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樣,到晚清間斷爆發的回民起義和震驚中外的義和團運動,也都與宗教有密切的關系。換句話說,清代宗教與國家的關系是貫穿清代歷史的一條主線,反映了清代少數民族政權的獨特性。因此,需要從宏觀角度把握宗教在清代的作用和影響。
一、清朝宗教政策產生的基礎及其實踐
宗教的本質是人類特有的意識形態,是早期人類認識自然界和自身組織結構的一種理論完成。之后,宗教逐步演化為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并漸趨成為一種強制的意識形態。因此,擁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就演變為一些民族特征和國家特征。
一般認為,在中國歷史上,與信仰基督教、伊斯蘭教的民族相比,漢族不是一個全民擁有正統宗教信仰的民族,盡管佛教曾經興盛,但也只是產生了一些間斷性的影響,并沒有形成全民信仰。從歷史文化角度究其原因,可能在正統宗教產生的社會條件具備之前,漢族祖先對自然的理解和對社會組織的認識就達到了“天人合一”的高度。早在殷商時期,帝王們已經帶有“天神”的背景,周朝把這種傳統直接定義為“天子”。此后,中國封建王朝的統治者都被賦予“天子”的身份,使世俗政權兼有“神授”的衣缽,沒有給正統宗教產生和傳播留下空間。孔子把這種實踐精神提升和完善為“儒家”理論體系,被以后的封建統治者尊崇,封建知識階層奉孔子為宗師。后世將儒家學說稱為“儒教”,是因為漢族傳統中的“仕”階層對“儒學”的崇拜方式類似宗教,以這種形式把世俗意義上的倫理規范變成一種“天賦教義”來約束人們的思想行為,使專制封建制度建立在“和順尊卑”的等級基礎上。概括地說,中國傳統文化土壤中生長出來的“儒教”,是以倫理意識占據了宗教的位置。因為它取代了“神系”或者“神譜”的產生及其形成的權威性,使正統宗教難以施展影響,其他宗教只有應和“儒教”建立的宗法觀念才能傳播。無論是最早傳入的佛教,還是后來傳入的伊斯蘭教、基督教,都經歷了一個被儒教教化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說,“儒教”的內涵遠遠大于宗教,這是漢文化體系的獨特性。
滿族的崛起,在經濟和文化上深受中原漢文化體系的影響。努爾哈赤所在的建州女真地區,毗鄰撫順等漢族聚居區,與內地互市通商、輸進鐵農具等,彼此經濟來往密切。其先輩包括父祖一代,一直為明朝的地方官,經常進入漢地、明廷,明朝甚至應女真貴族頭人的要求,在遼東地區為其建“快活、自在二城”[1](P1053),吸收部分頭人進入錦衣衛等機構任職,而努爾哈赤也一再討封“龍虎將軍”,這些都說明他們熟悉漢制和尊卑禮法,并極力想融入漢地社會及其評價體系。在努爾哈赤初建女真政權時,龔正陸等漢族文人就受到重用,“努爾哈赤的倫理觀已飽受漢族儒家倫理道德思想的洗禮”[2],從他愛讀《三國演義》、《水滸傳》,以及其弟舒爾哈齊家的大門上“跡處青山,身居綠林”的對聯,就可以看出中國傳統社會中儒家學術尊奉的“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等倫理道德觀念對他們的影響之深。
1616年,努爾哈赤正式稱汗,建元“天命”,即所謂“天命之為汗”,宣揚“天的意志”高于一切,體天心、順天意、畏天威,成為他高懸于上的行動法則。這種對“天神”的崇拜雖然與滿族傳統信仰中的薩滿教密切相關,但是努爾哈赤的天命觀是對薩滿教天神信仰的改造和升華,雖然沒有達到漢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認識高度,但繼承了漢文化體系中的“天子”觀念與身份認同傳統。而這正是滿族社會宗法和等級觀念濃厚的必然反映。基于此,才能理解滿族沒有成為具有正統宗教信仰的民族的思想文化根源,才能認識到“祖先崇拜”在滿族精神信仰中的主導地位,也才能領會清朝統治者在統治思想上與中國傳統社會的繼承關系。這些思想或觀念,最終體現在統治者的統治方式上就是對神的敬畏低于對人的服從,而這又使他們在接受儒家文化的影響時不僅沒有來自宗教信仰方面的障礙,反而成為其認識宗教的文化和思想基礎。
與此同時,由于地處白山黑水的滿族與蒙古諸部毗鄰,在氣候、環境、生活方式、語言上的相似性,使兩個民族從一開始就在政治文化和地緣利益上相互影響。明朝后期,喇嘛教被蒙古貴族提倡和崇奉,并逐漸成為左右蒙古地區人心的重要的政治力量。女真社會也深受其影響,據朝鮮使臣記載,“奴酋常坐,手持念珠而數。將胡頸系一條巾,巾末懸念珠而數之”[3](P43)。基于與蒙古貴族政治聯盟的需要,努爾哈赤充分發揮滿族與北方民族“近宗同源”的優勢,有意識地將利用喇嘛教作為“北婚蒙古,連兵萬里”的前提,努力塑造為喇嘛教最高保護者的形象。1615年,努爾哈赤親自主持在赫圖阿拉城修建七大廟。1621年,又明令保護寺廟:“任何人不得拆毀廟宇,不得于廟院內拴系馬牛,不得于廟院內便溺。有違此言,拆毀廟宇,拴系馬牛者,見即執而罪之”[4](P267)。他還給予西藏東來科爾沁布教的囊蘇喇嘛“尊禮師尊”的優遇,囊蘇喇嘛圓寂后,又為其建舍利塔。努爾哈赤對喇嘛的優禮,并以法律的形式把尊崇喇嘛教固定下來的宗教政策,在當時產生了廣泛的政治影響,消除了一些大喇嘛和蒙古族眾的疑慮,吸引他們聚集在自己的號令之下,為戰勝明朝、鞏固和擴大“后金”政權做好了宗教文化方面的準備。
太宗皇太極時期,繼續推行尊崇喇嘛教的政策,重視喇嘛教的政治功用。1635年,察哈爾墨爾根喇嘛載護法“嘛哈噶喇”金身歸附,以及元代玉璽的獲得,奠定了皇太極作為蒙藏護法者的地位。此后,皇太極更加積極與藏傳佛教中心的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建立聯系。1639年,應蒙古喀爾喀三汗的請求,皇太極致書延請達賴喇嘛稱:“大清國寬溫仁圣皇帝致書于掌佛法大喇嘛:朕不忍古來經典泯絕不傳,故特遣使延致高僧,宣揚佛教,利益眾生,唯爾意所愿耳”[5](P651)。1642年,達賴、班禪的使者到達沈陽,受到皇太極的隆重接待,使者返藏時,皇太極又致書達賴云:“今承喇嘛有拯濟眾生之念,欲興扶佛法,遣使通書,朕心甚悅,茲特恭候安吉”[6](P190)。
清朝統治者對喇嘛教優禮與籠絡政策,主要是收買和利用高僧大德、上層喇嘛,撫順、安定蒙藏人心,所以那些普通信眾尤其是滿漢地區的“崇佛”行為或借信教之名斂財的“惡僧”,從一開始就受到抑制和打擊。1636年,剛剛改國號稱大清皇帝的皇太極,就發布禁令不準私建廟宇和私自出家當喇嘛:“有私建的寺廟喇嘛、班的、和尚數目,明寫在冊上……今后未奉上命私為和尚、為喇嘛,及私建寺院者,問應得之罪。要做和尚、喇嘛,要建寺院,須知禮部,稟明無罪。”[7](P14)但這種抑制主要是為其發展生產和增殖人口服務的,與其優禮尊崇喇嘛教的基本政策無關。正如蘇聯學者符拉基米爾佐夫指出的:“滿洲皇帝在(蒙古)人民大眾的眼中成了佛的化身,好像是佛教的領袖。佛教僧侶封建主,為數眾多的寺廟和喇嘛,自然地把滿洲皇帝當作了他們信仰的光輝和他們增進福祉的泉源而傾心歸附于他了。”[8](P299300)此后喀爾喀歸附、土爾扈特回歸,均曾議及在選擇清朝時,是否能夠成為宗教的保護者起了關鍵的作用。
順治時期,是清朝佛教信仰影響至深的時期。順治帝篤信佛教,迎五世達賴進京,冊封金印,建西黃寺居住。順治帝本人也成為清朝歷史上唯一公開皈依禪門的皇帝,允許滿族人出家當僧人。其時清廷在商議是否向五世達賴征詢關于時局的意見時,滿大臣即言:“倘不一加詢問,使喇嘛含慍而去,則外國喀爾喀、厄魯特必叛”[9](P566)。可見清廷在考慮與藏傳佛教的關系時仍著眼于解決蒙古問題,但是即便如此,也沒有放松對寺院與僧眾的管理。順治九年(1652年)九月,諭令禮部,“佛教清凈,理宜嚴飭”,已領度牒僧眾,務要恪守戒規,敬供神佛,穿戴、居住不得亂行。未領度牒及冒充僧尼往來者治罪,喇嘛私收徒弟、婦女私拜喇嘛或寺廟庵觀者治罪。[10](P537 538)
至康雍乾時期,諸帝對喇嘛教均有清醒的認識。康熙云:“蒙古之性,深信詭言,但聞喇嘛胡土克圖胡必爾汗,不詳其真偽,便極誠叩頭,送牲畜等物,以為可以獲福長生,至破蕩家產,不以為意。”[11](P574)但為平息準噶爾與喀爾喀的紛爭,康熙帝不得不多次致信求助達賴喇嘛對準噶爾施加影響。雍乾時期,無論是將七世達賴喇嘛移住川邊理塘、將哲布尊丹巴移居多倫,還是后來又護送他們回到拉薩、庫倫,都是在削弱與扶持、抑制與籠絡大喇嘛的政治影響中尋求平衡。清朝統治者認識到宗教的影響是客觀存在的,雍正帝謂:“如僧、道、回回、喇嘛等,其來已久,今無故欲一時改革禁除,不但不能,徒滋紛擾。”[12](P425)但同時也確立了自己作為“帝王”之尊凌駕于佛道之上的地位自信,他曾在《當今法會》序言中謂:“朕居帝王之位,行帝王之事,于通曉宗乘之虛名何有?”乾隆帝不僅深諳儒家治國之術,而且佛學修養極高,他認為“誰云儒教異佛教,試看不同有大同”,在他看來,無論以儒治國,還是以佛治心,最終目的都是為鞏固封建專制統治服務,是高明的統治技巧。乾隆帝能夠達到自覺自愿地崇拜佛祖,實質是他對宗教的理解達到了“治人與治心”合二為一的境界。
總之,清朝統治者順應了時勢和多民族國家治理的需求,在統治思想上兼顧了儒家文化和藏傳佛教在漢地和蒙藏地區的教化作用,以達到“助王化之遐宣”的目的。有研究者認為,康雍乾諸帝對喇嘛教的政策,主要以準噶爾勢力的消長來決定,勢長則籠絡多于抑制,勢衰則抑制多于籠絡。“迨準噶爾覆滅,則清廷勢將喇嘛教完全置于政治監督之下,僅成為撫慰蒙藏的一種工具。”[13](P341)這一觀點雖有偏頗,但道出了清朝尊崇喇嘛教政策的功利性質。及至道光以后,清廷已不慮蒙古之離心叛亂,優禮大喇嘛之制漸衰,馭制日趨嚴密,活佛的權勢、地位、影響與清前期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可以說,統治者的宗教實踐,是清朝準確把握宗教的功用和影響的前提。
二、清代各類宗教演變與政教關系
可以說,滿族及其建立的清朝,開啟了真正融合北方游牧文化與中原農耕文化的時代,滿族特色的本質是中國長城內外兩種文化聚合、融匯而生成的新文化體。如此,才能理解和認識清朝的宗教特色必定是以儒家文化和藏傳佛教為主導,兼顧傳統釋道和伊斯蘭教,排斥新“入侵”的基督教的宗教發展狀況。各類宗教在清代國家進程中的角色和影響如下。
(一)藏傳佛教
佛教從古印度傳入中國后已有兩千年,成為中國信徒最多、影響最大的宗教。中國境內的佛教有大乘、小乘兩大派,從語言系統,又可分為漢語系、藏語系、巴利語系佛教。藏傳佛教是指以藏族語言傳播的佛教一系,始于公元7世紀。15世紀上半葉,藏傳佛教中的黃教一派興起,并繼而得到蒙古貴族的扶持和崇信,成為蒙古地區全民信仰的宗教,這就是喇嘛教。喇嘛是藏語漢譯,意為“上師”,指寺院的首領和高僧,將藏傳佛教稱為“喇嘛教”,是尊稱。這與藏傳佛教崇尚密教、注重“喇嘛”上師灌頂有關,“無喇嘛上師,如何得近佛?”正是對“喇嘛”地位尊崇的體現。
滿族入關前對內地佛教不陌生,后金天聰朝設立僧錄司,管理佛教事務。入關后,清廷對內地佛教采取控制總體數量、逐漸減少扶持的政策,通過廢除試經度僧和度牒制度、降低寺院等級、清理信徒隊伍、打擊非正統教門諸派,內地佛教的影響和作用逐漸下降。與此同時,藏傳佛教在清代進入了一個鼎盛時期。
順治十年(1653年),統治西藏的蒙古固始汗在拉薩去世,西藏陷入爭奪達賴轉世和蒙古汗王的紛爭中,為清軍入藏創造了條件。清政府從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開始入藏到乾隆末年,經過70多年不斷調整完善,形成政教合一、活佛轉世、金瓶掣簽、冊封賞賜和寺院僧眾參與管理的一整套制度,構成清代政治制度的一部分,為西藏地區社會穩定和強化中央對藏治權發揮了重大作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清廷頒布《欽定西藏善后章程二十九條》,這是中央有效實施政教合一制度的標志。
清代在藏區實行政教合一制度與西藏的農奴制是相適應的,把統治者“神圣化”是對農奴實施“奴隸般”統治的精神枷鎖。信徒崇拜的神偶與統治者合二為一,前提是信眾相信他們崇拜的人是“神”。清廷正是通過控制人轉“神”的最終認定有效地行使治理權:規定駐藏大臣的權位與達賴、班禪相同等,明確要求駐藏大臣不準叩拜達賴喇嘛,以顯示皇權始終凌駕于神權之上。直到清末,西藏基本保持穩定,這與清廷把握和利用藏傳佛教有直接的關系。
需要注意的是,清朝對喇嘛教在蒙藏地區的政策是有區別的,在藏區是“馭政于教”,在蒙地則是“馭教于政”。在西藏,從七世達賴喇嘛開始,達賴喇嘛就成為西藏地方政府的最高首腦,并受到清廷的高度信任,清廷視其官僚身份優先于宗教身份,故而強調駐藏大臣與其平等,不得叩拜;在蒙古,哲布尊丹巴始終只是宗教領袖,逶迤于蒙古王公貴族和清廷之間,且清廷始終堅持其呼必勒罕必須轉世藏地,以杜絕地方貴族勢力和宗教領袖勢力的結盟,但卻要求庫倫大臣叩拜哲布尊丹巴以示敬重。可以說,清朝對蒙古地區政教分離的控馭是非常重視的,但結果卻與西藏一樣,清末藏人出身的八世哲布尊丹巴仍能集政教權力于一身,成為蒙古國的“皇帝”,這是值得深思的。
(二)伊斯蘭教
伊斯蘭教在清代稱“回教”、“回回教”,用今天的民族識別看,當時信仰回教的民族主要有回、撒拉、東鄉、保安、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烏孜別克、塔塔爾、塔吉克等。在中亞,分布眾多的民族轉信伊斯蘭教,與伊斯蘭教凝聚教眾的功效有直接關系,民族之間頻繁的征伐和擴張,勢必需要一種超越民族的精神凝聚力,伊斯蘭教滿足了這樣的精神需求。靠近中亞伊斯蘭傳統地區的西北少數民族,民風民俗異于內地,歷史上不斷有民族建立地方政權,也從未間斷彼此伐掠搶奪。從清軍入關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回變”之前,清廷對伊斯蘭教采取“從俗從宜,各安其習”的政策,使該教迅速發展。在康熙朝,對新疆穆斯林的政策是依據準噶爾厄魯特蒙古的歸順情況做出調整。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噶爾丹遭到重創,康熙轉變了對新疆穆斯林的看法,主張準噶爾應與回子各行其道,“永相和好”[14](P896)。到雍正時,雖然認為伊斯蘭教“原一無所取,但其來已久,且彼教亦不為中土所崇尚”[15](P11),但基本上保持一種寬容的政策。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在結束“大小和卓”叛亂后,清政府終于確定對新疆穆斯林實行政教分離政策,放棄“不易其俗”的規定,改變地方官員地位低于阿訇的體制,這是因為清政府看到,伊斯蘭教教坊合一的社會組織生活,模糊了宗教與世俗首領的界限,極易混淆政教關系。清中后期,內地和新疆釀起多次反清“回變”,清政府的寬容政策逐漸向“恩威并用,剿撫兼施”發展,但總的方針是“興教勸學,化導回民”。一方面設“義學”教以孔孟,一方面在穆斯林聚居區添建廟宇寺觀。左宗棠在奏本中提到,“回民鮮讀孔孟之書,故不明義理,因而不知趨向”,所以“朝廷惇大之施,不鄙夷其民者,圣化覃敷之義。長治久安,或基于此”[16](P16)。光緒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推動了民族地區的相互交流,鞏固了中國西北邊疆。
(三)道教
盡管在清朝初年統治者就提出“儒釋道三教并舉”,但實際上清朝統治者始終秉持儒家之學治國,自然對道教不信不扶。順治、康熙、雍正年間為籠絡漢人,基本參照舊例,對道教沒有過多貶抑,全真、正一兩大道派呈現中興。及至乾隆初期,屢頒沙汰禁令,嚴防民間教派作亂,道教重陷衰落。此后,道教時與民間各色道門教派混雜,爭奪教眾,頻發事件,受此牽累,難有起色。加之西學東漸,道教的“神功”、“密禪”受到懷疑,大大影響了道教的信仰空間。其實,道教從宋朝開始就時起時落,到明代官方更是排斥道教,正統儒家精英大多視道教為異端,因為道教主張的個人修煉和借鑒天地之氣,存在威脅封建專制皇帝獨享的“奉天承運”的可能,所以,排斥貶抑不遺余力。道教本是成長于中國傳統文化土壤的宗教,正由于如此,道教始祖老莊的“崇尚自然”、“無為而治”精神貫穿在道教的教義當中,使道教沒有嚴格的脫離塵世的“神譜”。道教供奉的最高神“三清”,即玉清元始天尊、上清靈寶天尊和太清道德天尊都與中國的神話傳說有關系,卻與“創世和造人”關系不大。也就是說,道教崇拜對象本身的“神圣性”不似其他正統宗教,因而,道教主張通過道士們的自我修煉達到“通靈天地”的境界。從純粹的信仰和修煉角度看,道教更適合個人和“同類人”范圍的普及,因此,道教非常適合中國小農經濟和局部文化差異大的社會特點。但是,道教教義本身就是對“儒教”的反對,是對儒學正統地位的挑戰,所以,招致儒學精英們的反對是正常的。此外,道教修煉的神秘性和道門組織的嚴密性也對中央集權制度構成威脅,在每一個王朝末期,道教總是開始活躍并時常扮演“反對派”的角色,說明道教的民間基礎和依附道門利益的可能性。因此,道教雖然沒有被歷代封建政權所禁止,但也沒有獲得正統宗教的地位,更無法和“儒教”相比較。因為“儒教”的實質不是宗教,“儒教”是對始終占統治地位的儒家理論的“類稱”(或許是因為孔孟的“牌位”尊崇形式讓域外之人認為是宗教的緣故),正如順治稱“儒釋道三教并舉”是對“儒教”的誤解一樣,“道教”和“儒教”不能類比,不是一類事物。“儒教”的正統地位不是靠宗教性質,而是一整套統治思想和實踐理論。及至清末,天下大亂,全真道及民間道士又活躍起來,直到新中國成立初期專門打擊會道門,道教正統才得以恢復。
(四)基督教
清代對西方宗教的無知正如對西方文明的無知是一樣的,所以,清統治者對基督宗教的理解從一開始就偏離真實,原因是東西方文明在理解自然和人的關系上存在巨大差異,儒教不能接受崇拜宗教的“上帝”超過崇拜王朝的“天子”,基督教也不能接受對人的崇拜超過“神”。從這里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宗教在傳統中華文明中的地位。順治二年(1645年),教宗英諾森十世頒布禁止中國教徒行祭祖尊孔禮儀的通諭,表面上是“禮儀之爭”,實質是東西方文明在宗教產生的“本原”上存在根本分歧。所以,早期西方傳教士們就懂得只有通過統治階級才能有效地宣揚上帝。在順治元年(1644年)清軍入京時,居留內城天主堂的耶穌會士湯若望就知道直接上書攝政王多爾袞,請求留居原地修道。多爾袞獲知傳教士新法對朝廷修歷的重要性,遂批準了湯若望的請求。[17](P67)后來他成為欽天監監正,因而其傳教不加限制。康熙親政后對天主教的傳教頗為寬容,后因禮儀之爭改變政策,開始禁教,不過并未嚴格實施。自雍正元年(1723年)開始,清廷開始全面禁教。雍正帝曾召見三位傳教士面諭禁教緣由,稱:“朕之禁絕汝教,蓋有不得已之苦衷,汝輩知之乎?向也,汝輩人少,從汝教者亦無多,可無過慮。今則來者日眾,散往各省傳教,教堂林立,徒黨眾多。愚民無知,一經入教,惟汝言是聽。一旦有變,豈不危我國家?”[18](P361)這應該是雍正帝的真實想法。當時禮部議復閩浙總督滿保查禁天主教的奏議,提出了禁教的具體措施:第一,除了精通歷數和有技能的西洋人可居留北京外,其他西洋人一概送到澳門安插;第二,所有天主堂改為公所;第三,嚴行禁諭信教民人并令其改易信仰,聚眾誦經;第四,地方官不實力查禁天主教將被嚴加議處。這些禁教措施獲得雍正帝批準,全國由此而禁教。經乾、嘉、道三朝,禁教尺度各個時期雖略有差異,但總體是越來越嚴厲。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中國戰敗。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廷被迫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允許租地建堂。此后,在中法《黃埔條約》、《天津條約》和中英、中法《北京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支持下,西方宗教全面進入中國。清朝統治者把利用喇嘛教解決“域內”問題的成功經驗應用到應對“域外”的基督宗教時,不但沒有取得成效,反而遭遇了嚴重挫折,其中主要原因并不是來自宗教本身,而是來自對整個西方世界的認識,用現有的知識和思想根本無法準確理解基督宗教和背后的工業革命。所以,清中葉以后,統治者對西方宗教的態度寬嚴反復,西方傳教也時禁時開,反映了統治者們在辨別和利用西方宗教影響方面沒有把握,同時也說明了此時恰逢西方殖民主義利用宗教和宗教本身劇烈變遷的時代,中國原有的佛教和道教意識受到沖擊,部分漢族民族主義開始利用西方宗教反抗民族壓迫。
三、清朝宗教與國家關系的實質
總體來看,清廷對各類宗教基本采取一種政治功利化的態度,有利有用則推舉,無利無用則抑制。所以在清代,統治者始終沒有為后來的某一宗教所控制,各教派的興衰基本被限制在皇權之下。
首先,清朝統治者對宗教的態度是以維護專制皇權為前提的。這一前提決定了統治者必然推崇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排斥試圖超越“皇權”的各類神權,打擊各色引誘民眾的旁門左道。順治十三年(1656年)十一月,諭禮部:
朕惟治天下必先正人心,正人心必先黜邪術。儒釋道三教并垂,皆使人為善去惡,反邪歸正,遵王法而免禍患。此外乃有左道惑眾,如無為、白蓮、聞香等教名色,邀集結黨,夜聚曉散,小者貪圖財利,恣為奸淫;大者招納亡命,陰謀不軌。無知小民被其引誘,迷罔顛狂,至死不悟。歷考往代,覆轍昭然,深可痛恨。[19](P811)
有清一代的宗教政策基本肇端于此,但在實踐中實為遵儒,虛以敬佛,抑制禪道,主動扶持藏傳佛教,被動開禁基督宗教,對伊斯蘭教則恩威并重,推行政教分離。這樣析門別類的宗教對策,是以某一宗教的發展是否與朝廷旨意“違逆”為依據的。
第二,清朝時期宗教的作用和影響是復雜的,當宗教信仰居于社會的主導地位時,政治就只能成為它的附庸;當宗教階層世俗化官僚化以后,宗教就成為政治的工具。清初滿族統治者利用喇嘛教結盟蒙古和控制西藏的政策是成功的,原因在于大喇嘛被視為天神,一定程度上左右著當地的政治形勢,從而也影響著國家政策的走向。但是到了清朝中期,隨著蒙藏政治局勢的穩定和對大喇嘛身份的控制,喇嘛教的政治影響開始衰落。嘉慶朝陳登龍的《理塘志略》即論及:
夫大喇嘛為我皇上之所簡放,以治斯民,則大喇嘛固傾心輸誠于我皇上也。彼見大喇嘛而傾心輸誠于皇上,即佛之傾心輸誠于皇上也。佛而傾心輸誠,彼民焉遂凜王之章,服王之教,聽命于我皇上也。[20](P40)
第三,清朝的宗教實踐還說明,當宗教作為一種統治思想和社會活動存在時,對國家的作用和影響是巨大的,因而必然受到既有統治秩序的制約。對于違背統治利益“大干法紀”的大喇嘛,清朝統治者也毫不猶疑予以懲處。例如:1697年,康熙帝處死了私逃準噶爾有“煽惑蒙古之心”的歸化城掌印札薩克達喇嘛伊拉古克三呼圖克圖,懲處了奉差往達賴喇嘛處卻包庇第巴隱匿五世達賴喇嘛死訊的大喇嘛丹巴色爾濟等人[21](P310、348);1720年,清軍驅準入藏后逮捕了準噶爾喇嘛百余人,將其中為首五人“即行斬首”[22](P816);1791年,乾隆帝以廓爾喀侵藏之際,用占卜盅惑眾心不予抵抗的孜仲喇嘛“剝黃處決”,“示以彰明憲典之意”強調奉教必先守法。[23](P716717)但不能否認的是,長期依附宗教的政治格局,也麻醉了統治者的思想意識。比如說遇到天災人禍時,寄托于洪宣梵義、喇嘛誦經以消弭災禍、百姓馴順。所以,盡管就整體而言,清代的宗教始終在國家政權的控制之下,但利用宗教的結果卻逐漸背離了統治者的設想,這是我們在思考宗教與國家關系時應該深思的問題。
第四,在處理基督宗教問題上,清廷處在“知己不知彼”的被動局面下。基督宗教在中國傳播不開、影響有限,中西文化差異是其主要原因。及至清代晚期,鴉片戰爭為歐洲列強借助宗教延伸殖民勢力提供了機會,也為西方宗教在中國的強行傳播創造了條件。所以,清代教案引發的沖突,是以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為后盾的,西方列強不斷壓迫清廷放棄對教案“持平辦理”的原則,要求“保教權”。引起具體沖突的主要原因是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奕行文各省:習教之人除政府征收的正項差徭外,可免于攤派地方社會祈神、演戲、賽會等費用。光緒七年(1881年)五月十七日,在美國公使安吉立的要求下,基督教信徒也獲清廷同意免攤此項費用。這一權利使得教民因信教而分離于傳統地方社會之外,成為無數教案糾紛的根源。直到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法國駐華公使通知清廷,放棄對他國的保教權,此后只保護本國教徒、教士,至此教案才停止下來。清代教案是歐洲強權文明干涉別國宗教事務的典型例證,在當時的歐洲人眼里,除他們以外的所有文明都是愚昧的,他們有責任把這些不信上帝的愚民從文明的泥潭里拯救出來,所以,那些傳教士們是以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勇氣和決心來到“蠻荒之地”的,但在中國他們遇到的卻是文化的抵抗,同時他們中一些人也被中國傳統文明所吸引。
第五,當不同文明遭遇時,宗教始終扮演“先鋒和后盾”的角色。漢族的精神信仰就寄生于儒家文化傳統之中,不用擔心被“異教”同化,相反,異族文化和宗教往往會“融化”在漢文明當中。蒙元時代是一個真正實施宗教寬容的朝代,這與當時蒙古帝國兼容并包的多樣性有直接關系。明代基本延續前朝的宗教狀況,對儒學傳統信仰依舊自信。清代卻不同,清初除“儒釋道”三教外,皇帝對天主教和伊斯蘭教沒有清醒的認識,屢次親臨教堂,賜匾制碑,褒獎西教,“通國教士教民,咸受庇蔭”[24](P261),所以官員百姓并不仇教。然清廷的這份文化自信在不斷以宗教面目出現的“違逆”事件威脅下開始退縮,鎮壓各種以教派會黨名義反清的起事,客觀上擴大了宗教信仰的影響,為各種宗教的傳播創造了條件。出現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清代中后期處在兩股世界性潮流當中:一股是宗教借助西方工業化推向殖民地,另一股是封建專制國家向近代多民族國家轉型,這兩股思潮對清代社會產生持久的沖擊,導致中國傳統的“儒、釋、道”面臨崩潰,在西方文明面前失去了自尊自信。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滿族統治者利用喇嘛教密結“滿蒙”關系,鞏固對西藏的治理,就清王朝本身而言是成功的,但對蒙古民族、藏族甚至自身來說卻筑壘了發展的一大障礙,盡管這是民族自身的選擇,但也與統治者不遺余力地推崇利用有直接的關系。
[1] 《明太宗實錄》卷七十八,北京,中國書店,1983。
[2] 孫明:《努爾哈赤倫理思想形成初探》,載《黑龍江民族叢刊》,2009(1)。
[3] 李民寏:《建州聞見錄》,沈陽,遼寧大學歷史系,1978。
[4] 《滿文老檔》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
[5] 《清太宗實錄》卷四十九,北京,中華書局,1985。
[6] 王先謙:《東華錄》,載《續修四庫全書》第36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7] 《清太宗實錄稿本》,沈陽,遼寧大學歷史系,1978。
[8] Б·Я·符拉基米爾佐夫:《蒙古社會制度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
[9] 《清世祖實錄》卷七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85。
[10] 《清世祖實錄》卷六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85。
[11] 《清圣祖實錄》卷一百四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85。
[12] 蔣良騏:《東華錄》卷二十六,北京,中華書局,1980。
[13] 李毓澍:《外蒙政教制度考》,臺北,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
[14] 《清圣祖實錄》卷一百七十六,北京,中華書局,1985。
[15] 高文遠:《清末西北回民之反清運動》,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8。
[16] 左宗棠:《安插就撫回眾請增設平涼通判都司折》,載《左宗棠全集》,第5冊,長沙,岳麓書社,2009。
[17] 《清世祖實錄》卷六,北京,中華書局,1985。
[18][24] 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河北省獻縣天主堂,1931。
[19] 《清世祖實錄》卷一百零四,北京,中華書局,1985。
[20] 《甘孜藏區社會形態的初步考察》,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辦公室編:《甘孜藏區社會調查資料匯輯》,北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辦公室,1957。
[21] 王先謙:《東華錄》,載《續修四庫全書》,第37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2] 《清圣祖實錄》卷二百八十九,北京,中華書局,1985。
[23] 《清高宗實錄》卷一千三百九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86。
(責任編輯 張 靜)
A Brief Surve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n and State in the Qing Dynasty
QI Mei-qin
(The Institute of Qing Histor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Manchu,together with the Qing Dynasty which it established,ushered in a new era that integrated the northern nomadic culture and the agricultural culture in the Central Plains of China,an era that witnessed intense collisions between Chinese traditional ruling ideology and modern western Christian civilization.Because of such characteristics as mentioned above,the feature of religious policies in Qing Dynasty was bound to be dominated by Confucian culture and Tibetan Buddhism,taking Buddhism Taoism and Islam into account while rejecting the new invasive Christianity.In the Qing Dynasty,though the circumstances for interior Buddhism,Taoism,Islam and Christianity were different,Tibetan Buddhism indeed had an unusual impact on the dynasty.But generally speaking,the Qing Dynasty adopted a political utilitarian attitude towards all kinds of religions:have it promoted if beneficial and useful,and restrained if profitless and useless.That wa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why Manchu rulers had never been controlled by any of the religions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different religious sects were basically confined to the range of imperial power.
Qing Dynasty;religion;state
祁美琴: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