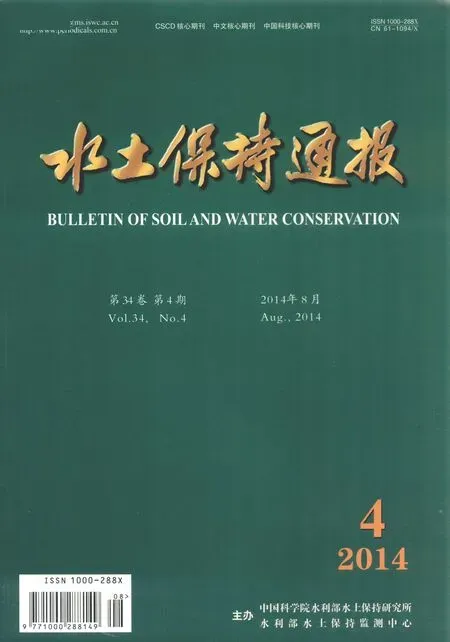寧鎮揚丘陵區土地利用空間結構的動態演變
——以江蘇省鎮江市為例
張榮天
土地利用/覆蓋變化(LUCC)研究是當前地理學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1],而其中土地利用空間結構研究又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2]。目前關于土地利用的研究已經涉及到土地利用變化時空演變、生態環境效應、驅動機制、模擬預測等多個領域[3-5],多采用分形理論[6]、RS 與 GIS 技 術[7]、景 觀 格 局 指 數[8]等 數理方法對土地利用/覆蓋變化(LUCC)進行探討,這些研究方法大多為傳統的地理學研究方法,結果不夠直觀,洛倫茨曲線作為重要的經濟學分析方法已經在土地利用結構得到了應用[9-10],它能較準確、直觀地反映土地利用結構演變的規律。1948年美國工程師Shannon[11]最早提出信息熵的概念,此后信息熵理論被運用到自然與社會科學等研究領域[12-13]。土地是一個具有耗散結構的自然與歷史綜合體,具有結構與功能的有序性特征,因此可以運用信息熵來刻畫土地利用結構的有序性規律[14];國內有不少學者對土地利用結構信息熵作了探討,不僅對東南沿海低山丘陵區、洞庭湖區、黃土丘陵溝壑區等典型區域[15-17],同時也對中小尺度地區(市域、縣域)的土地利用空間結構演變進行了實證探討與研究[18-19]。運用信息熵理論探討土地利用的空間結構的動態演變,可以綜合反映某一區域在一定時段內各種土地利用類型的動態變化及其轉換程度,為區域土地科學合理利用指出了新的思路與方向。
鎮江市位于江南平原與丘陵山地之間的過渡地帶,屬于寧鎮揚(南京—鎮波—揚州)丘陵區,土地利用類型復雜多樣,土地開發利用程度較高,其中丘陵崗地面積占63.4%,圩區、洲地面積占到19.5%,平原占17.1%,是江蘇省丘陵面積比重最大的地級市之一,是寧鎮揚丘陵區頗具代表性的地區。本研究以江蘇省鎮江市為研究的實證區域,基于鎮江市的1997—2009年的土地利用現狀數據,運用空間洛倫茨曲線,分析鎮江市域土地利用類型在區域內的空間分布差異情況,即分布相對分散與集中程度;同時采用Shannon信息熵理論,計算出鎮江市1997—2009年不同時期土地利用結構的信息熵H與均衡度E,揭示出13a間鎮江市土地利用結構的熵值動態演變及其區域分異的規律,以期為寧鎮揚丘陵區土地利用空間結構的調整與優化提供科學的理論依據和實踐參考。
1 研究方法及數據來源
1.1 研究方法
1.1.1 信息熵 Shannon信息熵主要用于描述系統的存在狀態,熵值變化可以表征系統具體的演變方向[20]。理論上信息熵越小,系統就有序程度越高,結構性就越強,它可以深入定量描述區域土地利用空間結構特征,熵值變化可綜合反映某區域在一定時段內各種土地利用類型的動態變化及其轉換程度,可用來刻畫區域土地利用系統的有序程度,計算公式為:

式中:H——信息熵,其值大小反映區域土地利用類型的多少及各類土地利用類型空間分布的均勻程度;

式中:E——均衡度;Hmax——信息熵的最大值;N——土地利用類型。均衡度E的取值區間范圍為[0,1]。當E=0時,區域土地利用結構處于最不均衡狀態;而當E=1時,土地利用結構達到平衡狀態。若E值越大,表明區域不同土地利用類型越多,且各類用地的面積相差越小,土地利用結構的均衡性越強。
1.1.2 空間洛倫茲曲線 洛倫茨曲線(圖1)最早是20世紀初經濟統計學家Lorenz[22]提出的一種關于研究工業集中化的統計方法,利用頻率累積數繪制成曲線,用來表示區域不平等差異程度,此后該方法在經濟學、地理學等領域中也得到廣泛運用。它可用于刻畫土地利用的空間分布特征,描述土地利用空間結構的分散與集中程度。因此,它是研究土地利用空間結構的一種重要方法。洛倫茲曲線b為向外凸起的曲線,與橫坐標成45°夾角的直線稱為絕對均勻線a。各土地利用類型曲線至絕對均勻線的離差就是該地類實際空間分布與其在全區均勻分布的差異測度。若越接近絕對均勻線,曲線的離差較小,表明該土地利用類型在區域范圍內分布越均勻;反之,該土地利用類型在區域內的分布差異較大,空間分布則較為的分散。Pi——景觀斑塊類型i占總面積的比例。為更好地說明區域土地利用類型之間的規模差異及其結構分異,引入土地利用均衡度的概念[21],具體公式為:

圖1 空間洛倫茨曲線示意圖
1.2 數據來源
研究基礎數據來源于江蘇省鎮江市1997—2008年土地利用變更統計數據(shp矢量格式),以及2009年的第二次的土地利用調查數據,為了使得研究的數據具有可比性,結合我國土地利用現狀分類系統(GB/T21010—2007),并且根據研究區土地利用現狀的具體特征,基于ArcGIS 9.3軟件分析平臺,把鎮江市的土地利用類型劃分為耕地、園地、林地、牧草地、其它農用地、居民點及工礦用地、交通水利用地、水域及未利用地的9大類型,并計算出每種地類的面積及比重,得出1997—2009年鎮江市土地利用結構(表1)。

表1 鎮江市1997-2009年土地利用結構 %
2 土地利用空間結構動態演變
2.1 土地利用類型的空間分布特征
利用空間洛倫茨曲線來說明研究區內各地類的空間分布集中與分散的規律。首先,利用鎮江市1997和2009年各土地利用類型面積的原始數據,分別求出兩個時段鎮江市各地類的區位熵,區位熵是指某一地區某土地利用類型面積占區域該土地利用類型總面積的比值與該地區土地總面積占區域土地總面積之比;其次,按照區位熵大小從低到高依次排列,并計算出鎮江市土地總面積的累計百分比和各土地利用類型的面積累計百分比;最后,將總土地面積累計百分比為橫坐標,以某地類面積累計百分比為縱坐標,各取100長度,繪制出直角坐標圖。以各累計數繪制坐標點,得到的曲線與絕對均勻線的離差就是該土地利用類型實際分布與在鎮江全市均勻分布的差異測度。根據空間洛倫茨曲線繪制的具體步驟,繪制成鎮江市1997和2009年2個時段的各土地利用類型的空間洛倫茨曲線可以看出,1997—2009年,鎮江市的居民點及工礦用地、耕地距離絕對均勻線較近,表明這兩種土地利用類型在鎮江市域內空間分布較為的分散,也就是意味著這兩種土地利用類型在鎮江市各區(縣)之內的分布較為均勻;而水域、未利用地、園地等依次遠離絕對均勻線,其中林地、牧草地距離絕對均勻線最遠,表明林地和牧草地在鎮江市域范圍內空間分布較不均衡,因為鎮江市地處寧鎮揚丘陵地帶,整體上鎮江西部的地形較高,而中東部地區相對平坦,因此林地主要集中分布在地形較高的鎮江市西部地區,而在鎮江市東部地區則較少分布。
2.2 土地利用結構演變的時間規律
根據Shannon信息熵的計算公式,對鎮江市1997—2009年的土地利用結構信息熵分別進行計算。由圖2可知,整體上研究區土地利用結構的信息熵自1997年以來就不斷升高,這充分表明了鎮江市土地利用結構正在朝著無序方向發展,土地利用結構穩定性逐漸減弱,但13a間,鎮江市土地利用結構的動態演變表現出十分顯著的“階段性”特征,總體上可以劃分出3大階段:(1)緩慢增長期(1997—2000年),1997年鎮江市土地利用結構信息熵為1.638 6,此后開始逐漸升高,但增長的幅度較小,到2000年僅1.643 5,年增長的幅度為0.12%,表明土地利用結構無序化進程極度緩慢,區域發展中土地利用結構的均衡度較高,各土地利用類型比例的變化偏小,變動較為顯著的為耕地和居民點及工礦用地;(2)快速上升期(2001—2004年),從2001年開始,信息熵開始快速上升,到2004年達到了最大值1.692 1,年增長的幅度為1.05%,這一時期信息熵H值急劇上升,表明該階段研究區的土地利用結構發生了劇烈變化,主要是耕地、居民點及工礦用地和牧草地的變化較為顯著。其中,耕地比重下降了2.96%,牧草地的比重下降了0.42%,而居民點及工礦用地的比重上升了1.77%,這一時期鎮江市土地利用結構無序發展程度最大;(3)穩步發展期(2005—2009年),從2005開始,土地利用的信息熵進入一個相對平穩時期,熵值H大致就在1.695 0左右波動,年增長幅度僅僅為0.04%,明顯低于前面兩階段,這一時期土地利用結構進入低水平的有序發展狀態。均衡度E與信息熵H 變化趨勢相似,也呈現出呈十分顯著的“階段性”演變規律,也大致劃分為3個階段,但整體上均衡度指數E一直處于不斷上升的趨勢,表明1997—2009年間鎮江市土地利用結構的均衡度在提高,占優勢地位的土地利用類型在減弱,但是通過與全國其它地區的信息熵指數對比分析可知[23],總體上而言,鎮江市土地利用有序程度還處在較低的狀態,表明鎮江市的土地利用結構尚處于低水平的均衡狀態,土地利用結構還有待于進一步的優化與調整。

圖2 鎮江市土地利用結構信息熵及均衡度演變
通過進一步分析,鎮江市土地利用結構信息熵變化主要是由于土地利用結構內部變化與調整,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1)工業化與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導致城鎮用地的需求量不斷增加。鎮江市正處在由傳統農業向現代化、工業化的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之中,同時由于滬寧線的開通,南京都市圈的打造,鎮江市城鎮化速度加快,促使城市建成區不斷向外圍地區擴展,使得大量耕地轉變為建設用地,農地景觀轉變為非農地景觀的現象在城郊地區尤為地顯著;13a間居民點及工礦用地面積增加了2.34×104hm2,交通水利用地面積增加了1 718hm2,建設用地快速增長導致區域土地利用結構信息熵不斷發生變化;(2)農業內部結構的調整,也是造成土地利用結構信息熵變化的重要原因。林地和牧草地的都呈現出不斷減少的趨勢,其中林地減少了1 439hm2,牧草地減少了2 860hm2;而園地呈現出不斷上升的趨勢,用地面積增加了3 460hm2。基于SPSS統計分析軟件,運用相關分析法定量地探討鎮江市土地利用類型與信息熵之間內在關系。在顯著性水平p<0.01時,園地、林地、水域及未利用地與信息熵成負相關,而居民點及工礦用地、交通水利用地與信息熵成正比;在顯著性水平p<0.05時,其它農用地與信息熵成反比,而耕地和牧草地與信息熵成正比,通過相關分析可知,耕地、牧草地面積的減少,居民點及工礦用地、交通水利用地面積的增加,直接促使鎮江市土地利用信息熵不斷上升,土地利用結構持續向無序的方向發展。
2.3 土地利用結構演變的區域分異
尺度是地理學的一個核心問題,尺度對于分析土地利用結構意義重大,因為不同尺度的選擇會得出相異的結論。市域尺度上的土地利用結構信息熵值是不能全面表征其它更小尺度上土地利用信息熵演變特征,即土地利用的整體有序程度無法表達部分的有序度,因此需要探討更小尺度(縣域、鎮域)土地利用結構演變的區域分異規律。鎮江市下轄市區(京口與潤州)、丹徒區、新區、揚中市、丹陽市及句容市,各個區(縣)由于經濟發展模式的差異以及工業化和城鎮化都處于不同的階段,導致其土地利用方式和程度也存在較大的分異。因此,鎮江市域不同區(縣)的土地利用結構的信息熵也會各不相同;同時即使在同一區(縣)范圍之內,在不同的時間段,其土地利用結構的信息熵也會出現相異的動態演變特征。根據上述的分析思路,基于GIS空間分析軟件平臺,提煉出鎮江市各區(縣)土地利用的類型數據,運用Shannon信息熵公式計算出鎮江市各個區(縣)土地利用信息熵H值,并運用Excel軟件繪制出信息熵演變圖(圖2),從而來探討鎮江市土地利用結構演變的區域分異規律。從圖3中可以看出,鎮江市區的土地利用結構信息熵值普遍地高于其所下轄的各區縣,但同時各區縣的變化趨勢也呈現出顯著的分異特征:(1)鎮江市區的信息熵值呈現出波動下降的態勢,鎮江市區1997年的信息熵H為1.717,之后信息熵就開始連續下降,到2009年,下降到僅僅為1.671,主要的原因為市區是鎮江市域城鎮化最為重要的空間載體,隨著城鎮化的步伐不斷加快,市區周圍大量的農業用地不斷轉化為建設用地,建設用地成為市區最主要的景觀用地,市區的土地利用結構不斷趨向單一化,這就造成了市區土地利用信息熵值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2)新區的土地利用結構的信息熵也出現了波動減小的趨勢,從1997年的1.667減少到2009年的1.631,表明新區的土地利用結構也正在朝著無序方向發展,這是由于新區近些年來,也逐漸成為城鎮用地不斷向外拓展的地區,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水平也處在較高的水平,城鎮用地逐漸變為新區的占據優勢地位的土地利用類型之一;(3)除市區和新區外的其余4個稍欠發達縣區的信息熵值呈現出波動上升的態勢,隨著1997年以來經濟社會的快速增長,導致區域土地利用結構均衡度有所增加,逐漸打破了這一區域內農業或者林業土地利用類型占據優勢的空間分布格局,從而導致鎮江西部丘陵區及中部過渡區土地利用信息熵值呈現不斷上升的態勢。

圖3 鎮江市各區(縣)土地利用結構信息熵變化
3 結論
(1)通過空間洛倫茨曲線分析可知,居民點及工礦用地、耕地距離絕對均勻線較近,這兩種土地利用類型在鎮江市域范圍之內空間分布較為分散;而園地、水域、林地、未利用地等依次遠離絕對均勻線,其中牧草地距離絕對均勻線最遠,表明林地和牧草地在鎮江市域范圍內空間分布較不均衡;
(2)鎮江市土地利用結構信息熵在時間上呈現出十分顯著的“階段性”特征,1997—2000年為緩慢增長期;2001—2004年為快速上升期;2005—2009年為穩步發展期;耕地和居民點及工礦用地的面積變化與土地利用結構信息熵的變化顯著地相關,是鎮江市土地利用結構演變的主要影響類型;
(3)鎮江市土地利用結構在空間上呈現出較為顯著的區域分異規律,經濟發達的市區及新區的信息熵整體上高于其它區縣,且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土地利用結構的有序性逐漸提高,而其它稍欠發達4個區縣的信息熵卻呈現出日益上升的態勢,土地利用結構的有序性不斷降低。
(4)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本研究僅對鎮江市1997—2009年的土地利用空間結構的演變特征進行了描述,時間尺度不夠長,而大時間尺度的研究更能揭示區域土地利用結構演變的特征及規律;本研究初步地分析了鎮江市域信息熵呈現出不斷上升趨勢與各地類面積變化的相關性的定量分析,弱化了關于市域信息熵演變階段性特征及區域分異深層次驅動因子的分析與探討,而這種分析更加有利于針對性地提出優化區域土地利用結構的策略與方案;再者,本研究只是選取了寧鎮揚丘陵區典型案例地鎮江市,通過以點帶面的研究方法探討了寧鎮揚丘陵區土地利用結構演變規律,這樣研究模式在某種程度能揭示該區域的一些共性規律,但是還是不夠全面和科學的,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積極探索將鎮江、南京及揚州市的土地利用作為整體進行相關研究,并且探討寧鎮揚丘陵區土地利用結構動態演變的內在機理,這對于揭示寧鎮揚丘陵區土地利用結構的總體演變特征規律以及為這一地區土地利用規劃與整理、城鄉統籌發展提供更為有益的理論與實踐的參考,從而使得寧鎮揚丘陵區的土地利用向著更加科學、合理的方向發展。
[1] Turner B L,Skole D,Sanderson S,et al.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R].Stochkholm:IGBP,Science/research land IGBP Report No.35and HDP Report No.7,1995.
[2] 史培軍,李曉兵.土地利用/覆被變化研究的方法與實踐[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66-90.
[3] 郭旭東,陳利頂,傅伯杰.土地利用/土地覆被變化對區域生態環境的影響[J].地理科學進展,1999,7(6):66-75.
[4] 李平,李秀彬,劉學軍.我國現階段土地利用變化驅動力的宏觀分析[J].地理研究,2001,20(2):130-138.
[5] RaoKS,Rekha P.Land use dynamics and landscape change pattern in a typical micro-watershed in the mid elevation zone of central Himalaya,India[J].Agriculture,Ecosystems and Environment,2001,86(2):113-124.
[6] 張榮天.寧鎮揚丘陵區土地利用空間結構的分形研究:以鎮江市為例[J].水土保持研究,2013,20(3):98-10.
[7] 彭文甫,周介銘,楊存建,等.基于RS與GIS的縣級土地利用變化分析:以四川省成都市雙流縣為例[J].遙感技術與應用,2008,23(1):24-30.
[8] 張榮天,張小林,李傳武.鎮江市土地利用景觀格局分析[J].經濟地理,2012,32(9):132-137.
[9] 鄧晶,刁承泰.基于空間洛倫茨曲線和基尼系數的土地利用結構分析:以重慶江津市為例[J].國土與自然資源研究,2008(1):38-40.
[10] 扈傳榮,姜棟,唐旭,等.基于洛倫茲曲線的全國城市土地利用現狀抽樣分析[J].中國土地科學,2009,23(12):44-50.
[11] Shannon C E.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J].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1948,27(1):623-658.
[12] Yan Aimin.Human resource ecosystem and its evolutionary rules[J].Ecological Economy,2007,3(2):365-372.
[13] John E C,Shi Lei,Samantha J.Environment as the stage for economic actors[J].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07,5(4):3-8.
[14] 譚永忠,吳次芳.區域土地利用結構的信息熵分異規律研究[J].自然資源學報,2003,18(1):112-117.
[15] 周生路,黃勁松.東南沿海低山丘陵區土地利用結構的地域分異研究[J].土壤學報,2003,40(1):37-45.
[16] 申海建,郭榮中,劉剛,等.洞庭湖區土地利用結構信息熵分異規律研究:以湖南省岳陽市為例[J].河北農業科學,2008,12(2):92-97.
[17] 石培基,張學斌,羅君.黃土丘陵溝壑區土地利用空間結構的計量地理分析:以甘肅省天水市為例[J].土壤,2011,43(3):439-445.
[18] 趙晶,徐建華,梅安新,等.上海市土地利用結構和形態演變的信息熵與分維分析[J].地理研究,2004,23(2):137-146.
[19] 周子英,段建南,梁春鳳.長沙市土地利用結構信息熵時空變化研究[J].經濟地理,2012,32(4):124-129.
[20] 陳彥光,劉繼生.城市土地利用結構和形態的定量描述:從信息熵到分數維[J].地理研究,2001,20(2):146-152.
[21] 吳燕芳,石培基,劉寧寧.隴南山地土地利用結構動態演變分析[J].水土保持研究,2010,17(6):133-137.
[22] 邊靜,何多興,田永中,等.基于信息熵與空間洛倫茲曲線的土地利用空間結構分析:以重慶市合川區為例[J].水土保持研究,2011,18(5):201-204.
[23] 毛良祥,林燕華.基于信息熵的我國土地利用結構動態變化研究[J].國土資源科技管理,2008,25(6):4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