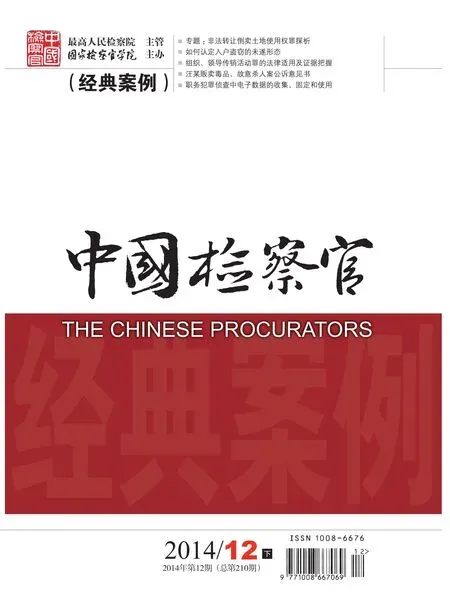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罪司法實踐疑難問題
文◎龍長海
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罪司法實踐疑難問題
文◎龍長海*
《憲法》第10條規定了所有權和使用權相分離的土地制度。根據該條規定,土地的所有權歸國家或集體所有,“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占、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一切使用土地的組織和個人必須合理地利用土地。”為了落實《憲法》關于土地制度的規定,我國刑法第228條規定了非法轉讓、倒賣土地使用權罪。近年來,我國工程建設事業快速發展,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建設用地需求大幅增加。由于土地是極其重要的稀缺資源,在土地問題上,國家要采取嚴格的保護措施。在司法實踐中,認定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罪的爭議非常大。例如劉某涉嫌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案(以下簡稱“劉某案”)中,法檢兩家就劉某行為的定性問題,產生了爭議。
劉某原系內蒙古甲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公司”)董事長。2005年3月8日,甲公司同呼和浩特市國土資源局簽訂出讓合同,約定將18.22畝的土地出讓給甲公司,并于同年6月取得了該土地的使用權。劉某代表甲公司轉讓爭議地塊時未經另兩位股東同意。因三方對該地塊的開發有所約定,故土地使用權證取得后一直由甲公司另一股東持有。劉某于2006年2月20日轉讓該土地時以甲公司的名義向呼市國土局出具了土地使用權丟失、正在補辦的證明,隨即土地變更至金石公司名下,甲公司因此獲利160多萬元。一審法院認為甲公司、劉某行為不構成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罪。二審法院以一審法院判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撤銷原判,發回重審。經重審仍然認定,甲公司和劉某不構成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罪。后檢察院抗訴,被二審法院駁回。[1]
本文試結合司法實踐中有關“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罪”的案例,對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案件的幾個典型疑難問題進行探討。
一、土地轉讓行為違法性的判斷
刑法第228條使用的是空白罪狀的立法模式,即構成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罪的前提條件是轉讓行為違反了土地管理法規。主要指2001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三百四十二條、第四百一十條的解釋》對此進行了明確規定,即刑法第228條規定的“違反土地管理法規”,“是指違反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等法律以及有關行政法規中關于土地管理的規定”。但實踐中在認定是否“違反土地管理法規”的問題上,出現了許多需要解決的新情況。在上述劉某案中,法檢兩家有關劉某行為是否構成犯罪的關鍵問題,便集中在了劉某轉讓土地使用權行為的違法性判斷上。
在劉某案中,法院認為劉某轉讓土地行為合法、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犯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罪,罪名不成立的理由有兩個。第一個理由是土地轉讓時投資未達到投資總額25%,只造成合同標的物瑕疵,而不影響合同的效力。第二個理由是該土地轉讓協議已經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批復準許。[2]
如何評價法院上述論證土地轉讓行為合法的裁判理由呢?筆者認為,應該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一)甲公司與金石公司土地使用權轉讓行為的效力及其影響
法院認定劉某不構成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案的重要理由是“轉讓的土地未達到25%以上的投資,屬合同標的物的瑕疵,違反該規定不是認定土地使用權轉讓合同效力的法律強制性規定”。應該說,這一論述理由是成立的。《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39條規定,以出讓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權的,轉讓房地產時,應當符合“完成投資開發總額的25%以上”這一條件。對此,1996年《國家土地管理局對〈城市房地產管理法〉中有關條款的請示的復函》明確規定:“《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39第(二)項中規定的投資總額,是指基礎設施、地上建筑物以及其他設施的開發投資總額,不包括土地使用權出讓金。按照本條規定,屬于房屋建設工程的,必須完成開發投資總額的25%以上,方可轉讓房地產。”從劉某案的證據來看,在轉讓土地時,其投資額未達到完成投資總額25%以上的要求。但是,這能否否定轉讓爭議土地使用權合同的效力呢?這一點需要結合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判例來認定。
最高人民法院就當事人在取得國有土地使用權證后對轉讓土地的投資開發未達到投資總額25%以上的,是否影響轉讓合同的效力問題在其審理的“桂馨源公司訴全威公司等土地使用權轉讓合同糾紛案”中明確指出:《城市房地產管理法》“關于土地轉讓時投資應達到開發投資總額25%的規定,是對土地使用權轉讓合同的標的物設定的于物權變動時的限制性條件,轉讓的土地未達到25%以上的投資,屬于合同標的物的瑕疵,并不直接影響土地使用權轉讓合同的效力。”[3]因此,從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來看,在《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39條規定的“應當”是管理性的應當而非效力性應當,當不符合這一“應當”條件時,并不能否定轉讓土地合同的效力。因此,從民事關系上看,盡管投資開發總額未達到25%的規定,但甲公司和金石公司的轉讓土地使用權的合同是有效的。
但是,這種甲公司和金石公司之間的有效土地轉讓協議,是否等于肯定了甲公司土地轉讓行為的合法性呢?筆者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從《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39條的規定看,盡管甲公司和金石公司的達成的轉讓土地的協議有效,但這一民事上的有效行為,不能否定其對《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39條的違反,也就是說,甲公司的行為仍然是違反土地管理法規的行為。
(二)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影響土地轉讓行為的違法性判斷
劉某案中,法院判決書否定劉某成罪的另一理由是“土地轉讓協議經呼市人民政府批復準許,現金石公司已取得相關轉讓土地國有土地使用權證”。那么,應該如何評價法院的這一觀點呢?筆者認為,這需要從如下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首先,呼市政府的批復文件并不能將甲公司的違反土地管理法規的行為變為合法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系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的法律,其效力低于《憲法》,卻高于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呼市市政府對土地使用權轉讓行為的批準不過是一個具體的行政行為,而該具體行政行為并不能否定某一行為的違法性。至于為什么在違反土地管理法規的情況下,呼市市政府還要進行批復,這需要對相關人員的行為是否違法、是否有瀆職行為進行單獨評價,但一紙政府的批復文件并不能把違法的行為變為合法,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其次,金石公司獲得土地使用權證是基于合法的民事行為獲得的,這一點也不能否定甲公司違反土地管理法規轉讓土地使用權的性質。如上所述,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盡管土地轉讓行為的標的存在瑕疵,但并不影響轉讓行為的效力。金石公司完全可以取得該轉讓土地的使用權,并在該土地上進行相應的施工建設,但這并不能否定甲公司轉讓土地行為的違法性。對甲公司而言,其轉讓土地行為違法性的判斷,要依據具體的土地管理法規進行,很明顯,在甲公司進行土地轉讓時投資未達到投資總額25%規定的情況下,甲公司的這一轉讓行為已經違反了《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39條的規定。之所以一項違法的行為并不影響民事行為的效力,主要理由在于保護交易安全,維護交易對方的合法權益。
筆者認為,一項民事上有效的行為,并且在經過政府的批復受讓人取得轉讓土地的使用權的情況下,仍然不代表肯定了土地出讓方轉讓土地行為的合法性。上述案例中,甲公司實施的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的行為符合刑法第228條要求的“違反土地管理法規”這一要件。
二、犯罪主體的確定
按照刑法第231條的規定,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罪的犯罪主體,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單位。單位犯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責任人員判處刑罰。進而,在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犯罪中,有關犯罪主體是單位還是自然人的問題,就成了司法實踐中的爭議點。
在上述劉某案中,劉某代表甲公司將18.22畝國有土地使用權非法轉讓給金石公司的行為,到底是單位行為還是劉某的個人行為呢?法檢兩家對這一問題存在著較大分歧。檢察院起訴書指控甲公司構成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罪、劉某個人也構成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罪。一審刑事判決書完全否定了甲公司和劉某個人構成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罪。刑事抗訴書明確指出:甲公司股東不服判決、請求抗訴,抗訴書堅持認為甲公司和劉某都構成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罪。但這一刑事抗訴再次被法院駁回。此后,檢察院再次抗訴,并在刑事抗訴書中明確指出:“即使被告單位按一審法院的理由無罪,被告人劉某的個人行為也構成了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罪”,這一抗訴意見似乎認可了一審法院認定的甲公司不構成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罪的判決。但是,這一抗訴再次被二審法院裁定駁回。從上述檢法兩院的訴訟文書中可以看出,對甲公司是否構成犯罪的問題,經歷了一個從檢察院認為單位構成犯罪到逐漸認可法院否定單位犯罪的過程。
在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罪中,到底該如何認定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的行為是自然人的個人行為還是單位的行為呢?筆者認為在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犯罪中,認定單位犯罪的依據在于如下兩個要素,即單位決定和為了單位利益。
在單位決定問題上,一般存在單位集體研究決定和單位負責人個人決定兩種情形。在劉某案中,顯然劉某是個人決定。劉某案中,一審刑事判決書否定甲公司構成犯罪的理由是“被告人劉某以甲公司的名義轉讓土地,但未召開股東會,其他股東均不知情,因此,被告單位內蒙古甲公司不構成犯罪”。那么,法院否定甲公司構成犯罪的理由是否成立呢?筆者認為劉某是否具有代表甲公司處分爭議土地使用權的權利應該依據劉某任甲公司董事長時的甲公司章程的規定進行判定。如果當時甲公司的公司章程明確賦予了時任該公司董事長的劉某處分公司土地使用權的權利,則劉某的行為可以代表甲公司,甲公司符合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罪的主體要件。但是在起訴書、判決書、抗訴書和裁定書中都未提及這一點。如果當時的公司章程對公司負責人的職權范圍并未做明確的規定,則作為甲公司負責人的劉某處分爭議土地使用權的行為,可以認為是單位負責人決定。只有在劉某任甲公司負責人時甲公司的章程對負責人處分公司土地使用權的行為進行明確限制的情況下,才能否定甲公司符合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罪的主體要件。另外,劉某將該土地高出買入價格160多萬賣出,且賣出款項進入甲公司賬戶,可以認為是為單位牟取利益。
因此,在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罪中,將土地使用權進行非法轉讓是由能夠代表單位的負責人個人或者單位集體決定并為了謀取單位利益時,則應該認定為單位犯罪,單位和直接負責人都應該對這一非法轉讓行為承擔刑事責任。
三、主觀目的的作用
按照刑法第228條的規定,構成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罪要求行為人主觀上具有牟利的目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按照刑法第228條的規定,在牟利目的的驅使下,該如何區分“非法轉讓”和“非法倒賣”這兩種行為呢?究其實質而言,“非法倒賣”也應該屬于“非法轉讓”行為方式的一種。但在228條的罪狀中,卻將“非法轉讓”和“非法倒賣”并列,這便說明二者之間存在差別。另外,從司法實踐上的判例來看,在該類案件中,有的被告人被以“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罪”追究刑事責任、有的被告被以“非法倒賣土地使用權罪”追究刑事責任,“非法轉讓”和“非法倒賣”之間也存在區別。
在牟利目的這一主觀要件的要求下,到底該如何界分“非法轉讓”和“非法倒賣”呢?
筆者認為行為人實施“非法轉讓”和“非法倒賣”行為在客觀上都可能獲取到了一定的差價,但這種同樣是為獲取差價的違法行為,在評價上應該從行為人最初取得土地時的主觀目的來認定。這里的“非法倒賣”應該是指行為人在獲取土地使用權時,主觀上便具有出賣牟利的目的。也就是說,在認定“非法倒賣土地使用權罪”時,應該證明行為人獲取土地使用權時便具有出賣的非法目的。而行為人在實施“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罪”中的“非法轉讓”行為時,盡管也獲得了一定的差價,但行為人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權時卻并不具有倒賣的非法目的。因此,對“非法倒賣”和“非法轉讓”的區分可以同意如下的觀點,即“所謂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是指行為人不是以出售牟取為目的,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權后,違反法律規定將土地使用權轉出、讓與他人的行為。所謂倒賣土地使用權,是指違反法律規定以出售牟取為目的,買入土地使用權后又賣出的行為。”[4]很明顯,這種對“非法轉讓”和“非法倒賣”行為的劃分,完全依據行為人的主觀目的。然而,在司法實踐中,要想證明存在主觀目的,必須有相應證據的支持。
那么,在實踐中應該如何對主觀目的進行證明呢?筆者認為如果行為人能夠供述其自始獲取土地的目的是為了出賣,則行為人的行為直接可以評價為“非法倒賣”;如果行為人否認其獲得土地時的目的就是倒賣牟利,并且其取得土地的行為方式合法,則應該按照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罪追究刑事責任;如果行為人并未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權,便將土地進行出售牟利的,則直接可以認定為非法倒賣土地使用權罪。例如在陳某某案中,陳某某在未辦理相關土地使用手續的情況下,以建設農副產品交易市場為名將該塊土地規劃成宅基地出售。法院認定,被告人陳某某構成非法倒賣土地使用權罪。[5]
如前所述,在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案件中,行為人在非法轉讓土地的同時,往往會獲得一定的差價,那么,是不是所有獲得了差價的非法轉讓行為,都符合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罪中的“以牟利為目的”這一主觀構成要件呢?有觀點認為:“如果行為人有合法的理由轉讓土地使用權,而不是為了通過轉讓行為單純獲利,那么即便在客觀上真的獲取了利潤,也不能以非法轉讓、倒賣土地使用權罪論處。”[6]那么,如何評價這一觀點呢?
筆者認為盡管這一觀點有一定的道理,但在實踐中可操作性不強。在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案中,行為人總是能夠為自己找到各種轉讓土地的理由。盡管行為人找到各種借口為自己辯解,但這種借口的背后都無法掩蓋行為人非法轉讓土地獲取巨額利潤的客觀事實。例如劉某案中,劉某通過非法轉讓土地行為,獲取了高達160多萬的利潤。因此,盡管在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案件中,我們不能采用客觀歸罪的做法,但是在認定被告人牟利目的的證據方面,偵查機關能夠獲取的客觀證據證明行為人有通過非法轉讓行為獲取巨額利潤的事實,便可推定行為人主觀上具有牟利的目的。目前,這一做法被司法實務部門所采納。筆者認為司法實務應該繼續堅持上述對行為人牟利目的進行推定的做法。否則,在非法行為人客觀上通過非法轉讓土地行為已經獲取巨額利潤的情況下,卻因被告人的某種辯解而否定其主觀牟利的目的,將使檢察機關承擔過重的舉證責任,不利于土地市場秩序的維護和對土地資源的保護。另外,這種根據客觀情況對行為人主觀目的進行推定的方法,在司法實踐中廣為采用,并不會出現客觀歸罪情形的出現。
因此,在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罪中,對行為人主觀目的的判定,既影響具體罪名的確定,也影響行為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的判斷。
注釋:
[1]案例來源:內蒙古呼和浩特市人民檢察院。
[2]參見(2012)賽刑初第40號刑事判決書。
[3]最高人民法院(2004)民一終字第46號判決書。
[4]彭文華、劉德法:《論非法轉讓、倒賣土地使用權罪》,載《法學家》2001年第5期。
[5]參見(2014)桐刑初字第00123號刑事判決書。
[6]劉傳稿等:《非法轉讓、倒賣土地使用權罪實務探析》,載《工會論壇》,2013年第1期。
*內蒙古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人民檢察院公訴處副處長,法學博士[0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