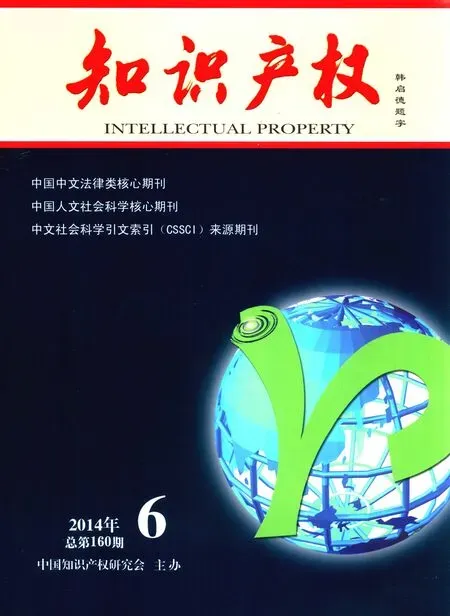價值流轉中的知識產權評估研究
徐 皝
價值流轉中的知識產權評估研究
徐 皝
知識產權等無形資產在現代經濟社會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知識產權價值的流轉已成為社會經濟生活中日益頻繁和普遍的一種需求和現象。目前主要影響知識產權價值流轉的,一是對知識產權的價值評估,二是對知識產權風險的分擔和補償,三是知識產權交易市場的建設與完善。從促進知識產權流轉的角度出發,通過對知識產權價值評估難的分析,提出知識產權價值評估應遵循的客觀標準,并對如何堅持市場化取向、主觀把握好知識產權價值評估做了具體的探討。
知識產權 價值評估 客觀標準 主觀把握
知識產權具有巨大的經濟價值和品牌價值,已經成為當前社會的共識。就其天生的公權與私權兼顧的特性來說,知識產權的價值流轉具有必然性a在傳統反壟斷法中,拒絕交易和流轉是濫用市場支配行為的一種,會受到反壟斷法等相關法律的規制。見呂明瑜:《知識產權壟斷的法律控制》,法律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第290頁。。知識產權的價值流轉是知識產權利用的更高階段,而知識產權價值評估是知識產權價值流轉的前提。“對知識產權類無形資產價值進行科學評估,是維持知識產權資產再生產、從價值形態上進行定額補償的需要,也是資源優化配置的必要條件。”b陳昌柏:《知識產權戰略——知識產權資源在經濟增長中的優化配置》(第二版),科學出版社2009年2月第2版,第260頁。但目前對知識產權的價值評估很不規范,評估人員素質低,評估主觀隨意,評估結果差異較大。整個知識產權評估行業既缺少統一的評估標準和規范,也缺少來自政府部門和行業協會的有效監管和違規懲處。在實務中,知識產權評估甚至隨意到連不具備評估資質的機構也能開展評估業務的程度。如北京某銀行在版權質押時就要求出質方必須到中國版權交易中心去進行評估,而中國版權交易中心并無進行知識產權評估的資質。至于評估機構偏向于支付評估費用一方得出評估結論的情況更比比皆是。
如何處理知識產權本身無形財產權的特點而帶來的評估困難,以及如何滿足市場流轉特殊目的對知識產權價值評估提出的特殊要求,則是當前尚難解決的理論和實踐難題。本文從促進知識產權市場流通的角度出發,通過分析知識產權價值評估的客觀標準和主觀把握,對解決這個難題提出了看法。
一、價值流轉中的知識產權評估難
因為知識產權的無形性、未來收益的不確定性和較高風險性,以及變現方面存在的困難和風險,導致了知識產權的價值評估之難。
但知識產權價值c本文所討論的價值均為經濟價值。評估之難,并不難在評估方法的選擇上,因為方法總是達到目的的工具,根據評估目的(即價值類型)的不同,總能找到相對最為適宜的方法;知識產權價值評估之難,也不難在對知識產權價值評估主觀性較強上,因為無論主觀認識的差異有多大,總能找到公認的、公允的客觀基礎價值,主觀認識總是圍繞著客觀基礎價值上下波動的;知識產權評估之難,也不難在缺乏統一的評估標準上,因為標準問題僅僅是技術問題,而技術問題是想辦法就可以解決的,如可以由政府、行業協會根據需要出臺各種評估標準和規范以解決當前知識產權價值評估失范的問題。
知識產權價值評估之難,難在如何根據市場取向,確定市場認可的客觀價值并在此基礎上根據交易具體情況進行主觀調整,以使評估結果容易為市場所接受,從而實現知識產權的順利流通和便利交易。
二、如何保證知識產權價值流轉的客觀共識
“評估”二字從字面上看就天然地蘊含著主觀性。根據目前知識產權價值評估主觀隨意性較為普遍的現狀,從平衡主客觀的角度,需要強調知識產權評估的客觀性。畢竟,評估價值仍然是知識產權內在價值的一種表現形式。本文認為,知識產權的價值可以分為公允價值(或基礎價值)和溢價價值(或發現價值)兩部分。公允價值是下限價值(即公允的基礎價值),溢價價值是上限價值(即交易各方主觀認同的在基礎價值之上的溢價價值,溢價多少依主觀認同的程度而不同)。
以著作權為例,著作權的公允價值就可能包括“作為知識財產的著作權交易市場許可費、著作權價格、數據編輯費、數據輸入費、軟件使用費、硬件使用費、網絡經費等……這是由著作權交易市場最小值論展開的著作權交易市場的多樣性決定的。d北川善太郎著:《著作權交易市場—信息社會的法律基礎》,郭慧琴譯,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第149頁。”
為了保證知識產權價值評估的客觀性,有以下幾個原則應該予以綜合運用:
第一,及時性原則。知識產權有保值難(價值易消減性)的特點,價值可控性差,許多環節很難預料和控制,容易產生“價值漂浮”。“對處于變動狀態的知識產權價值而言,評估價值與知識產權價值往往不一定等值。”e李鵑:《知識產權擔保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第157頁一般而言,知識產權的價值會因為科技的發展與應用情況的變化而處在不斷的變化之中,大多數情況下會因時間的流逝而逐漸降低。因此,圍繞市場交易的知識產權評估時間越接近越及時,評估的結果就會越準確。
第二,價值類型原則(即方法服從于評估目的)。不同的主觀目的決定了評估的側重點不一樣。從融資角度研究知識產權價值評估重點在研究知識產權收益能有多大的還本付息能力,除了從質押融資角度研究知識產權價值評估外,還有其他幾種主要的知識產權價值評估研究角度:如從股權投資角度研究知識產權價值評估,重點在知識產權經濟狀態的評估,即研究知識產權商業應用前景及未來可能的經營收益情況(如能否連續三年盈利,達到企業上市條件從而通過上市退出);還有以“進一步研發”為目的的知識產權價值評估(技術狀態評估),側重于對知識產權所蘊含的技術的產業前景進行評估;以及對知識產權價值法律狀態的評估等。而且因為評估目的不一樣,對知識產權價值可能進行全部評估也可能進行部分評估。
第三,規則統一性原則。要有統一的無形資產評估準則,提高知識產權價值評估的可操作性,規范評估中的隨意性。我國雖然制定了無形資產評估準則,但操作性不強,尚未形成規范化、系統化的知識產權評估體系,評估的隨意性比較強。為此,要適應知識產權融資創新的需求,不斷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并建立規范的評估標準和專業的評估機構,由專業的評估機構和人員(通常為各種評估中介機構和注冊資產評估師)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資產評估準則,對知識產權的價值進行分析、估算并發表專業意見。
第四,數據決定原則。所有的知識產權價值評估方法都可概括為數據分析法,都要依賴有質量保證的數據來源。所以能否獲得真實、有效、全面的數據,決定了評估方法的選取。或者說,獲取數據的條件和能力在事實上決定了評估方法的選取。在這個意義上說,數據質量決定評估方法。
第五,復合評估原則。復合評估法是知識產權價值評估的通行做法。復合評估法指為了獲得評估結果的準確性,通常要根據評估對象的特殊性質、所能獲得數據的質量和數量,確定一種評估方法作為主要評估方法,再以兩到三個以上的其他評估方法獲得的評估結果進行參驗。多種評估方法的綜合運用,能使評估結果的準確度得到很好的調校
第六,專利的深度檢索原則。知識產權評估須以專利檢索、分析工作為基礎。“知識產權評估的核心要素,即撰寫知識產權評估報告的重點在于開展專利、專利技術的深度檢索、分析、評估”f魏衍亮:《知識產權價值評估問題研究》,載《電子知識產權》2006年12期。依靠對技術的檢索、分析,工作團隊既要熟悉相關技術也要熟悉相關市場。雖然資產評估的基本方法有成本法、收益法、市場法三種,但具體到無形資產,因為知識產權的技術含量較高,對知識產權價值評估來說,基本方法有檢索法、成本法、收益法、市場法四種,其中以知識產權檢索為主要內容的檢索法是其他幾種方法能付諸實施的依據和基礎。
第七,知識產權評估工作的專業化原則。知識產權也稱智力成果權,其技術含量是很高的,對知識產權的價值評估,即使交易(流轉)各方可以根據自己的接受度來對知識產權價值達成一致意見,還是要通過專業的評估機構(最好是中立的中介機構)來給出更為權威、相對準確的評估意見。從這個意義上說,知識產權價值評估屬于專業中介機構承擔的技術工作。為此,要大力發展知識產權中介機構(評估機構和擔保機構等)。
此外,知識產權價值評估是高度專業化和經驗化的工作,所以應大力培養金融科技復合型人才,提高評估的專業化水平和準確度。
三、對客觀標準的綜合運用:知識產權價值評估的主觀把握
對于知識產權價值評估究竟需不需要專門的方法,當前學界也存在著不同的意見。有強調方法與評估公式重要性和準確性的,也有認為方法不那么重要的。認為方法不那么重要的意見又分兩種,一種是覺得知識產權評估本來就是一種主觀性非常強的行為,其價值的最終確定取決于知識產權交易雙方的反復談判和妥協(影響因子包括交易目的、交易地位、交易信息對稱度等),方法只是用來談判的工具(魏衍亮);一種覺得知識產權價值的評估還應更多地著眼于專有權使用期限,是否第二專利,是否涉及侵權訴訟、技術的穩定性等知識產權本身的特性(鄭成思),他們甚至在方法的選取上贊成一些看似很隨意的方法(如贊成對商譽價值的評估采用汽車沖程的辦法)。本文認為,對知識產權價值的主觀把握還是要借助工具(各種評估方法)的幫助才能達成。
以下是幾種在實務中常用且被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的知識產權評估辦法。
(一)收益法
指通過估算被評估資產未來收益并折算成現值,借以確定資產價值的方法。相比較市場法而言,知識產權這種無形資產的評估用收益法更為妥當,關鍵是未來收益額、市場占有率、折現率、收益期限等參數的選取。
本文認為,收益法很好地體現了資產評估中將利求本的思路,既具有注重知識產權市場變現能力的優點(這點是融資提供方所特別注重的),也具有重視知識產權技術價值商業化、產業化的優點,比單純考慮融資需求方知識產權重置成本的成本法更容易為融資提供方接受,也比較為輕視知識產權技術價值的市場法更容易為融資需求方所接受。
但是,相比成本法和市場法受主觀因素影響不大的優點而言,在參數選取上受主觀因素影響較大的收益法若要真正獲得相對客觀、準確的評估結果,就得對參數選取進行公正、客觀的規范。
知識產權的未來收益額和市場占有率受多種因素影響和制約,對這些影響因素的綜合判斷往往帶有很強的主觀性。同時,“由于折現率是對未來風險及不確定性的估計和預言變成單一數字后的集聚體,所以折現率的主要特點是缺乏信息”g[美]帕爾、史密斯著:《知識產權價值評估、開發與侵權賠償》,周叔敏譯,電子工業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第40頁。。因此,未來收益額及折現率常被一些職業道德水平低下的評估師用于操縱評估結果。
收益法是一種技術性較強的評估方法。收益法的人為主觀因素的影響過大,應研究如何約束這些主觀因素對評估結果的影響,特別要解決操縱評估結果的行為。未來收益額、收益期限、市場占有率和折現系數的選取,是影響收益法評估結果準確性的幾個重要因素。要通過評估準則來規范參數的選取及防止評估方法和結果的主觀隨意性。
(二)市場法
又叫市場價格比較法或現行市價法。指選擇若干與被評估資產相似的已交易資產作為參照物,在修正參照物價格的基礎上得出被評估資產的價值。有研究者認為,市場法是最直接、最容易理解的評估方法,這可能是指市場法的運用是通過直觀的對比調整的方法,來比較一個或幾個與評估標的相類似的資產的成交價格和交易條件。本文卻認為,市場法是最難運用、最難實施的評估方法,因為在當前知識產權交易市場很不發達的情況下,完成交易的知識產權本就不多,還要找到與評估標的相類似的已交易資產就更難。換句話說,姑且不論市場法能否很好地評估出知識產權的價值,目前尚不具備實施市場法的條件,多數情況下沒有參考物可比。
市場法采用的是比較和類比的思路,根據替代原則來估測資產的價值。因此,市場法的正常運用既需要有公開活躍的市場和可比的資產交易活動,也需要有能很好進行對比的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員。這樣,才能在評估物和參照物功能對比、市場條件對比、資產特征對比等方面獲得一個比較客觀、公正、準確的結果。換句話說,在資產市場相對比較成熟和完善的國家地區具備運用市場法的條件,在資產市場尚不發達的國家地區(比如我國),運用市場法來評估知識產權價值就難以實施。而且,市場法所依賴的參照物交易信息的準確、全面搜集是件非常難的事情。受市場環境和信息條件的雙重限制,知識產權評估實踐中對市場法的相比成本法和收益法少很多。
(三)成本法
成本法是指按被評估資產的重置或再生產的現行成本扣減各項有形、無形損耗(實體性損耗、功能性損耗、經濟性損耗等)來確定資產價值的方法。低于成本,知識產權人將失去交易(流轉)的動力,甚至失去進行知識產權創新的動力。成本法是從知識產權所有人角度出發,運用成本收益原則的“保底”評估方法,即確定知識產權評估價值下限的方法。這種方法,因為新技術的發展可能使得以舊技術為主的專利失去大部分價值,只能作為知識產權價值評估的輔助方法。鄭成思認為,“將有形物(無論動產或不動產)評估中的‘重置成本’等傳統原則應用于知識產權評估,是我國目前評估中出現各種問題的主要原因。”h鄭成思:《論知識產權的評估》,載《法律科學》1998年第1期。
成本法的應用,要求用于評估的知識產權必須是可復制、可再生的,即可以重建的。此外,還要求有關于重建成本的歷史資料,被評估的知識產權必須處在持續使用的狀態,即必須依然具有技術使用價值,若因新技術的產生淘汰了被評估的知識產權使其失去技術使用價值,也就沒有進行價值評估的意義了。
全面預算管理,主要是利用預算的方式,通過在財務資源以及非財務資源的有效配置等,來對企業內部的各個職能部門的業務活動進行有效約束,進而確保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按照經營計劃執行,以確保經營管理目標的順利實現。對于鐵路運輸企業來說,實施全面預算管理,能夠對鐵路運輸企業的業務流、信息流以及資金流等進行全方位的整合,并依靠全面預算管理過程中一系列系統科學的控制方法,來確保企業的戰略發展規劃、日常活動管理順利推進,促進實現企業的利益最大化。
成本的資產價值屬性對應的是勞動價值論,這與知識產權價格屬性對應效用價值論不一樣。而勞動價值論與效用價值論的分歧也就是知識產權價值決定理論的分歧。在效用價值論看來,商品的價值取決于它的效用,效用越大則價值也越大。
從當前知識產權評估實踐看,收益法的適用已成為主流,市場法運用得較少,成本法已經很少使用了。
(四)質押系數法
與常用的成本法、市場法和收益法不同,質押系數法特別考慮了知識產權質押期間各種因素對價值波動的影響,并將這些影響用于調節前三種常用方法估算出來的知識產權價值。知識產權質押系數法的公式為:知識產權質押評估價值=擬質押知識產權的市場價值×(1-質押系數)。
提出質押系數法的研究者認為,在這種方法下“質押”這一特殊評估目的被分離出來,因此可以分別得出知識產權正常市場條件下的非質押價值和質押條件下的知識產權質押評估價值,這便于更準確地判斷知識產權質押融資中的貸款額度和質押率。本文認為,質押系數法雖然在對知識產權質押價值評估中同時考慮了知識產權的市場價值和質押價值,但并沒有解決知識產權質押價值評估中預期收益、市場份額、折現率等參數選取的難題,而且質押系數的確定也缺乏一個客觀、公允的辦法。
(五)數學模型和評估公式類的評估方法
當前,“借助計算機廣泛的適用性和特殊的專用軟件,結合基于統計學與概率論的一些步驟,能使人們在知識產權價值評估程序中增加大量的復雜技術”i[美]帕爾、史密斯著:《知識產權價值評估、開發與侵權賠償》,周叔敏譯,電子工業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第40頁。。但是,數學模型和評估公式類的評估方法作為一種太過專業和繁瑣的技術手段,使用的普遍性并不高。而且本來很客觀的數學模型和評估公式,近年來因為某些評估人員的職業道德水平低下,通過人為任意設定評估參數,再套入數學公式進行計算,變成了“偽科學”的計算游戲,廣為社會詬病。
根據具體評估對象的不同,采取何種評估方法才能準確評估出知識產權的公允基礎價值和市場承認的公允溢價,這是一個偏技術性的問題,由評估機構具體把握。但是單一的評估方法總是有自己的局限,在知識產權評估實踐中,應根據具體情況,以一種評估方法為主,再參照其他評估方法確定的評估值,最后綜合得出一個相對合理與準確的評估值。
此外,知識產權價值評估無論采取何種方法,都要兼顧到評估的目的、遵循客觀公正的原則,并需要依照政府和行業協會規定的標準程序。判斷一個評估方法是否適合,可以從評估的質量、評估的準確性、評估結果(客觀、公允、公正、合理)為交易雙方的接受程度等方面來判斷。
四、堅持知識產權價值評估的市場化取向
知識產權價值的溢價價值由市場決定,基礎價值由技術內涵決定。在此前提下,任何知識產權交易價值均由供求關系決定,融資背景下知識產權評估的最準確途徑就是市場的供求關系。
即使是立法特別完善、在涉及領域上幾乎無孔不入的西方發達國家,也沒有對具有明顯市場交易主觀性質的知識產權價值評估進行立法,而僅是頒布了一些促進知識產權商業化、產業化以推動知識產權價值充得到分利用的法規。
社會發展進入到信息社會和知識經濟時代,無形資產的流轉性越來越強,各種資產要素(包括技術要素)在全球范圍內快速流動。現代知識產權的一個重要特性就是動態性,單純靜態性的知識產權已經很少了。現代知識產權的這種動態性,決定了對它進行價值評估的必要性(鄭成思教授提出:“根據大多數國家的實踐,知識產權在‘靜態’中,并無必要去評估它們”j鄭成思:《論知識產權的評估》,載《法律科學》1998年第1期。),也決定了知識產權的價值評估必須服務于促進知識產權動態流轉(市場化交易)的目的。
西方國家主要把知識產權價值評估作為市場交易行為,而我國在目前的知識產權價值評估中大多以政府為主導,所以應警惕和避免知識產權價值評估行政化的危險。當然,在知識產權價值評估業務開展之初,確實需要政府從長遠利益的角度來推動,以克服市場行為往往出于短期利益考量的不足。但是,堅持知識產權價值評估的市場化取向是須臾不能忘的。因為只有實現了知識產權價值評估的市場化,才能真正實現知識產權價值的正常流轉,并保證知識產權價值評估的公允性與合理性。
The intangible assets such 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re playing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modern economic society. The transfer of the valu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s been a kind of frequent and general demand in society at present. There are three factors affecting the transfer of right value. The fi rst is the evaluation of IPRs. The second is the sharing and compensation of IPRs. The last one is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market. This artic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moting the transfer of IPRs an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iffi culty of IPRs evaluation, holds that the value assessment of IPRs should obey the objective standards. Also,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problem of how to adhere to marketing orientation and how to well understand the evaluation of IPR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IPRs) ; value assessment; objective standards; subjective understanding
徐皝,北京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