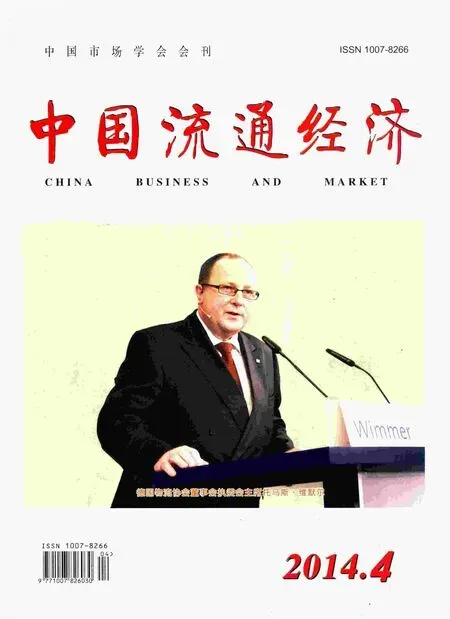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與中國“走出去”戰略
戴仁榮
(南京大學法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3)
自WTO多哈回合談判陷入僵局后,美國、日本和歐盟等西方大國紛紛把目光轉向優惠貿易協定(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PTA①)上,一個以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TTIP)為主體架構的國際貿易新格局正日益顯現。在這個過程中,中國至今被排除在國際貿易規則制定之外,面臨著被邊緣化的風險。日前TPP發展已進入收尾階段,TPP對中國“走出去”戰略有何潛在影響?中國該何去何從呢?本文對此作一嘗試性探討,以期有所啟示。
一、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的產生與發展
為促進亞太地區的貿易自由化,新加坡、新西蘭、智利和文萊在APEC框架內簽署了“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Partnership Economic Agreement,簡稱 P4),該協定自2002年開始醞釀并于2006年起正式生效。因P4成員國經濟影響力有限,該協定起初并未引起世界其他國家的過多關注,而這一狀況隨著美國2009年的高調加入并開始主導TPP談判隨之發生巨變。之后,越來越多的亞太國家紛紛基于自己國家戰略考量宣布加入進來。截至2013年年底,TPP先后經過了19輪談判,成員國已有包括美國、日本、加拿大等經濟大國在內的12個國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50%以上,GDP總量占全球的近40%,貿易額占世界貿易總額的1/3,其影響力已不容小覷。而且,由于TPP具有開放性的特點,肯定還會有其他國家加入這一新的區域貿易綜合組織中,韓國、印度、俄羅斯、泰國以及中國等國家相關部門都在研討加入TPP的可行性。
按照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所說,目前TPP談判已經完成所涉21個議題的65%,談判已經進入收尾階段。②但實際上,TPP談判并不像美國和日本一再宣稱得那么樂觀,至少可從美國所預定的結束談判日期從2012年底推遲到了2013年底可窺一斑,而且據專家估計2014年能否收官都尚不明朗。其中最大的難點在于TPP綱要文本所涉及的知識產權、勞工與環境標準、政府采購、競爭政策以及國有企業等條款在成員國之間始終難以協調一致。而且,從基礎框架結構來看,TPP從原來的P4到現在的P12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最初P4成員國旨在創立一個“高質量”的貿易協定,實現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試圖推行無條件的“一籃子協議”。可以說,因P4成員國基本上都屬于發達國家或中等收入國家,實行較高水平的貿易自由化不存在較大的國內阻力。但隨著TPP成員國的增多而帶來利益協調的復雜性,TPP欲實現最初無例外的“多邊一攬子安排”的談判肯定會困難重重。
二、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發展的動因——背后的中美亞太戰略博弈
后金融危機時代,世界經濟發展放緩,亞洲成為全球經濟發展最為活躍的地區,西方大國尤其是美國把本國未來經濟增長點投注到亞太地區,同時為應對中國的和平崛起,抑制中國有可能成為亞洲經濟發展的中心,美國決心“重返亞太”,實現其“再平衡”戰略。在經濟領域,美國以TPP為抓手圖謀牢牢把握住亞洲地區經貿規則制定的主導權,實現其亞太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greement of the Asia Pacific,FTAAP)構想,建立“美國的太平洋世紀”。
有數據顯示,美國參與并主導TPP并不僅僅出于經濟考量,實際上美國從TPP獲得的經濟收益并不算大。例如,美國學者佩里(Petri)等根據福利分析計算出,美國通過TPP每年將獲得約780億美元的福利,GDP僅能增加約0.4%,出口約增加2.0%,增加就業機會限于3萬人以內。[1]再比如,從TPP成員國構成來看,美國已經和澳大利亞、新加坡、智利等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除日本外的成員國經濟實力都不太強,很顯然美國仍竭力推動TPP談判必然另有原因。正如有學者指出,國際經濟合作歷來就不僅僅是經濟協同,更是政治角力。[2]事實上,自20世紀80年后期發展起來的擴及全球范圍的新區域主義皆帶有明顯的政治意涵。[3]TPP作為當前最大的跨區域貿易組織自然有一定的政治考量因素。目前中國經濟總量已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對亞洲乃至全球經濟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中國至今都沒有被邀請參加TPP談判,顯然這不是無意的忽視,其背后肯定有美國的政治考慮。有學者認為,TPP談判的本質特征就是TPP各成員國在一定規則之下的決策較量,即推動其他國家接受美國版本的服務貿易、投資、知識產權等條款,這是一個典型的博弈現象。[4]中國當前被排除在外實際上使中國喪失了在國際經貿規則制定上的話語權,但TPP內容的目標指向又是一場“沒有中國參與的有關中國的談判”,這恰恰是美國亞太戰略的用意所在。
中國其實也早已看出美國的戰略意圖,一方面一直跟進研究TPP發展的動態,另一方面也在制定自己的戰略對策。針對美國主導的TPP的“圍堵”,中國正大力構建自己的自貿區網絡,其中在東亞地區推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談判和中日韓自貿區談判。就當前發展趨勢來看,一個不包括美國的RCEP與一個不包括中國的TPP并存有可能成為現實,但兩者會不會相互競爭,進而演變為中美之間的競爭,將影響亞洲區域合作的未來。[5]可以說,亞洲區域經濟合作正處在十字路口,面臨著方向性選擇,[6]而其未來命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美亞太戰略博弈的走勢。
三、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給亞太地區經濟發展帶來的潛在影響
TPP談判在美國的主導下開展得聲勢浩大,成員國數由原來的4個迅速增為12個,隨著日本的加入,TPP的影響力大大增加,但TPP最終能否談判成功取決于成員國經濟、政治、外交以及軍事等因素的總考量。不過,在美國主推下TPP談判成功的幾率仍比較大。而TPP談判一旦成功勢必會給亞洲區域經濟合作原有的進程乃至發展方向產生重大影響。
1.在戰略層面,TPP將有力沖擊亞太地區現有區域經濟合作機制
為抑制中國的和平崛起實施“再平衡”戰略,美國決定“重返亞太”,試圖通過主導全球貿易規則的制定權來分享亞太地區經濟發展的紅利。作為其實現亞太自由貿易區的優選路徑,奧巴馬政府把TPP確立為在亞太地區落實其經濟政策的基石,以實現其“出口倍增計劃”。可見,美國參與并主導TPP有深遠的戰略考量。在其大力推進下,TPP談判已進入焦點議題的收官階段。而不管TPP談判最終以何種法律文本形式出現,一旦成功的話,勢必給亞洲地區現有的“ASEAN+X”合作機制和正在進行的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等帶來強烈沖擊。其中,受到影響最大的無疑是中國,因為中國并沒有參與TPP談判,而與中國有區域經濟合作的中國-東盟自貿區(CAPTA)和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的成員國大多參加了TPP談判。
2.TPP規則很可能會成為未來亞太地區國家區域合作的新模版
按照最初P4國家的設想,TPP是實行貿易高度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的區域協定,在美國2009年參加并主導TPP談判后,其目標進一步定位為建立一個“面向21世紀、高標準、全面的自由貿易協定”。依據TPP成員國2011年11月在APEC峰會期間達成的“綱要文件”,TPP內容主要包括關稅、貿易便利化、服務業、投資、國有企業、知識產權以及爭端解決機制等21個條款,同時還專門設立了勞工條款和環境條款2個附件,目標于2015年全面實現零關稅。從設定的標準和覆蓋領域來看,TPP絕對算得上是超級優惠貿易協定,甚至已經超越了WTO的框架范圍。考慮到美國的巨大影響力和TPP的開放性特點,將會有越來越多的APEC成員方和非成員方加入進來,屆時美國實現其亞太自由貿易區的宏偉目標有可能變為現實。雖然中國目前加入TPP的時機尚未成熟,但中國不可能永遠置之度外。其中的緣由如同中國并不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但OECD不斷推出新的準則,由于中國的主要貿易伙伴都在適用這些規則,迫使中國不得不接受并采用OECD規則。實際上,中國官方也充分意識到這個問題,所以中國政府相關部門一直在跟蹤并研究TPP談判的進展情況,并對其持開放態度,這從一個側面也說明TPP影響確實巨大并存在成功的可能性。
3.TPP將給非成員國經濟發展帶來嚴重影響
依據WTO規則,TPP在性質上屬于區域貿易協定,是作為WTO非歧視原則的例外而“合法”存在的。換句話說,TPP對非成員國實行的是歧視性貿易政策。正如中國社科院世界政治與經濟研究所副所長何帆所言,區域貿易協定實則是一把“雙刃劍”,在帶來貿易創造好處的同時也可能帶來貿易轉移。[7]如此以來,造成的可能后果是TPP成員國和非成員國之間的貿易恐怕會難以為繼,只能轉移到區域內進行了。這樣由原產地規則帶來的貿易轉移效應,使TPP非成員國對外貿易環境變得惡化,其對外經濟發展空間可能會受到前所未有的擠壓。
四、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對中國“走出去”戰略的啟示
從目前參與TPP談判的成員國構成來看,大部分談判國都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同盟國,這正是美國實施“中國除外”(Anyone But China)戰略的一部分。面對TPP國際貿易新規則的巨大“沖擊”,中國不應也不能靜待其變,否則,中國實施多年的“走出去”戰略會首當其沖遭受嚴重打壓。因此,中國應積極主動采取相應對策。而且,換個角度而言,這未嘗不是中國調整“走出去”戰略和促進國內改革的一次契機。
1.在政府層面,中國需要總體設計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內外自貿區網絡
中國“走出去”戰略離不開中國政府的大力支持,針對TPP給中國自貿區建設帶來的巨大挑戰,中國政府部門必須結合中國實際經濟發展水平和全球經濟戰略考量對中國的自貿區網絡進行頂層設計。目前,中國正在建設18個自貿區(已簽署12個,正在談判6個),涉及31個國家和地區,③已初步構建起橫跨東西的周邊自貿平臺和輻射各洲的全球自貿網絡,但總體來看,中國自貿區數量還比較少而且地域范圍較窄。在國內,中國2013年10月成立的上海自貿易區尚屬于試驗階段。為此,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和“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表明中央已意識到提升中國特色自貿區網絡建設水平的重要意義。
(1)繼續鞏固和拓展中國與亞洲周邊國家的自貿區建設并不斷創新合作模式。在亞洲地區,中國最早建立的是與東盟國家為核心的自貿區,確立了“10+X”多種合作模式,但這些經濟合作整體水平偏低,需要進一步整合升級。當前最為可行的做法是中國應積極推進全新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的談判,作為未來可能與TPP相抗衡同時符合中國實際發展水平的自貿協定。此外,中國還應加快推進正在談判的中韓自由貿易協定、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建設以及嘗試打造“中印緬孟經濟走廊”和“中巴經濟走廊”等。
(2)積極發展與金磚國家的經濟協作并在條件成熟時創立區域貿易協定。金磚五國同屬于新興的發展中經濟體,在應對國際經濟和政治格局的挑戰時有著共同的利益訴求,但目前金磚國家都不是TPP的成員國,面臨著來自TPP成員國的貿易歧視和貿易轉移所帶來的經濟競爭壓力。所以,中國應積極推動金磚國家的經濟合作,在條件成熟時建設五國優惠貿易協定,以集體發聲的方式增強其在國際經貿發展和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以應對TPP帶來的嚴峻挑戰。
(3)適時進一步擴大中國自貿區的地域范圍,打造多區域合作藍圖。目前和中國簽訂自貿協定的地區主要集中在東亞、東南亞、中美洲以及歐洲個別國家,還不適應中國企業“走出去”發展現狀的現實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國企業擴大出口和海外投資的增長。因此,中國有必要尋求拓展自貿區建設的范圍,構造多區域合作藍圖。2013年9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訪中亞四國期間提出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可以說正是此藍圖的一個創造性構想。
(4)中國應堅持“以開放促改革”的思路,積極嘗試構建并推廣國內自貿區。2013年中國成立的上海自貿區可以說是一次偉大的嘗試,上海自貿區進行了一系列大膽改革,如接受中美投資協定談判中的“負面清單”投資管理體制,并進行行政審批體制改革。這些改革措施很多都接近或達到了TPP條款的要求,實質上是我國通過自貿區的方式來檢驗對TPP條款的適應和抗壓能力,為將來我國可能加入TPP或抗衡TPP做足準備。
2.在法律層面,中國相關法律法規需要借鑒TPP規則進行自我完善
中國經過入世13年多的改革洗禮,經過一系列修訂或重新制定后已形成自己特色的法律體系,但離TPP高標準所要求的知識產權保護、環境與勞工標準、競爭性政策、國有企業等方面的立法標準仍有不小的差距。客觀地講,雖然TPP門檻過高,中國目前尚不能承受TPP高標準之重,但TPP的很多貿易規則有其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未來貿易的發展方向。[8]如根據相關統計,中國已經連續14年位居全球貿易摩擦目標國榜首,成為他國起訴反傾銷和反補貼最多的國家,國際貿易爭端案件一直居高不下。究其原因往往多為中國相關法律規定未能與國際規則標準相銜接,致使在中國企業“走出去”時很容易被別國以不遵守“國際游戲規則”為由引發貿易爭端。因此,面對TPP新規則,中國需要認真思考和全面清理目前的市場規范和行業技術標準,站在下一個10年甚至20年、30年角度,重新制定與國際接軌甚至具有超前性的標準。[9]
當然,我們也需要客觀地認識到,中國的立法不可能一下就能符合TPP高標準的規則要求,這也是中國目前不選擇加入TPP的一個重要原因。由于TPP談判尚未完成,TPP最終法律文本尚不得而知,但就2011年公布的“綱要文本”和各種媒介透露的TPP條款信息分析,美國主導下的TPP很多規則采取的是“美國化”超高標準,而且是毫無例外的“一籃子協議”接受方式,一方面使得TPP成員國內部對此分歧很大,談判遲遲無法獲得實質性進展;另一方面有些規則有失公平,如就TPP國有企業條款來說,新加坡、新西蘭有國有企業,中國也有國有企業,但中國國有企業很多屬于壟斷部門,如不顧一國社會性質和經濟發展水平上的差異而采用“一刀切”方式則有失公允。因此,中國在立法完善時應區別對待TPP條款內容,對那些反映國際貿易普遍發展趨勢要求的規則,可重點去修改完善,否則,暫時不予考慮。如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中國的立法水平確實還比較低,“走出去”的企業涉及侵犯專利權和商標權案件比較多,那么,我們應該合理借鑒TPP規則進一步提升中國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水平。
3.在企業層面,中國企業需銳利改革提升自己的國際競爭力
TPP在某種意義上可以成為改革的外在動力或者壓力,以TPP“倒逼”國內改革,這有利于提升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10]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這也為中國企業改革指明了方向和路徑。如前所述,TPP旨在打造21世紀的全球貿易規則的新模板,待TPP實施時中國企業在“走出去”時必然會遭遇TPP規則的挑戰。因此,中國企業應做到未雨綢繆,從現在起就養成企業國際化戰略思維,銳利進行改革。在國家整體“走出去”戰略指引下,改革的具體思路可從制度化、規范化和法治化等方面入手,主要包括大力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不斷提高產品質量,逐漸形成自主知識產權的有競爭力的國際品牌產品;建立健全與國際接軌的現代企業相關制度,如以國家自貿區網絡建設為導向建立雙邊投資合作機制、構建“走出去”服務體系、建立“走出去”風險預警機制等;嚴格遵守本國法、投資國國內法及國際法的規定,遇到貿易糾紛或摩擦時積極尋求運用法律的手段,使企業運行切實走向法治化的道路。
注釋:
①“新區域主義”下的區域性自由貿易協定因不再局限于地理位置的相鄰性而多具有跨地區的特征,西方學界較多采用PTA的用語,本文亦使用PTA這一具有廣義性質的術語,泛指關稅同盟(CU)、自由貿易區(PTA)、過渡協議等形式。
②參見美國政府網站.http://www.ustr.gov/about-u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3/September/Readout-Washington-TPP-discussions,2014-2-12.
③數據來源于中國自由貿易區服務網網站.http://fta.mofcom.gov.cn/index.shtml,2014-2-16.
[1]Peter A Petri,Michael G Plummer.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nd Asia-Pacific Integration:Policy Implications[J].PIIE Policy Brief,2012(6):22-25.
[2]李曉玉.TPP協議“難產”究竟難在何處?[N].中國經濟導報,2013-10-29(04).
[3]殷敏.跨區域貿易協定的發展及我國的選擇[J].法學,2012(6):98-106.
[4]賈引獅.美國與東盟部分國家就TPP知識產權問題談判的博弈研究[J].法學雜志,2013(3):85-93.
[5]Beginda Pakpaha.Will RCEP Compete with the TPP[EB/OL].[2012-11-28].2014-02-20?.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2/11/28/will-rcep-compete-with-the-tpp/.
[6]李向陽.2012~2013年亞太形勢分析與展望[C].∥亞太藍皮書[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8.
[7]轉引自劉玉海,高瑩.上海自貿區:TPP規則逼近下的中國棋局[N].21世紀經濟報道,2013-10-21(15).
[8]Masahiro Kawai,Ganeshan Wignaraja.Asian Free Trade Agreements:Trends,Prospects and Challenges[J].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2013(3):19-20.
[9]章昌裕.WTO困境下的國際貿易新格局與挑戰[J].對外經貿實務,2013(12):4-8.
[10]戴仁榮.TPP的演變邏輯及中國的策略選擇[J].對外經貿實務,2013(12):4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