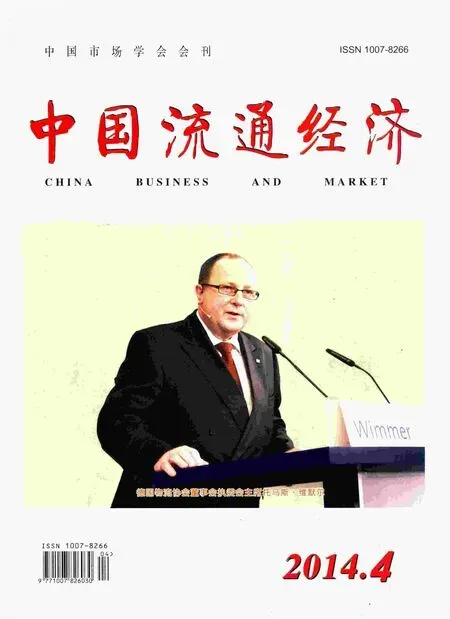絲綢之路經濟帶與通道經濟發展
高新才
(蘭州大學經濟學院,甘肅 蘭州 730000)
兩千一百多年前,張騫出使西域,以長安(今西安)為起點,經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并聯結地中海各國,開辟了一條橫貫東西的絲綢之路,促進了東西方的文化交流,帶動沿途城鎮商貿、加工和服務業迅速崛起,形成了我國歷史上最早的通道經濟。隨著海上交通的發展和世界經濟發展格局的變化,這條經濟通道逐漸暗淡。2013年9月7日,習近平主席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構想,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和熱烈反響。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加快同周邊國家和區域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是對當前我國統籌向東向西開放、深化與沿線國家在經貿、人文、科技等多領域合作交流的形象概括,是對兩千一百多年以來絲綢之路精神的進一步傳承和發揚,絲綢之路通道將重新煥發生機與活力。
通道經濟理論可以追溯到佩魯和布代維爾的增長極理論以及沃納·松巴特的“點—軸”開發理論。增長極理論從經濟角度是指主導產業部門對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從地理角度則是指區位條件優越的地區宜于經濟發展。“點—軸”理論對經濟布局有重要影響,[1]是對增長極理論的延伸。沃納·松巴特的“點—軸”開發理論強調了點軸的極化效應和擴散效應是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兩種機制。[2]發展通道經濟,將交通運輸和區域經濟發展有機結合,是落后地區經濟發展的利器。“點”是通道經濟中的增長極,具有自身極化效應和向軸擴散效應。通過極化效應和擴散效應加強區域的產品、資金、人才、信息流動,增強經濟發展動力和創新能力。[3]絲綢之路經濟帶是“世界上最長、最具有發展潛力的經濟大走廊”,是橫貫東西、連接歐亞的經貿合作與文化交流大通道,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根本上就是通道經濟的發展。這條經濟通道被譽為陸上絲綢之路,具有特色化的文化資源稟賦。例如,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就是古絲綢之路的南要沖,是絲綢之路經濟帶上伊斯蘭文化、民族產業的獨特地標。在新的發展機遇下,要實施五位一體、四輪驅動的發展戰略,以通道經濟方式發揮極化效應和擴散效應,在絲綢之路經濟大走廊上開拓民族產品的廣闊市場。
一、通道經濟的內涵
1.通道經濟的屬性
通道經濟必須以地理的聯結為前提,依托交通優勢,以發展區域經濟為中心,以經濟合作為紐帶,布局和規劃產業結構,實現產業向通道集散,促進區域間、城鄉間、產業間的經濟聯系。[4]我認為,通道經濟至少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的屬性:
(1)通道經濟在本質上屬于流通經濟。通道是人、物、資金、技術、信息流通的主渠道,通過提高區域的流通能力,實現人便其行、貨暢其流、訊通天下,最大限度地提高流通的經濟效益,挖掘第三利潤源。
(2)通道經濟在形式上呈現為開放型經濟。交通運輸體系將區域內外聯結起來,拓展經濟發展的空間,打破區域割據、行業封鎖,促進區域間互相開放和經濟合作,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及物流、信息流、資金流、商流的快速流動,形成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開放經濟格局。
(3)通道經濟的發展需要完善的服務業與之協調。道路暢通是通道經濟發展的首要條件,但作為通道經濟更需要信息化支撐和系統化服務與之配套。發展現代服務業,增加產品的附加值,延伸通道經濟的產業鏈,形成產業生態鏈,是通道經濟發展的不竭動力。
(4)發展通道經濟的目的在于帶動通道沿線區域產業經濟的發展。通道沿線區域要發揮地緣優勢、資源優勢,發展特色優勢產業,完善通道經濟產業鏈,提高行業自主發展的能力和市場競爭力,從而對區域產業結構調整產生積極影響,帶動相關產業迅速發展。
2.通道經濟的建設層次
通道經濟的建設分為兩個層次:一是運輸通道,強調流通費用的經濟性;二是經濟通道,強調依托交通通道優勢發展區域經濟。高新才等[5]對中國西北城市區域的分散性特征進行了描述,提出沿歐亞大陸橋及相關重要鐵路支線和黃河主干線構建西北城市經濟帶的設想,使得分散型的城市彼此關聯,發揮城市對周邊地區的輻射作用,促進西北地區發展成為具有綜合性、多產業結構和協調發展的經濟系統。黃云[6]從民族經濟的角度分析了民族地區要克服邊境與內陸地區的屏蔽效應,打破過境運輸的局限,通過跨國經濟通道來發展民族經濟。李瓊[7]在論述渝東南通道經濟的發展問題時指出通道經濟是雙面的,如果物質資源向發達地區匯集的集聚效應大于發達地區的要素向落后地區傳遞的擴散效應,則民族地區的發展資源將被轉移出去,出現區域經濟發展軸線上的“凹陷”。因此,欠發達地區發展通道經濟,必須借助通道建設,以發展區域經濟為著力點,加速資源、資金和人才的集聚,帶動工業產品和高附加值產品的產出,促進區域產業發展、技術進步,提高社會效益。
二、發展通道經濟的戰略意義
絲綢之路經濟帶橫貫東西、連接歐亞,途徑中國和中亞、歐洲40多個國家和地區,地域遼闊,總人口近30億,市場規模及合作潛力巨大,將是世界經濟發展格局中最具潛力、最具活力的經濟增長區域。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就是以綜合交通通道為展開空間,依托沿線交通基礎設施和中心城市發展通道經濟,對域內貿易和生產要素進行優化配置,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最終實現區域經濟和社會同步發展,戰略意義重大。
以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為契機,發展通道經濟,全面提升我國與沿線國家的經貿合作水平和層次,加快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構建一體化區域經濟發展格局,對于我國掌握發展先機、贏得發展空間、提升發展位勢意義重大;絲綢之路經濟帶還是文化交流的通道,發展通道經濟,將全方位深化我國與沿線各國文化、旅游、科教等領域的交流和合作,不僅能夠鞏固、擴大與周邊國家和睦相處的社會和民意基礎,而且能夠傳播弘揚華夏文明,強化彼此認同,奠定我國文化強國的戰略地位,全面提升我國軟實力和文化影響力;發展兩端開放的通道經濟,將充分釋放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點”的巨大潛力,把內陸區位優勢和地緣優勢轉化為強勁的發展活力,從要素供給和市場拓展兩方面增強絲綢之路“軸帶”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有助于實現我國“沿海”、“內陸”、“沿邊”全方位的開放,推動我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30億人口,少數民族人口比重大,民族文化、宗教文化作用強。以伊斯蘭文化為例,這一區域中有13億穆斯林人口,與眾多穆斯林國家和地區文化相通、血緣相親,因此,當前著力打造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必然是伊斯蘭世界最重要的經貿通道、文化通道,大力發展通道經濟有助于中國與中亞、西亞等穆斯林國家和地區的友好交流和商貿往來。
絲綢之路經濟帶所轄地區大多為我國欠發達地區,發展通道經濟,有助于加快其開放步伐,積極參與區域經濟分工協作,提升綜合實力,促進民族團結,實現經濟社會轉型跨越發展;有助于加快民族優勢產業發展,形成地區相對比較優勢,打造區域主體功能定位和區域自我發展能力匹配的地區經濟增長極,通過對周邊地區產生積極的輻射帶動作用,增強民族地區經濟實力,推動我國欠發達地區的大開發、大開放,開創多民族共同奮斗共同發展的局面;有助于促進穆斯林地區對伊斯蘭文化的共同認知,弘揚伊斯蘭教追求和平、崇尚和諧的理念,為全世界樹立民族和睦相處、宗教和諧并存、經濟蓬勃發展的成功典范,有利于促進世界和平與民族團結。
三、發展通道經濟的優勢
陸大道[8]提出,“點—軸”系統中的“點”是各級中心地,是各級中心城鎮、各級區域的集聚點;“軸”則是在一定方向上聯結不同中心城鎮而形成的聯絡線和經濟密集帶,具有較強的經濟實力和潛力。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西部大開發的深入實施以及向西開放步伐的加快,將使這一區域當中各地區的區位優勢和民族產業優勢進一步顯現。本文以伊斯蘭文化為例,分析在絲綢之路經濟帶發展通道經濟的諸多優勢。
1.民族文化優勢
伊斯蘭文化源遠流長,民族風情濃郁,是絲綢之路經濟帶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在這一區域,分布著我國多個伊斯蘭文化中心,例如,清朝以來,甘肅臨夏就是西北穆斯林經堂教育的中心,伊斯蘭教三大教派、四大門宦及其分支俱全,是中國伊斯蘭文化孕育和傳承的圣地,清真寺、拱北等伊斯蘭風格建筑遍布全州,獨特的文化背景、鮮明的生活習俗、風格迥異的民族建筑,形成了五彩繽紛的民族風情畫卷。
2.民族產業優勢
為壯大絲綢之路經濟帶特色產業,我國建立了多個國家級民族文化產業園、穆斯林物流園區和重點經濟(工業)開發區(園)等,它們已經成為絲綢之路各地區發展產業的重要平臺,很多地區已經獲得一定的產業基礎。例如,甘肅臨夏擁有以圣澤源、康美、八坊清河源、燎原乳業、學和、興強等為龍頭的民族產品加工企業,形成了以清真食品和民族用品加工為主導的產業結構。
3.交通區位優勢
絲綢之路,顧名思義就是運輸通道,這條通道上的諸多地區因為運輸節點的身份,通過物流模式繁榮地區經濟。例如,位于黃河上游的甘肅臨夏是西部牧區和中原農區的交錯帶,是唐蕃古道、甘川古道交匯地,向西經河西走廊,從新疆通往俄羅斯和中亞地區以及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亞地區,從東南入川,經泉州通往東南亞,直至歐洲,是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
4.商貿傳承優勢
漢唐以來,通過這條陸上絲綢之路,我國就與中亞、西亞、東南亞有商貿往來。改革開放初期,按照“南來北往、東進西出”的戰略部署,我國絲綢之路經濟帶所轄地區大多在北京、南京、深圳等地設立辦事處,還成立了穆斯林工貿公司等。目前,穆斯林民間貿易遍布中東的伊朗、埃及、沙特、土耳其,非洲西部的安哥拉、尼日利亞,中亞五國及東南亞的印度尼西亞、文萊、馬來西亞等國家和地區。現有歸僑僑眷2600多人,海外華人、華僑1500多人,擁有一批通曉阿拉伯語、熟悉國際穆斯林市場和國際貿易規則的經商人才,國際商貿發展優勢明顯。
四、發展通道經濟的重點
絲綢之路經濟帶發展通道經濟,必須以具有強有力的極化效應和擴散效應的“點”為著力點,以有形通道建設為載體,以高效通道服務為助力,拓展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通道,實現地區間、城鎮間的專業化協作,形成有機的地域經濟網絡和“點—軸”模式的經濟發展空間和結構形態。
1.依托民族產業優勢,形成民族產業貿易集聚中心
貿易集聚中心是通道經濟中重要的中心“點”。“點”的集聚能力和擴散效應強弱直接關系著通道經濟發展水平。很多地區商貿流通已具備面向省內、藏區等區域市場開放的基礎,但對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開發開放程度不夠,未形成現代商貿流通體系,流通網絡亟需完善,現代化、信息化和國際化的民族產業貿易集聚中心亟待形成。
(1)優化貿易中心布局,強化商貿輻射功能。加快形成以商貿核心區為主體,物流園區為支撐,中小專業市場有效補充的商貿體系。以實地調研的臨夏地區為例,其應當以百益國際商貿中心、天元國際商業綜合體等大型商貿綜合體為重點,將臨夏打造成面向中亞、西亞、東南亞地區的伊斯蘭商貿中心;加快推進臨夏穆斯林物流園區、大河家物流園區、三甲集皮毛物流園區建設,強化倉儲加工、物流集散、信息服務等功能,發揮集散效應,建成立足西部、面向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暢通有序、富有活力的商貿集散區;以各縣的重點集鎮為補充,建設培育功能完善、輻射范圍廣、溝通方式新、帶動作用強的批發交易市場。
(2)完善貿易服務體系,提供多元貿易服務。加強信息服務、中介服務和勞務輸出服務的平臺和渠道建設,增強商貿軟實力。提高市場信息服務水平,加大與其他專業市場和地區市場信息共建力度,提高商品市場信息透明度,提升企業適應市場變化的能力和貿易現代化水平;加強渠道建設,設立海關、商檢、工商、稅務、商標注冊、知識產權保護等一站式政務服務中心,發展媒體宣傳、會計、翻譯等專業的現代中介服務;準確把握勞務輸出的結構和方向,及時發布國際勞務需求信息,積極開展國際勞務輸出。
(3)力推現代商貿業態,大力發展會展經濟。以政府主導、市場化運作成立電子商務服務公司,引進國內知名的電子商務團隊,構建B2B、B2C平臺,形成較為完善的電子商務管理體系,助力商貿流通業發展。積極舉辦各類文化交流論壇、產業會展等,堅持共享、共贏,推動現有會展向更大規模、更廣領域、更高水平邁進,突出專業化辦展、品牌化經營、市場化運作、國際化拓展,提高展會吸引力,同時積極參與國內外文化論壇、文化產業大會和民族產品展銷會,加強對外宣傳,謀求更廣更深的經濟合作,提高通道經濟影響力。
2.依托民族文化優勢,形成走向伊斯蘭市場的經濟貿易大通道
通道是復合型發展軸,一是需要多式運輸方式的同步發展,以滿足對運輸多方面、多層次的需求,這就要求做好交通通道建設;二是通道建設必須滿足流動客體的多樣性要求。高斌、丁四保[9]在對我國“點—軸”開發模式發展實踐的分析中指出,我國許多交通軸帶上存在著對“點”發展無效的“過境流”,要規避這種現象,除打通交通通道外,還必須強化通道中商品、人員、信息和服務的流通功能,搞好經濟通道建設。
(1)交通通道建設。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大背景下,西部地區地緣優勢突出,但交通能力有限,亟需完善多種形式的交通基礎設施,保障通道經濟發展中的物流暢通。全面加快公路、鐵路、航空、內陸港建設步伐,構建“向西、向南、向東”的現代化立體交通通道。
加快高速公路和鐵路建設,完善渝新歐陸上貨運運輸體系,打通陸上大通道;強化西部地區與泉州、廈門、連云港等港口城市的經貿合作,建設內陸港,借船出海,打通海上大通道;加快質、量并重的機場建設,開辟西部至中亞、西亞、東南亞等地區重點城市的航線,打通空中大通道。
(2)經濟通道建設。充分利用與“絲綢之路經濟帶”上國家和地區地緣相近、文緣相承、商緣相連、語言相通的文化優勢,促進中國與中亞、西亞等國家和地區間的經貿往來及文化交流活動的開展,整合國內外兩種資源,瞄準兩個市場,加快對外開放步伐,創新國際合作模式,形成面向中亞、西亞、東南亞,輻射歐洲乃至更廣大地區的商品大通道、人才大通道、信息大通道、貿易服務大通道。
積極爭取在中哈霍爾果斯國際邊境合作中心建立貿易區,盡快與伊朗庫姆省等絲綢之路沿線城市建立友好城市關系,與友好城市互辦產業周、互設產業園,打通商品大通道;加強專業技術人才、經營管理人才、商貿技能人才隊伍建設,鼓勵和支持語言教育機構的發展,創新聯合辦學模式,積極培養和輸出產業技術、商貿技術、語言技能等人才和勞動力,形成人才大通道;加大科技與人才投入力度,推動建立企業和科研機構、高等院校共同參與的各類技術創新合作組織,形成民族產業區域創新戰略聯盟,聚集國內外創新要素,促進企業間、企業與科研院所間的信息傳遞、知識溢出和技術創新,推進信息平臺對接,提升市場信息開放度、透明度,提高信息準確性、及時性,打通信息大通道;加快發展電子商務、現代物流等服務業,培育和發展金融服務業,增強產業關聯帶動能力,加強與中亞、西亞、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的貿易服務協作,建立貿易協作機制,積極發展貿易中介服務,打通貿易服務大通道。
總之,絲綢之路經濟帶作為東西方商貿往來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發展通道經濟既是根本要求,也是充分發揮文化優勢、區位優勢、產業優勢,激發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潛力的必然選擇。西部地區發展通道經濟,必須發展壯大民族特色優勢產業,特別是要增強貿易集聚中心的極化效應和擴散效應,拓寬交通通道,強化信息通道、人才通道、貿易服務通道功能,推進“點—軸”漸進式擴散進程,融入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
*本項目系連云港市科技廳軟科學研究計劃項目(項目編號:RK1304)的階段性成果。
[1]陸大道.關于“點—軸”空間結構系統的形成機理分析[J].地理科學,2002,22(1):1-6.
[2]周茂權.點—軸開放理論的淵源與發展[J].經濟地理,1992,12(2):49-52.
[3]王瑛.發展通道經濟的理論探討[J].改革與戰略,2004(10):45-47.
[4]莫晨宇.廣西發展通道經濟的研究[J].東南亞縱橫,2007(9):44-47.
[5]高新才,張馨之.論中國西北城市經濟帶的構建[J].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30(4):1-18.
[6]黃云.跨國運輸通道是民族經濟外向擴展之道[J].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28(1):87-91.
[7]李瓊.發展通道經濟 促內陸興邊富民[C]//興邊富民行動理論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4:4.
[8]陸大道.區域發展及其空間結構[M].科學出版社,1998:137.
[9]高斌,丁四保.點—軸開發模式在理論上有待進一步探討的幾個問題[J].科學管理研究,2009,27(4):6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