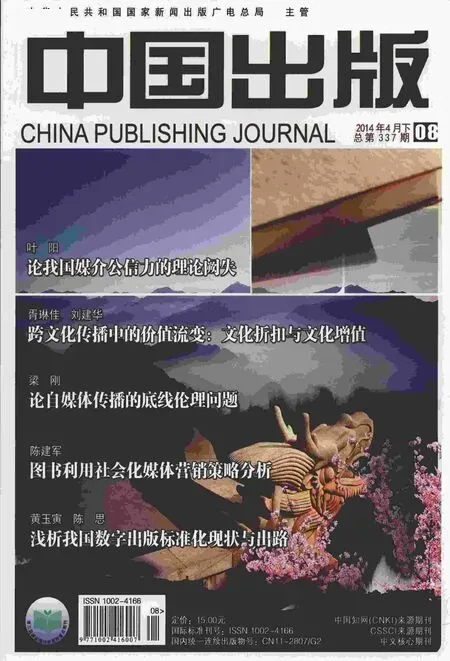論自媒體傳播的底線倫理問題*
文/梁 剛
*本文系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網絡文化背景下黨的意識形態領導方式創新研究”(12YJC710037)、北郵社科基金項目[2012BS06]及網絡系統與網絡文化北京市重點實驗室(北京郵電大學)的研究成果。
美國著名傳播學者保羅·萊文森提出媒介“三分法”:舊媒介、新媒介和新新媒介。簡單說來,互聯網誕生前的一切媒介都是舊媒介;新媒介指互聯網上濫觴于20世紀90年代的第一代媒介;新新媒介則指濫觴于20世紀末、興盛于21世紀的互聯網上第二代媒介。近年來以博客、微博等為典型代表的自媒體無疑屬于萊文森所說的新新媒介,其巨大影響力和傳播力沖擊并改變了既有媒介格局,漸成新興輿論場域。與此同時,自媒體倫理失范現象頻發,甚至跌穿社會公序良俗底線。因此,維護自媒體良性和諧傳播秩序,探討自媒體傳播的底線倫理問題,具有現實緊迫性。
一、兩個重要概念的界定
一是自媒體。美國著名硅谷IT專欄作家丹·吉爾默在《自媒體:草根新聞,源于大眾,為了大眾》(We the Media: 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一書中提出并闡明自媒體概念,認為“20世紀的大眾媒體結構,轉變成某種更有草根意味和深化民主的東西。……通訊網絡本身就是人人發聲的媒體”。自媒體,有學者譯為草根媒體,這不無不可,但更確切的理解可能是Web2.0時代的新興公民媒體。在丹·吉爾默看來,“我們不能再將新聞視為由大型組織機構控制的商品。身為社會的一分子,我們不能再忍受有限的選擇。”非職業新聞傳播者的興起,有助于讓沉默的大眾發出聲音,從而激發了“真正資訊充足的公民觀念的復興”。[1]這就是說,自媒體打通了公共傳播與私人傳播、專業領域與業余領域之間的鴻溝。它所催生的傳播革命“已經普遍地將‘權力’從媒體轉移到了受眾。在這個層面上受眾有了更多的媒介選擇,而且能夠更主動地使用媒介。”[2]如果說與傳統大眾媒介相對應的是原子化的中心控制性大眾社會,那么與自媒體對應的則是開放性和多元化的公民社會。從信息傳播模式上說,信息交流實現從居高臨下的訓示到交談與協商模式重新定向。不妨這樣說,Web2.0時代的自媒體傳播標志著互聯網理念的一次升級換代,從原來的自上而下、由少數資源控制者主導的互聯網體系,轉變為由廣大公民用戶集體力量主導的互聯網體系。
二是底線倫理。“底線倫理”是上世紀90年代由著名學者何懷宏提出、闡發并產生重要影響的倫理學說。不同于中國傳統的圣賢倫理或高蹈道德,底線倫理強調的是基準道德水平。用何懷宏的話說,“底線倫理即每一個社會成員自覺遵守最低限度的道德規范。雨果說,做一個圣人,那是特殊情形;做一個正直的人,那是為人的常軌……你可以做不到舍己為人,但你不能損人利己;你可以不是圣賢,但你應該認同道義和人道。你攀升不到道德最高境界, 但道德最低下限必須堅守,那是人類最后屏障!”[3]顯然,底線倫理與現代社會的公民道德有相當密切的關聯和很大程度的重合,但是底線倫理還包含制度倫理或制度正義的特殊內涵。也就是說,底線倫理不僅涉及個人道德義務問題,而且涉及社會的公平正義問題。其實,底線倫理正是以公平正義的價值取向和道德選擇為尺度的。規則面前沒有例外,制度面前沒有特權。底線倫理是一種屬于公民社會的溫和的道德義務論。底線倫理一方面告別高調的“君子國”式的道德烏托邦,另一方面也堅決拒斥一切“逃票者”或特殊公民。
二、自媒體傳播底線倫理的核心價值
底線倫理把道德裁決的能力賦予給每個個體公民,對每一個公民充分信任,公民既有主張個人權利、實現自我利益的充分自由,也有服從社會良俗、履行公共責任的基本義務。正如梁啟超所言:“義務與權利對待者,人人生而有應得之權利,即生而有應盡之義務,二者其量適相均。”[4]自由(權利)和責任(義務)構成自媒體傳播底線倫理的核心價值。
1.自由
自由具有復意性。一個基本意思相當于英文中的Freedom,它指的是一種自由的狀態, 即擺脫某種羈絆或束縛后所獲得的自由解放狀態;另一個基本意思則相當于英文中Liberty,是可度量的作為權利表達或呈現的自由,因而也是能夠明確界定的。新世紀以來勃興的自媒體無疑極大解放了民眾的傳播理念、傳播方式和傳播行為。丹·吉爾默不無興奮地指出:“新聞由普通民眾生產出來,他們想發言、想自我表現;新聞不再只由‘正式’的新聞機構提供——傳統上,新聞機構才是決定歷史最初面貌的發言人。這一次,為歷史添上新色彩的執筆人,卻有部分是傳統的閱聽大眾。這是可能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互聯網上有新興的出版工具。……我們見證了新聞的未來;很多時候,我們就是未來新聞的一部分。”自媒體的高度開放性、透明性和可分享性,決定了它作為最新中介,已當之無愧成為社會信息的公布欄和社會意愿的發聲筒,成為個體吸納與整合社會能量的接收器,同時也是個體能量放大為社會能量的轉換器。這樣就帶來一個頗為嚴峻的問題。我們生活的世界是一個“相互作為主體,同時也相互作為對象” 的世界,沒有一個人能使自己永遠處在主體的位置。那么,如何處理個體非職業自媒體傳播者之間可能的“自由”的沖撞呢?美國當代著名哲學家羅爾斯是自由主義理論的堅定捍衛者,但同時他又主張對自由加以必要的限制。在羅爾斯看來,不加限制的自由是必然要發生沖突的。他由此提出:第一,對自由的限制的標準要用平等補充自由,即自由是平等的自由,人人都有自由的權利;第二,對自由進行限制的最終目的只能是維護自由。在這個意義上說,對自由的限制,就是使自由變得平等。在自媒體傳播活動中,把關者和審核人是缺失的環節,從而帶來極強的用戶自我賦權功能,給予公眾參與者空前的傳播自由。有學者謂之當代媒介的“民眾化轉向”。立足于自媒體傳播的底線倫理和媒介良序運行,應當更加強調這種具有明確邊界的權利意義上“平等的自由”,而不是一味肯定作為“革命”或“解放”意義上的抽象自由。
2.責任
大眾媒介的社會責任規范理論早就指出,大眾傳媒應該是自由卻又自我約束的。這一點顯然也應同樣適用于新興的自媒體。微博等自媒體必須承擔公共責任、履行公共義務。每當微博“大V”們發布一條微博,便會有大量受眾閱聽,加上網友的互相轉發,微博“大V”在無形中已成為社會輿論的發動機。據統計,目前在新浪和騰訊微博中,10萬以上粉絲的“大V”超過1.9萬個,百萬以上粉絲的“大V”超過3300個,千萬以上粉絲的“大V”超過200個。一些微博大V傾向于認為,在以商業運作為基礎的現代媒介中,公共利益是什么和什么能吸引公眾眼球是合二為一的東西,這是有失偏頗和危險的。事實上,“表達自由一直包括抑制表達的自由”,“沒有公認的道德義務就沒有精神權利。如果發布者是一個撒謊者或是一個激起仇恨和猜疑的不誠實的煽風點火者,那么他的要求就是沒有基礎的。……他已經利用他的自由來破壞他的自由。”[5]這就是說,表達自由必須融入責任義務要素,兩者合則雙美,離則兩傷。
基于微博特別是名人微博的傳播具有馬太效應的影響力,微博主們應當時時提醒自己恪守底線責任倫理。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曾深刻提出意圖倫理和責任倫理的區分。簡單地說,意圖倫理以意圖的好壞作為善惡的標準,只要動機是好的,即使辦了壞事也是可以原諒的;責任倫理則注重效果,認為只講意圖而不顧效果是不負責任的。比較而言,現代社會倫理更加傾向于責任倫理,即不能因為行為的良善初衷而免除道德和法律責任。有學者明確認為,“網絡倫理實質上是一種責任倫理”,是很有見地的。[6]在此意義上,擁有千萬粉絲的姚晨所發一則微博就很值得稱道:“昨兒憤慨之下,差點轉發救小悅悅的陳賢妹被辭退的新聞,但腦子里瞬間閃念:消息來源準確嗎?觀望一下再發不遲。果然,今日又看見澄清的新聞,陳大姐沒被辭退、也沒被房東趕走。感慨之余慶幸:第一,不管怎樣,好人沒遭惡報,這再好不過。第二,這仨月飾演記者,俺都鍛煉成記者思維了,入戲啊! (2011-12-27 09:51)”姚晨的“憤慨”和“差點轉發”是出于道德義憤,所幸未被“意圖倫理”謬誤綁架,而是三思后行的“記者思維”即“責任倫理”思維占了上風。在Web2.0時代“病毒式”信息擴散活動中,社會輿論風險系數倍增,亟待提升并強化全體傳播活動參與者的責任意識,把傳播自由與公共責任的匹配和對應,置放在自媒體底線倫理價值結構的中心性位置。
三、堅守自媒體傳播的底線道德原則
底線道德原則,是指構成一種倫理規范體系中最具普遍性和共識意味的基本準則。在道德實踐中,它作為道德判斷的根本依據、道德選擇和評價的最后標準起作用。任何一個社會,無論是實在的還是虛擬的,都需要一種基本的道德共識才能維系和良性發展。在自媒體傳播過程中,每個人兼任信息的提供者、使用者和消費者,既是用戶又是把關人。每一主體都處于與自我、他人、群體的復雜關系之中。借鑒羅爾斯“重疊的共識”(overlapping consensus)的觀點,從平臺管理者、運行者到億萬普通用戶都應共同遵循并維護以下底線道德準則。
1.誠信原則
誠信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儒家倫理思想把誠信作為“仁義禮智信”五常之一,以至于可以“去兵”“去食”,而不可無信。“民無信不立”的格言尤其體現了誠信道德的精神基石意義。在自媒體傳播模式中,人們的社會關系在整個傳播活動中扮演基礎性底層結構角色,信息沿著社會關系網絡流動,而相互信任正是人際關系系統正常運作不可或缺的社會資本要素。例如,微博傳播就是一種基于“關注”和“被關注”的信任鏈,高度依賴人與人之間的社交關系才能完成。
在網絡媒介進入Web2.0時代的背景下,丹·吉爾默指出:“媒體集團享有高額毛利。有太多例子顯示出,嚴肅的新聞以及公眾信賴感都陸續被犧牲。這些讓新聞業出現破洞,而新興的記者正在填補這個缺口,尤其是平民記者。”然而令人憂慮的是,公民記者或草根發布者的出現并不會自動兌現信息真實性的新聞倫理準則,恰恰相反,網絡流言或虛假信息等不時攪動起輿論漩渦,極大挫傷了自媒體傳播的公信力。因此,這里必須強調指出,誠信原則不僅是一種個人美德倫理,更是一種社會規范倫理;既要充分重視誠信作為個人人格美德的內在自律力量,更要注重有效建立誠信作為社會公共倫理底線的外在普遍性約束機制。事實上,現代信用倫理對個人人格信用的要求更多地訴諸社會組織化、制度化的制約上。新浪微博平臺構建的用戶信用積分機制就頗具可操作性。每個微博主的初始信用積分均為80分,上限為100分;按照分數高低,微博用戶信用分將分成4個等級,超過90分為高信用,60分以下為低信用。如果賬號存在違規行為,將被扣除一定的信用積分;信用積分低于60分,用戶的相關頁面將顯示“低信用”圖標,積分為零則將被刪除賬號。在普遍推廣這一做法基礎上,各網站還可考慮設立統一數據格式、可信息共享的“謠言粉碎機”和“釣魚網站曝光臺”等。當各方面條件成熟時,還可進而打造全國性網站辟謠聯盟,讓誠信成為傳播者進入自媒體空間的“通行證”。
2.無害原則
從比較倫理學角度來看,從來沒有這樣的社會:它的道德準則不包含不傷害他人的禁令。這里所說的無害或不傷害原則,就是指作為一種獨立個體的人之間的互不侵犯、互不侵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英國哲學家密爾認為,“人類之所以有理由有權利可以個別地或集體地對其中任何成員的行動自由進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御。這就是說,對于文明群體中的任何一個成員,之所以能夠使用一種權力反對其意志又不失為正當,唯一目的只能是防止傷害到他人”,因為安全是人類最強烈的需要,“所有人都把它看做是一切利益中最重要的方面,缺少了它,沒有人能夠生存”。[7]就自媒體倫理問題來講,無害原則更有其特殊的重要意義。自媒體傳播是一種基于社交關系的大眾傳播。一條信息經過意見領袖的轉發、評論,會立即形成信息傳播的爆發式增長點,出現“幾何級放大效應”。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沈陽教授曾用軟件對250個大V的微博進行分析——選擇了四個常用罵人詞語,最終搜索出臟話微博6246條,臟話率大于千分之三點八,明顯高于一般網友。[8]語言污染繼而導致話語暴力乃至現實肢體沖突,催生了網絡罵戰,“大V約架”等公共事件。
這里還要特別提及網絡人肉搜索觸碰公民合法權益底線,尤其是未成年人合法權益底線的社會倫理風險及其危害。在這方面,“丁錦昊事件”可謂一起典型案例。2013年5月24日,網友@空游無依在新浪微博發布了一條關于埃及3500年前文物被中國游客刻上“丁錦昊到此一游”的微博。該條微博隨即引起了廣大網友的關注,被迅速轉發超過8萬次,評論近2萬條。接下來,該事件在網絡上持續發酵,網友@蠟筆小球“人肉”出肇事者可能是曾就讀于南京某小學13歲中學生丁錦昊;25日,丁錦昊母親出面道歉;26日,丁錦昊曾就讀的南京某小學網站被黑。數千年前的文物被涂鴉固然令人痛惜,但接下來成人自媒體世界所發生的一切更值得反思。例如有網友痛罵其素質低劣,“給祖國丟臉”,甚至聲稱要“清除民族敗類”。對海外旅游中的不文明行為進行公開討論或譴責無可厚非,但這種過于激烈的言辭很容易在讓人獲得某種道德優越感的同時對當事人造成精神創傷和權利傷害。事實上,如果一定要有人對此事件負責的話,首先是丁錦昊的監護人即父母;其次,當時的陪同導游因未盡勸止義務亦難辭其咎。《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未成年人是指未滿十八周歲的公民”;第五條第一款規定“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嚴”;第三十九條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個人隱私。”這場關于中國人海外旅行不文明行為的網絡討論顯然不應造成對一個年僅13歲少年名譽權和隱私權的雙重侵害。所有自媒體傳播者必須明確認識到: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換言之,法律構成底線倫理的底線。
3.公正原則
這里所說的公正原則,就是作為公平的正義原則。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指出:“在某些制度中,當對基本權利和義務的分配沒有在個人之間做出任何任意的區分時,當規范使各種對社會生活利益的沖突要求有一恰當的平衡時,這些制度就是正義的。”[9]也就是說,每一具備公民資格的個體都沒有等級貴賤之別,都享受完備性的道德主體身份。“每個人都被看做一個,而不是更多”,用社會制度的眼光來看,沒有哪一個人比別人享有更多的分量。
公正原則就是要求不偏不倚地對待所有成員,沒有歧視,也沒有偏愛。對于自媒體傳播而言,這也就意味著微博大V和網絡名人必須同樣接受社會傳播制度及基本倫理規范的約束,他們不應該也不可能成為網絡共同體中的特殊成員。有學者敏銳發現:“微博上意見領袖與公眾間的來往是雙向的、直接的,而這種雙向的互動又是不平等的。以某些意見領袖為中心形成了一個個“意見部落”,真的能實現哈貝馬斯所說的理性對話嗎?顯然是不能的。”[10]這一對于微博輿論領袖教主化、民粹化傾向的擔心絕非杞人之憂,而是客觀看到“圍觀就是力量”的正反兩面,提請關注網絡自媒體社會動員的負面效應。越是“音量大”的網絡名人,越要自覺承擔社會責任,這也是社會公正倫理提出的起碼傳播規范和道德要求。
公正原則作為一種社會德性,它還要求公平地分配權益和義務,把個人應享有的和應承擔的分配給個人,使人人各得其所。在這個意義上,“正義就是均衡、相稱,也就是有原則或者有法律、持之以貫,而不是隨意安排”。[11]對于自媒體傳播秩序的治理而言,相關管理機構和司法部門也應遵循行政倫理和法治倫理,嚴格依據傳播逾矩行為所造成的社會損害程度來定責處罰,堅決杜絕執法偏差。凡不是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的,以春風化雨的批評教育為主;誤傳謠言造成一定不良后果的,公開道歉并刪帖;在傳播活動中明顯損害他人名譽權的,承擔民事責任;對已被證明是虛假信息的仍反復傳播、炒作甚至加工、夸大造成嚴重后果的,必須承擔刑事責任。這無疑是公正原則“糾正”的正義或“矯正”的正義的具體體現。
[1]Dan Gillmor.We the Media: 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O’Reilly Media, Inc, 2006
[2]丹尼斯·麥奎爾.麥奎爾大眾傳播理論[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
[3]肖英.生命的原則——訪北京大學教授何懷宏[N].中國青年報,1998-12-09
[4]梁啟超.新民說[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5]美國新聞自由委員會.一個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6]劉大椿等.網絡倫理的若干視點[J].教學與研究,2003(7)
[7]約翰·密爾.論自由[M].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
[8]范承剛等.大V近黃昏?[N].南方周末,2013-9-12
[9]約翰·羅爾斯.正義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10]許紀霖.微博、知識分子與話語權力的轉移 [N].組織人事報,2011-4-28 .
[11]何懷宏.倫理學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