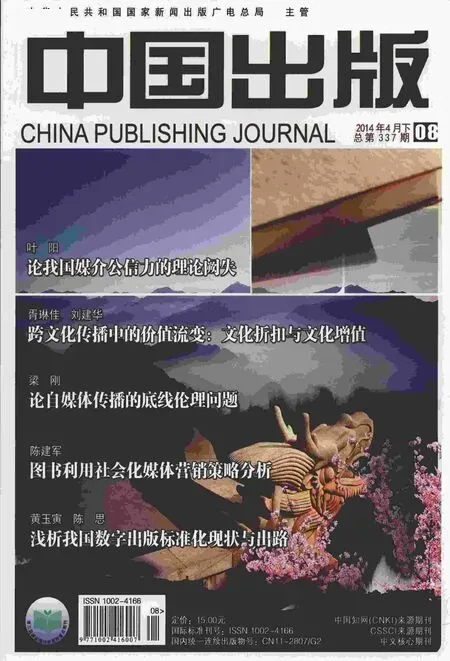深度報道與拯救報業*——對《華盛頓郵報》出售的三點思考
文/張世海
2013年8月5日,華盛頓郵報公司宣布以2.5 億美元的價格將《華盛頓郵報》及其資產出售給亞馬遜公司首席執行官杰弗里·貝佐斯,10月1日,這筆收購正式完成。《華盛頓郵報》創辦130 多年來,有過多次沉沉浮浮,在歷史上也在1899年、1905年和1933年經歷過三次易手。前幾次也都是因為遭遇各種困境,易手之后人們對它的未來還有預期,但此次易手卻在新聞界引起極大的關注:盡管貝佐斯信誓旦旦地承諾要挽救紙質版的《華盛頓郵報》,但它從此可能將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落甚至消失。
美國報業的衰落已經持續多年,《華盛頓郵報》的出售也是預料之中的事情,但《華盛頓郵報》是美國報業的杰出典范,它的案例值得我們深入分析,并汲取對我們有借鑒意義的經驗。
一、報業的成功經驗不能移植到網絡媒體
對業內人士而言,《華盛頓郵報》在新聞領域獲得的巨大成就早已耳熟能詳,此處不再羅列。這些成就足以說明,在紙媒時代,《華盛頓郵報》有一條行之有效的新聞業務原則,并積累了豐富的新聞業務經驗。按照簡單的邏輯,受眾對高質量的新聞需求一直都存在,《華盛頓郵報》只需要用網絡技術傳播它的新聞即可,只要受眾仍然閱讀它的新聞作品,并愿意支付費用,它就能繼續吸引廣告商,持續紙媒時代的運作模式。這個運作模式以前是通過紙媒,現在則通過網絡。這也是很多報業轉型的思路。但報業里不少的案例證明,這個思路在網絡上行不通了。網絡受眾已經養成免費獲取信息的閱讀習慣,讓他們接受收費還需要很大努力。另外,數字閱讀方式,無論是通過電腦屏幕還是手機屏幕,都與傳統的紙質閱讀方式不同。
《華盛頓郵報》最擅長深度分析類的政治報道,對于一些重大政治新聞,它長篇累牘,不惜篇幅。那些大氣堂皇、嚴謹冗長文章,動輒數千字,很多文章還充滿艱深的術語,交叉著各種復雜的背景介紹,在報紙上都是密密麻麻的一片。閱讀時,讀者需要專門抽出時間平心靜氣地跟隨作者的思路和編輯的編排,有時還需要結合上下文反復揣摩才能吸收豐富的信息含量。現在受眾越來越多地使用移動智能終端接收信息,對于這些新媒體,那種大塊文章也許是不適合的。這樣一來,《華盛頓郵報》多年積累的引以為豪的“獨家報道、專有的編排、自有的觀點、特別的敘述方式”[1]以及面面俱到的鴻篇巨制在網絡媒體上反而是個劣勢。對于網絡傳播,《華盛頓郵報》還是個新手,它必須從頭學起,但網絡媒體已經獨立發展了多年,這些經驗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學到的。華盛頓郵報公司也不是沒有嘗試過,它旗下的《新聞周刊》2003年開始模仿網絡媒體的風格,大量刊登短小、淺顯的新聞;意識到這一招不靈之后,2009年5月起,《新聞周刊》又重新開發有原創價值的深度報道,力圖成為“思想領導者”,最后還是以失敗告終。
2008年華盛頓郵報集團公司董事會主席唐納德·格雷厄姆在股東大會上說:“在我投入37 個年頭從事報業工作后,我會告訴你們——正如你們也期望我會說的,我認為報刊作品與報紙記者對華盛頓多年來的政治和經濟生態產生了重大的積極影響。但是,時間證明我們并不全然明白向今日的受眾傳遞新聞最聰明的方法。”[2]
網絡傳播的各種優勢已經成為常識,無須做任何論證。除此之外,網絡時代的各種信息技術手段還改變了受眾獲取信息的方式。最明顯的一點是,在傳統媒體時代,新聞信息的傳播方式是“信息源—大眾媒體—受眾”,現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省掉大眾媒體這個環節,變成“信息源—受眾”這樣的傳播方式。比如我們如果想了解某個政治人物的觀點,通過他的個人媒體,比如推特、微博、微信等,往往比大眾媒體來得更直接準確。在這種媒介技術環境下,新媒體的角色可能是提供開放的公共平臺,制定信息發布的規范和作品標準,設置議程,吸引更多的受眾參與,然后在此基礎上建立商業模式。現在美國《赫芬頓郵報》也是這種思路,創始人之一的喬納·柏瑞蒂認為,網絡新聞媒體應該是“一個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共享的事業”。[3]《華盛頓郵報》雖然也嘗試努力過,但它難以擺脫既定思維,它的很多做法與成熟的網絡媒體相比還是很笨拙的。那些習慣從網上獲取信息的受眾也不愿再給《華盛頓郵報》機會了。
二、報業若不能成功轉型就盡早出售
從管理學的角度說,一個公司經營破產或被迫出售資產,我們都可能從它的經營行為中找到各種失誤。但華盛頓郵報公司此次出售報紙業務,我們看不出它此前有什么重大決策失誤,它的決策層確實盡力了。2009年年初,《華盛頓郵報》從亞馬遜公司延聘維賈伊·諾維丹擔任首席數字主管,希望能在數字時代找到更好的傳播新聞的方式。2010年3月,《華盛頓郵報》推出iPhone 有償新聞下載服務,全年訂閱費僅收1.99美元。2010年7月,公司收購了一家提供新聞聚合服務的網絡公司,然后為受眾提供新聞閱讀方面的聚合服務,用戶可以通過華盛頓郵報公司的相關網站,自行選擇感興趣的內容,創建屬于自己的新聞網站。[4]
這些努力都收效甚微,但同時公司的其他部分業務仍然發展得很好,比如它全資所有的卡普蘭教育培訓中心在美國教育培訓市場上具有強大的競爭力,公司的收入主要靠這個培訓機構。一個專業的報業公司沒有什么決策失誤,卻竭盡全力都經營不好報業,這無可辯駁地說明,報業確實在衰落了。既然所有的努力都失敗了,最好的辦法就是出售,而出售又必須選擇最佳時機,并尋找最佳買家。
《華盛頓郵報》并未苦撐到油盡燈枯的地步,而是在元氣尚存的時候尋找新的東家,這也是一種雙贏的明智之舉。對郵報公司一方來說,能最大化減少損失,得以全身而退,不至于身陷債務泥淖;對亞馬遜來說,郵報的根基仍在,潛力巨大,無論貝佐斯將來如何改造郵報,都有一個很好的基礎。
在《華盛頓郵報》的經營史上,有很多不成功的出售教訓。在麥克萊恩家族經營《華盛頓郵報》時,它的盈利能力和公信力一度降到谷底。1929年美國大蕭條前夕,尤金·邁耶愿以500 萬美元收購《華盛頓郵報》,但被小麥克萊恩拒絕。到1933年,小麥克萊恩終于支撐不住,只以87.5 萬美元就賣給了尤金·邁耶。
最近的一次出售是在2010年。當年8月2日,華盛頓郵報公司以1 美元的價格把旗下負債7000 萬美元的《新聞周刊》賣給91 歲的美國富翁西德尼·哈曼。早在2007年,《新聞周刊》就開始走下坡路,但公司沒有及時出售,而是勉力苦撐了3年。我們不知道華盛頓郵報公司最后是基于什么考慮把《新聞周刊》的未來托付給一個91 歲的老人,現在看來那個決定是錯誤的。哈曼雖然豪情萬丈,但畢竟年事已高,2011年4月5日即去世,他的理想和抱負也都落了空。
隨著技術的革命性進步和人們需求的變化,依托新技術的新產業取代舊產業是一種常態,報業也是如此。在網絡媒介環境中,傳統報業的信息傳播方式和營利方式都受到了顛覆性的挑戰,已經難以為繼,無論報業過去多么輝煌,也無論對報業懷有多么深厚的感情,我們都不得不接受報業最終將萎縮的趨勢。對我國的報業來說,現在是時候思考如何收縮報紙業務了,并為未來可能更困難的形勢未雨綢繆,以把握主動權,避免到最后應對失策。既然網絡媒體及其他各網絡移動終端已經成為當代受眾接受信息的主要方式,如果報業想轉型,思路就應該從傳統的報業信息傳播方式中走出來,透徹地研究網絡的特性和潛力,把網絡的技術特性作為我們思考問題和做決策的依據。從這個意義上說,麥克盧漢的觀點“媒介即信息”非常具有啟示意義。
三、報業衰落的影響多年后才能顯現
現在以新興網絡技術為主要傳播渠道的新聞傳播方式的開放性、即時互動性和草根性也正符合一些學者的新聞理想。早在1978年,美國學者蓋伊·塔奇曼就在其出版的《做新聞》一書中認為,傳統新聞業由職業新聞人運作,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構建了社會現實,他們的新聞生產阻礙了大眾對社會真相的探索,也阻塞了大眾通往真理的道路。[5]對一些已經習慣數字閱讀的受眾來說,他們看到的也多是傳統報業的劣勢,以《華盛頓郵報》為代表的報業的衰落似乎沒有什么影響,報紙早就變得可有可無。
但實際上,在人類歷史上任何一種新傳播技術的誕生和普及都會產生多方面的影響,包括人們的思想觀念、思維方式、藝術表達、文化形態、經濟生產和組織結構等各個方面。這種影響的結果復雜多樣,可能要幾十年之后才能充分顯現。在20 世紀30年代,美國學者劉易斯·芒福德就覺察到電報和電話等通訊工具可能帶來的弊端:“取消人類直接交流上的限制,其危險性在初始階段好比眾多人口涌入一個新的地方,它增加了發生摩擦的機會。……閱讀、寫作和繪畫是思維的高度提煉,也是深刻思想和沉思熟慮的行動的媒介,現在卻被這種即時交流削弱了。”[6]失去了深度思考,人類就會自我迷失,并失去前進的智慧和動力,而紙質媒體是最適宜深度思考的媒體。單憑這一點我們就堅信,紙質媒體永遠不會消失。也許當網絡媒體的熱潮退去之后仍然存在的紙質媒體會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但將要經歷一段痛苦的堅守和煎熬。
美國另外一位媒介思想家波茲曼在考察印刷術的歷史影響時認為,“印刷術樹立了個體的現代意識,卻毀滅了中世紀的集體感和統一感;印刷術創造了散文,卻把詩歌變成了一種奇異的及精英的表達方式;印刷術使現代科學成為可能,卻把宗教情感變成了迷信;印刷術幫助了國家民族的成長,卻把愛國主義變成了一種近乎致命的狹隘情感。”[7]這種思考問題的角度和方式也適用于網絡技術。我們現在能看清楚數字技術給我們帶來了哪些便利和好處,但我們還看不清楚失去傳統報業可能會給我們帶來哪些壞處,但這個問題是客觀存在的,必須引起我們的關注。假如《華盛頓郵報》未來停止印刷紙質版,它的網絡版可能會變成一個高端的時政論壇。紙質版的《華盛頓郵報》白紙黑字地記錄著歷史,被很多機構作為文獻保存著,讓任何有敬畏歷史之心的人都認真看待。網絡版能否像紙質版一樣在政治領域發揮影響力還未知。
美國報業還有更多重要的功能,它的歷史先于美國的歷史。美國報業直接參與締造了美國這個國家,并在美國200 多年的歷史中,深刻影響著美國的社會運動、政治運行和其他領域。失去了報業的美國將會發生什么變化也是值得深思的。就《華盛頓郵報》而言,在政治領域,我們現在還沒有看到,在美國有哪個網絡媒體能具有像印刷版《華盛頓郵報》那樣的影響力。它是美國媒介監督政府的一個典范,是美國新聞理想的一個重要載體,以《華盛頓郵報》為代表的美國報業與政府的關系又是美國政治運作體系中最核心的幾個支柱之一。以它為代表的一大批報紙的衰落,不僅僅是報業的存亡問題,它會引發人們更深的思考:美國政府與美國新聞界的關系是否會失去平衡,未來新聞界如何與政府進行互動并建立新的平衡關系。
四、結語
《華盛頓郵報》是美國傳統報業的杰出代表,它在報業領域里的很多貢獻已經載入美國新聞史,盡管它現在的新東家貝佐斯希望能扭轉它的頹勢,但當代的媒介環境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它若想恢復到20 世紀70年代以來的輝煌是很難了,這對很多紙媒新聞人來說是一件很傷感的事情。但是以《華盛頓郵報》為代表的傳統報業的新聞理念以及新聞專業主義精神是一筆永恒的財富,值得未來美國新聞界珍惜。還有一點可以欣慰的是,由于先前多元化戰略的成功,華盛頓郵報公司在出售《華盛頓郵報》之后,仍能繼續經營其他產業,未來更名后的新公司成功轉型也是有可能的。現在我國的報業傳媒集團絕大多數也都進行多元化的經營,華盛頓郵報公司的這個戰略也非常值得借鑒。
[1]連俊.傳媒業整合邁出重要一步[N].經濟日報,2013-08-08
[2]覃羿彬.華盛頓郵報的破與立[N].21 世紀經濟報道,2008-11-18
[3]胡泳.報紙已死,報紙萬歲——報紙轉型的關鍵戰略[J].新聞記者,2011(8)
[4]陳璐編譯.《華盛頓郵報》為何忙著推出個性化閱讀網[N].中國文化報,2011-02-15
[5][美]蓋伊·塔奇曼.麻爭旗,劉笑盈,徐揚譯.做新聞[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8:172
[6][美]劉易斯·芒福德.陳允明等譯.技術與文明[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2009:213-214
[7][美]波茲曼.章艷,吳燕莛譯.娛樂至死[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