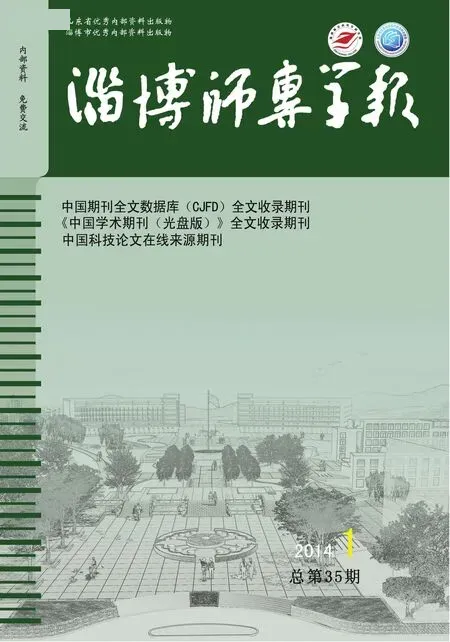孔子“成圣”學說與當代大學生的信仰拯救
石敏杰(上海大學 社會科學學院,上海 200444)
孔子“成圣”學說與當代大學生的信仰拯救
石敏杰
(上海大學 社會科學學院,上海 200444)
在當代,隨著社會轉型和西方文化的影響,大學生群體中的一部分學生出現了信仰缺失的現象,主要表現為享樂主義、拜金主義與心靈的空虛化,嚴重影響著其正確三觀的樹立。傳統儒學中的“成圣”理念以個人道德修持為中心,注重仁愛之心的擴充弘揚與禮法規定的自我遵循,同時又對義與利的關系進行了準確的把握,對于個體道德信仰之確立、道德境界之提升有著極為積極的推動作用。因此,在日常的教學活動中,應該注重借助開發傳統成圣理念的合理成分來拯救大學生的信仰缺失。
成圣; 孔子; 大學生信仰;德育
在當代,西方文化的沖擊以前所未有的深度與廣度對國人的價值觀念與行為方式造成了巨大影響,其中自然包涵著一些諸如過度性解放、極端個人主義與盲目功利化的消極因素。此外,市場經濟與商品物質的極大豐富又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物質享樂主義與拜金主義,造成心靈精神的相對空虛,對個體之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偏離起了助推作用。然而,在所有人群之中,大學生群體因其所處年齡階段之特殊性,三觀形成的不穩定性以及從學校的象牙塔到接觸社會的過渡性等諸多因素而成為受當代文化與社會之負面影響最嚴重的人群之一,成為眾多社會學家、哲學家和心理學家所關注的對象。
總體來看,當代大學生所面臨的問題日益多樣,表現形式不一而足。就其根源,我個人認為信仰之偏離、異化乃至缺失是當代一部分大學生所面臨的最大危機。這種信仰危機使一部分大學生喪失了支撐其學習工作的精神動力與指導,具體表現為當代一部分大學生之價值理念的異化、社會責任感的丟失與傳統禮法的空白等方面。受此影響,當代一部分大學生遺失了自古以來孔學之中所保存下來的修齊治平之道,修己安人之為,天人合一之境,尊圣敬賢之心。因此,應和國家對以孔子為代表的國學之回歸,應極力探尋孔子學說中的合理性思想以拯救當代大學生信仰層面的危機,使之符合當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符合社會主義新青年的標準與形象,為構建和諧社會貢獻一己之力。這是國人的迫切任務也是本文的應有之義。本文擬通過對當代大學生信仰缺失問題之分析與孔子成圣學說的淺析來初步探尋二者結合的可能性與途徑,以求找到孔子思想對當代大學生拯救與指導的作用。
一、當代大學生面臨的主要問題——信仰缺失
近些年來,高校大學生的數量迅速增加,而其作為一個日益龐大的整體,所面臨的問題也日益增多,引起各方關注。大學生犯罪率居高不下,云南馬加爵一案震驚全國,與此同時,一些如自殺、自卑、不誠信等心理、道德方面的問題也日益增多。諸此種種現象都在揭示當代一部分大學生在心理與精神層面正面臨嚴重的信仰危機。
這種“信仰”并非等同于宗教學領域中對超自然神靈的信奉,而更多的是一種精神追求與立身修身之原則。它決定了一個人的精神境界與心靈修養層次,且可以外化為指導人們為人處世、安身立命的準則。孔子所謂“三十而立”的“立”亦即此信仰準則的建立,它源于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學”的勤奮思與學以及后世生活之體悟,由此方能立“四十而不惑”的基礎。正是孔子內心信仰道德律的建立,使他“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即便是四處碰壁,“累累若喪家之犬”,仍不改其志,一心以“仁”臨天下,“學而不厭,誨而不倦”,以至“不知老之將至”。因此,合理正確的信仰的建立意義重大,于人生受益甚巨,相反,其信仰的偏移或缺失,則會貽害終生。
當代一部分大學生信仰危機的主要表現首先是其價值理念的錯位,如拜金化、功利化傾向。以近期某網絡紅人的拜金現象為標志,一部分大學生過分關注金錢等物質利益的追求,同學之間甚至以金錢、房子、車子等外在物質為攀比對象,導致價值觀與人生觀產生扭曲。由此導致一部分大學生在找工作時并非以其工作性質所能帶來的社會價值與人生價值的統一與實現為標準,也并非考慮工作內容與自身之喜好能力的相符,而是一味盲目關注其個人薪水、待遇、級別的最大化。此外,對利益的過度關注還使一部分大學生甚至走上違法犯罪道路,如為了攀比而偷盜、替考乃至從事其他違法活動。
其次,信仰缺失還導致了一部分大學生社會責任感的淡薄。由于沒有崇高信仰的指導與支撐,一部分大學生無法從整體全局出發去認識個人與他人,個人與集體,個人與社會之間固有的緊密聯系。因此,過分局限于狹窄的小我之中,以自我為中心,陷入了“我執”的困境而割裂了與他人的聯系。由此便導致了對他人的冷漠與信任危機。一方面不肯對人施予關愛與包容,形成“只掃自家門前雪,不問別人瓦上霜”的自私自利心理;另一方面也不肯信任他人,在心理上與他人豎起了隔閡,遮蔽了心靈的溝通。沿此進入更深層次發展則是對社會集體的淡漠,一切以自我為出發點與歸宿,看不到社會與個人血脈相關的整體性聯系,不肯為社會盡自己的貢獻。
再次,信仰危機還伴生了一部分大學生敬畏之心的空白,對圣賢敬仰的缺席以及對社會習俗、法則等傳統禮法的違背與破壞。近代以來,因科學的極大發展,宗教的地盤日漸縮小,人類理性戰勝了愚昧迷信,但一個相伴而生的現象卻是人類自身的神圣敬畏感在逐漸消退。“人類中心主義”導致了人對大自然的盲目掠奪式開發與破壞,對古代圣賢的不合理輕視,以及對一些具有極大社會效益與文化因素的習俗禮法進行全盤否定。大學生群體作為知識分子階層,自然也有一部分人受到“人類中心主義”與“個性張揚主義”的影響而產生自大自負的心理。這種心理使一部分大學生不能正視原有之文化觀念,以一種簡單化、片面化的觀點去看待古代的天人思想、尊賢思想、仁義禮法,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全盤否定之。
最后,心靈的空虛同樣是信仰危機的表現。物質享樂主義的盛行與當代網絡文化的負面效應以及對優秀傳統文化的關注不足造成了一部分大學生在心理上面臨著危機。一部分大學生終日沉迷于網絡與游戲之中,迷失了自己的人生目標,更不重視對文化成果的學習與汲取,使得心靈日益荒蕪,表現在后果上便是能力下降帶來的“畢業即失業”的窘境。久而久之,這種心靈空虛的狀況必定會導致其精神狀態的萎靡不振,對于終生發展更是貽害無窮。
二、孔子哲學思想的現代價值啟示——成圣信仰的支撐
(一)“成圣”信仰的挺立
孔子創立儒學至今歷經兩千多年而不失其色,自然有其積極合理內核做支撐。在筆者看來,所有孔子思想中影響最為深遠的就是他為世人提供了一個永恒崇高的信仰理念與精神寄托。簡單說來,孔子的信仰體系即以追求成圣為終極目標,以通過“修己以安人”而達至“內圣外王”為途徑。這其中的修身聚焦于道德意識的自覺與日常踐行,遵循的主要原則就是“仁”,外化而為“禮”,具體展開則是“仁義禮智信”,從個人人格完善出發追求一種兼濟天下的情懷與責任,終極歸宿是大同社會的構建。因此,孔子成圣學說可謂是一個囊括其全部精華的龐大體系,既是其思想之瑰寶又是其人生信仰之所賴,值得人們去深入挖掘。
所謂“信仰”即推動一個人行動之精神動力與規范,指導日常言行舉止的理念,以及于人困厄之中進行鼓舞奮發的恒守信念。它根植于心靈而成為精神高原的燈塔。因此,以“成圣”作信仰正好與孔子畢生的軌跡相穩符。郭奇勇教授在《儒學之精神》[1](P267)中就曾把孔子的理想人格境界分為三類:以圣人為代表的理想至上境界,以賢人為代表的現實理想境界,以君子為代表的現實道德境界。這其中的圣人是在現實中難以實現的,因為他是一切美德的總匯者,是完美踐行“仁義”之天道本性的人。孔子曾對此論述過,“子貢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在孔子看來,圣人是高于“仁”的范疇,是廣博地施于百姓而幫助眾人實現其之所求。這種理想境界的圣人是連堯舜也難以做到的,因此只應作為信仰去無限逼近,作為修身之目標,具體實施還是應從“仁”做起。只要做到“仁”,就可以達到堯舜的層次上,正如“人皆可以為堯舜”。因此,圣人在孔子儒家看來是一種人格的極致,指知行完備、至善之人,是有限世界中的無限存在,在人格完善上“止于至善”,故謂之“才德全盡謂之圣人”。在《孔子家語·五儀》中,孔子之圣人形象有著最為貼切的解釋:“公曰:“何謂圣人?”孔子曰:“所謂圣者,德合于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 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識其鄰,此謂圣人也。”這種能體察天地萬物之理而又潤物無聲的極致存在只能是作為信仰的對象給人以前進的動力和指導。因此,孔子把他設為信仰對象意在對自我修煉的鞭策,對大眾行為的導引,對社會風俗的淳化,其積極意義不可估量。
孔子“內圣外王”的信仰體系還有一個更詳盡的進展路線,即《大學》開篇所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它作為儒學兩千多年的主線貫穿于始終,是理解其精神內涵與整體學說思想的關鍵所在。它以個人修身明德為起點,以齊家管理為手段,最終達到國治天下平。這條由己而推廣到天下的進路其實表明了儒家關于個人與社會的看法,即儒家絕非片面割裂地偏重個人修養抑或兼濟天下而是把個人與社會相即不離地統一起來,即達至“內圣外王”的統攝。這種“內圣外王”的宗旨是通過個體的道德自覺來推廣至社會,以道德性約束為秩序紐帶溝通個人、家庭與社會。正是在這一構想之下,個人與他人與集體乃至全天下都息息相關,個人也便不再是單純之孤立個體而是融攝于社會之中的細胞。達至這一境界的人才算是初步踐行了理想中的成圣信仰。
“修身”作為道德起點,又是以“仁智勇,天下之達德也”(《中庸》)為其核心。循三綱五常而動,以求做到“萬物皆備于我”。在這種境界下,人格完善而推及他人以馭天下,會使天下井然。“《論語》說‘修己以安人’,加上一個‘以’字,正是將外王學問納入內圣之中,一切以個人的自己為出發點。即專重如何養成健全人格。人格鍛煉至精純,便是內圣;人格擴大到普遍,便是外王。儒家千言萬語,各種法門,都不外歸結到這一點。”[2]這種成圣理想強調自身的社會責任感與擔當意識,規定了圣人品格中應有的對社會之貢獻,同時從其社會整體之維來把握則是把這種理念推而廣之,使眾人在追求自我超越之際共同構筑一個大同的理想社會,“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禮記。禮運》)。如果說成圣信仰之外有一個更終極的理想存在的話,那便是這大同社會的構建,這是成圣理想內在的超越:由個人之人格修養達致社會之大治。真正通過自己的努力為大同社會的建成貢獻出力量,使民風歸樸,社會井然才是真正實現了成圣的理想,趨近了圣人的標準。
“內圣外王”“修己以安人”的信仰把個人與他人社會相連,體現在現代社會里的價值不容估量。這種思路有助于現代人克服自己的分別心,消弭因過分自我而割裂開的與他人集體固有之關聯。小到個人之間的爭名奪利、爾虞我詐,大到民族間及區域間的領土爭端、利益沖突、價值觀矛盾,許多動蕩與仇恨都因過分局限于“小我”之內,忽視人格之健全并推廣至他人而萌生。假使眾人都能回歸儒學“修己以安人”的模式之中,不斷更新自身,完善人格,以“仁智勇”的品格心態推及他人,就會沖破小我束縛,實現社會之大和諧。同樣,對于當代大學生而言,對他人的冷漠與不信任,自私自利的觀念正是因為不清楚自己本與他人是一體相聯的關系,亟需用儒家信仰予以填充之,方才可以從根本上治愈。
(二)成圣理想的內核——仁與禮的規定
以“內圣外王”為主線的孔子思想體系注重“人格”的完善與外推而達到的社會之和諧,而實現這一信仰則無疑需要以仁與禮為其著力點與重心。因而,圣人之所以不同即在于他踐行了仁與禮而實現了內在的超越。仁與禮是圣人的本質規定性,構成了成圣信仰的內核,也是達致圣人標準的唯一途徑。唯有把握孔子所述的仁學與禮學之切要內涵,才有可能從根本上發揮其成圣學說的積極意義,拯救當代大學生之信仰危機。毋庸置疑,孔子的學說體系最為閃光之處即在于“仁”與“禮”二字,這兩方面互為表里而共同成為儒學兩千多年來的核心,并對塑造中華民族的性格與文化特性產生了深遠影響。梁啟超也曾指出“孔子學說,最主要者為‘仁’。‘仁’之一字,孔子以前,無人道及,《詩》及《尚書》二十八篇,皆不曾提到,以仁為人生觀的中心,這是孔子最大的發明,孔子所以偉大,亦全在此。”[1]盡管梁氏的考據不甚精細,如據現代專家考據證明在《尚書》和《詩經》中已開始在很少場合出現“仁”字,《尚書·金滕》中有“予仁若考”,《詩經·鄭風·叔于田》:“洵美且仁”等,但仁作為一個思想體系的出現則無疑自孔子始。
孔子講仁,都習慣從不同側面指出其所包含的精神特征,僅“仁”一字在薄薄的《論語》中就出現了百余次之多,且其含義不盡相同,或為“仁者愛人”或為“克己復禮”或為“忠恕之道”,共同構成一個龐大體系。其中最為首要的一面應屬“仁者愛人”,以對人之尊重與關懷為重點,主張對他人本身需求的回歸并將其作為畢生之行動準則。“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論語·顏淵》)這種對人的關愛還需以知人為前提,即需要換位思考后對他人處境與需求的體悟,并以此為基礎去關愛他人。故而這種“愛心之仁”并非一種虛偽程式的寒暄,實為一種心靈溝通后的雪中送炭,真正助人以實,給人以需。孔子后又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為仁的具體實施原則,從正反兩方面規定了人們在日常生活之中如何消弭分別心,如何克服自我利益為中心的束縛去幫助他人,輔助他人最終實現自我的內在超越,達到如尼采的酒神精神一樣的大我境界。然而,以“愛人”為出發點與歸宿的“仁”卻并不是普遍無差別的抽象博愛,而是一種“差等之愛”。孔子等早期儒家主張“泛愛眾”,但應遵循先親后遠的程式,即如孟子所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切愛人的舉動必要以親人開始逐漸外推,且程度會有不同。這種仁愛觀“與基督的‘博愛’,墨子的兼愛是有區別的。愛有差等是人之常情。人對自己父母、兄弟之情推而廣之,將心比心,推己及人,愛周圍的人,社會上的人”[1]因而,這種“仁愛”是順應人性的原則,具有更為現實可行的特點。
“禮”作為“仁”的外在表現又是成圣信仰體系中不可省去的部分。在孔子“仁學”之中,“禮”亦居于至關重要的地位。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由此可知,禮亦為仁之部分,它規定了人們日常行為之準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禮還是仁的外化之形式,以“愛人”為核心的仁表現于外便是對禮的遵守,故而“仁”與“禮”的關系可謂是內容與形式的關系。但同時,孔子又一再強調禮必需以仁為內容方才有效,失去了內核性的“禮”之情感,則徒有外在空洞形式,于己于人毫無益處。所謂“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論語·八倄》)只有內容與形式的統一才是真正“仁至矣”。“禮是借此在一切生命領域之中形成了應有氛圍的一些形式,諸如對事物的真切同情,信賴,尊敬,禮引導著人們通過教育而使他們獲得某些共同的東西,這些東西成為他們的第二天性,因此人們在感知禮的普遍性時,并不把他作為外在的強制,而是作為自身所固有的本質存在著。”[3]禮即人的內在情感的自然流露,本于“仁”而非外在之強制。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禮”作為程式化的日常儀軌,還有利于人們深化內心之“仁”,使人在每天踐行“禮”之規則之際時時刻刻修煉其人格,純化其心志,真正返回到“心之四端”的內在仁義之心。《大學》中講“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中庸》也一再強調“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一直為孔子乃至儒學所看重,認為是實現天人合一,體悟天命與天道的條件,而這種內在心理的“誠”無疑需要在外在儀軌化的禮之實踐中去輔助到達。唯有誠心誠意的踐行禮才能返歸天人合一的境界,回歸本性,即人之為人的本質規定性——仁。于是,孔子一方面通過禮來規范人們的行為去整合社會關系,調節社會秩序以求穩定,另一方面也是期望人們以“誠”對“禮”,在日常每天的踐行中去體悟其中所內蘊的“仁”,不斷深化理解。彭國翔教授也曾指出《論語·鄉黨》中的生活細節體現了孔子在日常生活中借助禮來進行身心之修煉,他認為“作為自我修養方式功夫的禮儀實踐,進一步來說,根本是一種在日用常行中各種境遇下無時不處在進行的身心修煉。”[4]
總而言之,孔子之“仁”起于愛人,而又以“知人”為前提,外化于對禮的遵守,而循“差等之愛”的原則推廣至“泛愛眾”,這種對他人的體愛無疑對于提升個人之境界與促進社會整體之和諧意義深遠。而“禮”作為人們行為之調節與內心道德修養之手段又有利于人們自律意識的增強,基本價值理念的深化,以及內心情感的真實。這兩方面共同勾畫了成圣信仰中理想圣人的人格形象,即滿懷仁義之心,謹遵圣禮之道。由此,方能實現“獨善其身”之后的“兼濟天下”。這是圣人的本質規定性,更是成圣信仰的實現路徑。當今社會,自由與個性伸張的觀點在一部分大學生中極為盛行,他們只看到了一己欲求的實現,很多時候忽視了對他人的關懷。這種割裂人與人關系的“自我中心主義”導致了人際關系間的冷漠,加劇了信任危機與幸福安全指數的下滑。因此,發揮孔子思想中仁者愛人等學說的價值以喚醒其道德自覺意識與人文關懷理念便凸顯出重要作用。
(三)成圣理想的具體規定——義利關系的辯證把握
“義利”之辯一直是儒者探討的重要話題,雖于孟子時為高潮但無疑肇始于孔子,而成為對圣人品質與境界的具體規定。“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義與利成為了區分君子與小人的標準,語句中明顯體現了孔子對義的看重與對利的貶低。正是語氣中強烈的褒貶色彩使這句話成為了被后人誤解最多的一句古訓。人們誤以為孔子是舍利而專取義,對利全盤否定的不近人情之師。其實,縱觀《論語》中孔子對義利的論述,孔子不僅沒有完全否定利益而且對義利的關系以十分辯證合理的眼光去審視,對后人具有很大啟發。
首先,孔子肯定了“利”為眾人之所需所求,有其當然合理性,但同時又警惕世人不要因利棄義,而應取之有道。“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論語·里仁》)在孔子看來,仁與義是君子終生無時無刻都應遵循的原則,任何利益與之相沖突都應舍棄,只有在仁與義之范圍內的利益才是正當之利。這種義利觀影響到后世,塑造了眾多仁人志士的高貴氣節,如朱自清寧肯餓死也不吃美國大米的感人事例便是對這種義利觀的踐行。
其次,孔子反對過分擴張自己的物質性欲求,而主張以求道代替縱欲。“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為學也已。”(《論語·學而》)此處之意,即人應克服自然欲求的膨脹性,而達到超越自然的層次。表面看起來,孔子的言論似乎有點過于苛刻,但其實卻有其深意。因為人之欲望無盡,若不加以節制,則只會使得此欲望剛剛滿足,彼欲望又再度升起,如此縱欲循環只會使人沉湎于物質層面而忽視對道的體悟追求。故而可知,義利辯證之論也是符合于孔子修齊治平的終極信仰,使自身在日常操守中時刻不忘追求信仰的實現,是孔子對圣人品質的具體性規定。
這種義利觀帶有辯證色彩,對于糾正一部分大學生只重利而不重義的價值理念之偏斜意義頗豐,有助于引導學生在面對抉擇之際首先以義去篩選之,做到義利的平衡。同時,對于道的孜孜以求則又會讓學生的心靈得到充實,找到一個積極地前進目標,避免心靈空虛帶來的頹廢迷失。當然,這種“道”在今天應被賦予現代的時代精神與內容,即個人與集體利益的統一,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的實現,社會和諧的構建與自身層次的提升。這樣才能保證當代大學生在自我超越中實現人生意義。
三、孔子思想對大學生信仰拯救的意義
天安門廣場上孔子塑像的矗立標志著以孔子思想為代表的傳統國學開始復興,這將對當代中國社會產生更為深遠的影響。而在眾多傳統思想文化中,孔子學說以其獨有的價值與人格魅力對于拯救當代大學生的信仰缺失具有極大作用。
孔子本人就曾樹立了高遠的人生信念,即上文所述的成圣信仰與“修齊治平”之道。這種信仰不同于莊子恬淡自適、“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我行我素,也不同于佛家求得“萬法皆空”之般若智慧的超凡脫俗,而是一種立足于現實,用力于人世,歸宿于大同的執著境界。這種信仰是在社會之中實現“天人合一”,把個體之小我與社會之大我相關聯,實現終極的“榮辱與共”。因此,孔子的這一信仰十分符合當代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呼聲,實現人與人,人與社會之和諧一統。復興孔子的這一信仰,使之為當代大學生所接受,有利于大學生自覺地把自己與社會緊密聯系在一起,凡事都從二者之統一性來著眼,而不再拘于自己的小世界中,克服自我中心主義與自私自利的惡習。這必然使得大學生的社會參與度提高,社會責任感增強,主人翁意識更為明顯,在人生路途中找到信仰,堅定信仰,彰顯價值。
圣人的首要規定性便是對內心仁德踐履,因此孔子主張“仁者愛人”,以人為本的人文理念中包含著關懷意識。這種關愛之心的推廣亦是孔子信仰的具體表現與踐行。通過以仁愛教誨當代大學生,提高其“助人為樂”的思想道德修養水平,則又是破除大學生對人淡漠之心的一劑良藥。孔子以“成圣”為信仰,其核心與出發點即仁,所謂“仁之方”。當今,一部分大學生對同學、朋友,以及與陌生人顯示了難以理解的冷漠,不愿“救人于危難中”,正是’仁愛“的嚴重缺失,是信仰的離位。因此,弘揚“仁愛”精神,找回大學生信仰中人人互助的理念是拯救其危機的關鍵所在。
《青年博覽》在2006年第三期曾刊登了一篇題為《一位母親的辛酸來信》的文章,文中指出現在一部分大學生對父母的關愛視為理所應當,卻不知回報,實在令人寒心。這種“孝”道觀念的失位凸顯了在當代由于信仰的空白而導致一部分大學生對幾千年來傳統禮法的遺忘。“禮”作為“仁”的外化,規定著基本的道德要求與操守準則,承載著價值理念,自然也是圣人品格的應有之義。其中“孝”自古便被提高到十分重要的地位,成為了禮法之中首要的一項內容。“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與!”“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論語·學而》)。這種孝的觀念外化便是對長輩的尊敬與奉養,以一顆感恩之心去報答養育恩情,對先祖則是以祭祀儀式表達慎終追遠之情思。“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經·開宗明義篇》)孔子將其列為“德之本”自然不乏其道理:既然仁者愛人且愛有差等,那么仁愛之出發點自然應始于至親,對父母之孝便理所應當的成為根本之源。假使人人能保有這一根本,則“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孝經·開宗明義篇》)。盡管其中有些“愚孝”的糟粕應當剔除更新,但總體而言,這種禮節之遵循,孝德之傳承又是不可缺少的。它和謙讓之心與義利之心等一同構成禮法觀念是“成圣”信仰的既有組成部分,同樣對于修正一部分大學生的認識錯誤和行為過失有著積極作用。充分發揮“禮”中合理成分的作用有利于大學生堅定其信仰,端正其行為,從而有助于調動起才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孝的進一步擴展便是以天下為父母,以萬物為兄弟的“天下一家”的廣博胸懷。“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5]孔子的孝道發展到后世被推廣到對社會整體的關愛,因此便從其氣學角度加以發揮,體出了民胞物與的可貴思想,極大地擴充了孝之內涵。在張載看來,在宇宙萬物之中,天地相互交感而創生萬物,至誠無私的庇養萬物,是乾坤精神的最偉大體現者,堪稱人類萬物共同的父母;人類和萬物則共同稟受天地而生,故自我和他人為相互依存的血脈同胞,萬物和人類是親密無間的友好伙伴。宇宙中一切存在者的親和關系由此建立起來,成為了溝通萬物的基石。這種孝又必然使人們更加關注自然萬物,關注國家蒼生,將自己融入到最廣闊的舞臺之中。
最后,孔子成圣信仰的學說落實到當代社會有利于增強大學生的愛國情懷與凝聚意識。成圣的終極歸宿在于大同社會,而這種大同的第一載體就是國家,所以沿此進路的首要任務便是肩負起對國家的責任。所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只有“國治”才會有后來的“天下平”。鑒于此,弘揚成圣信仰自然應當與大學生對國家的貢獻與責任相關聯,讓學生認識到自己和國家其實是血脈相連的關系,才能自覺地把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統一起來。
總而言之,當今一部分大學生信仰的缺失是造成其問題頻出的總根源。唯有幫助大學生樹立正確信仰,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所面臨的困境。我們認為,孔子思想中“內圣外王”“修齊治平”的成圣理想正是拯救危機的良藥。它以社會之大同、和諧為己任,以“仁禮”為內核,以義利關系的辯證把握為具體規定,有利于大學生找到正確崇高的信仰以及日常言行的準則,對于發揮大學生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作用也無以替代,值得人們深入探索與大力弘揚。
[1]郭奇勇.中國儒學之精神[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
[2]梁啟超.儒家哲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3]雅斯貝爾斯.大哲學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4]彭國翔.作為身心禮儀的實踐[A].中國儒學(第四輯)[C].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5]張載.張載集[M].北京:中華書局,1978.
(責任編輯:胡安波)
In modern times, with the impact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western culture, the lack of faith appear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mainly in the form of hedonism, money worship and spiritual emptiness, which seriously affects the setting up of their right values. The "holiness" philosophy in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focuses on personal moral cultivation, stresses the expansion of benevolence and self-discipline prescribed by etiquette, and meanwhile accurately grasp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ustice and benefit, which plays a very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personal moral faith and the enhancement of moral realm. Therefore, in daily teaching activities, we should make good use of the reasonable elements in traditional holiness philosophy to save the lack of faith of college students.
Confucius; college student belief; moral education
2013-10-15
石敏杰(1990-),女,河南平頂山人,上海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哲學專業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政治哲學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
B222.2
: A
:(2014)01-0020-07
高等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