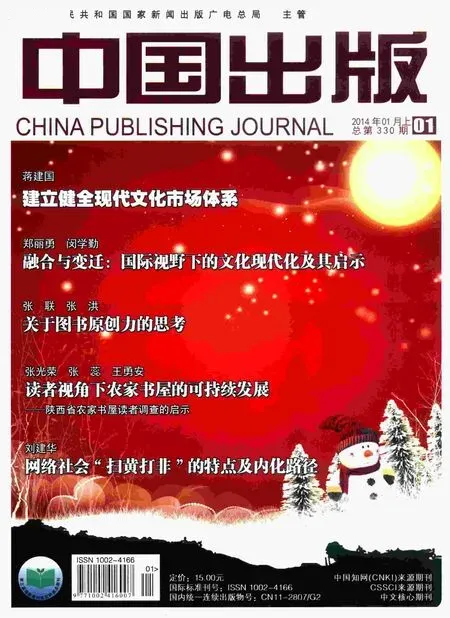關于圖書原創力的思考
文/張 聯 張 洪
出版活動的流程,出版公司的功能,可以組合出長長的一大串,無論怎樣排列,開端肇始的必定是作者、書稿。內容至關重要,作者造就出版,尋找內容不可辯駁地成為圖書出版業的最大前提。原創知識占據最高級知識論地位,超越既有,在沒有前提制約的自由思維驅使下得以完成,是出版業最為青睞的,最應追求的。
一、原創力是作者和出版者立身之本
在出版業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中,從社會效益下的重點書、獲獎書、重印書、編校質量,到規模結構里的圖書品種、造貨碼洋、銷售收入、資產總額,30多年來,諸多板塊、狀況、能力和因素觀照下,研究者和管理者設計執行了多重視角,從不同維度來衡量出版社的高低上下,進而推論某一時段或某一區域整個出版行業的發展趨勢。這中間,微觀上出版企業長期忽略圖書文本質量標準的自我把握,即出版物價值和影響力構成的分析與審查。寫作圖書時的主導性,編印傳播圖書過程的拓展凝聚效果,由于上述影響很難用某種市場要素簡單評價,即無法確定它的價值邊界,從某種程度上講,這種評價是不可能的。而圖書出版物價值的增值的實現是一種將來時,功過往往留待后人評說,“它的質量問題不僅關乎到消費者個體,而且關乎整個國家和民族的文明進程。基于上述理由,圖書出版物的質量問題應該成為對其進行評價的核心內容”。[1]
我們試圖以圖書的原創力來總領圖書價值和使用價值的統一,來體現出版物內容和形式上的創新。圖書原創力是作者和出版方投入到有形圖書的所有勞動,是出版物無形資產的不斷釋放和持續所得。圖書原創力沒有簡單的標準和統一的規格,它是精神產品唯一性的集中體現,它是出版物最核心的驅動程序,它與名頭、價格、篇幅等外在裝飾無涉,更與短暫的喧囂、制造的轟動、權威的推薦保持距離。如果平移現成的出版術語,我們把圖書原創力與經典和古籍可以作類似的比較。借用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的觀點,經典是可以每次重讀都像初讀那樣帶來發現的書。關于古籍,中西方的定義驚人相同:100年前的書。只不過對圖書原創力的追求,是在當下放眼未來,而經典和古籍則是回望已成定論的好書。看似最不起眼的自費書,也往往是靠原創力起家。彌爾頓自費出版了《論出版自由》,惠特曼自己印刷了《草葉集》,盡管收獲的反應幾乎除了冷漠就是嘲笑。
回首歷史,作者和作品的原創力量更加清晰,原創力的有效保護是出版業走向自尊和自重的開始。從18 世紀下半葉開始,歐洲圖書業使作家和知識分子在公眾中贏得了知名度。同時,系列產品的問世,使小說等文學形式成為大眾文化,文學家誕生了,產業化革命也在英國取得了成功。如簡·奧斯丁5 部作品的出版,可以自己掌握職業生涯,為了收益與出版商直接打交道了。作家意識到圖書業的成功,取決于他們的作品和他們的版權,開始尋求分享更大的份額。而在此前的兩個世紀里,“絕大多數作家都囊中羞澀,微薄的收入并非來自于書籍的銷售,而是國家和私人的贊助”。像約翰·彌爾頓在1660年代完成《失樂園》一書后,出版商只付他10 英鎊,他去世時,其妻也只收到8 英鎊而已。[2]19 世紀40年代,為了維護自己的原創利益,狄更斯跨越大西洋到美國加拿大抗議作品被盜版,結果鎩羽而歸。直到19 世紀末,美國通過了《國際版權法》,出現了暢銷書榜,出版業才真正隨之成熟,并迅速迎來了其黃金時代。集中介紹水路系統,以闡明合眾國形成歷史的《美國的河流》書系,歷經近50年,推出了65 種書。
再來看中國近代出版的兩個例子。商務印書館與某些作者“保持良好而長久的維系,其中一些例子更是超乎一般純生意性質的合作”,吸納作者為股東,如嚴復、林紓、王國維等。將部分作者拉入編譯所工作,或者鼓勵編譯所職工從事著述,出版自己的作品。[3]1925年初創辦的北新書局,抓住“大家”,引領“小家”,通過同人和師生之誼,獲得了魯迅、周作人、郁達夫等人的支持,一共出版了魯迅的24 部作品,如《吶喊》《中國小說史略》《苦悶的象征》等,魯迅作品的初版權基本都給了北新書局,北新書局也為魯迅開出了25%的高額版稅,遠遠高于普通作者的15%和周作人、郁達夫的20%。[4]積極有效地傳播新文學的北新書局,20 多年里出版了500 多種文學書籍,留下一批經典之作。
二、原創力是出版業健康成長的不竭動力
尊重作者的原創,是出版真正繁榮的不二法則。2009年1月,二月河提出作家稿費應該免稅,引來各方激烈爭論。立足出版的長遠發展,減少重復浪費,拂去泡沫粉塵,消除盜版、私印,摒棄跟風、模仿,為原創指數高,富于創新的作品付出高額報酬,是完全應當的。“書家以肖似古人不能變體為書奴”,黃賓虹的慨嘆針對書畫界,同樣適宜于圖書的原創與自審。文化多樣性的呈現,民族記憶圖譜的描繪,必然借助于原創圖書品種的大量推出。支持文化多樣性的產品,鼓勵創造,容忍異端,使相關人員享受特殊的財政待遇,如降低增值稅率,給予公共借閱補貼等,也是國際上通行的慣例。在數量標準凌駕于質量標準之上的“過度出版”時代,圖書往往成為一種產品,而不僅僅是書。“出版社的目的不是生產好書,而是復制其他出版社已經取得過的經營上的成功”。[5]
過于糾纏一時一地的利益,不敢決策著眼未來的投入,往往扼殺了個性色彩濃厚的原創作品的問世。德國出版商、卡夫卡研究學者瓦格巴赫的觀點值得深思。“新奇的、瘋狂的、創新的甚至試驗性的作品印數都不高”。“卡夫卡的處女作只印了800 本,布萊希特的只印了600 本。假如當初有人覺得不值得出版他們的著作,那世界會變成什么樣子?”[6]原創力積弱不振,麻痹著出版社的神經,損害著全社會創意階層的培育。呼喚圖書的原創力,不啻于是一劑治療急功近利的猛藥。50年前,賀友直為創作長篇連環畫《山鄉巨變》,到湖南農村體驗生活捕捉感覺,在傳統中尋找語言,從創作實踐中發現自己,畫出了故事情節,畫出了氣息情調,先后推翻兩稿,歷時三四年。圖書的研發、寫作和生產持續三五年,甚至10年20年,本是正常的事情。而如今,這樣的例子幾成空谷足音。
勾勒30年教輔圖書市場的震蕩,從饑渴、成熟走向飽和、衰退、混亂。短視的出版企業“站在出版的立場看教育”,視而不見課程改革,忽視教育產業發展,造成教輔圖書缺失創新,“同質化”現象嚴重等問題,原創力的匱乏使教輔圖書滯后于教育發展。[7]1981年葉圣陶撰文《我呼吁》,呼吁教育者、家長、出版社,切實減輕學生負擔。出版社不要再印行高考試題解答、各科輔導、假期作業之類。現在的情形早已不知比當年厲害了多少倍。兒童閱讀領域的暢銷書火拼,經常采取的捷徑也是舍棄沉潛涵詠的原創,“作者追求‘速食主義’,快速生產作品,快速賺取稿費;家長主張實用主義,希望孩子看書后向天才更近一步”。[8]改革開放30年間,商務、外研、上海外語教育、上海譯文四家主要外語辭書編纂機構直接或間接引進國外品牌辭書所占出版總量的比例,前兩家超出50%,后兩家在40%上下。而自創辭書品牌比例最高者不過剛剛超出10%。超過80%的出版社參與外語辭書出版,粗制濫造屢見不鮮,距離“辭書強國”的目標更是相差甚遠。[9]德國作家格林兄弟的《灰姑娘》《白雪公主》等童話故事,大家耳熟能詳。作為語言學家的兄弟兩人,年過半百后著手編輯《德語大辭典》,創立新體例,收詞跨越300 多年。20 多年后兩人去世,一批專家遵循先賢繼續編纂,即使“二戰”后的冷戰期間,東西德學者都一直合作不輟,這部80 卷的詞典總共進行了122年,才大功告成。不重視原創,不能不說是放棄優勢和責任的輕率之舉。至于投身童書和教輔的出版社比例,肯定比辭書還要高,攤子足夠大了,重量級有影響的原創產品就難免相形見絀、難覓蹤影了。
佐證圖書原創力內涵的最佳釋例是文學翻譯。“只有完美的原著,而往往沒有完美的譯作”。經過一定的周期,嚴肅認真的重譯是不可或缺的。如孫致禮重譯《傲慢與偏見》時,曾列舉了四個方面,表明自己譯本超越了三十幾年前王科一的譯本。十幾年時間里,他又先后五次“手術”,不斷修訂自我。[10]像波斯名著《魯拜集》,漢語譯者有胡適、郭沫若、朱湘、李霽野、聞一多、林語堂、伍蠡甫、王蒙、黃克孫、唐德剛等十幾位,遍及海峽兩岸和海外華人圈。只有完美的原作,而往往沒有完美的譯作。在紐約公共圖書館一間特別收藏室,典藏著《魯拜集》500 多種版本,讓我們為人類經典名著的不竭原創力而慨嘆不已。
圖書出版的文化使命和歷史責任,首先取決于作者和出版者的自我承擔,是否敢于解釋難以解釋的事情,是否發布沉潛深思的心得之作,是否嘗試傳播某種不易言傳的東西,原創力的起點正在于此。當然,外界牽引可以有助于這種正向成長,如五六年前開始啟動的“三個一百”原創圖書出版工程等。終究,是否自我創造自我更新,是否有意義有價值,必須從自身的自覺叩問開始,它決定著出版業到底能健康地走多遠。高揚原創力的主旋律,是去除雜音的利器,是迎接出版強國的先聲。
[1]徐小傑.圖書出版產業評價體系[M].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1:64-65
[2][英]約翰·霍金斯.創意經濟——如何點石成金[M].洪慶福等譯.上海三聯書店,2006:65
[3]李家駒.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273
[4]陳樹萍.北新書局與中國現代文學[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245
[5][美]阿爾伯特·N.格萊科等.21 世紀出版業的文化與貿易[M].丁以繡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199
[6][美]安德烈·希夫林.出版業[M].白希峰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5:132
[7]齊峰.縱論出版產業的科學發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177-178
[8]岳月.中德少兒出版之比較,海外新聞出版實錄2010[C].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1:42
[9]魏向清等.中國外語類辭書編纂出版30年(1978-2008):回顧與反思[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148、267、355
[10]楊絳等,鄭魯南.一本書和一個世界[C].北京:昆侖出版社,2005: 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