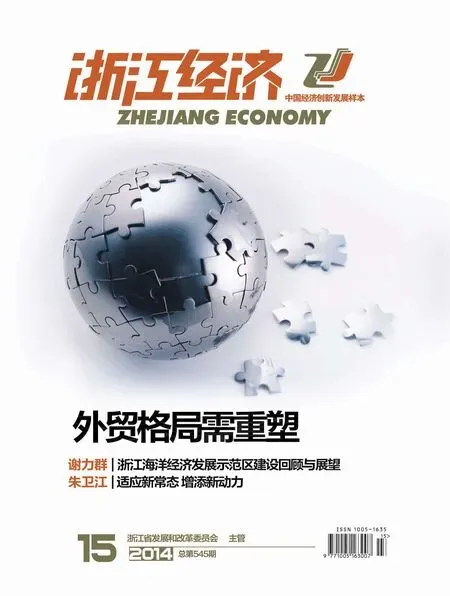從經濟史看房地產十年
李明艷
從經濟史看房地產十年
李明艷
2014年2月,杭州成為最早開啟房價下跌的城市,其高達12萬套的商品房庫存成為全國媒體關注的焦點。4月,由《中國經濟周刊》、中國經濟研究院聯合研究并發布的《我國23個省份“土地財政依賴度”排名報告》顯示,2012年底浙江省、市、縣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債務中,承諾以土地出讓收入為償債來源的債務余額為2739.44億元,占省市縣三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債務余額4133.91億元的66.27%,在所有調查省份中位居第一,比廣東省(26.99%)高一倍多。因此,如果說2003年到2013年是中國房地產行業的黃金十年,對浙江而言則可能是瘋狂的十年。但火爆的土地和房地產市場沒能為浙江經濟快速發展注入動力,相反則導致大量資本撤離了實體經濟,產業“空心化”的現象十分嚴重。
巧合的是,經濟史學家諾斯似乎早就注意到了土地和房地產價格上漲在經濟結構演變中的重要地位和影響。他在《經濟史中的結構和變革》一書中已經為我們描繪好了我們看到的過去十年的圖景:
“為簡明起見,讓我們來描述在一個政治經濟單位里發生的變化。這個單位土地固定,沒有外部貿易(或生產要素的流動),經歷了人口增長。直接后果是食品(和原料)價格上升,因為短期供給曲線完全沒有彈性……工人的實際收入下降,因為他的工資買到的食物減少了;地主的實際收入增加了,因為他出售的產品,雖然數量相同但得到的收入卻多了。由于擁有土地可能盈利的能力提高,土地的價格被哄抬上去。投資者將提高資本對土地的比率,因為運用資本越多(改變排水系統、增加灌溉等),從一定數量的土地上得到的產量越多,結果便越有利可圖……”“工人(特別是城市工人)可能鬧事以抗議食物成本上漲,或者呼吁政府限價以阻止漲價……在對土地沒有獨占產權的情況下……農民會請求國家改變產權,以便他們能得到土地產權的獨占收益,但如果把以前使用土地的人排除在外,他們將會反對產權的這種改革”。
由于諾斯主要考慮的是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農業還是主要的產業,灌溉、水利還是主要的基礎設施投資。如果我們把諾斯討論的農業換成工業(制造業),農產品換成工業產品,則恰恰與我們過去十年看到的景象一致。同樣的故事還在我們眼前上演,只不過工業取代了早期的農業。更有趣的是,不知道諾斯推演的產權和制度改革是否會在今天的中國展開。
回顧過去十年和諾斯的例子,我們應該認真反思土地和房地產的飛速擴張,特別是重新認識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關系。首先,城市化很難成為經濟發展的基礎力量,工業化才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之源。一個城市特別是人口規模比較大的城市一定是以實體經濟為依托的,是工業和服務業、高技能人員、普通產業工人以及服務業從業者的有機整體。房地產開發建設只能輔助要素的集聚和基礎設施的完善,而不能成為經濟活動的主體。其次,快速的房地產投資和基礎設施投資非但不能幫助反而會擠出和傷害實體經濟。政府希望通過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和快速的房地產開發來改善城市的生活和生產條件,但這樣做的后果通常是“過尤不及”。在資金、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有限的條件下,房地產的擴張會推升要素成本和生活成本,給制造企業的生存、產品創新研發以及居民幸福感帶來不利影響。基礎設施的投資也應該尊重企業和居民的意愿,不能通過抬高地價,提升房價讓生產者和消費者買單。
浙江成為土地和房價增長的區域中心,一定程度上是過去收入財富積累的負面作用,可以說是“先發劣勢”。但房地產的泡沫式繁榮與實體經濟的迅速衰退表明,城市化不能成為經濟發展的基礎力量,其要素集聚的功能是以產業活力為基礎的,單純依靠城市化不能促進產業結構升級,也就不能實現財富的再創造,只有回歸工業化和產業內部才能從根本上實現轉型升級。
供稿: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區域經濟所
房地產的泡沫式繁榮與實體經濟的迅速衰退表明,城市化不能成為經濟發展的基礎力量,只有回歸工業化和產業內部才能從根本上實現轉型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