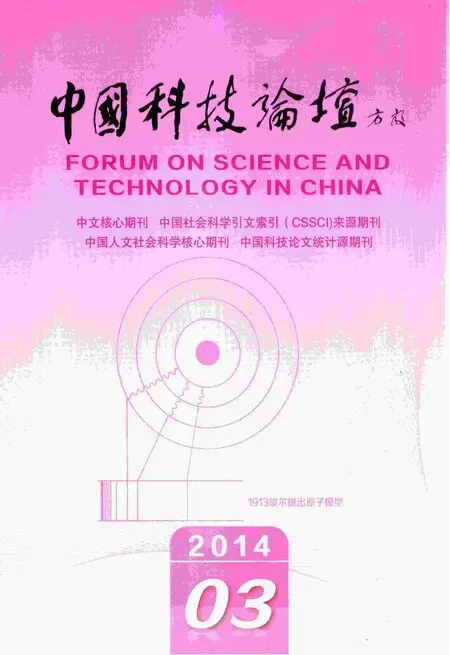面向公眾的科學(xué)傳播研究:一個(gè)綜述
杜志剛,孫 鈺
(天津商業(yè)大學(xué)公共管理學(xué)院,天津 300134)
隨著科學(xué)的進(jìn)步和信息傳播技術(shù)的發(fā)展,科學(xué)技術(shù)日益更具公共性和社會(huì)性、更具新聞報(bào)道價(jià)值也更具爭(zhēng)議性。關(guān)于健康、能源、環(huán)境、生物技術(shù)以及其他領(lǐng)域內(nèi)的科學(xué)發(fā)現(xiàn)的新聞不僅僅是它的潛在發(fā)展進(jìn)程,更重要的是他們經(jīng)常導(dǎo)致的短期內(nèi)的大事件和長(zhǎng)期內(nèi)的道德困境。當(dāng)前,國(guó)內(nèi)外科學(xué)傳播研究者圍繞面向公眾的科學(xué)傳播理論研究做了大量工作,因此,有必要以公眾為中心,對(duì)此進(jìn)行分析研究,以便總結(jié)出科學(xué)傳播研究的一般研究框架、重點(diǎn)內(nèi)容和研究范式,以便開展原創(chuàng)性和基于中國(guó)情境背景的研究。
1 科學(xué)傳播的主體
1.1 科學(xué)家與科學(xué)共同體主體
由于社會(huì)分工和專業(yè)性優(yōu)勢(shì),科學(xué)家始終是科學(xué)傳播中主要的信息源,信息量的方向主要仍然是從科學(xué)家(科學(xué)共同體)流向公眾的[1]。Tsfati Y.等發(fā)現(xiàn)科學(xué)家如果相信媒介有足夠的影響力,就會(huì)提升自己尋求媒介報(bào)道的動(dòng)機(jī)和努力,這反過(guò)來(lái)又導(dǎo)致獲得更多的媒介暴露[2]。在新媒介的賦權(quán)下,科學(xué)家擺脫傳統(tǒng)媒體的束縛,直接通過(guò)博客和維基、共享網(wǎng)站或?qū)I(yè)社區(qū)發(fā)表信息[3-4]。在公民制造內(nèi)容時(shí)代,科學(xué)家被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較大的社會(huì)責(zé)任[3,5],并應(yīng)當(dāng)表現(xiàn)較高的社會(huì)良知[6]。Nisbet 和Moony 認(rèn)為,科學(xué)家需要有策略地向公眾推介自己的科學(xué)工作,從而贏得公眾支持一些爭(zhēng)議性科學(xué)研究并認(rèn)同自己的科研思想[7]。科學(xué)家還應(yīng)當(dāng)具有較強(qiáng)的社交技能知識(shí),在通過(guò)各種媒介與公眾溝通時(shí)充分做到傳播的平衡性、開放性和透明化。
科學(xué)家的媒介素養(yǎng)是一個(gè)重要變量。在歐美等一些國(guó)家,政府或非政府組織制定政策并建立許多培訓(xùn)機(jī)構(gòu)來(lái)訓(xùn)練和指導(dǎo)科學(xué)家、工程師提升與公眾溝通的技巧和能力,這對(duì)社會(huì)各成員均大有好處[8]。近年來(lái),由于新媒體工具的普及,對(duì)科學(xué)家的媒介素養(yǎng),特別是利用社會(huì)化媒介與公眾溝通的動(dòng)機(jī)、能力和特征進(jìn)行了一些理論研究或者開發(fā)測(cè)量量表[9]。
1.2 媒介主體
人們可以通過(guò)不同媒介獲得科學(xué)技術(shù)的相關(guān)知識(shí)并形成觀點(diǎn)[10]。社會(huì)化媒體提供了迅捷和非正式的方式的傳播渠道,以便科學(xué)家、媒體從業(yè)者、其他利益相關(guān)者以及公眾生產(chǎn)和傳播科學(xué)信息。這不僅使得信息海量化,同時(shí),人們共享信息的方式也發(fā)生急劇變化,博客和維基、視頻共享網(wǎng)站等成為知識(shí)共享的新場(chǎng)所[11-12]。例如,只有12%的美國(guó)人關(guān)注由傳統(tǒng)印刷類報(bào)紙期刊提供的網(wǎng)絡(luò)信息,而大約半數(shù)以上的美國(guó)人依賴于非傳統(tǒng)的、產(chǎn)生于網(wǎng)絡(luò)上的信息來(lái)源[13]。來(lái)自《Science》上的研究表明,上網(wǎng)時(shí)間長(zhǎng)短是與對(duì)科學(xué)的積極態(tài)度成正相關(guān)的,即上網(wǎng)時(shí)間越長(zhǎng),對(duì)科學(xué)越持正面態(tài)度。例如,經(jīng)常上網(wǎng)者更可能在一些調(diào)查中表明他們支持基礎(chǔ)科學(xué)研究,即使他們自己沒有什么好處[13]。
1.3 政府主體
很多國(guó)家都明確把提高本國(guó)國(guó)民的科學(xué)素質(zhì)視為政府的戰(zhàn)略目標(biāo)。在各國(guó)推動(dòng)國(guó)民科學(xué)素質(zhì)的建設(shè)中,美國(guó)“2061”計(jì)劃具有很大的影響力,美國(guó)公民科學(xué)素質(zhì)培養(yǎng)擬“從娃娃抓起”,從系統(tǒng)正規(guī)的學(xué)校教育入手,有可行性很強(qiáng)的具體的實(shí)施方案和評(píng)價(jià)體系,對(duì)世界范圍內(nèi)基礎(chǔ)科學(xué)教育課程和教學(xué)改革都有指導(dǎo)意義。中國(guó)也有類似的“全民科學(xué)素質(zhì)行動(dòng)計(jì)劃”(簡(jiǎn)稱2049 行動(dòng)計(jì)劃),該計(jì)劃擬“面向全民”,充分動(dòng)員和發(fā)揮從政府、企業(yè)、非政府組織到社區(qū)的全社會(huì)的作用,努力實(shí)現(xiàn)“全體公民人人具備科學(xué)素質(zhì)”。
基于證據(jù)的政策制定已經(jīng)在不同層級(jí)政府管理以及不同科學(xué)領(lǐng)域(例如醫(yī)學(xué)、基因技術(shù)等)得到應(yīng)用和推廣。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科技發(fā)達(dá)國(guó)家在重大科研項(xiàng)目建設(shè)體系中常常一開始就系統(tǒng)性、有機(jī)性的納入科學(xué)傳播模塊,從而促進(jìn)社會(huì)公眾對(duì)科研項(xiàng)目的了解和認(rèn)同。例如,歐盟框架計(jì)劃主要通過(guò)兩種途徑來(lái)增進(jìn)基礎(chǔ)研究與科學(xué)傳播的結(jié)合:設(shè)置獨(dú)立的科學(xué)傳播板塊和在非科學(xué)傳播項(xiàng)目中嵌入科學(xué)傳播內(nèi)容。
政府機(jī)構(gòu)與官員的媒介素養(yǎng)和科學(xué)素養(yǎng)也是影響科學(xué)傳播效果的重要因素。政府管理機(jī)構(gòu)的媒介素養(yǎng)包括“管理者”素養(yǎng),通過(guò)制定傳播政策和提供傳播條件保障信息傳播渠道的通暢和公開,也包括應(yīng)對(duì)公共危機(jī)事件時(shí)的媒介使用和媒介管理能力,而科學(xué)素養(yǎng)則包括基本的科學(xué)知識(shí)、科學(xué)精神、協(xié)調(diào)動(dòng)員科學(xué)家以及科學(xué)共同體等方面的能力。
1.4 社會(huì)公眾主體
在科學(xué)傳播理論研究中,公眾的人口學(xué)特征,例如性別、年齡、職業(yè)、收入、宗教信仰和教育水平等,都可能影響面向公眾的科學(xué)傳播的效果。性別因素方面,在對(duì)科學(xué)技術(shù)和環(huán)境風(fēng)險(xiǎn)的感知方面,女性更敏感,更容易高估風(fēng)險(xiǎn)水平[14]。在基因技術(shù)上,性別因素差異非常顯著,男性對(duì)基因技術(shù)關(guān)注度不高,在評(píng)估基因技術(shù)風(fēng)險(xiǎn)時(shí)更容易看低風(fēng)險(xiǎn)而秉持積極態(tài)度,對(duì)基因技術(shù)產(chǎn)品也表現(xiàn)出更高接受水平[15-16]。在科學(xué)教育因素變量上,Ho.S.S.等的研究發(fā)現(xiàn),較高的科學(xué)知識(shí)預(yù)示著對(duì)干細(xì)胞研究的更積極的態(tài)度,并表現(xiàn)出對(duì)科學(xué)權(quán)威的順從,而對(duì)那些較低宗教虔誠(chéng),更多政治自由性的人,也是如此[17]。而對(duì)比其他大學(xué)生,科學(xué)專業(yè)相關(guān)的學(xué)生表現(xiàn)出對(duì)科學(xué)的更積極態(tài)度。這些結(jié)果表明,科學(xué)教育在對(duì)提高科學(xué)技術(shù)的認(rèn)識(shí)和信心上確實(shí)有效。國(guó)別、職業(yè)或立場(chǎng)因素也會(huì)影響公眾對(duì)科學(xué)技術(shù)的感知,例如,對(duì)于轉(zhuǎn)基因作物的接受上,美國(guó)公眾相對(duì)歐洲公眾要更為積極,而作為生產(chǎn)者的農(nóng)民的接受意愿和作為消費(fèi)者的接受之間也存在顯著差異[15,16,18,19]。
媒介素養(yǎng)和科學(xué)素養(yǎng)也是重要的影響變量。與科學(xué)傳播有關(guān)的媒介素養(yǎng)是公眾了解大眾媒體對(duì)于科學(xué)訊息的篩選、包裝、選擇與組合的方式的能力。科學(xué)素養(yǎng)方面,Kolst 提出了八項(xiàng)要素,在提升公眾科學(xué)素養(yǎng)方面很有借鑒和實(shí)踐應(yīng)用價(jià)值。在實(shí)證研究中,一個(gè)總體、寬泛的科學(xué)素養(yǎng)變量量表并不具有普適性,人們?cè)诓煌瑢W(xué)科領(lǐng)域上的科學(xué)素養(yǎng)往往存在差異,因此,學(xué)者們?cè)诓煌茖W(xué)領(lǐng)域開發(fā)了科學(xué)素養(yǎng)量表,例如基因能力評(píng)估工具、干細(xì)胞知識(shí)量表[19-20]等。
2 科學(xué)傳播互動(dòng)情境因素
為了達(dá)到有效的公共對(duì)話的目的,科學(xué)家以及更廣泛意義上的科學(xué)共同體已經(jīng)在日益開展多形式的科學(xué)傳播活動(dòng)。借助社會(huì)化媒介,科學(xué)傳播各個(gè)主體之間的互動(dòng)可以在不同場(chǎng)所和空間中進(jìn)行。
2.1 網(wǎng)絡(luò)空間
數(shù)字化媒體已經(jīng)改變了科學(xué)傳播的社會(huì)化活動(dòng)。他們擴(kuò)展了無(wú)數(shù)渠道,以便科學(xué)家、媒體從業(yè)者、其他利益相關(guān)者以及公眾傳播科學(xué)信息。除了傳統(tǒng)的BBS 和門戶網(wǎng)站,web2.0 時(shí)代的專業(yè)社區(qū)、興趣社區(qū)甚至視頻網(wǎng)站都正成為共享科學(xué)知識(shí)的場(chǎng)所,人們通過(guò)博客和維基、視頻共享網(wǎng)站合作創(chuàng)造、討論相關(guān)主題。而不斷涌現(xiàn)的新的互動(dòng)媒介,例如微博、微信等在科學(xué)傳播上的碎片化、去中心化、交互性對(duì)有效傳播科學(xué)、破除謠言有著重要應(yīng)用和研究?jī)r(jià)值[21]。
2.2 科學(xué)咖啡屋
科學(xué)咖啡屋是一種線下社會(huì)化媒介。科學(xué)咖啡屋于1997年發(fā)源于英國(guó)和法國(guó),其特點(diǎn)在于科學(xué)議題的討論和質(zhì)疑是以一種開放式的對(duì)話情境中進(jìn)行的,主要討論的也是科學(xué)研究帶來(lái)的后果以及應(yīng)該如何開展科學(xué)活動(dòng)。中國(guó)和日本都是2005年引入[22]。科學(xué)咖啡屋的組織者,包括大學(xué)、研究所、非營(yíng)利組織、本地政府、書商、個(gè)人以及志愿者團(tuán)體[23]。有研究表明,有五種因素使得科學(xué)家不愿意參與咖啡屋方式對(duì)話:①麻煩或費(fèi)時(shí);②成為科學(xué)代言人的壓力;③超出自身研究領(lǐng)域;④個(gè)人沒什么直接收益;⑤對(duì)建立起有效的公眾對(duì)話模式心存憂慮[23]。
2.3 共識(shí)會(huì)議
共識(shí)會(huì)議也是一種典型的線下社會(huì)互動(dòng)場(chǎng)景。共識(shí)會(huì)議使得公眾與科學(xué)共同體、政府之間就科學(xué)技術(shù)問題建立平等對(duì)話關(guān)系成為可能。在這種背景下,共識(shí)會(huì)議作為公眾參與技術(shù)評(píng)估的一種新形式,于20 世紀(jì)80年代中期在丹麥誕生。2008年,我國(guó)也在北京召開了以“轉(zhuǎn)基因食品”為議題的第一次試行性的共識(shí)會(huì)議。劉兵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辯證看待共識(shí)會(huì)議,一方面,“共識(shí)”的形成不是統(tǒng)一意見,而是對(duì)公眾意見的凝練和提升;另一方面,應(yīng)尊重并強(qiáng)調(diào)持有不同視角和立場(chǎng)的公眾的“非共識(shí)”意見[24]。
2.4 科學(xué)博物館與網(wǎng)絡(luò)博物館
科學(xué)博物館是傳統(tǒng)科普的一種重要方式,近年來(lái)在中國(guó)得到廣泛發(fā)展。科技館傳播在面向公眾的科學(xué)傳播中有新的內(nèi)涵和要求,強(qiáng)調(diào)展覽空間和展品的設(shè)計(jì)需要由受眾的角度出發(fā),基于受眾的情感體驗(yàn)和心理訴求,目的是傳播科學(xué)知識(shí)和激發(fā)興趣與教育。伍新春和季嬌通過(guò)對(duì)北京育才中學(xué)開設(shè)在北京自然博物館的生物課進(jìn)行了跟蹤研究,發(fā)現(xiàn)學(xué)生對(duì)科學(xué)家的消極刻板印象有所降低,同時(shí)對(duì)從事科學(xué)研究職業(yè)有了更清晰的認(rèn)識(shí)和了解,這證明了科學(xué)博物館的非專業(yè)性教育作用。博物館還可與大眾傳媒聯(lián)合進(jìn)行科學(xué)傳播,例如,美國(guó)雙子城公共電視臺(tái)與科技館合作制成科教專題片,在美國(guó)國(guó)家電視臺(tái)和學(xué)習(xí)網(wǎng)絡(luò)上播放,幫助孩子們認(rèn)識(shí)科學(xué),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博物館結(jié)合社會(huì)化媒介的一個(gè)重要應(yīng)用是網(wǎng)絡(luò)博物館。國(guó)外許多先進(jìn)博物館在網(wǎng)絡(luò)化技術(shù)應(yīng)用方面,已經(jīng)進(jìn)行了較多嘗試,歐美很多國(guó)家的博物館已經(jīng)有了網(wǎng)絡(luò)博物館版本。網(wǎng)絡(luò)博物館主要傳播科學(xué)知識(shí)、科學(xué)理論、科學(xué)研究過(guò)程、科學(xué)工作心得、科學(xué)研究之社會(huì)意義等類型內(nèi)容,此外,基于智能移動(dòng)終端的博物館APP 應(yīng)用也已經(jīng)通過(guò)個(gè)人手機(jī)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中進(jìn)行傳播。然而,中國(guó)科技類博物館網(wǎng)站在內(nèi)容的豐富程度和科學(xué)傳播內(nèi)容上離美國(guó)的還有較大差異。
3 公共熱點(diǎn)事件科學(xué)傳播
公共熱點(diǎn)事件(Hot-issue Publics)一般是在一個(gè)觸發(fā)事件或是媒介報(bào)道集中引起對(duì)某一問題的關(guān)注后才成其為公共事件,當(dāng)媒介關(guān)注逐漸減弱后,公告熱點(diǎn)事件也會(huì)逐漸消散。公共熱點(diǎn)事件圍繞某單一主題進(jìn)行大量的、活躍的傳播,絕大多數(shù)社會(huì)人口卷入其中并得到極度廣泛的媒介報(bào)道。和科學(xué)技術(shù)有關(guān)的公共熱點(diǎn)事件,通常會(huì)形成社會(huì)性科學(xué)議題(Socio-Scientific Issue,SSI)[15]。這種因?yàn)榭茖W(xué)及科技的進(jìn)步所應(yīng)運(yùn)而生的SSI,具有極為復(fù)雜的屬性,雖以科學(xué)及科技為主體,但實(shí)則牽動(dòng)著社會(huì)、政治及文化等因素,并造成巨大的社會(huì)影響。原本這些科學(xué)議題的社會(huì)化爭(zhēng)議,理應(yīng)是一般民眾借以了解科學(xué)及科技發(fā)展的最佳素材,也是協(xié)助社會(huì)公眾參與科學(xué)技術(shù)進(jìn)程的重要憑借[11]。
SSI 通常有兩類,一類是重大科學(xué)(科技)事件,通常是主動(dòng)性的、可控的、有計(jì)劃的,如中國(guó)的神舟飛天、全球變暖、中國(guó)首艘航空母艦等議題。這類事件通常是政府部門或科技協(xié)會(huì)主導(dǎo)組織的科普和宣傳活動(dòng),通常較少分歧和爭(zhēng)議,因此科學(xué)傳播的宗旨在教育和激發(fā)公眾尤其是青少年對(duì)科學(xué)的興趣和熱情。這方面的理論研究主要集中在于國(guó)家競(jìng)爭(zhēng),例如,不同國(guó)家碳排放量指標(biāo)的爭(zhēng)議、尖端技術(shù)所引發(fā)的國(guó)家實(shí)力和科技專利等宏觀、戰(zhàn)略、法律方面的爭(zhēng)端,對(duì)公眾的日常生活影響不甚緊密,相關(guān)的理論研究也較少。另一類是突發(fā)性科學(xué)事件,這類事件通常由某類生活中的事件引起,牽涉到相關(guān)的科學(xué)議題,例如,由黃金大米引發(fā)的轉(zhuǎn)基因事件,由地震引起的搶鹽事件、由SARS 引起的衛(wèi)生事件等,這類事件通常存在嚴(yán)重的對(duì)立和矛盾,并有可能引起群體性事件。這類事件政府通常更多是被動(dòng)應(yīng)對(duì)、難以預(yù)先計(jì)劃,需要協(xié)調(diào)媒體、公眾和其他相關(guān)主體關(guān)系,政府的主要工作可能是危機(jī)管理,而嵌入事件中的科學(xué)傳播則可成為應(yīng)急科普傳播或危機(jī)科普傳播。這方面的研究也較多,主要的研究集中在危機(jī)傳播上,通過(guò)新媒介所帶來(lái)的媒介融合傳播模式,政府發(fā)揮社會(huì)化媒介的及時(shí)性和互動(dòng)性以及大眾傳播媒介的可靠性、權(quán)威性和全面性特點(diǎn)進(jìn)行危機(jī)溝通和社會(huì)動(dòng)員,從而解決危機(jī)。
因?yàn)槊嫦蚬姷目茖W(xué)傳播,領(lǐng)域廣泛而又常常富有爭(zhēng)議性,即很少有明確定論,因此,如何考察公眾科學(xué)傳播的效果,也是困擾科學(xué)傳播研究者的一大問題。總體而言,科學(xué)傳播的效果研究主要有兩個(gè)維度,其一是態(tài)度上的,包括興趣、理解和贊同;其二是行為上的,包括參與和互動(dòng)。現(xiàn)有研究中,“支持”和“接受”是較為常見的效果變量。Hallman.等的研究發(fā)現(xiàn),公眾會(huì)對(duì)基因技術(shù)進(jìn)行風(fēng)險(xiǎn)-收益評(píng)估,然后決定是否支持該技術(shù)[15],而Connor 和Siegrist 則考察了公眾轉(zhuǎn)基因食品和轉(zhuǎn)基因藥品的不同接受心理[16]。此外,“信任”因素也是評(píng)估傳播效果的常用變量。Paul和Barbara 考察了人們對(duì)環(huán)境科學(xué)信息不同來(lái)源的信任性[25];而Dijkstra 和Gutteling 發(fā)現(xiàn)公開性和透明性是獲得公眾信任的兩個(gè)基本要素[26];Bauer 等則發(fā)現(xiàn)參與和商議是重新獲得信任的重要方式[27]。也有學(xué)者考察了其他效果變量,比較重要的就是Ronald.和Yaros 研究中公眾對(duì)科學(xué)的“興趣”和“理解”[28]。
框架理論是科學(xué)傳播實(shí)證研究中應(yīng)用最為廣泛的理論之一,霍夫曼發(fā)現(xiàn)了媒介報(bào)道的一些框架,科學(xué)傳播研究者也已發(fā)現(xiàn)了大量可再現(xiàn)的框架影響公眾和科學(xué)之間的交流,科學(xué)議題的信息框架確實(shí)對(duì)公眾的理解和認(rèn)知產(chǎn)生影響[29-30]。Donk A.等研究了新聞報(bào)道的正面和負(fù)面框架,他對(duì)德國(guó)2000—2008年期間9 種印刷媒介對(duì)納米技術(shù)的報(bào)道框架進(jìn)行了一個(gè)內(nèi)容分析,發(fā)現(xiàn)德國(guó)媒體納米技術(shù)主流媒體報(bào)道框架基本都是正面的,特別強(qiáng)調(diào)了納米技術(shù)帶來(lái)的醫(yī)療和經(jīng)濟(jì)價(jià)值,這個(gè)結(jié)論在其他國(guó)際媒體報(bào)道的實(shí)際情況也發(fā)現(xiàn)如此[31]。Lilla Vicsek.則考察了成本和收益框架,他考察了受試對(duì)于媒介報(bào)道中所提及的干細(xì)胞研究/治療的成本和收益進(jìn)行了成本和收益的評(píng)估,并通過(guò)對(duì)匈牙利5 種主流報(bào)紙的內(nèi)容分析和一個(gè)焦點(diǎn)小組的訪談研究,發(fā)現(xiàn)受試在評(píng)估該收益和成本時(shí),大多是順應(yīng)著媒體在該領(lǐng)域內(nèi)的處于優(yōu)勢(shì)的議程框架[28]。Craig O.Stewart 重點(diǎn)考察了科學(xué)進(jìn)展、經(jīng)濟(jì)前景和政治沖突這三種新聞框架,他對(duì)這三類新聞框架效果、科學(xué)背景以及干細(xì)胞來(lái)源對(duì)干細(xì)胞研究的有用性、可信性和倫理歸因的影響做了研究,雖然并沒有得出明顯影響倫理道德感知的框架效應(yīng),但是科學(xué)專業(yè)學(xué)術(shù)比非科學(xué)專業(yè)學(xué)生更容易感知到倫理性[23]。情緒往往也是一種影響信息決策的常用框架,Z.Janet 和LeeAnn 發(fā)現(xiàn)人們?cè)谡妗⒎e極的感情框架下,傾向于減少信息搜尋,而在負(fù)面、消極的感情框架下,傾向于更多地進(jìn)行信息搜尋。
4 小結(jié)
4.1 科學(xué)傳播實(shí)證研究的總體框架提出
新媒體的興起和媒介融合傳播的發(fā)展,使得科學(xué)、公眾與媒體之間的關(guān)系日益變得復(fù)雜。從相關(guān)文獻(xiàn)的整理分析來(lái)看,學(xué)者們對(duì)于面向公眾的科學(xué)傳播的研究取得了一些共識(shí),但也存在分歧。概括來(lái)說(shuō),科學(xué)傳播的一般模式,是從傳播的關(guān)鍵主體(包括科學(xué)主體、政府主體和媒介主體)出發(fā),通過(guò)不同互動(dòng)情境(如博物館、科學(xué)咖啡屋或是危機(jī)事件),設(shè)計(jì)適當(dāng)?shù)男畔⒖蚣埽槍?duì)社會(huì)公眾的特質(zhì)開展科學(xué)傳播活動(dòng),從而達(dá)到良好傳播效果,這個(gè)過(guò)程就構(gòu)成了完整的面向公眾的科學(xué)傳播機(jī)制,如圖1 所示。不同學(xué)者的研究雖然較為零散,但基本內(nèi)容和研究視角基本上都是圍繞如圖1 所示框架進(jìn)行。因此,圖1 實(shí)質(zhì)上也指出了當(dāng)前科學(xué)傳播研究的主要內(nèi)容、主要研究視角和研究框架,這些主要內(nèi)容之間也構(gòu)成了一個(gè)面向公眾的、以公眾為中心的科學(xué)傳播機(jī)制。
4.2 現(xiàn)有研究的局限和未來(lái)研究趨勢(shì)
從現(xiàn)有研究來(lái)看,有關(guān)科學(xué)傳播的研究還存在一些不足和有待完善的空白。

圖1 面向公眾的科學(xué)傳播研究框架
(1)由于研究視角和方法的差異,學(xué)者們關(guān)于影響公眾理解和參與科學(xué)傳播的主要變量及其維度和測(cè)量方法存在差異,對(duì)科學(xué)傳播的效果評(píng)估更是沒有統(tǒng)一,相關(guān)研究也顯得非常零散和不夠系統(tǒng)。最重要的是,學(xué)者們雖然確認(rèn)了一些有用的影響因素,但是尚無(wú)人提出較清晰的面向公眾科學(xué)傳播的影響機(jī)制。本文分析總結(jié)現(xiàn)有研究,提出了一個(gè)面向公眾的科學(xué)傳播內(nèi)容框架,為后續(xù)研究提供了綱領(lǐng)性的指導(dǎo)。
(2)當(dāng)前,關(guān)于公眾理解和參與科學(xué)傳播的實(shí)證研究基本上是國(guó)外學(xué)者基于國(guó)外樣本所進(jìn)行的,國(guó)內(nèi)的相關(guān)實(shí)證研究還非常少見,因此缺乏符合中國(guó)情況的科學(xué)傳播實(shí)證研究,國(guó)外現(xiàn)有研究結(jié)論是否符合面向中國(guó)公眾的科學(xué)傳播還沒有得到驗(yàn)證,因此后續(xù)需要中國(guó)學(xué)者結(jié)合中國(guó)公眾實(shí)際特點(diǎn)和認(rèn)知模式特征的開展原創(chuàng)性和富有中國(guó)特色的理論研究。
(3)當(dāng)前的研究仍然是基于大量的文本信息,這也是報(bào)紙媒介和網(wǎng)絡(luò)社區(qū)上的文字信息容易被采用作為主要媒介對(duì)象和信息來(lái)源的重要原因,而電視、網(wǎng)絡(luò)等影響力更廣的媒介較難以作為研究對(duì)象,主要是和技術(shù)能力有關(guān)。可以相信,伴隨著大數(shù)據(jù)時(shí)代和數(shù)據(jù)深挖掘方法的發(fā)展,來(lái)自視頻、音頻等巨量的非結(jié)構(gòu)化信息,將成為未來(lái)研究的主要信息源。
[1]Kouper Inna.Science blogs and 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practices,challenges,and opportunities[J].Journa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2010,9(1):1-10.
[2]Tsfati Y,Cohen J,Gunther A C.The influence of presumed media influence on news about science and scientists[J].Science Communication,2011,33(2):143-166.
[3]Chai S,Kim M.What makes bloggers share knowledge?An investigation on the role of trust[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2010,30(5):408-415.
[4]Joachim Allgaier.On the shoulders of YouTube science in music Videos[J].Science Communication,2013,35(2):266-275.
[5]劉兵.科學(xué)家的社會(huì)責(zé)任感與面向科學(xué)家的科學(xué)傳播[J].科學(xué)對(duì)社會(huì)的影響,2011,1(1).
[6]Tsse S E.Aiming for social or political robustness?Media strategies among climate scientists[J].Science Communication,2013,35(1):32-55.
[7]Nisbet M C,Scheufele D A.The future of public engagement[J].The Scientist,2013,21.39-44
[8]Besley J C,Tanner A H.What science communication scholars think about training scientists to communicate[J].Science Communication,2011,33(2):239-263.
[9]Baram-Tsabari A,Lewenstein B V.An instrument for assessing scientists'written skills in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J].Science Communication,2013,35(1):56-85.
[10]Brossard D,Nisbet M C.Deference to scientific authority among a low information public:understanding US opinion on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2007,19(1):24-52.
[11]黃俊儒,簡(jiǎn)妙如.在科學(xué)與媒體的接壤中所開展之科學(xué)傳播研究:從科技社會(huì)公民的角色及需求出發(fā)[J].(臺(tái) 灣)新聞學(xué)研究,2010,(105):127-166.
[12]Rajendra Babu,Gopalaswamy.Use of Web 2.0 tools and technologies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in biomedical sciences:A special reference to blog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2011,3(5):85-91.
[13]Dominique Brossard,Dietram A Scheufele.Science,new media,and the public,Science,2013,339,40.
[14]Davidson D J,F(xiàn)reudenburg W R.Gender and environmental risk concerns a review and analysis of available research[J].Environment and Behavior,1996,28(3):302-339.
[15]Hallman W K,Hebden W C,Aquino H L,et al.Public Perception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A National Study of American Knowledge and Opinion[M].Food Policy Institute,Cook College,Rutgers,2003.
[16]Connor M,Siegrist M.Factors influencing people's acceptance of gene technology:the role of knowledge,health expectations,naturalness,and social trust[J].Science Communication,2010,32(4):514-538.
[17]Ho S S,Scheufele D A,Corley E A.Value predispositions,mass media,and attitudes toward nanotechnology:the interplay of public and experts[J].Science Communication,2011,33(2):167-200.
[18]Hoban T J.Trends in consumer attitudes about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J].AgBioForum,1998,1(1),3-7.
[19]Kolst S D.Scientific literacy for citizenship:tools for dealing with the science dimension of controversial socioscientific issues[J].Science Education,2001,85(3):291-310.
[20]Bowling B V,Acra E E,Wang L,et al.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a genetics literacy assessment instrument for undergraduates[J].Genetics,2008,178(1):15-22.
[21]Craig O Stewart.The influence of news frames and science background on attributions about embryonic and adult stem cell research frames as Heuristic/Biasing Cues[J].Science Communication,2013,35(1):86-114.
[22]Holliman R.From analogue to digital scholarship:implications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researchers[J].Journa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2010,9(3):C05.
[23]楊鵬,史丹夢(mèng).真?zhèn)尾┺?微博空間的科學(xué)傳播機(jī)制——以“謠言粉碎機(jī)”微博為例[J].新聞大學(xué),2011,4:020.
[24]黨偉龍,劉萱.論歐美“科學(xué)咖啡館”的實(shí)踐及其啟示[J].科普期刊,2013.
[25]Mizumachi E,Matsuda K,Kano K,et al.Scientists'attitudes toward a dialogue with the public:a study using“science cafes”[J].Jcom,2011,10:4.
[26]劉兵,江洋.對(duì)共識(shí)會(huì)議之“共識(shí)”的反思[J].中國(guó)科普理論與實(shí)踐探索——2010 科普理論國(guó)際論壇暨第十七屆全國(guó)科普理論研討會(huì)論文集,2010.
[27]Paul R Brewer,Barbara L Ley.Multiple exposures:scientific controversy,the media,and public responses to bisphenol A[J].Science Communication,2011,33(1):76-97.
[28]Dijkstra A M,Gutteling J M.Communicative aspects of the public-science relationship explored results of focus group discussions about biotechnology and genomics[J].Science Communication,2012,34(3):363-391.
[29]Bauer M W,Allum N,Miller S.What can we learn from 25 years of PUS survey research?Liberating and expanding the agenda[J].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2007,16(1):79-95.
[30]Ronald.A Yaros.Effects of text and hypertext structures on user interest and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J].Science Communication,2011,33(3):275-308.
[31]Shirley S Ho,Dietram A Scheufele,Elizabeth A.Value predispositions,mass media,and attitudes toward nanotechnology:the interplay of public and experts[J].Science Communication,2010,33(2):167-200.
- 中國(guó)科技論壇的其它文章
- 科技金融服務(wù)機(jī)構(gòu)支持科技型中小企業(yè)融資發(fā)展的案例研究
- 專利中間商——?jiǎng)?chuàng)新催化劑抑或市場(chǎng)阻礙者
- 基于專利的技術(shù)創(chuàng)新網(wǎng)絡(luò)演化動(dòng)力挖掘
- 關(guān)于青年科技創(chuàng)新人才成長(zhǎng)的思考與對(duì)策
- 基于CEM 的移動(dòng)服務(wù)供應(yīng)鏈結(jié)構(gòu)模型研究
- 現(xiàn)代服務(wù)業(yè)產(chǎn)業(yè)集聚與區(qū)域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的耦合關(guān)系研究——以皖江城市帶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