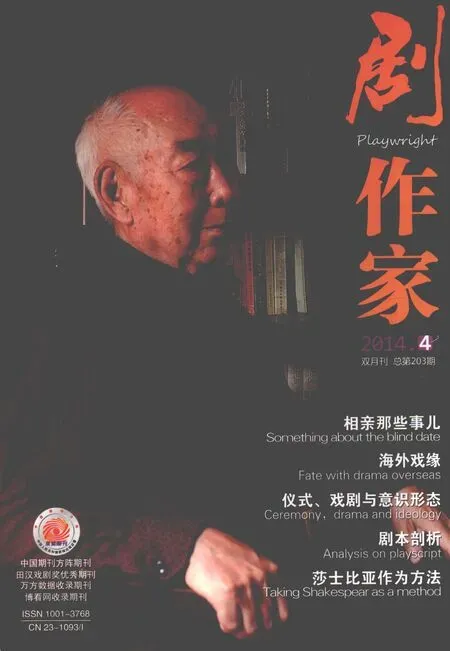你不是羅密歐,她也不是朱麗葉
——話劇《羅密歐與朱麗葉》
孫韻豐
在紀念莎士比亞誕辰450周年的2014年4月,國內外眾多劇院、劇團都紛紛重排莎劇以示對戲劇大師莎士比亞的敬意。中國國家話劇院導演田沁鑫重排的這部莎士比亞經典悲劇之一《羅密歐與朱麗葉》也顯出了這份對莎翁的誠意。這部由中國當代劇壇新銳導演執導、多位知名青年演員聯手呈現的《羅密歐與朱麗葉》自2月在香港成功首演后便開始了它的全國多地巡演。
走進田沁鑫的劇場,這版《羅密歐與朱麗葉》的舞美裝置一定讓觀眾意外:幕布敞開,布景暴露臺上,兩根醒目的舊電線桿子矗立臺前,舞臺兩側是象征兩家勢力范圍的二層鋼筑體,深處是一張中國上世紀80年代常見的網格鐵門,臺上散亂堆放著如今公路騎行運動常見的“死飛”自行車。演員沒有在后臺候場,而是在臺上呈現出生活甚至排練的常態。臨近演出正式開始,沒有響起正式場鈴,一個近似業余播報的聲音出現:“演出馬上就要開始,三、二、一。”一時間分不清正式演出或還在排練中。一部經典悲劇就這樣拉開序幕。
盡量“接地氣”,結合本土元素
《羅密歐與朱麗葉》,一部對西方觀眾來說百演不衰的嚴肅悲劇,在中國觀眾眼里,或許充其量是一個帶有浪漫色彩而結局不如《牡丹亭》中杜麗娘與柳夢梅那樣起死回生走運傳奇的故事。不同的中西哲學與文化,讓我們看到中國古典文學中少有純粹的悲劇,從來都以悲喜劇為主,以大團圓結尾。是的,在中國上演的西方經典名劇總是遭遇這樣一個尷尬的境地:不同的文化語境和歷史背景,使觀眾在讀解作品時本能地存在一道隔閡。田沁鑫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曾提到:“中國人演莎士比亞的戲總讓人有種距離感,即使是我們的演員穿著本土化的服裝來演出,抑或是我們用實驗的方式來詮釋,總顯得不親,因為那畢竟不是我們血液里流淌著的東西。我只想讓莎翁落個地,用我們的方式,講出他的心里話。”
這部戲保留了原版主要的故事情節,把
時間拉到現代,把空間挪到北京大院,將焦點聚在“愛情”。一個義無反顧的青春愛情故事就在“發展中的當代中國”這特定時空中展開。在中國印刷發行較多的是朱生豪譯的莎劇劇本,只要讀過朱老先生譯的劇本,就能體會莎劇中文版華麗如詩般的字句,為能“接地氣”,田沁鑫首先就在劇本改編上下功夫,除保留了原本中的幾處經典橋段外,其余則讓語言變得更樸素,更口語,更當代。這在開場就有直觀體驗——
“當年你二姨那什么了我姥姥,我怎么允許你們家那什么我姥姥!”
“當年你大舅怎么著了我大爺,我怎么能讓你們家怎么著我大爺!”
朱家和羅家的男男女女們互相用京片子罵罵咧咧開始了爭斗,因為一部自行車,兩家矛盾爆發。還有另人印象深刻的一處橋段,便是從戲中充滿喜感的神父口中念出的一段中國特色的相聲快板,這令全場觀眾捧腹大笑。此外,自行車成為這個舞臺上的重要道具,對此,田沁鑫認為這種“既懷舊又時尚”的自行車代表著已經消逝的“自行車時代”以及正“時尚地發展的中國”。舞臺上的兩根電線桿也同樣成為田沁鑫眼中“接地氣”“很中國”的時空符號,正如她所說:“電線桿子現在已經消失了,但電線桿子又是我們所有人的記憶。”
青春的身體,愛無禁忌

在田沁鑫的作品中,我們總是可以看到她對于身體的展現。這部關于愛情的戲劇,青春的身體成為展現的對象。劇中開場的群毆戲中,一群青年男女穿著時尚,女生露背露臍穿著緊身皮褲,男人們露出胸肌,從頭到腳流淌著躁動的血液。參加過田沁鑫戲劇工作坊的演員一定知道“隔空發力”這種訓練方式,一人發力,并不作用在對方身上,受力方根據發力方的角度和力度來判斷自己的受力方向和程度從而及時做出行為反應。在《羅密歐與朱麗葉》的這場群毆戲中,我們看到了田沁鑫根據這種訓練方式而展現在舞臺上的行為處理。
在羅密歐與朱麗葉相識的派對舞會上,我們看到的是一副副年輕身體展現激情與魅力的舞動群像。其中,朱麗葉的扮演者殷桃穿著一身黑色短蓬裙,頂著一頭爆炸短發出現在舞會上,和所有人一樣,她舞姿性感,狂熱奔放,單純而美好,青春的氣息從上自下撲面而來。或許也只有這樣的女孩才會和羅密歐擁有一段撕心裂肺的愛情。田沁鑫在選擇殷桃作為朱麗葉的扮演者時談到,她人漂亮,直接而本質,能夠把自己的生命力張揚出來,具有很強的爆發力。戲中的朱麗葉這一角色在田沁鑫看來,是一個“在我們中國女孩頭上的,不是傳統審美意義下的那種女孩,乖乖的,或者天使范兒的,公主范兒的,女神范兒的都不是。”她像一只一心向愛情之火撲過去的飛蛾,她的身體里充滿著感性細胞。羅密歐,在田沁鑫心里,應該是一個“愛神丘比特”的定位,為愛而生,為愛而死,形象上則要展現出男人的陽剛,李光潔扮演的羅密歐帥氣而有些頹廢,獨特而純粹。
在羅密歐與朱麗葉的多場對手戲中,吻戲不少,甚至有一場戲羅密歐一邊說著臺詞“我一見到你就不想讓你離開,我身體里所有的細胞都在叫嚷著,讓我擁抱你,捏死你,把你揉進我的身體里”,一邊將衣服脫到只剩底褲。熟悉田沁鑫作品的觀眾一定了解,在田沁鑫所有的作品中,從《生死場》到《青蛇》,身體姿態的狂放已經成為田沁鑫作品中人物表演的特點。《羅密歐與朱麗葉》也不例外,身體的展現是一方面,從技巧層面來說,田沁鑫也做了解釋:“哎呀,沒辦法,還是莎大爺這事兒,因為莎老先生他在寫的時候就寫了這一對年輕人,這就是兩人死扛著往下戀,所以到了一段的時候,兩個人真的在一起的時候,我怎么能把我身體的一部分給你,我怎么能夠把你怎么樣,說這話的時候,如果讓兩人站著說,這顯然都不符合這個人的情感了,他沒辦法,只能下一步進行這樣的遞進動作。”正是這樣充滿激情、青春洋溢的身體,才會為了愛而打破禁忌、沖破束縛、不顧一切勇往直前。
奢侈的愛情教育,現實的男女境況
田沁鑫排《羅密歐與朱麗葉》,在舞臺上展現純粹的愛情,這是一堂奢侈的愛情教育課。還記得愛情最初的樣子是什么嗎?在這個社會、經濟處于轉型期的中國,愛情,逐漸被物質欲望、世俗觀念沖淡。彩禮問題、“門當戶對”、穩定安逸的生活標準都成為附加于愛情之上的籌碼,對于這一點,田沁鑫也有所體會。該戲將原版中的乳媽改成奶爸康花花,這一角色的部分臺詞創作也都是來自于田沁鑫參加過的一場婚禮。婚禮上冗長的儀式以及新人父母對新人的要求“孝敬父母,侍奉公婆,團結領導,團結下屬,愛護同事,回報單位,回報社會”,讓婚姻在中國成為了愛情的墳墓。愛情不再是最初的那個樣子。在中國,想要擁有幸福的婚姻就必須先擁有將愛情變現的能力——鉆戒、房子、車子、存款,雖然這些條件并不能保證所有婚姻的完整,但至少,它們能夠保證雙方在步入婚姻的那一剎那是“幸福美好”的。
田沁鑫為了能讓這部西方愛情悲劇更接近中國觀眾,編排上加入了眾多中國元素,用意就是在于讓觀眾懂得什么是愛情,愛情應該是怎樣的。在我們的成長經歷中,從小學至高中期間的愛情是“早戀”,大學四年畢業以后,父母便指望子女忽然間找到合適完美的戀人帶回家,按部就班地完成婚姻大事,好好地過日子。毫不夸張地說,如今收視飄紅的各類相親節目以及婚姻家庭糾紛節目正是基于這樣的現實背景。
在田沁鑫眼里,純粹的愛情里是沒有世俗標準的,這才是純凈而美好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在獲得掌聲的同時,獲得的也許是部分觀眾深深的感動與共鳴,只是,離開觀眾席,劇場外面,等待他們的依舊是那個無法逃避的殘酷社會以及無法抗拒的生活壓力。正所謂“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愛情,多么奢侈,甚至以生命為代價。然而在中國,你不會是羅密歐,她也不會是朱麗葉。
客觀地說,當下的社會已經很難會有一部作品能真正改變這個社會的主流觀念、一部戲能真正改變觀眾的愛情觀。但這部戲,至少為我們對于愛情的理解提出了問題,提出了導演自己的想法和態度。在這個務實的年代,你可以不是羅密歐,她也可以不是朱麗葉,但你們應該需要知道,真正的愛情,這樣存在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