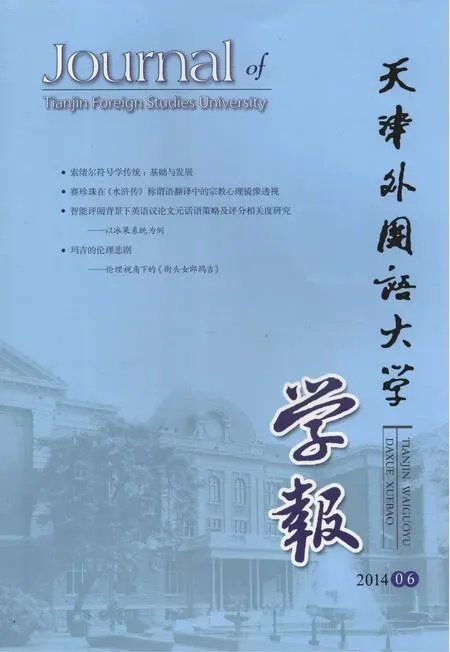漢英交替傳譯中語法隱喻的一致與背離
何 偉,肖歡歡
(北京科技大學 外國語學院,北京 100083)
一、引言
口譯實踐活動比筆譯出現得早,但是與筆譯研究相比,其學術探討相對滯后,現在正處于不斷發展和完善的階段(何其莘、仲偉合、許鈞,2009)。綜觀國內口譯研究方面的文獻,不難發現國內學者對口譯的研究主要囿于兩個方面:一是對口譯理論的研究,如鮑剛(2005)、劉和平(2005)、劉宓慶(2006)等;二是對口譯技巧、口譯策略及口譯教學等實踐性的研究。我國學者在口譯實踐方面的研究做出了較大的貢獻,如梅德明(2003)、劉和平(2005)、仲偉合(2006)等。隨著國內學者對口譯研究的不斷深入,以及國際交流的日益頻繁,越來越多的學者對口譯主要類型之一的同聲傳譯(以下統稱同傳)產生興趣,此方面的研究已初見端倪。我國學者對同傳的研究最早見于李長栓(1998),此后學界相繼有人研究英漢同傳技巧,如仲偉合(2001)。然而,與同傳相比,作為口譯另一主要類型的交替傳譯(以下統稱交傳)卻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綜覽相關文獻,可以發現交傳的研究少之甚少,而且僅有的研究仍主要局限于交傳的記憶模式(張威,2006)、筆記(趙文,2010)以及交傳技巧(張睿、方菊,2009)等方面。鮮有學者利用語言學理論對其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而何偉和衛婧(2011)曾在此方面作出嘗試。本文擬用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來研究漢英交傳中對語法隱喻的處理問題,旨在找出漢英交傳中譯者對語法隱喻處理的一致和背離現象,同時為提高口譯質量提供借鑒。
二、語法隱喻
語法隱喻這一概念是由系統功能語言學的創始人韓禮德于1985年在《功能語法導論》一書中首次提出。語法隱喻這種現象其實由來已久,只是之前的學者對隱喻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詞匯隱喻這一層面上。不同于其他語言學家,韓禮德(1994)認為,隱喻不僅僅發生在詞匯層,還發生在語法層。他還指出,語法隱喻不同于詞匯隱喻,它不是用一個詞去代替另一個詞,而是用一種語法結構去代替另一種語法結構。從語言元功能的角度來看,韓禮德最初將語法隱喻分為概念隱喻和人際隱喻兩大主要類型,后來又將語法隱喻細分為13種,本文重點研究概念隱喻和人際隱喻。
概念隱喻主要涉及的是及物性系統內各過程間的隱喻化,即物質過程、心理過程、關系過程、行為過程、言語過程和存在過程這六種過程之間的轉換,而名詞化則是概念隱喻的主要表現形式。作為語法隱喻的另一主要類型的人際隱喻又可劃分為語氣隱喻和情態隱喻兩種。語氣隱喻指被選用的語氣不是表達通常所表達的言語功能,而是表達其他言語功能的現象。通常情況下,陳述語氣用來表達陳述的言語功能,疑問語氣表達疑問的言語功能,但事實上“一種語氣可以體現不同的言語功能,一種言語功能可以由不同的語氣體現”(范文芳,2000:30),其中不常見的語氣表達形式即為語氣隱喻。至于情態隱喻,韓禮德認為,情態取向可分為明確主觀、非明確主觀、明確客觀和非明確客觀四種,而其中明確主觀和明確客觀取向的表達就是情態的隱喻式表達,即情態隱喻。
韓禮德最初提出的語法隱喻理論主要應用于如科技語篇這樣專業性及學術性較強的書面語篇。我國學者董宏樂(1998)就曾專注于此方面的研究,曾著書專門研究英語科技語篇中的語法隱喻現象,如在《科技英語中的語法隱喻》一文中重點分析了科技英語中的語法隱喻以及語法隱喻的重要性,此后又出版《科技語篇的隱喻性》一書來深入研究科技語篇中的語法隱喻問題。除了中國學者對科技語篇中的語法隱喻感興趣外,外國學者如Ravelli(2003:49)就曾指出:“語法隱喻是書面語尤其是科技和學術語篇的核心。”越來越多的學者將語法隱喻的研究從單一的語篇研究擴展到了與其他學科相結合的跨學科領域。近年來許多學者將語法隱喻理論與翻譯研究相結合,如何偉、張嬌(2006)、黃國文(2009)等。他們的研究為后來的翻譯研究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
三、漢英交傳中語法隱喻的一致與背離
交傳是口譯的一種,具有口譯特點之一的口語性,不如筆譯那般正式。然而,由于交傳應用場合之特殊性,如演講、國際會議、新聞發布會、商務談判等正式場合,這又決定其不像一般的日常口語那么隨意,也具有書面語的特點。概括地說,交傳中的語言是一種介于口語與書面語之間的特殊語言,具有獨特性。正如韓禮德(Halliday,1994)所說的那樣,在成人的談話中完全沒有隱喻的情形是不存在的。而以往對語法隱喻的研究多側重于書面語,而研究漢英交傳中的語法隱喻問題就顯得尤為重要。下文列舉大多為2008-2010年間溫家寶總理答記者問的交傳實例。
1 名詞化之動與靜
名詞化是概念隱喻的主要表現形式,也是語法隱喻的主要手段。由于名詞化具有可以壓縮信息,使表達具有凝練客觀事物的作用,在漢英交傳中名詞化手段受到源語發言人和譯員的青睞。但過多地使用名詞化會使語言單調刻板,缺乏生氣。經驗豐富的譯員在交傳的過程中會采用化動為靜和化靜為動這樣動靜結合的方式,使整個語篇生動形象。至于何為動和靜,只是相對而言。而此處所提及的動與靜具體是指“英語傾向于多用名詞,因而敘述呈靜態;漢語傾向于多用動詞,因此敘述呈動態”(連淑能,2010:133)。優秀的譯員只有充分利用動靜結合的翻譯策略才會把好的翻譯呈現在受眾面前。
名詞化現象是漢語的主要特點之一,究其原因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點:一是由于說話人代表的是政府機構,具有權威性,語言中會涉及許多政治和經濟方面的相關術語;二是由于“名詞化能夠提高語篇的專業化程度,系抽象化了的直觀信息”(肖英、呂晶晶,2007:75);三是由于名詞化可以整合信息,具有簡潔、精煉的特點,符合政論體裁的要求。對于源語中出現的名詞化現象,譯員通常將其直譯成譯語中相應的名詞化形式即可。這樣的處理方式一方面符合目標語英語靜態的特點,另一方面又為譯員口譯節省了時間。例如:
(1)正如這位記者所說的,中印關系這些年有了顯著的改善和發展。
As you rightly said, China-India relations have experienced marked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漢語中的“改善”和“發展”屬于名詞化形式,是抽象性名詞。傳譯中的慣常做法是采用相應的名詞化表達,即improvement和development,這樣一方面符合目標語英語多用名詞的特點,便于目標語受眾接受,另一方面又減小了譯員的工作壓力。
目標語和源語名詞化的不同之處在于詞形上是否發生曲折變化,漢語不涉及曲折變化,而英語則不然。譯員只有清楚地了解漢英兩種語言的不同特點,才能在漢英交傳的過程中對兩種語言間的轉換做到游刃有余。雖然通常情況下,漢語的名詞化不涉及詞形變化,但是并不意味著就無跡可尋,而事實上在一些情況下名詞化也會有其特有的標記。例如:
(2)中國的現代化絕不僅僅指經濟的發達,它還應該包括社會的公平、正義和道德的力量。
China’s modernization drive is not only about achieving economic prosperity. It also includes our endeavors to promote social equity and justice and enhance our moral strength.
源語中“現代化”是以“化”字為標記的名詞化形式。這樣具有標記的名詞化現象在漢語中并不多見,主要是以“化”、“性”、“度”等字為標記詞,而這些詞大多是外來語。譯員只需將其譯成英語中與之相應的名詞化形式modernization即可,這是約定俗成的譯法。如“現代化”、“全球化”及“工業化”這樣的固定短語都有其相對應的英文翻譯。譯員頭腦中如果事先儲存了這些信息,在交傳時就可以脫口而出,便可大大提高口譯的效率與準確率。
以上兩個例子主要涉及對源語中名詞化表達的翻譯,即原本就是表示靜態的名詞被譯成英語中相應靜態的名詞。這是一種順譯的方式,符合口譯受時間限制的特點,省時省力。
漢英交傳中出現的源語與譯語在名詞化方面不一致的情形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源語中沒有使用名詞化形式,而譯員在英譯中采用了名詞化表達,這種現象在漢英交傳中屢見不鮮;二是漢語中采用名詞化形式,而譯語中沒有選用相應的名詞化形式,這種現象在漢英交傳中也偶有發生。例如:
(3)第一,中國這些年經濟雖然發展很快,但是由于城鄉不平衡、地區不平衡、再加上人口多、底子薄,我們確實還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
First, it is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in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But China is still a country with a big population,weak economic foundation and uneven regional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China is still at the primary stage of development.
源語中“城鄉不平衡、地區不平衡、再加上人口多、底子薄”是四個并列小句,用來形容中國發展中所遇到的問題,是一種動態的表達。而英譯卻采用了介詞with加四個名詞詞組a big population,weak economic foundation,uneven regional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的譯法。源語中四個小句與“由于”共同構成一個非常復雜的狀語從句,如果保留原來的句式結構,譯文會顯得拖沓冗長。而將四個小句壓縮成四個名詞詞組一方面壓縮了信息,簡化了句子結構;另一方面將動態的動作轉化成靜態的狀態,是一種化動為靜的翻譯策略。由于漢英交傳是受時間限制的,在盡量短的時間內用盡量簡短的形式表達盡量多的意義就是考驗譯員水平的關鍵。
(4)我們將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We will continue to reform the RMB exchange rate regime and keep the RMB exchange rate basically stable at an appropriate and balanced level.
上例這種情形在漢英交傳中并不常見,源語中“改革”是一種名詞化形式,而譯員卻在譯語中采用了reform這一動詞形式。這樣化靜為動的處理方式看似有違常規,實則是譯員為了豐富語言表達。過多的名詞化會使譯文顯得單調,而適當地使用動詞會給譯文增加活力與生機。
2 語氣隱喻處理之靈活性
漢英交傳中,除了概念語法隱喻的使用頻繁這一特點之外,另一大特點就是語氣隱喻的使用。因為漢英交傳中的語言介于書面語和口語之間,而口語在交際當中會涉及人際功能,其中就不乏語氣隱喻。語氣隱喻主要集中體現在記者提問的過程中,比較單一,而且對語氣隱喻的處理并無太多規律可循,需要結合具體語境及譯員的口譯習慣選擇相應的譯法,就難免會出現誤譯的情況。
在漢英交傳中語氣隱喻一致的情形并不多見,是指源語中選用了語氣隱喻,目的語中也采用語氣隱喻。語氣隱喻具有很強的語境依賴性,尤其體現在與人際功能相關的語旨因素上。例如,記者在向溫總理提問時就可能采用語氣隱喻的方式,這可能是由于對話雙方身份、地位的差距,記者為了表達對總理的尊敬,采用陳述句間接地詢問信息,這樣的表達比較委婉,不突兀。例如:
(5)我想知道您對這件事的看法。
I would like to know your comment on it.
記者用陳述語氣表達的其實是疑問的言語功能,即“您是如何看待這件事的?”而此處之所以采用了語氣隱喻的表達,是與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文化習慣有關。中國人比較含蓄,并不習慣直接用問句提問,以免給對方造成不必要的負擔和壓力。譯員在翻譯的過程中往往會將其譯成譯語中對應的語氣隱喻形式,這就是交傳技巧之一的直譯法。這樣的字字對譯省時省力,同時表達又準確無誤。又如:
(6)人們還不知道您當時的心路歷程。
People still want to know what was on your mind at the time.
源語中想要表達的是“您當時的心路歷程是怎樣的?”記者卻用了陳述句,間接地提問,并且把主語變成“人們”,可以體現出廣大中國人民對總理的關心,想要了解總理當時的想法。而如果直接采用問句形式,就無法表達出這種關心。譯員在英譯中也選用了陳述句形式,準確地再現了源語的意義及語言風格。
漢英交傳中,源語與目的語在語氣隱喻方面不一致的情形較多。因為很多時候漢語中的“請”、“您”或“請您”都可以表達本該由語氣隱喻方式來表達的委婉和禮貌。例如:
(7)您怎么看待輿論的這種擔心?
I would like to get your perspective on the worries of the public.
記者直接使用疑問語氣來提問,向總理詢問信息。英語中沒有與漢語“您”相對應的敬稱表達,故而譯員在譯語中采用陳述語氣,成功地再現了源語中的人際意義,這是譯員在交傳中常用的一種策略。同時譯員還使用了perspective這一名詞來翻譯源語中的動詞“看待”,一方面符合英語多用名詞的特點,另一方面會增加語言的專業性。在漢英交傳中譯員通常都采用名詞perspective或view來表達漢語“看待”這一動詞的意思。
(8)請問總理,您有這個擔心嗎?
I wonder if you have the concern for the Chinese economy.
“請問總理”這種表達方式已經傳遞了委婉、禮貌的含義,因此不采用語氣隱喻也是可以接受的。漢語中的“請”并不完全等同于英語常用于祈使句中的please。在譯語中譯員卻使用陳述句來表達源語的提問句式,主要是考慮到溫總理答記者問的場合比較正式,受眾也是相關的專業人士,采用語氣隱喻形式會顯得更加禮貌、正式,也便于目標語的受眾接受。
(9)請問財政風險是否可控?
So I’d like to know are the fiscal risks within control?
此例更加正式、準確的表達應該是So I’d like to know whether the fiscal risks are within control.譯員的表達是比較口語化的,在一定語境中是可以接受的。譯員本來打算采用陳述句來表達源語的提問,卻加入了插入語I’d like to know,并選擇了疑問語氣。雖然這樣的表達從嚴格的英語語法角度來說是有問題的,但是考慮到口譯譯員臨場受到的壓力,受眾也能夠理解,所以勉強可以接受。譯員一定要做到嚴謹,減少這些不必要的失誤。
3 情態隱喻之顯隱性表達
在漢英交傳中,漢語中明確出現“我認為”或者“我覺得”這樣的情況并不多見。由于東方文化比較含蓄,不鼓勵人們直接表達自己的觀點,反映在語言上就是注重意合,很多含義都隱含在字里行間,不像英語那樣顯性地將其表達出來。通常情況下,只要是源語中出現了情態隱喻,譯員都會采用英語中相應的情態隱喻形式來表達。例如:
(10)第一,我認為人民幣的幣值沒有低估。
First, I don’t think the RMB is undervalued.
源語中“我認為”表明說話人的主觀看法,是漢語中的情態隱喻表達方式。譯員也采用了英語中相應的情態隱喻形式I think,它相當于這句話的狀語部分,表達觀點看法,而不是一個真正的命題,也就是說,這句話的核心內容是RMB is undervalued而不是I think。譯員采用了以隱喻譯隱喻的方法,不用過多考慮,幾乎可以脫口而出。這是一種直接有效的習慣譯法,同時也符合英語的表達習慣。
漢英交傳中情態隱喻不一致的情況分兩種:一是源語中沒有出現 “我認為”或者“我相信”這樣明確表明看法的情態隱喻,但譯員可以從字里行間推斷出說話人的主觀想法;二是漢語中使用了情態隱喻,但在英譯中情態隱喻表達的位置發生了轉移。例如:
(11)其實你說的情況和每年大量的外資進入中國的實際并不符合。
I don’t think the situation that you described in your question accords with the reality, that is, there is a large in flow of foreign capital into China every year.
在源語中并沒有使用“我認為”這樣的情態隱喻來表達說話人的主觀看法,但可以看出“其實”之后的內容是溫總理個人的看法。結合當時的語境,譯員在譯語中采用了I think這樣的情態隱喻,明確地表達了說話人的觀點。這樣顯性的表達在英語中是很常見的,而漢語卻習慣采用隱性的表達,句子之間的關系都隱藏在字里行間。在漢英交傳的過程中,譯員要充分考慮到上下文的語境,根據自己的理解作出判斷,同時給出恰當的翻譯。
漢語的句式通常都是松散自由的,而英語句式比較嚴謹。在漢英交傳的過程中譯員往往會對發言人的信息進行整合,將源語句子之間的順序進行相應調整,譯出規范、地道的譯文。例如:
(12)而社會的公平正義,是社會穩定的基礎。我認為,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
I believe equity and justice form the basis of social stability. And social equity and justice can shine even more brightly than the sun.
源語中“我認為”所表達的看法不僅僅是后面的內容,也包括之前的內容。譯員將I believe放到了句首,表明這兩句話都是I believe所涉及的內容,這樣更便于目標語受眾理解。
四、結語
本文從系統功能語言學語法隱喻角度來研究漢英交傳。通過研究發現,漢語源語和英語譯語中的語法隱喻在名詞化、語氣隱喻以及情態隱喻方面存在著一致和背離的情形。這一現象可以從漢英兩種語言的不同特點以及交傳自身的特點中找到合理的解釋。在漢英交傳的過程中,譯員只有將兩種語言的特點爛熟于心,并在兩種語言之間的轉換中采取相應的翻譯策略,才會使交際雙方的交流順利進行。而對于語法隱喻的翻譯,只有充分利用好動靜結合與化隱性為顯性的翻譯策略,并結合一定的翻譯技巧,才能達到令人滿意的效果。
[1]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 London: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1994.
[2] Ravelli, L. Renewal of Connection: Integr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in An Understanding of Grammatical Metaphor[M].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3] 鮑剛.口譯理論概述[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2005.
[4] 董宏樂.科技英語中的語法隱喻[J].上海鐵道大學學報, 1998, (7): 108-112.
[5] 范文芳.英語語氣隱喻[J].外國語, 2000, (4): 29-34.
[6] 何其莘,仲偉合,許鈞.交替傳譯[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 2009.
[7] 何偉,衛婧.英漢交替傳譯中銜接手段的轉換[J].中國科技翻譯, 2011, (2): 21-24.
[8] 何偉,張嬌.《醉翁亭記》英譯文的語法隱喻分析[J].外語與翻譯, 2006, (1): 12-19.
[9] 黃國文.語法隱喻在翻譯研究中的應用[J].中國翻譯, 2009, (2): 5-9.
[10] 李長栓.英漢同聲傳譯的技巧[J].中國翻譯, 1998, (6): 12-16.
[11] 連淑能.英漢對比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12] 劉和平.口譯理論與教學[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2005.
[13] 劉宓慶.口譯理論研究[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2006.
[14] 梅德明.英語口譯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15] 肖英,呂晶晶.語法隱喻理論對學術語篇翻譯的指導作用[J].西安外國語大學學報, 2007, (1): 74-77.
[16] 張睿,方菊.交替傳譯中“單純繁復數字”傳譯技巧[J].中國科技翻譯, 2009, (3): 24-27.
[17] 張威.口譯過程的認知因素分析:認知記憶能力與口譯的關系——一項基于中國口譯人員的調查報告[J]. 中國翻譯,2006, (6): 47-53.
[18] 趙文.關于交替傳譯中筆記的思考[J].大學英語, 2010, (2): 84-86.
[19] 仲偉合.口譯訓練:模式、內容、方法[J].中國翻譯, 2001, (2): 30-32.
[20] 仲偉合.英語口譯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