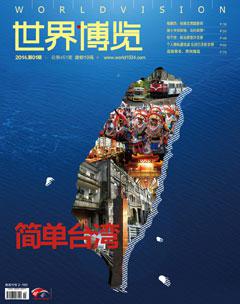生態(tài)兩難
張怡微
上個月采訪吳念真時,在他的工作室見到《看見臺灣》的海報。他為這部電影配音。這些年來,臺灣本土電影看似復興,實際票房誰都不敢保證,拍一部環(huán)保生態(tài)片的困難可想而知。導演齊柏林本來是公務人員,2009年莫拉克風災時,他搶在直升機前進入高雄縣甲仙災區(qū)。“毀天滅地的景況,就像世界末日到來。”山河變色令齊柏林不忍卒睹,他竟放棄三年后就能提領的百萬退休金,抵押房產(chǎn),借貸投入拍攝。
這是他首部執(zhí)導的紀錄片。以悲情始,恐怕又會以悲情止。真正領情的臺灣民眾,未必和他的預期謀和。《看見臺灣》耗資9000萬臺幣的紀錄片,花費近三年時間拍攝,以航拍鳥瞰的視角俯視整個臺灣的美麗與哀愁。獲得第50屆金馬影展最佳紀錄片之后,影響力正持續(xù)延燒。許多與他素未謀面的臺灣人為他喝彩,迄今票房已破億新臺幣。但許多與他素無冤仇的人,又不免恨他怨他。
《看見臺灣》熱映后,最先波及的便是南投清境農(nóng)場的民宿,因涉及泥石流威脅,被列為違建。自由行的陸客們對清境定不陌生,高山草原的壯美、清新一直是中部風景獨好的代表。隨著中橫開辟,合歡山成為臺灣人最容易親近的高山,位于合歡山必經(jīng)之路的清境地區(qū),原為原住民獵場,長滿了高聳入云的大樹。冬季賞雪,夏季避暑,雖不如日月潭、阿里山一樣深植老一輩大陸游客的內(nèi)心,卻很快風靡臺灣旅游的各大論壇,成為年輕人熱愛的環(huán)島地標。
但誰想清境地區(qū)合法民宿僅有四家,其余的一百三十家都有安全問題。政府第一時間提供數(shù)據(jù),證明他們對此早有調(diào)查。像是一種放棄、或出賣,又像是一種搪塞。導演齊柏林試圖展示的,應該是過度開采的觀光業(yè)對于自然生態(tài)的侵蝕。點名的還有臺灣各處溫泉旅店、被切割的海岸線、被過度抽取的地下水、垃圾掩埋等,在鳥瞰視野之下,觸目驚心。電影的意圖并非針對清境。但電影熱映后,清境民宿率先面臨拆除危險,意味深長。新聞中有一位經(jīng)營者是退伍老兵。他看著鏡頭哀哀地說了一句特別過時又令人心疼的話,接近于“我們還在等上級安排,安排我們?nèi)ツ睦锞腿ツ睦铩薄>拖駱s民一生命運的寫照。
1960年代,政府將從滇緬戰(zhàn)區(qū)撤臺的軍隊安置在這里,開啟了情境農(nóng)場的開發(fā)。本是天涯淪落人,偏安而居、自力更生,將荒山開墾為良田。上世紀九十年代起,商業(yè)入駐,順應時代變遷。如今再度遭逢遷徙之變,雖然有緣有故,到底令人慨嘆世事無常。軍人自有一貫的服從意識,再大的風險居然都能夠吞下。如今渙散的年輕人都做不到了。
幾年前去阿里山玩時,下山見到窄窄的公路下墊著數(shù)十只巨大的集裝箱,問司機怎么回事。司機說前幾天剛剛泥石流塌方,來不及修,先墊集裝箱。那是山的背面,公路上依舊車水馬龍,運載觀光客。去花蓮旅游時,找的司機特別樸實,不太會講話,硬要兼做導游,就常常說些讓人摸不著頭腦的話。譬如“那里你們要不要去,那里很有名誒,上次掉下來大石頭,砸死過大陸客。”這些看似平淡的景觀及語言,早就成為日常的淡然,內(nèi)化為靠山吃山的在地人的世界觀。他們比誰都更早知道危險,卻也比誰都更需要依傍著這種危險活下去。
生態(tài)作家吳明益曾經(jīng)寫到過“解嚴”對臺灣自然書寫有很大的影響。“因為在戒嚴時,臺灣連帶把海岸跟山脈都戒嚴了,一個海島國家竟少有人假日選擇出海,只能在可憐的海水浴場泡水,有時候連舉起相機都可能違反軍事法令。” 處理環(huán)境問題最大的阻礙和兩難顯而易見。同意發(fā)展觀光的是政府,最后要取締觀光的也是政府。政治和利益掛鉤的深淵,豈是一部《看見臺灣》所能承受之重。然而,《看見臺灣》卻依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契機,幫助我們這些“外人”理解文藝背后的嚴酷。如奈保爾的游記散文,如康拉德的海洋。小的時候是沒看懂,長大了,是很怕看得懂。
2013年,無疑是馬政府最冷一年。如今無論是食品安全、環(huán)境問題,甚至妯娌不合互相戕害的社會案件,都被輿論引向經(jīng)濟太差、人心焦慮。《看見臺灣》的熱映更是雪上加霜,為本就深陷經(jīng)濟寒潮的臺灣人注入了煽情的力量。政府順應民意的“正義”背后,是那一百三十家民宿業(yè)者,及相關觀光產(chǎn)業(yè)的工作人員未來要怎么生活下去。
吳念真的旁白說:“這樣的臺灣,如果你沒看過,那是因為你站得不夠高”。許多臺灣人看完電影都哭了,因為即使他們站的夠高,依然對他們身邊的人及深愛的下一代,無能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