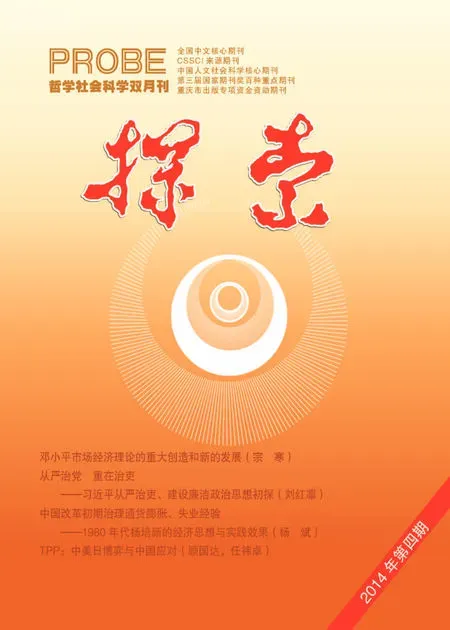現代性視域下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體系的反思與重構
張建忠
(華東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上海 201620)
現代性(modernity)是萌生于近代商品經濟的土壤之上,與啟蒙主義聯系在一起,用于表征現代社會的價值原則、思維方式、人生取向的一種文化精神。由于現代性是伴隨著商品化、社會化的生產方式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它實際上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時代精神”,無形地規范和統攝著現代社會的經濟結構、政治制度、文化精神和社會運轉等各個方面,深刻地影響著現代人的生存方式。我們所面對的很多理論或實踐的重大問題都或直接或間接地與現代性問題構成深刻的關聯。以致在現代社會中,某一實踐模式要想取得成功,其價值目標與行為方式必須契合現代性的內在要求,否則有可能歸于失效。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作為一種教育實踐行為,也必須遵從現代性的基本精神。然而,長期以來,我們的思想政治理論課不論在教學導向的選擇、教學方法的運用,還是價值目標的定位上,都游離于現代性精神之外。這也許是長期困擾思政課教學實效性的深層原因。因此,我們有必要將思政課的教學體系置于現代性的精神場域中加以審視,并以之為指引進行調整和重構。
一、現代性與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體系的定位
就起源語境而言,現代性無疑是在西方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的歷史語境中步入世界歷史舞臺的。盡管在時間先在性的維度,現代性的生成與西方資本主義有著內在的淵源關系,但時間先在性并不能證成現代性就是資本主義的精神專利,它實際上是現時代的“時代精神”,對身處現代社會的各個國家和民族具有一般性的價值范導意義,這種普適性的規范意義并不是建立在抽象的理性邏輯的演繹之上,而是建立在以資本為驅動、以市場為資源調配方式的全球性的社會化大生產之上的。由于當代中國仍處于市場經濟的歷史階段,現代性仍然處于生成和發展當中,其內蘊的價值體系非但沒有過時,反而是我們現代化過程中的主體價值導向。
就精神特質而言,現代性無疑是個多維的精神模塊,它是由具有內在關聯的各種要素組合而成的有機整體。也因為其內涵的豐富性,現代性問題成為包括文學、政治學、法學、哲學、經濟學等在內的各個領域的學者所探討和爭論的熱門話題。筆者在此無意盡可能全面地羅列出現代性的豐富內涵,而是基于與本文主題的相關性來簡要探討現代性如下三個基本的精神特質:
1.理性精神。現代性是在反對宗教迷信和世俗權威的過程中,伴隨著商品經濟和科學技術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首先是作為一種理性的文化精神而存在的。現代性的理性精神為近代啟蒙主義運動奠定了基礎,也在啟蒙主義運動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在這場思想革命中,恩格斯曾說道:“宗教、自然觀、社會、國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無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思維著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1]理性一開始是反對宗教神學和世俗權威的有力武器,對人類的思想解放和政治解放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始初具有很強的人文意蘊,只是在往后的發展過程中由于工具理性的膨脹抑制了價值理性的發展。
如果說理性是現代性最顯著的精神品格之一,那么“反思”和“批判”則是理性的品格。現代性由于理性固有的反思和批判精神得以不斷修正和超越,呈現出開放性和包容性的特征。“隨著現代性的出現,反思性具有了不同的特征,它被引入系統的再生產的每一基礎之內,致使思想和行動總是處在連續不斷地彼此相互反映的過程之中。”[2]從某種程度上說,現代性社會就是一個反思性社會,它對人的實踐過程及其結果不斷地做出階段性的思想的反思和實踐的修正。相比較而言,前現代社會正是由于缺乏反思和批判精神而趨于僵化和保守。
2.個體主體性。個體主體性可視為理性化過程的邏輯必然。正是理性精神賦予個體以自覺的品格,促進了個體主體性的生成和發展。在前現代,絕大部分個體是生活在經驗文化模式之下,類本能地遵照既有的經驗、常識、習俗、慣例自發地生存,這是傳統小農經濟的自然結果,而統治者的“愚民教育”則強化了這一結果。因為“愚民教育”力圖消解人的主體性和批判意識,使民眾維持在經驗文化的模式下,進而維持原有的社會運行模式。只是由于小農經濟的解體和商品經濟的發展,“愚民教育”所灌輸的經學體系才趨于瓦解,個體的主體意識才開始覺醒,人才得以走出自在自發的生存樣態,現代性意義上的人才真正產生。個體主體性原則的確立,是人類社會歷史的重大轉折,它構成了現代社會運行的支柱,“在現代,宗教、生活、國家和社會,以及科學、道德和藝術等都體現了主體性原則”[3],現代社會的創新能力、內在活力和驅動力都跟個體主體性的發展有著內在聯系。
理性促進了個體從自發走向自覺,而個體運用理性能力不斷地向傳統、權威、習俗等發出挑戰。理性與主體在一開始就形成了某種聯姻模式。近代哲學開創者笛卡爾提出“我思故我在”的懷疑論命題,確立了理性主體之“我”和主體理性之“思”的雙重向度,實際上是對現代性如上雙重特質——理性原則和個體主體性原則——的經典確證。
3.人本情懷。人本情懷是個體主體性原則的題中之意。步入現代社會之后,得益于工業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人們不再去設定一個萬能的造物主或抽象的精神實體,而是把自己視為這個世界的主人——不僅是自然界的主人,也是社會的主人,還是自己思維和意志的主人。人作為主體,不僅是認識和實踐意義上的主體,也是價值主體。即是說,現代人不再把自己看作是實現某個抽象的精神實體的工具,而是看作目的本身,更加關注人在當下和現世的生活體驗和存在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說,康德的“人是目的”是現代性人本精神的偉大宣誓。盡管在實踐的層面,人從前現代的“神役”(神對人的奴役)和“人役”(人對人的奴役)的狀態重新墮入了“物役”(物對人的奴役)的境地,但“人是目的”始終是現代性價值關懷之所在。這一人本精神貫穿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及其后一系列的社會思潮和社會運動之中。國內外學者不論是從現代性內部對現代性進行反思,還是以“后現代”的名義對現代性進行批判,都不曾也不敢撼動“人是目的”這一現代性原則,倒是以之為基本的理論武器和精神旗幟。
理性精神、主體意識、人本情懷,三者共同構成現代性的基本價值譜系。其中,理性精神是邏輯前提,主體意識是邏輯展開,人本情懷是邏輯歸宿。它們既是人類社會步入現代社會的結果,一經形成之后,又對現代社會的各個領域和各個方面產生重要的引導和規范作用,滲透到社會實踐的方方面面。
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同樣蘊含著現代性的如上精神品質,它是對現代性精神的繼承和超越,而不是否定和拒斥。比如,馬克思就非常提倡理性的批判懷疑精神,強調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其所有著作無不閃耀著批判懷疑的理性光輝;馬克思也十分強調個體主體性原則,他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由于其不合理的分工體系和私有制結構致使個體喪失了自由個性,陷入了片面化、畸形化的發展狀態,并把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看作是繼“人的依賴性”、“物的依賴性”之后的“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的生產能力成為從屬于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4]的第三個階段,提出未來社會要“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5]。這些無不從正反兩個方面體現了馬克思對“個體主體性”原則的捍衛和弘揚;人本精神當然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價值依托,不論是他對資本主義“異化勞動”的批判,還是對未來社會“每個人自由全面發展”的憧憬,無不體現著馬克思的人本情懷[6]。
因此,作為以馬克思主義為內容承載的思想政治理論課,理應將現代性的如上三個方面的價值原則作為整個教學體系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摒棄各種有悖于現代性價值原則的教學導向、教學方式和價值目標。
二、傳統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體系的現代性反思
如果以理性精神、主體意識、人本情懷等現代性價值為參照系去審視傳統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體系,我們便會發現,不論是在教學導向和教學方法的選擇上,還是在價值目標的定位上,都存在著與現代性精神相背離的一面。
1.在教學導向方面,過分強調“知識本位”而忽視理性思維能力的培育。
在我國,教學一直被視為引導學生掌握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長期積累的科學文化知識的活動,教材無形中被看作是無需檢驗、只需理解和記憶的“圣經”。教師的主要任務就是如何盡可能多地將自己所掌握的知識傳授給學生,讓學生最大限度地吸收知識。這種“知識本位”的教學取向是整個應試教育體制的通病,當然也是我們過往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弊病之一。在以“知識本位”為導向的思政課教學過程中,教師往往比較在乎理論體系的完整性,并片面地對學生進行抽象的理論知識的灌輸,而忽視學生對理論的探索和思考以及批判性思維的養成。教學成為知識的“搬運”——從教師頭腦搬到學生頭腦,學生的頭腦充塞著一個個“非反思性”的結論。這種“非反思”的知識,“易得”但也“易失”,因為它在被學生接受的過程中就不曾被質疑和討論過,而學生接受了現成的知識之后,一聽到不同的“雜音”,就很可能迅速加以拋棄。
“知識本位”的教學取向由于不注重學生理性思維能力的訓練,缺乏批判、反思、質疑的過程,結果就會像巴西教育家弗萊雷所說:“學生對灌輸的知識存儲得越多,就越不能培養其作為世界改造者對世界進行干預而產生的批判意識。他們越是原原本本地接受強加于其身上的被動角色,就越是只能適應世界的現狀,適應灌輸給他們的對現實的不完整的看法”[7]。在“知識本位”的思政課教學模式之下,學生與理論知識之間缺乏真正的對話,兩者僅僅是占有和被占有、利用和被利用的冰冷關系。這勢必不利于學生創新意識的養成,不僅會泯滅學生的生機與靈氣,而且會使學生淪為盲目服從、缺乏理性思維和批判反思精神的庸眾。同時,由于這一教學導向不自覺地夸大了所傳授的理論知識的客觀性、確定性、普適性,如此一來,一旦既有的理論觀點隨著歷史情境的變化而需要調整甚至摒棄時,學生就會重新陷入迷茫和困惑,進而滋生對主流意識形態的不信任情緒,使思政課教學流于失效。
2.在教學方法方面,過分強調教師的主導地位而忽視學生的主體地位。
“知識本位”的教學導向必然會輔之以“灌輸式”的教學方法。在“灌輸式”教學模式下,教師與學生在某種程度上便是控制與被控制的關系:教師維持課堂秩序、講授課程內容,學生則聽從教師講授、記錄課堂筆記,默默地接受教師的控制。教師成為整個教學過程的主體,學生淪為教學的客體。教師灌輸的知識越多,越是好教師,學生越溫順地接受教師的灌輸,就越是好學生。學生長期處于這種課堂模式下便會喪失主體意識和參與意識,放棄自己內心的體驗和感受,把主要精力用于死記硬背教師傳授的理論知識,轉而依附教師這個行為主體。如此一來,“學校在一定意義上成為世俗化的‘教堂’;教師像牧師一樣傳播著‘真理’與‘福音’;學生像是‘迷途的羔羊’匍匐在教師腳下,亦步亦趨”[8]。
在“灌輸式”教學模式下,學生不僅對于教師這個主體而言是客體,對于知識而言也是客體,因為在這一模式下,學生只是裝知識的容器。知識成為目的,學生卻淪為手段,不再是知識的真正主人。在“灌輸式”教學過程之中,教師與學生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學生與知識之間,由于缺乏真正的交流、對話、討論,致使整個教學過程變得封閉化、機械化:說它封閉化,是因為教師教什么、怎么教,學生學什么,怎么學,都是按照既定的統一模式和程序進行的;說它機械化,是因為在這一模式下個體學生對知識的掌握和占有與其他學生對知識的掌握和占有是割裂的,學生個體之間的關系也是一種類似“單子式”的機械關系,老師與學生的關系也是缺乏互動的機械關系,班級不曾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學習共同體。
雅斯貝爾斯曾說過:“所謂教育,不過是人對人的主體間靈肉交流活動……人與人的交往是雙方(我與你)的對話和敞亮,這種我與你的關系是人類歷史文化的核心,可以說,任何中斷這種我與你的對話關系,均使人類萎縮。”[9]思想政治理論課作為思想傳承、理論探討和價值引導的人文類課程,本應該發揚和踐行“對話”這一人類歷史文化的核心。而“灌輸式”教學是一種單向、獨白、機械、沉悶、缺乏互動的教學模式,它不僅不能激發學生的主體意識,反而會消解學生的主體意識,使學生形成順從依賴的性格和定勢專斷的思維方式。這與個體主體性這一現代性精神是根本相悖的。
3.在價值定位方面,過分強調“社會本位”而忽視“以人為本”。
在東方整體主義的文化傳統與以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為主體的經濟結構的雙重制約下,新中國成立以來無論在主流意識形態所倡導的價值觀層面,還是在社會制度的建構和具體的行為層面,我們一直比較強調國家、集體和社會的利益,個人的存在價值和合法權益往往處于被“兼顧”的地位,未能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甚至淪為抽象的共同體利益的犧牲品。這種以集體、國家和社會為本位的價值理念和思維方式又集中地呈現在我們思想政治教育領域之中,整個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功能定位和價值取向一直是以實現政治共同體的目標和任務為主。盡管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不同歷史時期,由于政治路線和黨的工作重心的轉換,思政課所承載的具體內容不盡一致,但“社會本位”的價值導向始終未曾偏離。比如,我們通常自覺不自覺地把思想政治理論課當作某種思想政治宣傳,以期實現如下三重社會功能:一是為社會經濟的發展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類似于“動力機”的功能;二是為政治發展提供方向上的“思想保障”和“價值引導”,類似于“導航儀”的功能;三是統一人們的思想、協調人們的行動,以實現社會和政治的穩定有序,類似于“穩定器”的功能。盡管思政教育在如上三重社會功能的定位上在不同歷史時期有各自的側重點和偏向——比如在強調經濟建設的歷史階段,可能注重發揮思政的“動力機”功能;在政局不穩的特殊時期,可能強調思政課的“穩定器”功能和“導航儀”功能——但三者都以服務國家和社會共同體為根本目的。
應該說,在后發國家實現現代化的趕超戰略的過程中,思政課在價值目標上強調“社會本位”也有其特殊的歷史合理性,因為它可以凝聚和整合社會個體的力量來促進共同體目標和利益的實現。但“社會本位”的價值導向也易使我們的思政課教學陷入“見物不見人”的歧途,因為它實際上是以工具理性為導向來定位思政課功能的,這很可能使我們的思政課教學在根本上漠視人自身的價值、意義、尊嚴、幸福、理想等超越性的價值追求。
三、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體系的現代性轉向
過往由于思想政治理論課“知識本位”的教學導向、“灌輸式”的教學方法和“社會本位”的價值定位,都與現代性的理性精神、主體意識和人本情懷相悖,自然而然就無法收到滿意的效果。因此,有必要對思政課的教學體系進行變革和重構,使之契合現代性的內在要求。
1.教學導向:從“知識本位”到“能力本位”。
在“知識本位”的教學導向之下,即使學生掌握了很多知識,也不能使他們的理性能力得到鍛煉和提升。因為學生在灌輸式的教學過程當中是不被當作主體來對待的,只是教師說教的客體和對象,學生沒有多少機會運用和發展自己的個體自主性。但人的理性恰恰是主體運用自己理智的能力和結果,理性的品格非常強調個體能夠自主、獨立、自由地進行思考、反思和批判。理性的啟蒙本質上是一種自我啟蒙,正如康德所言:“啟蒙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狀態。”所謂的“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10]。“勇敢地運用你自己理智”是啟蒙運動的口號。所以,啟蒙本質上只能依靠自己的理智,它是無法通過他者給自己啟蒙的,否則就是“被啟蒙”,“被啟蒙”與理性的自由自主之品格相悖。
從某種意義上說,當下中國社會中的相當一部分民眾尚不具備現代性之理性精神,這在網絡語境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很多網民往往僅憑一時沖動和好惡,無視事情的原委,對某些新聞事件進行一邊倒的批判和攻擊,缺乏一種理性的對話氛圍和自主的判斷意識,致使整個網絡輿情暴戾化。這固然有深刻的社會根源,卻也與我們過往的教育——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不注重對學生理性精神的培育有密切的關系。因此,我們的思政課教學應該積極順應現代性的需要,推動個體之現代性精神的養成和理性思維能力的提升。而要完成這一任務,思政課的教學導向就應該從“知識本位”轉向“能力本位”,即著眼于提升學生的理性能力,培養他們的主體意識和主體人格,把增強學生個人獨立所需要的能力作為思政課教學的核心使命,引導他們通過理性的反思和批判除卻自己的“心奴”,讓他們積極地去擁抱自我、確證自我、實現自我,使之成為自由自覺的、擁有獨立完整人格的現代性意義上的社會主體。
2.教學方法:從“灌輸式教學”到“討論式教學”。
不論是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還是理性思維能力的培育,其實現都有賴于特定的方法和路徑。而傳統的“灌輸式”教學法,一方面由于沒有把學生作為一個真正的生命主體,只是作為知識儲備的容器,根本上背離了以人為本的精神;另一方面又由于灌輸式教學是學生被動接受知識的過程,知識對他而言并沒有內化為自己的心性品質和思維能力。在這一教學模式下,學生容易形成獨斷、固執、封閉、僵化的思維模式,根本上有悖于理性的開放、反思、批判、包容、超越的精神。
因此,思政課的教學要貫徹以人為本的理念,培育學生的理性能力,就需要從傳統的“灌輸式”教學法轉向以“討論式”教學法為主。與“灌輸式”教學法不同,討論式教學是一種“主體——主體”的對話模式,這種主體間性的對話模式同時在三重向度體現出來:
(1)“教師——學生”。杜威曾指出,教育活動并不是一件“告訴”和被“告訴”的事情,而是一個教師和學生主動參與和共同建設的過程。傳統的灌輸式教學模式顯然有悖于這一正確的教育理念。而在討論式教學中,教師與學生就不再是簡單的灌輸與被灌輸的關系,而是兩個平等主體之間的交流和互動。通過師生的交流互動,不僅教師可以更好地了解學生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和內在需求,而且可以更有針對性地對學生進行引導和講解;學生也可以主動表達自己的所思所想,并對教師傳授的知識進行拓展和豐富,甚至可以形成某種“倒逼”機制,促使教師不斷地去更新、優化自己原有的知識結構,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教學相長。
(2)“學生——學生”。在灌輸式教學模式之下,學生與學生之間實際上處于某種“單子式”的機械關系之下,沒有形成有機的“學習共同體”。然而,正如羅爾斯所言:“人們有各種各樣的天分和能力,這些天分與能力不可能在一個人或一組人身上實現。所以,我們不僅從自己得到發展的傾向的完善本性得益,而且從相互的活動中得到快樂。仿佛是,我們自己的未能培養的部分是由他人來發展的。”[11]顯然,灌輸式教學沒能做到這一點。而在討論式教學模式下,由于學生各自的知識結構、成長經歷乃至價值取向都不盡一致,學生之間在討論過程中可以相互補充、質疑、問難,促使其對相關理論問題的理解更加全面和深入。
(3)“學生——知識”。德國教育學家斯普朗格認為:“教育絕非單純的文化傳遞,教育之為教育,正在它是一個人格心靈的‘喚醒’,這是教育的核心所在。”[12]傳統的灌輸式教學顯然只實現了師生之間的知識傳遞,不能有效“喚醒”學生的心靈。但在討論式教學之下,學生與知識逐漸融合,學生可以在與思想理論的對話中去感受理論的生命力和精神力量。知識不再是游離于學生之外的符號世界,而是內化于學生的心性之中,成為個體生命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思政課內容也就不再是冷冰冰的政治教條,而是成為負載人的生命價值和精神寄托的思想世界。
討論式教學實際上就是一種以語言為中介的交往行為,這一行為本身也極具教育意義。因為在討論式教學中,整個教學過程不再是單向的說教關系,而是平等主體間的交流對話,不論是教師還是學生個體都不能再理所當然地將自己視為唯一的主體或真理的持有者,而是要自覺地把他人作為平等的主體來對待。主體自身既要積極表現自己的主體地位(如發言內容的新穎性和批判性),也要具備“包容他者”的意識,以一種海納百川的胸懷認真傾聽他者的發言,還需要適時對自己的言行進行“反思”和“修正”。這不僅有利于培育學生的“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辯”的素養,使之生成互主體性模式下的“交往理性”,還可以塑造平等的師生關系,也會使學生的個體主體性處于健康的發展狀態。
3.價值定位:從“社會本位”到“以人為本”。
“以人為本”既是現代性的價值關懷,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馬克思主義的視域中,人不僅是實踐主體,也是價值主體,其整個歷史觀就是以從事實踐活動的現實的個人為出發點的,同時又以實現“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自己的價值歸宿。思想政治理論課作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主陣地,理應以“以人為本”這一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價值取向作為自己的價值追求。因此,思政課教學應該揚棄傳統的“社會本位”的價值定位,從工具主義的價值取向轉向樹立“以人為本”的價值理念,把“立德樹人”作為自己的邏輯起點和價值歸宿,以關注人自身的發展、解讀人存在的意義、建構人的精神家園、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目的。具體地說,就是以學生為中心,從學生個性化的發展需要出發,尊重學生的主體地位和心理體驗,把教育人、發展人、鼓舞人與尊重人、理解人、關心人結合起來,尊重學生的個體人格、個人差異和個性自由,培養學生的主體意識、認識水平和精神境界,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和諧發展、自由發展。相反,如果思想政治理論課缺乏現代性的人本精神和人文關懷,很可能就會蛻變為冷冰冰的政治教條而招致學生的排斥,注定無以深入人心,整個教學效果就會趨于低效甚至無效化。
實際上,“以人為本”的價值理念和社會發展并非是一種對立關系。馬克思就曾強調:“應當避免重新把‘社會’當作抽象的東西同個體對立起來。”[13]因為社會并非抽象的存在物,而是由諸多現實的個人按照特定的分工體系組成的共同體。“在人的世界中,人不是附屬于某個凌駕于人的世界之上的超人主宰的附庸,人本身就是人的世界的根本、主體。”[14]個人的發展固然離不開社會共同體,但社會共同體的發展同樣有賴于個體的發展,并以個體的發展作為價值目標。否則共同體就會蛻變為壓制個體之尊嚴、獨立、自由的“異在”。
總之,在實現中國現代化的歷史任務中,“人的現代化”是根本,而衡量人是否現代化,就看其是否具備現代性的精神素養和能力,這又需借助教育過程的培養和激發。在當下高等教育的課程體系中,思政課不僅承載著主流意識形態的宣傳教育功能,也是啟迪學生思想、提升學生智慧、培育學生現代性精神的主渠道。因此,我們的思政課教學理應積極順應現代性的內在要求,著眼于培養具有理性精神、人文情懷和自由自覺的社會個體。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
[2][英]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M].田禾,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33.
[3][德]哈貝馬斯.現代性的哲學話語[M].曹衛東,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22.
[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74.
[6]李愛國,林亞梅.人的全面發展理論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啟示[J].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1).
[7][巴西]保羅·弗萊雷.被壓迫者教育學[M].顧建新,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2001:26.
[8]于偉,胡嬌.現代性的教育觀的危機與出路[J].教育科學,2004,(4).
[9][德]雅斯貝爾斯.什么是教育[M].鄒進,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3.
[10][德]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22.
[11][美]羅爾斯.正義論[M].何懷宏,何包剛,廖申白,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354.
[12]鄒進.現代德國文化教育學[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73.
[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02.
[14]夏甄陶.論以人為本[J].新華文摘,20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