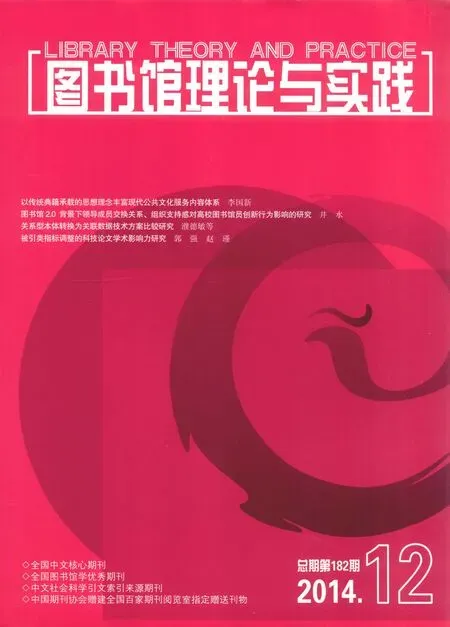歷代修志法規(guī)述評(píng)
●吳曉紅
(寧夏社會(huì)科學(xué)院,銀川750011)
歷代修志法規(guī)述評(píng)
●吳曉紅
(寧夏社會(huì)科學(xué)院,銀川750011)
修志;法規(guī);條例
2006年5月18日,國務(wù)院正式頒布新中國第一部修志條例《地方志工作條例》,使中華民族編史修志這一優(yōu)良文化傳統(tǒng)走上了依法修志的道路。本文將歷代中央政府頒布的主要修志政令及規(guī)定進(jìn)行整理述評(píng),從中不難看出,修志法令的出臺(tái)與志書體例一樣經(jīng)過了發(fā)育、豐滿、完善、成熟的漫長過程。
方志文化淵源流長,在兩千多年的漫長演變中,形成了橫排豎寫的特殊體例和述而不論的記述方法,重點(diǎn)記述一定行政管轄區(qū)域或一項(xiàng)專門行業(yè)范圍之橫切面內(nèi)容的文化載體,又稱“一方之全史”。古代方志其主要功能除資政、存史、育人外,還為“以備國史之征”,[1]45即為歷代大規(guī)模編纂國家正史提供資料,加之志書具有彰顯家鄉(xiāng)風(fēng)土人情之效,又從最初的官修發(fā)展為官民共修,編纂志書在全國各地普遍推廣,達(dá)到“無縣無志”和“無物無志”的一種罕見的民族文化特殊形式。歷代統(tǒng)治者非常重視編修志書,并為此制定頒布了一系列制度規(guī)定來推動(dòng)志書編修,使這種特殊的文化載體得以傳承下來。
1 志體形成前的歷代修志規(guī)定
據(jù)史載,漢代朝廷詔令地方官府編纂的《地志》(山川、物產(chǎn)、貢賦等)不僅是地方志的幼年形志,而且也算是中央指導(dǎo)修志最早的條令。[1]46據(jù)史料記載,漢代成書的《安定郡圖志》(已佚)為寧夏志書之祖。可見,偏居西北一隅的寧夏編史修志并不落后中原內(nèi)地。隋朝,朝廷為了加強(qiáng)中央集權(quán),發(fā)展經(jīng)濟(jì)文化,急需了解各地情況,于大業(yè)年間(606~616)“普詔天下諸郡,條其風(fēng)俗、物產(chǎn)、地圖,上于尚書”。[1]54這一政令促進(jìn)了各地圖經(jīng)的編修,隋煬帝親自督編了我國第一部官修總志《區(qū)域圖志》(已佚),即后世《一統(tǒng)志》的前身。[1]55
唐代對志書的編修期限和辦法有明確規(guī)定。建中元年(780),朝廷將原規(guī)定各州郡每三年編修一次圖經(jīng)報(bào)尚書省兵部職方的制度改為五年一修報(bào),并要求遇州縣增廢、山河改移等情況,則隨時(shí)報(bào)送。[2]854圖經(jīng)的內(nèi)容,要求備載古今事跡、地理山川、土地所宜、風(fēng)俗所尚。規(guī)定編修圖經(jīng)的經(jīng)費(fèi)一律從州縣雜罰錢中支出。其間,由宰相李吉甫主持編纂的《元和郡縣圖志》是唐代全國性總志的代表作。全書40卷,原有圖有文,南宋時(shí)圖佚,僅存文字,后人稱為《元和郡縣志》。該志以當(dāng)時(shí)的關(guān)內(nèi)、河南、河北等10道為綱,分別記述各府州縣的戶口、疆域道里、形勢險(xiǎn)要、地理沿革、山水湖泊、丘墓古跡、貢賦物產(chǎn)等。其體例對宋代《太平寰宇記》及元、明、清各代的《一統(tǒng)志》都有很大影響。由于朝廷重視修志,一些邊遠(yuǎn)地區(qū)也開始編修圖經(jīng),如在敦煌發(fā)現(xiàn)的《沙州都督府圖經(jīng)》和《西州圖經(jīng)》,就是記載今甘肅、新疆地區(qū)史事的早期志書。
宋代,方志內(nèi)容和形式基本定型,圖經(jīng)逐漸被“志”代替。朝廷于大觀元年(1107)創(chuàng)設(shè)九域圖志局,開國家設(shè)局修志之先河,并承襲唐代編修圖經(jīng)的制度,規(guī)定:“凡土地所產(chǎn),風(fēng)俗所尚,具古今興廢之因,州縣之籍,遇閏歲造圖以進(jìn)。”[2]856規(guī)定明確了三個(gè)要點(diǎn):一是固定了志書體例,即記(大事記)、志(專志)、傳(人物)、錄(附錄)、圖、表六體兼?zhèn)洌欢菍χ緯膬?nèi)容及纂修時(shí)間作了要求;三是正式將方志的名稱以“志”號(hào)名,至此,方志進(jìn)入定型和成熟階段。[2]160太祖、真宗、神宗、徽宗諸位皇帝均曾詔修志書,促進(jìn)了官修制度的實(shí)施。太祖開寶四年(971)正月,命知制誥盧多遜、扈蒙等重修天下圖經(jīng)。開寶八年(975)又詔寇準(zhǔn)修定《開寶諸道圖經(jīng)》。景德四年(1007)二月,真宗詔重修諸路圖經(jīng)。元豐八年(1085)七月,神宗詔令編成《元豐九域志》10卷。大觀元年(1107)徽宗為編修《九域志》,又諭各州縣編纂圖經(jīng)上報(bào)九域圖志局編成《四明圖經(jīng)》。
北宋初年成書的《太平寰宇記》在內(nèi)容和體例上都有發(fā)展和突破,記述的重點(diǎn)從地理轉(zhuǎn)到了人文歷史方面,“人物”和“藝文”逐漸占據(jù)重要位置,使地方志最終從地理學(xué)分離出來,在史學(xué)領(lǐng)域自成一體,可見,宋代方志對后世方志的影響。由于朝廷重視修志,多次詔修,方志編修空前發(fā)展,并形成了一定規(guī)模。其特點(diǎn),一是修志普遍形成傳統(tǒng),郡縣必修志;二是數(shù)量多,卷帙繁。如果一個(gè)地方?jīng)]有修志或編修不及時(shí),地方主官就會(huì)被問責(zé)。地方官員主持編修志書成為職責(zé)范圍內(nèi)的事。正因?yàn)槌⒑透骷?jí)官員十分重視編修地方志,宋代“今僻陋之邦,偏小之邑,亦必有記錄焉”。[3]
元朝統(tǒng)治者雖為少數(shù)游牧民族,但其深受中原漢儒文化影響,元世祖忽必烈曾采納大學(xué)士札馬剌丁“方今尺地一民,盡入版籍,宜為書以明一統(tǒng)”之諫,任用漢臣秘書少監(jiān)虞應(yīng)龍協(xié)助札馬剌丁主持編纂完成了我國修志史上第一部全國總志——《大元一統(tǒng)志》。全書以路和行省直轄府、州為綱,內(nèi)容舉凡建置沿革、坊廓鄉(xiāng)鎮(zhèn)、里至、山川、土產(chǎn)、風(fēng)俗形勝、古跡、人物、仙釋諸目等一應(yīng)俱全。[4]502此間,《開成府志》(已佚)應(yīng)為寧夏首部志書。
由此可見,經(jīng)濟(jì)繁榮,文化昌盛,盛世修志、志載盛世是方志文化發(fā)展的規(guī)律,為加強(qiáng)統(tǒng)治,國家對修志的要求也更加迫切,朝廷的各種指導(dǎo)具體的修志詔令應(yīng)運(yùn)而生。
2 明清修志法規(guī)性條例的出臺(tái)
明代是中國歷史上修志體系臻于成熟和修志制度正式形成的階段。明朝開祖皇帝在洪武三年(1370)就曾下令編修全國性總志。明永樂十年(1412),朝廷頒布了《纂修志書凡例》,這是現(xiàn)存最早的封建中央政權(quán)頒布的一項(xiàng)重要修志詔令。《凡例》規(guī)定,方志的編纂內(nèi)容應(yīng)包括17個(gè)門類,即:建置沿、分野,疆域、城池、里至,山川,坊郭、鄉(xiāng)鎮(zhèn),土產(chǎn)、貢賦,田地、稅糧、課程、稅鈔,風(fēng)俗、形勢,戶口,學(xué)校,軍衛(wèi),廨舍,寺觀、祠廟、橋梁,古跡、城郭故址、宮室臺(tái)榭、陵墓、關(guān)塞、巖洞、園地、井泉、陂堰、景物,宦績,人物,仙釋,雜志,詩文。[4]503明永樂十六年(1418),明成祖朱棣第一次以中央行政命令的形式頒布了《纂修志書凡例》,將編纂類目細(xì)分為21個(gè)門類,即: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山川,坊郭鎮(zhèn)市,土產(chǎn),風(fēng)俗,戶口,學(xué)校,軍衛(wèi),郡縣廨舍,寺觀,祠廟,橋梁,古跡,宦跡,人物,仙釋,雜志,詩文。[4]506《條例》固定了志書編修篇目,充分體現(xiàn)了方志“官修政書”的性質(zhì)。
此外,明朝在正統(tǒng)、景泰、天順年間均曾下詔修志,在弘治、正德、嘉靖年間還下令廣征志書,《寰宇通志》《大明一統(tǒng)志》就是在各地上報(bào)志書的基礎(chǔ)上編成的。不僅朝廷多次下詔修志,湖廣布政司左參政丁明也曾于嘉靖中期頒布《修志凡例》,浙江巡撫、河南汝寧府也曾令下屬府縣立即修志。由于朝廷三令五申,各地方志編修工作得到迅速發(fā)展。萬歷年間,張邦政就在(萬歷)《滿城縣志·序》中稱:“今天下自國史外,郡邑莫不有志。”藩封寧夏的朱元璋第十六子慶王朱栴編纂的《宣德寧夏志》為寧夏現(xiàn)存第一部志書,而且明朝寧夏鎮(zhèn)至少7次編修過全境的方志。
清代方志編纂與研究進(jìn)入強(qiáng)盛期,受明朝《凡例》影響,清廷也先后向全國頒布了各類修志規(guī)定。康熙、乾隆、嘉慶三次編纂《大清一統(tǒng)志》,每次纂修前,必先令各省、府、州、縣編修地方志,并三番五次督促按時(shí)進(jìn)呈,不得有誤。康熙十一年(1672),康熙帝采納保和殿大學(xué)士衛(wèi)周祚進(jìn)奏,令直省各督撫聘集夙儒名賢,接古續(xù)今,纂輯通志,同時(shí)將順治十八年(1661)河南巡撫賈漢復(fù)主修的《河南通志》頒為修志的樣式。康熙二十二年(1683),禮部奉旨檄催各省設(shè)局修志,并限期完成。雍正六年(1728)十一月,雍正帝針對各省志書采錄人物事跡明確要求:“登載一代名宦人物,較之山川風(fēng)土尤為緊要,必詳細(xì)確查,慎重采錄,至公至當(dāng),使偉績懿行,逾久彌光,乃稱不朽盛事。”[5]256還令根據(jù)志書編修的好壞,給予必要的獎(jiǎng)懲。不久又頒令各省、府、州、縣志書每60年重修一次。雍正十一年(1733)十月初八日,統(tǒng)志館草擬《修志條款》(15條),又稱《部頒例目》,由戶部傳發(fā)全國各省遵照執(zhí)行,方志界視其為修志“準(zhǔn)繩”。[6]677乾隆帝對纂修《一統(tǒng)志》極為重視,史臣進(jìn)呈稿本,都親自審閱,反復(fù)推敲,并提出修改意見。雍正六年(1728)十一月二十八日,朝廷頒發(fā)《雍正上諭》。[7]11雍正說:“朕惟志書與史傳相表里,其登載一代名宦人物,較之山川風(fēng)土尤為緊要,必詳細(xì)調(diào)查,慎重采錄,至公至當(dāng),使偉績懿行,逾久彌光,乃稱不朽盛事。今若以一年為期,恐時(shí)日太促,或不免草率從事。即如李紱修廣西通志,率意徇情,瞻顧桑梓,將江西仕粵之人,不論優(yōu)劣,概行濫入,遠(yuǎn)近之人,皆傳為笑談。如此志書,豈堪垂世”,[2]216從中可見,雍正為保志書質(zhì)量,對修志時(shí)間沒有做強(qiáng)行規(guī)定,“如一年未能竣事,或?qū)捴炼辍保⒁蠊賳T修志端正態(tài)度,修得不好則要“從重處分”,并對廣西巡撫李紱撰修的《廣西通志》提出批評(píng)。[1]80雍正十一年(1733)十月初八,在編修《大清一統(tǒng)志》時(shí),由于對“直隸各省府州縣戶口田賦、文武職官、公廨倉廒、營衛(wèi)兵數(shù)、監(jiān)場、土貢、土司等,與各書院、古跡、祠廟、寺觀中御賜匾額碑記”等資料“無憑查考”,內(nèi)閣一統(tǒng)志館向各省下發(fā)行查事項(xiàng)共十四條,要求中省“必須文到之日,限三個(gè)月內(nèi)條晰造冊報(bào)部送館,毋得遲滯,須至移會(huì)者”。
清朝對修志嚴(yán)格控制,州縣以上志書幾乎全為官修,私人編修的極少。省級(jí)志書《通志》以總督、巡撫領(lǐng)銜監(jiān)修,府、州、縣志則由知府、知州、知縣領(lǐng)銜纂修,修成后需呈報(bào)上一級(jí)審查。官府設(shè)有志局(館),一般由地方官員聘請文人學(xué)士或地方鄉(xiāng)紳編纂,也有的由地方官員親自編修。乾隆帝曾嚴(yán)禁私自編修刊印志書。光緒三十一年(1905),朝廷在原《部頒例目》的基礎(chǔ)上又頒布《鄉(xiāng)土志例目》,規(guī)定《鄉(xiāng)土志》應(yīng)包括“十五門”的內(nèi)容,還要求《鄉(xiāng)土志》要面向?qū)W堂學(xué)生普及傳授,“為后學(xué)者之感勸者是已”。[2]219清代除雍正、咸豐、同治三朝,其他各朝寧夏均有志書問世,尤以《乾隆寧夏府志》的流傳較廣,影響較大。[8]56
朝廷對修志規(guī)定的頻頻出臺(tái),促使各地紛紛制定相應(yīng)的細(xì)則用以貫徹實(shí)行和指導(dǎo)修志。康熙二十九年(1690),河南省巡撫衙門率先在省內(nèi)下發(fā)《通飭修志牌照》(23條);[2]215洪亮吉撰發(fā)了乾隆《登封縣志》敘錄;[7]14謝啟昆撰發(fā)了嘉慶《廣西通志》敘例;[2]216陳作哲撰發(fā)的光緒《聞喜縣志·原示》;[7]46黃彭年撰發(fā)了光緒《畿輔通志》凡例;[2]216張之洞撰發(fā)了光緒《順天府志》修書略例。[7]54
由此可見,清代編修志書,上至皇帝、一統(tǒng)志館,下至各級(jí)修志組織、主官、地方文人皆盡職盡責(zé)遵照執(zhí)行,在修志管理和法規(guī)建設(shè)方面較前代有較大的進(jìn)步,府志、州志、廳志、縣志等和基層的鄉(xiāng)志、里志、村志乃至各級(jí)專志、名山大川志、建筑物志、名優(yōu)土特產(chǎn)志等如雨后春筍般涌現(xiàn)出來,形成全國范圍內(nèi)無地?zé)o志、無物無志的空前盛況。
3 近代修志規(guī)定
民國時(shí)期,軍閥混戰(zhàn)、抗日戰(zhàn)爭及國內(nèi)戰(zhàn)爭導(dǎo)致局勢不穩(wěn),經(jīng)濟(jì)衰退,文化滯后,但對于編史修志,國民政府仍然先后頒發(fā)了編纂辦法。民國三年(1914),教育部即咨令各地編修鄉(xiāng)土志,一作學(xué)校教材,二供清史館征用。浙江省、黑龍江省專門成立通志局開始編修通志。民國六年(1917),北洋政府內(nèi)務(wù)部會(huì)同教育部通令各地修志。山西省公署率先下達(dá)編寫新志的訓(xùn)令,頒布《山西各縣志書凡例》,規(guī)定縣志要采用圖、略、傳、表、考5種體裁,酌分綱目。[7]69廣東成立通志館并于民國七年(1918)修成《續(xù)修廣東通志稿》19冊。
民國十八年(1929年),內(nèi)政部呈奉行政院轉(zhuǎn)奉國民政府令,頒發(fā)《修志事例概要》(22條)。[9]35《修志事例概要》對修志機(jī)構(gòu)設(shè)置、志書內(nèi)容、綱目、編修方法、審核辦法及文字表述、印刷等作了詳細(xì)規(guī)定。如要求各省建立通志館負(fù)責(zé)修志,要求輿圖由專人采用最新科學(xué)方法繪制,要編入有重要價(jià)值的照片和統(tǒng)計(jì)表;要據(jù)實(shí)編入天時(shí)發(fā)現(xiàn)的異狀,以供科學(xué)研究,但不得稍涉迷信,以期落實(shí)修志機(jī)構(gòu),提高志書的科學(xué)性和實(shí)用性。這些是封建王朝統(tǒng)治時(shí)期沒有要求也不可能要求的。修志體例概要的頒行,對督促推動(dòng)各地纂修志書起到了一定作用,使全國普遍開展了具體的修志工作。目前所見的民國志書,大都出于1929年至1938年這一階段。
民國三十三年(1944)5月2日,由內(nèi)政部公布、經(jīng)國民政府行政院第660次會(huì)議通過的《地方志書纂修辦法》(9條)[7]161出臺(tái),規(guī)定志書分省志、市志、縣志三種,省志30年一修,市縣志15年一修,編成的志書要報(bào)內(nèi)政部核實(shí)后方能印行。此次會(huì)議還通過了由內(nèi)政部轉(zhuǎn)發(fā)的《市縣文獻(xiàn)委員會(huì)組織規(guī)程》(12條),要求各省、市、縣未成立通志館的設(shè)立文獻(xiàn)委員會(huì),負(fù)責(zé)收集、管理地方文獻(xiàn),以備修志,并對征集材料范疇作了具體要求。同時(shí),指出通志館的組織機(jī)構(gòu)設(shè)置,也可按此“組織規(guī)程”參照執(zhí)行。[7]163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國民黨政府于民國三十五年(1946)7月16日由行政院第751次會(huì)議通過了《地方志書纂修辦法(修正)》(9條),并于同年10月1日修正公布。[7]173民國三十八年(1949)重新頒布了《地方志書纂修辦法》,規(guī)定省志30年一修,縣志15年一修。但此時(shí)的國民黨政府已搖搖欲墜,《地方志書纂修辦法》行如空文。
國民政府頒布的修志行政法規(guī),將志書種類定位省、市、縣三級(jí);纂修時(shí)間規(guī)定,省志每隔30年,市、縣志每隔15年續(xù)修一次;組織領(lǐng)導(dǎo)規(guī)定,在各級(jí)政府領(lǐng)導(dǎo)下,業(yè)務(wù)上歸同級(jí)文獻(xiàn)委員會(huì)指導(dǎo),具體工作在三級(jí)修志館的組織下進(jìn)行運(yùn)作;在志書的體例內(nèi)容和出版、印刷等方面作出14項(xiàng)要求,還規(guī)定志稿必須經(jīng)審定后方可付印;新志書出版后需分送行政院、內(nèi)政部、國防部、教育部、中央圖書館和有關(guān)部門備查、備案。[7]175從中不難看出,國民政府對修志工作的要求及管理已經(jīng)非常規(guī)范、合理,雖然所修志書在體例、內(nèi)容上仍屬舊志范疇,但還是反映了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新面貌和新特點(diǎn)。一是增設(shè)新內(nèi)容,如《民國江西通志稿》設(shè)置了地質(zhì)考,《民國邕寧縣志》設(shè)置了郵政、航政、電政、路政、商業(yè)團(tuán)體、最新學(xué)制等門類。二是創(chuàng)立“概述”,使志書七體兼?zhèn)洹|S炎培編纂《民國川沙縣志》時(shí),在堅(jiān)持原志書六體的同時(shí),又于各志之首創(chuàng)一體“概述”,“蓋重在簡略說明本志內(nèi)容之大要,而不盡闡明義例也。將使于此書者,讀概述后,進(jìn)而瀏覽全文,其繁者可以用志不紛,其簡者亦將推闡焉而有得,或竟不讀全文而大致了了”。[10]13三是圖表照片入志。張仁靜編纂的《民國青浦縣續(xù)志》,全境圖以1∶225000比例尺繪制,縣治圖以1∶55000比例尺繪制。《民國杭州市新志稿》首次編入了《近十年來本市茶葉出口數(shù)量及其價(jià)值表》《民國二十年杭州市商店家數(shù)分區(qū)統(tǒng)計(jì)表》等。《民國川沙縣志》編入數(shù)十種表格。照片入志書是民國首創(chuàng)。如柳詒徵等編纂的《民國首都志》收入照片75幅,有南京的鳥瞰照,街道、學(xué)校、醫(yī)院的照片;《民國邕寧縣志》,志首也收入照片20幅。
而偏居西北的寧夏,由當(dāng)?shù)鼗刈鍖㈩I(lǐng)馬福祥主持編修的《朔方道志》在全國也較有影響。該志于民國六年(1917)編成初稿,全書31卷加卷首計(jì)32卷近百萬字,民國十六年(1927)正式付梓。當(dāng)時(shí),寧夏當(dāng)局還頒布《凡例》(23條),對志書名稱、門類、篇目結(jié)構(gòu)、時(shí)空界限、體裁和圖例等均作具體規(guī)定。地方貫徹落實(shí)國民政府號(hào)召,率先制定相應(yīng)修志細(xì)則并編纂完成地方志書,可謂造福一方,功德無量。
4 當(dāng)代修志規(guī)定及《地方志工作條例》的頒布
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領(lǐng)導(dǎo)人十分重視地方志的編纂與利用。毛澤東提倡利用地方志提高領(lǐng)導(dǎo)水平,并倡議各地編修地方志。周恩來指出,要系統(tǒng)整理縣志及其他書籍中的有關(guān)科學(xué)技術(shù)的資料,做到“古為今用”。鄧小平提出,“摸清、摸準(zhǔn)我們的國情對社會(huì)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shè)的極端重要性”。為新方志編修指明了方向。1995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wù)委員李鐵映出任中國地方志指導(dǎo)小組組長,李鐵映明確指出:“修志工作絕不是可有可無的事,而是各級(jí)政府的職責(zé),主要是省、市、縣三級(jí)政府主要領(lǐng)導(dǎo)同志的職責(zé),是‘兩個(gè)文明’建設(shè)的重要組成部分。”“要堅(jiān)持‘一納入、五到位’,即把修志工作納入各地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計(jì)劃和各級(jí)政府的任務(wù)中。堅(jiān)持領(lǐng)導(dǎo)到位,機(jī)構(gòu)到位,經(jīng)費(fèi)到位,隊(duì)伍到位,條件到位。要堅(jiān)持黨委領(lǐng)導(dǎo)、政府主持、專家修志、‘三審’定稿制度。”中國地方志指導(dǎo)小組成員中增加了一些省市主管地方志工作的領(lǐng)導(dǎo)和各學(xué)科的著名專家學(xué)者,充分體現(xiàn)了黨中央和國務(wù)院對新編地方志工作的重視和關(guān)心。
同時(shí),在支持修志和制定指導(dǎo)性修志法規(guī)方面一直沒有停止摸索,國務(wù)院、中國地方志小組、中國地方志協(xié)會(huì)先后制定下發(fā)了多個(gè)辦法及規(guī)定,對地方志書的編修起到了積極的指導(dǎo)推動(dòng)作用。
(1)1956年,國務(wù)院科學(xué)規(guī)劃委員會(huì)在制訂《十二年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規(guī)劃方案》時(shí),將編修地方志列為20個(gè)重點(diǎn)項(xiàng)目之一。規(guī)劃委員會(huì)下成立了地方志小組,以加強(qiáng)對修志工作的領(lǐng)導(dǎo)。1958年10月,國務(wù)院科學(xué)規(guī)劃委員會(huì)地方志小組向全國發(fā)出了《關(guān)于新編地方志的幾點(diǎn)意見》,這是指導(dǎo)全國編修社會(huì)主義新方志的第一個(gè)帶有行政法規(guī)式的“條例”。《意見》明確指出:“方志是我國一項(xiàng)獨(dú)有的文化遺產(chǎn)”,“歷代續(xù)有編修”,新方志可分為省、市、縣、社4種,修志的組織應(yīng)在各省、市、縣黨委和人民委員會(huì)的領(lǐng)導(dǎo)下進(jìn)行,新方志應(yīng)貫徹執(zhí)行厚今薄古的原則等。還特別強(qiáng)調(diào)“應(yīng)當(dāng)考慮把修訂方志形成一個(gè)制度”。[4]268同時(shí),地方志小組起草了《新修地方志體例(草案)》《縣志編纂條例草案(討論稿)》下發(fā)征求意見。《草案》提供了六大門類較為完整的《篇目》供修志者參考。
(2)1983年4月,經(jīng)中央同意,中國地方志指導(dǎo)小組成立,具體負(fù)責(zé)指導(dǎo)全國的修志工作。1985年4月19日,國務(wù)院辦公廳以國辦發(fā)〔1985〕33號(hào)文件,轉(zhuǎn)發(fā)了《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院關(guān)于加強(qiáng)全國地方志編纂工作領(lǐng)導(dǎo)的報(bào)告》,通知對于有關(guān)條例的編制、隊(duì)伍、經(jīng)費(fèi)和出版等問題,明確“由地方各級(jí)政府根據(jù)實(shí)際情況,予以適當(dāng)解決”。[7]287表明修志工作開始真正納入各級(jí)人民政府的日常工作,也預(yù)示“修志條例”的制定和頒行開始走上官方文件運(yùn)行程序的軌道,標(biāo)志著全國編修社會(huì)主義新方志工作進(jìn)入一個(gè)嶄新的發(fā)展階段。中國地方志指導(dǎo)小組于國辦《通知》下發(fā)同日,討論、修訂并通過了《新編地方志工作暫時(shí)規(guī)定》(三章二十六條),于7月15日以中指組(1985)1號(hào)文件下發(fā)試行,以便全國各地在修志實(shí)踐中有所遵循。
(3)1997年5月8日,中指組召開二屆三次會(huì)議討論通過了《關(guān)于地方志編纂工作的規(guī)定》,并于次年2月10日以中指組名義下發(fā)《頒發(fā)〈關(guān)于地方志編纂工作的規(guī)定〉的通知》。同時(shí),宣布“原《新編地方志工作暫行規(guī)定》停止使用”。[4]274從此,新中國修志工作的法規(guī)性《規(guī)定》,由中央權(quán)威業(yè)務(wù)指導(dǎo)部門制定公布,在全國修志戰(zhàn)線貫徹執(zhí)行,對編修社會(huì)主義新方志事業(yè)起到了很大的推動(dòng)作用。
(4)2006年5月18日,國務(wù)院總理溫家寶簽發(fā)的第467號(hào)《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wù)院令》頒布了《地方志工作條例》。新中國編修地方志走過了半個(gè)世紀(jì)坎坷之路,終于迎來了依法修志的春天。《地方志工作條例》共22條,既各自獨(dú)立,又互相聯(lián)系,前后呼應(yīng)和互為補(bǔ)充。以高度精煉的文字、深邃的學(xué)術(shù)眼光和豐富的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對地方志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方面和新方志的基本要求都作出明確規(guī)定,內(nèi)涵豐富,重點(diǎn)突出,可操作性極強(qiáng),舉凡方志工作的地位、性質(zhì)、領(lǐng)導(dǎo)、職責(zé)、要求、目的和隊(duì)伍建設(shè)、續(xù)修年限、審查驗(yàn)收、出版?zhèn)浒浮鏅?quán)署名、讀志用志、獎(jiǎng)懲問責(zé)等方方面面。《條例》頒布后,各地政府紛紛出臺(tái)相應(yīng)的實(shí)施細(xì)則,寧夏于2007年11月率先出臺(tái)了《寧夏回族自治區(qū)〈地方志工作條例〉實(shí)施細(xì)則》,首次將每年的5月18日定為法定的“地方志工作宣傳日”。此舉走在全國前列,被中國地方志指導(dǎo)小組向全國推廣學(xué)習(xí)交流。
[1]來新夏.方志學(xué)概論[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2]黃葦.方志學(xué)[M].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1993.
[3]雷堅(jiān).中國的宮修地方志傳統(tǒng)與官員重視修志[J].廣西地方志,2009(4):21.
[4]中國方志大辭典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方志大辭典[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5]王曉巖.歷代名人論方志[M].沈陽:遼寧大學(xué)出版社,1986.
[6]黃葦.中國地方志辭典[M].合肥:黃山書社,1986.
[7]趙庚奇.修志文獻(xiàn)選輯[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
[8]范宗興,等.方志與寧夏[M].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9.
[9]傅振倫.中國方志學(xué)通論[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35.
[10]黃炎培.川沙縣志[M].臺(tái)北:臺(tái)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
K290
C
1005-8214(2014)12-0035-04
吳曉紅(1970-),女,寧夏社會(huì)科學(xué)院地方志辦公室副編審,主要從事寧夏地方史志編研。
2014-02-20[責(zé)任編輯]宋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