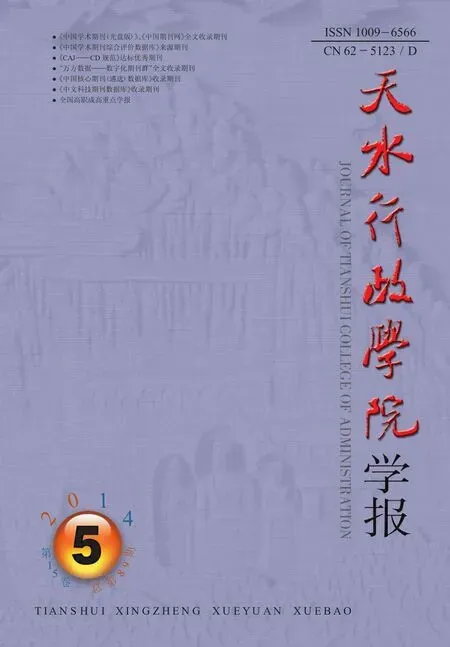環境行政規劃的斷片化分析
逯馭麟
(山東科技大學文法學院,山東青島 266590)
環境行政規劃的斷片化分析
逯馭麟
(山東科技大學文法學院,山東青島 266590)
環境問題日益成為經濟社會突出的問題,政府主導的環境行政規劃,是對環境問題最直接的指南針。可是在目前階段的環境行政規劃中,還存在著很多的問題亟待解決。本文先引入環境行政規劃的概念,分析目前我國環境行政規劃的斷片化現象,然后采用經濟學中成本—收益的分析模型對目前環境行政規劃立法與行政領域斷片化現象產生的原因進行分析,繼而得出如何解決環境行政規劃斷片化問題的方案。
環境行政規劃;斷片化;成本—收益分析
環境行政規劃是指為了在一定時期內實現某一特定的環境目標,環境行政主體做出的對其自身和對相對人具有一定的約束力,并要求環境行政主體在未來一定期限內必須采取具體措施予以實現的、關于某一環境問題的部署與安排[1]。現階段環境問題日益成為一個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問題,究其原因,其中最重要也是最關鍵的就是環境行政規劃不整合,存在管理、立法或執法的斷片化現象,導致環境問題仍然是末端治理為主,沒有體現現代環境法的預防為主的核心原則。
一、環境行政規劃的斷片化現象
政府行政規劃的斷片化現象起源于工業革命的時期,在那個時代,其專業的分工,功能布局分割的理念在一個多世紀的政府運行管理實踐中產生了十分積極的貢獻。在政府管理領域,“斷片化”指向的是部門內部各類業務間分割、一級政府各部門間分割以及各地方政府間分割的狀況[2]。這種斷片化的管理模式,基于一種專業分工,層級明確的政府組織結構模式,體現了當時的效率原則和一種理性的價值。但是這種行政管理模式,也產生了極大的弊端。
環境行政規劃的斷片化問題是指環境行政主體對某一環境問題的部署與安排,制定措施時,由于內部業務分割,導致不能統一規劃、統一部署、統一行動以致環境行政不能有效開展所出現的問題。
環境行政規劃的斷片化問題,既有傳統行政規劃斷片化自帶的原始弊端,又有其自身的新特性。
其一,更加強烈的部門主義色彩。按照傳統的行政分工的工作原則,環境行政職責涉及諸多的政府組成部門,每個部門各司其職,只做自己職責范圍內的事情。而每個部門都有自己利益上的訴求,單個的訴求集合起來,可能會達不到環境治理目標的整體訴求,忽視整體組織的使命。
其二,以管理本位的行政模式作為環境行政規劃的驅動模式,導致服務意識不強,解決問題能力較弱。每個環境行政職責部門只要在自己分攤的領域達到行政目標,完成既定的行政任務即可。行政的相對人一直處于一種被動的接受狀態中,并沒辦法提出自身的意見或者建議。人們對于行政公共服務沒有選擇的余地,只有接受。這樣的管理模式解決不了環境問題,達不到服務于社會的宗旨。
其三,內外溝通不暢,無法合理協調綜合治理。我國環境行政規劃體制呈斷片化之勢,不同的領域由不同的政府職能機關負責,而環保問題往往牽涉其中很多的領域,這就導致一項環境問題的產生,環保部門為了達到治理的目標,而需要溝通其他部門進行綜合治理。用經濟學的視角,把每個部門演化為一個合格“理性人”,他就不會涉足跟部門利益不相關的內容。反過來說,多部門同時治理一個領域的問題,就會出現政出多門,分別管理,難以到達預期的理想目標。
導致環境行政行為從規劃之初就產生斷片化問題的原因還有很多,諸如國家立法、行政執法以及公務員素質等要素。在此本文僅對影響環境行政規劃立法層面與行政管理層面上導致環境行政規劃斷片化問題進行研究。
二、環境行政規劃斷片化的立法之因
依法行政,是我國行政管理的主要原則之一。環境行政規劃,也應該在國家所制定的法律框架之內進行合理合法行政。環境法律的斷片化是導致環境行政規劃斷片化的主要因素之一。環境行政規劃的立法斷片化,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部門專業化立法不健全。目前環境立法只是集中在幾個問題多發的領域卻沒有涉及其他領域,在其各自的領域都有一定的成效,可是環境風險是各種各樣的,而能投入其中的行政資源卻是有限的,在投入一定比例資源后,其所產生的邊際效益正在逐步減弱,而其他沒有立法關注的領域的風險卻成幾何倍數的增加。
二是單方面的立法,很難解決復雜的環境問題。環境問題的產生與發展,不是單一因素造成的,我國的環境立法只關注了其中的幾個方面,沒有進行綜合性的立法,這對問題的解決造成了困難。
(一)從整體法律體系角度出發看環境法的不經濟性
在經濟學上,成本—收益分析,是比較提供一種公共物品的社會成本與社會收益的研究。它的目標是估算該項目對于作為一個整體而言的社會的總成本和總收益[3]。最后將各項目的比率加以比較,決定取舍,做出決策。
法律成本包含很多方面,從法治運作的角度闡述,它包括了立法、執法、守法成本。而在環境法律方面,高昂的立法成本是國家立法的普遍現象。司法成本在環境法的適用中,也和普通的法律一樣成本不菲。環境法的守法成本是在各項法律中最高的。我國目前的環境問題,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以犧牲環境帶來經濟高速發展的問題,是一種市場上越線發展帶來的超額利益的問題,而這種超額的利益,被目前的市場視為一種合理的利益,導致環境法運作成本增高。
法律規范、法律制度和法律活動歸根到底都是以有效利用社會資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會財富為目的,也就是以法律手段促進資源的最佳配置,促使有收益的結果發生,從而實現社會財富的最大值[4]。而環境法律的收益,與普通法律的收益,有著明顯的不同。一項環境保護法律的出臺,它的收益更多地體現在一種隱性的收益,增添更多的舒適感。但是這些利益反映在了賬單上,就變成人們為了遵守環境保護法,讓自己的既得利益變少了,導致整個法律的顯性收益偏低。
在國家宏觀立法角度上,環境立法與其他部門的立法有很大不同,它的高額成本與低效率的收益,導致環境立法在國家立法層面上的成本與收益不符,成本大于收益,這就致使了環境立法自身的先天不足,政策性強,難以實現,調控力度不夠。
(二)環境法律部門內的治理單一性
從環境法部門內的微觀角度看,環境法包括了污染防治領域、能源領域、資源領域等諸多方面,以污染防治領域為代表,分析環境法體系內部的成本-收益情況。
污染防治領域中,我國環境法調整的內容包括了水污染、大氣污染、固體廢棄物污染等諸多方面。在水污染領域,我國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在這部法律中,它的成本包括了:國家為了設立這項法律所進行的立法工作的投入;國家維持法律實施所投入的費用;公民、企業對于遵守這項法律所需要投入的成本。從這個角度看,我國水污染防治法的立法成本與司法成本與普通法律的投入成本大致相同,在守法成本領域,因為水污染防治法的調整領域單一,人們很容易重視并自覺接受法律的調整,所以該法守法成本與其他法律的守法成本并無明顯的漲幅。
水污染防治法的收益,表現為通過對水污染的防治、治理,人們會很明顯地感受到水域環境的改善,用水的安全性大大提高。該法的頒布,有效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明顯增加了幸福感,實現了資源的優化配置,最大限度增加了社會財富。這種近在眼前的收益,提高了整體水污染防治法的收益。整個水污染防治法的整體收益大于投入成本,是經濟的。
類比此項法律的成本—收益分析,對《大氣污染防治法》、《固體廢棄物污染防治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等諸多污染防治領域的法律規范進行成本—收益分析,他們在各自領域中,都達到了經濟性。
(三)綜合作用導致環境立法的斷片化
環境法作為一個整體的系統,每部法律都能實現自己領域的利益最大化,并不是代表整部法律的利益最大化。這就導致了在環境立法中,每個領域立法,都維護了本領域的利益,卻忽略了整體的環境法的本意。
在環境行政規劃立法角度上,通過此項分析,在整個宏觀立法領域,我國環境立法本身就存在著成本大于收益的先天不足,致使立法趨于表面化、政策化、不系統,導致斷片化。在環境法微觀領域中,我國環境法內部各項法律之間,追求各自領域的法律效果,在各自領域中有著很好的效果,但是形不成合力來綜合治理我國的環境問題,導致微觀上內部的環境立法的斷片化。
依照環境法律來指導環境行政的進行,在規劃之時,環境法律自身所帶來的斷片化問題的困擾,就使得環境行政先天不足。因此,所制定的環境行政規劃就會出現斷片化問題。
三、環境行政規劃斷片化的管理之因
從環境行政管理的角度出發,除了立法領域的不健全不系統導致環境行政斷片化之外,我國環境行政本身的缺陷也導致了環境行政在規劃之初就帶有斷片化的特點。主要問題集中在三個方面:
第一,不同的部門之間的不協調。我國的環保職能分割為三大方面:污染防治職能分散在海洋、港務監督、漁政、漁業監督、軍隊環保、公安、交通、鐵道、民航等部門;資源保護職能分散在礦產、林業、農業、水利等部門;綜合調控管理職能分散在發改委、財政、經貿(工信)、國土等部門。環境問題往往涉及各部門、行業和地區的權力和利益調整。環境治理方面的政績往往遭到多部門的搶功勞,但是環境惡化等方面的責任,卻常常是多部門之間互相推諉,逃避責任。
第二,同一部門的不經濟效應。在同一部門的內部,也會發生內部不經濟的情況。職能部門往往只盯住自己部門所管轄的項目,“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情況屢見不鮮,視野狹窄只限于實現自己規制的目標,在“最后一成”或者“最后一公里”的歷程上常常花費龐大的勞力和費用。這就會使邊際成本大量增高,而邊際效益卻趨近于0。而政府職能部門卻單一地只盯緊自己的行政目標不放,浪費大量的行政資源,如果把這部分行政資源節約下來,可以處理其他將要發生或者正在發生的環境風險,以跳出末端治理的怪圈。
第三,規制對象的斷片化。規制對象的斷片化是指,在進行環境行政規劃的過程中,只針對大型的排污企業進行規制,放棄了一些小型的企業,或者是市民階層。由于小型企業數量眾多,市民結構龐大,治理起來行政資源投入量大,成效緩慢。而大型排污企業的治理立竿見影,減排效果明顯,有利于當權者的政績名聲。當然,這樣做也是有合理成分的,大型企業的排污量大,治理起來效率高。政府在行政規劃之初,可以進行成本——收益分析,當到達臨界值的時候,就可以先把治理大型企業的流程進行“冷卻”處理,把更多的資金投入到小型排污企業和市民階層。
(一)宏觀環境行政的不經濟現象
上述問題,在表面上展現了環境行政規劃在管理斷片化的問題的不同方面,但是,其本質內容,都是基于環境行政規劃成本與其收益之間的關系。
行政成本是政府在維持自身運轉、履行職能的各種活動中所消耗的資源[5]。目前我國的環境行政體制來說,政府的行政成本無疑是巨大的,首先,有關環境管理的行政機關部門林立,人員繁多,正常的行政支出龐大。其次,地方政府為了追求地方上的經濟增長,也不愿意完全按照環境法律法規所規定的內容辦事,而地方上的環保機構隸屬于地方政府,這就導致一大部分環保的行政資源浪費在了內耗之中。最后,環保問題不單是一個部門的問題,它需要多個部門協同合作,在溝通與協助與行政程序上,也有一部分行政成本的損耗。
而環境行政管理的收益,則表現在具體的環境行政行為對社會的貢獻價值上。首先,在環境保護行政行為中,環保部門因為要行使行政執法權,對當地的企業進行處罰,這種處罰,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當地的GDP數額,降低了當地政府的財政收入,也使當地的企業對環保行政部門產生不滿。環保行政部門夾在其中,使行政工作人員不愿意去做這種“得罪人”的事,產生負面收益。其次,一項環境問題的出現,多部門協同治理后,環境恢復。一項環境修復的行政業績,由參與這次治理的諸多部門進行瓜分,這就導致利益分配不均,單個部門的環境行政收益不高。
國家的宏觀環境行政規劃的問題上,存在著環保行政不給力的現象,環保行政的職權被瓜分,又在內耗中減少,導致整體上的成本大于收益,致使很多有關職權的環保行政部門怠于行使行政職責,導致環境行政在宏觀方面的不經濟。
(二)微觀環境行政的“理性人”行為
以微觀的視角看環境行政的斷片化。以地方上的水利局為例,它的一項行政任務是保護當地的水資源,在水資源保護的單項問題上,它的行政投入也包含了整體上的正常投入如辦公人員經費、設施等,也存在當地政府因為想要追求地方上的經濟增長而變相忽略《水污染防治法》中所規定的內容辦事。但是,單就地方當地的水污染治理問題上,當地水利部門自己就可以完成行政執法任務,這就減少了不必要的溝通與內耗成本,變相地減少了整個水污染治理的環境成本。
作為水污染治理的單項的行政收益,是顯而易見的。這種行政執法之后明顯改善了水環境,增加了當地的生活質量,并且所有的行政收益都歸屬于當地水利部門,政績體現非常明顯,這就增加了當地水利部門積極采取措施進行水污染防治的行政動力。在當地水利部門進行水污染防治的單項的環境行政中,他的收益大于成本,這本身的環境行政規劃是合理的,是經濟的。
通過類推,我們可以認為其他的單項環保部門的行政規劃也是合理的,經濟的。
(三)宏觀方面與微觀方面共同作用導致環境行政規劃斷片化
每個微觀的環境保護部門在自己的領域中的經濟性反而是系統不經濟的根源,每個微觀環境行政部門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過程就舍棄了整體系統利益的最大化,致使整個環境行政沒有辦法形成一個合理有效的整體,而這種追求本部門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的行為就導致了目前我國環境行政就如同一個個部門塊狀堆砌成的整體。沒有有效的聯動機制,沒有辦法調動全局的力量來綜合治理環境問題,導致了微觀環境行政的斷片化現象。這種微觀的環境行政斷片化反映在了在宏觀的環境行政領域中體現為其不經濟現象,使整個環境行政的成本大于收益。
這種環境行政模式,在環境行政規劃開始就存在,并影響著環境行政規劃的開展,導致了環境行政規劃的斷片化問題,體現在具體問題中就出現以下現象:水利部門可以治理被污染的河流,但是被污染的河流致使魚類死亡就需要有漁政部門進行管理,被污染的河水污染了河道兩旁的農田,污染了耕地,被污染的河水,蒸發形成酸雨等問題,就不是水利部門自己能夠解決的了。每個部門在各自的領域中,都可以做到合理、經濟的行政,但是,這種單項的環境行政規劃,形不成整體治理大環境的合力。這就陷入到末端治理問題的怪圈,導致環境行政的斷片化現象。
四、解決環境行政規劃斷片化的對策
部署與安排環境行政規劃,包括了從環境行政立法角度指導環境行政規劃,包括從完善健全行政管理體系與機制來規避環境行政規劃斷片化問題,也包括了從政府調控市場,完善綠色市場導向的方式進行調控等諸多模式,這些模式的使用目的是為完成整個中國環境治理的大目標。每種方式應該綜合適用,如果只采用某種模式,又形成單方面調整環境行政規劃的斷片化問題,形成新的方面的斷片化。
(一)完善環境立法指導環境行政規劃
推進環境行政的法制建設,就是完善環境立法,用立法來指導行政,來制定出合理有效的以綜合治理為目標的環境行政規劃。
將立法活動視為一種積極的資源配置行為是經濟分析的前提。立法活動成本收益變化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法律的成本與收益會隨著法律的供給量的增加而增加,但是由于法律收益的增加額超過了成本的增加額,從而產生規模收益的傾向。第二個階段是,法律的運行中,法律的邊際收益在逐步減少,規模經濟降低,直至出現邊際收益為零,成本等于收益,在這一點上,可以視為立法的適度規模。第三個階段是,立法的成本的增加額大于收益的增加額,而導致規模的不經濟。
目前我國的環境立法正處于第一個階段中,即法律的成本與社會的收益隨著法律的供給量的增加而增加。我國環境法調整領域不斷擴展,由以前的以污染防治領域為主到目前涉足自然資源領域和生態保護領域,環境法曾經長期存在的各領域發展不夠均衡的局面正在大幅度改善[6]。但是目前的問題還是非常的突出,一是立法空白,在很多方面缺少相應的立法;二是立法規定太過原則,缺乏可操作性;三是法律規定不合理,甚至法律規定與立法目的相違背[7]。
統籌規劃,把可能出現的環境風險在其萌芽初期的時候,通過投入少量的資金和立法的配合的方式將其消彌于無形之中。當其爆發出環境危害時再去治理則又陷入了末端治理。為此,不能僅針對各領域進行斷片化考慮,而要把握環境風險的整體,將行政資源分配到能夠有效率地降低風險的領域[8]。所以,目前加大環境保護相關法律的立法的數量與質量,是實現環境法律規模經濟的有效措施。大力推動環境保護法律的法典化建設,讓環境保護法成為一個單獨的法律部門。讓環境問題從法制的角度統一把握,在進行環境行政規劃的時候做到有法可依。
(二)整合環境行政體制規避斷片化問題
改善環境行政體制,是在現有的環境行政模式之下,改變部門分立不能綜合治理現狀,讓環境行政規劃不是某一部門所制定的狹隘的部門行政規劃,而是有著全局視野的統一的對整體環境有著全局把握的環境行政規劃。
環境行政的不經濟性表現為成本支出的增長量過高,而行政效率和行政收益增長緩慢,致使整個的環境行政處于一種外部不經濟的狀態之中,要解決這種問題,通過部門之間的合作規劃,降低重復成本的支出額,降低由于部門溝通和信任問題所產的費用,增加辦事效率,提高行政收益,增加社會收益的形式,來改變目前規模不經濟的現狀。
環境行政機關在行政過程中,部門之間行政執法內容有交叉領域也有分散領域,使得環境行政的執法成本過高,而增加的收益額比成本的支出額要大,造成了規模不經濟。降低環境執法成本提高收益是現在環境行政執法的重要任務。
綜合性的環境問題,單靠環境保護部來承擔全國的環境保護任務,既不現實,也無可能。想要高效地對環境進行開發保護,就有必要建立一個跨部門、跨行業的環境保護的協同發展的部門。這種做法體現在環境行政成本中,會使行政資源重復支出額下降,部門之間聯系所需要的成本損耗降低,使環境行政的總體成本支出降低。
加強國家宏觀經濟部門的協調,包括與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國家能源委員會、科技部等部門的協調。協調的主要方面有:將環境保護重大計劃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產業發展計劃和國家重大科技計劃,解決環境保護的一部分甚至主要的國家資金投入問題[9]。
在政府職能部門中,公務員的升遷不能只看當地經濟發展程度,也要同時引入“綠色GDP”的概念。靠犧牲環境來換取經濟發展,用經濟發展來換取政績的做法要堅決摒棄,GDP的衡量應當扣除環境成本,做到可持續發展。
(三)全局出發進行風險總量控制
帕累托最優,是指在資源分配時的一種理想的狀態,當處于這種狀態時,無法讓至少一個人得到好處,而又不損害其他人的利益。想要在解決環境行政規劃的斷片化問題,就要先對環境風險進行總量控制。
對環境風險的總量控制的原因,反應在成本-收益分析模型上,就是在投入成本不變的情況下,減少環境問題出現的風險總量。把有限的環境行政規劃成本從無效率或者低效率的單項風險控制中解放出來,將其投入到邊際效益大的其他方向。這無疑會提高整個環境風險控制的總效率,增加總收益。這樣在不使任何一項情況變壞的前提下,讓其他各項享受環境行政資源投入所帶來的好處,以達到帕累托最優的狀態。
對環境風險進行總量控制,統籌全局發展。水污染風險、大氣污染風險、土地污染風險,作為環境風險的一個具體的部分出現,它的治理有很大的意義,但是在當邊際的治理費用和其邊際收益不能相符的時候,再就單一領域的高投入治理就沒有高效率,就不能得到帕累托最優的狀態,浪費了行政資源,卻沒有控制住整體的風險。在環境行政規劃之時,對各種環境風險進行統籌管理,從全局出發,用科學的方法,粗略測算出每種環境風險的投入和產出的臨界值,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把結余下來的行政資源投入到其他具有高效率的環境風險的治理上,這樣就會控制環境風險的總量。
在對企業排污治理中,也要運用總量控制的方法,不僅要治理大型排污企業,也要著眼小型排污企業。從社會整體費用的效果出發,當強行要求污染邊際消減費用高的企業降低污染,需要大量投資的時候,可以把這筆資金投入給污染邊際消減費用低的企業,在同樣的行政資源使用的前提下,這樣無疑是更有效率的,也控制了整個區域內的污染排放的總量。當然也可以運用環境容量使用權交易等方法進行總量控制,在環境行政規劃中運用經濟的方法,從而達到污染物的總量控制,在此再不贅述。
(四)運用市場調節機制反饋斷片化問題
在環境行政規劃之時,行政部門限于自身視野的局限性,并不能有效預見到可能出現的問題,導致斷片化的風險的提升。這樣就需要通過市場機制的反應來更加全面的進行環境行政規劃,預防斷片化問題。
進行綠色市場的輿論導向,引進推廣綠色營銷模式,綠色營銷除了傳統營銷的交換、滿足、價值、顧客、市場細分、定位和關系等基本分析工具之外,今天,它還包括生態、環保、健康、可持續發展等許多新概念[10]。
綠色市場的輿論導向的模式確立,引導企業和人們共同發現破壞環保的新問題,產生環境問題的新風險。政府部門通過大眾傳媒等介質進行信息采集與分析,看到目前環境問題的潛在風險和人民群眾所希望解決的問題所在,在調整部署環境行政規劃的過程中減少想當然的行政規劃,更加明確自身的目標,把一部分行政資源投入到在市場檢驗中發現的新問題與其潛在的風險領域。避免了由于行政部門自身視野的局限而導致的斷片化問題。
這樣以市場導向型的綠色市場的確立,社會輿論的熱烈響應,讓政府看到其本來沒有看到的有潛在環境風險的問題企業,這樣使政府避免了環境行政規劃的斷片化,提高了其環境行政規劃的整體性。●
[1]王雅潔.我國環境行政規劃研究[D].山東科技大學,2009.
[2]譚海波,蔡立輝.論“碎片化”政府管理模式及其改革路徑[J].社會科學,2010,(8):12-18.
[3](美)曼昆.經濟學原理[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228.
[4]謝地,杜莉,呂巖峰等.法經濟學[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77.
[5]郭婕.我國政府行政成本的現狀、成因及對策[J].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1):71-77.
[6]張梓太,李傳軒,陶蕾等.環境法法典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232.
[7]汪勁等.環保法治三十年:我們成功了嗎:中國環保法治藍皮書(1979-2010)[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354.
[8](日)黑川哲志.環境行政的法理與方法[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8.13.
[9]王樹義等.環境法前沿問題研究[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403.
[10]徐大佑,韓德昌.綠色營銷理論研究述評[J].中國流通經濟. 2007,(4):49-52.
Analysis of the Fragmentation Situation of Environment Administrative Planning
LU Yu-li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aw,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Qingdao266590,China)
Environmental issues are becoming remark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concerns in modern society. The government-orientated environment administrative planning is crucial in the areas that are related to these environmental issues.However,in the current environment administrative planning stages,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to be solved.This article not only introduced the concepts of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lanning,but also provided the analysis of the fragmentation situations of current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lanning. We used the economics cost revenue model to analysis the reasons why the fragmentation situation occurs in current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lanning legisl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areas.Finally,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mention above,the solutions to the fragmentation situation is provided.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lanning;fragmentation;cost revenue analysis
D922.6
A
1009-6566(2014)05-0040-06
2014-06-04
逯馭麟(1990—),男,山東濟南人,山東科技大學文法學院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