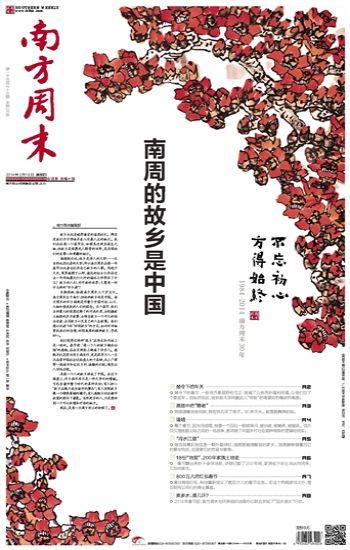市民權與城市化同步:障礙及其對策

編者按
既然倡導的是“人的城市化”,原則上,個人在某個城市穩定地工作與生活,就應該獲得所在城市的市民權。現實中,妨礙這一原則落地的,是普遍實行的將戶籍與福利捆綁的制度。當且僅當將相關福利沿著擴大個人選擇權與個人自負其責的方向有效剝離,才有可能從實質上或法律上廢止戶籍制度,讓市民權跟得上城市化的步伐。如何具體操作?作者給出了初等教育學位分配與部屬高校招錄改革的兩個實例。
◤在一國內部以戶籍維護大城市福利的政策不可能有長期穩定性,與其將來被自下而上的民權運動沖潰,不如自上而下因勢利導,立足早改徹底改,早日將各種福利從市民權中徹底剝離出去。
陳斌
市民權與城市化的鴻溝有多大?2013年10月,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數據中心發布中國城鎮化調查數據,稱非農戶籍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僅為27.6%,20年內僅多了7.7個百分點。而中國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劇增為2012年的52.57%,一年凈增一個百分點。在中國,市民不等于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前者比后者足足低了25個百分點。
市民不等于城里人
兩者的差額是外地移民。從宏觀上看,中國在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最壯觀的一幕是:數億農民工為了改善生活,放下了鋤頭,告別了家園與親人,從內地向東南沿海流動,成為新一代產業工人。這些被稱為“農民工”的群體用腳投票詮釋了“(推進城市化)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句話,并令“中國制造”崛起于世界。2009,美國《時代》雜志選中國工人為年度人物,致敬的正是這個群體。
不過,在市場經濟大潮中成為國家內部移民的并不僅僅是農民,還有城鎮與中小城市的市民。根據清華大學上述調查,中國每1000人中,農業與非農業戶籍人口分別為724人與276人,其中流動人口分別為152人與65人,分別占總流動人口的七成與三成。農業與非農業戶籍人口流動率分別為21%(152/724)與23.6%(65/276)。這是說,非農戶籍人口流動率比農業人口還要高。
所以,完整的圖景是這樣子的:不僅農村在向城市移民,城鎮與中小城市亦在向大城市移民,大城市尤其是東南沿海的大城市仍在膨脹中。所謂東南沿海再細化一下,無非是兩個重力中心:以上海為核心的長三角及以廣州與深圳為核心的珠三角。自然稟賦+全國人力資源的自由流動塑造了與塑造著這兩個都市區。
那么,填平這個鴻溝的最簡便方式難道不是順勢而為、令這些外地移民成為擁有完整市民權利與政治權利的本地市民嗎?難就難在HOW。
福利與市民權捆綁
我們當然可以說:市民權本質上是個憲法問題,是遷徙自由的題中應有之義。但在中國的語境之下,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市民權首先是個財政問題,即錢的問題,非常形而下,非常俗。目前,中國大城市的戶口很值錢,根據稀缺程度,市價在幾萬至幾十萬不等甚至更高。佛家說人身難得,投胎到中國后,最難得的當屬北京與上海的戶口。
2013年9月,《中國企業報》報道稱,多名戶口中介指出,如今北京戶口“20萬元都不一定能辦下來,多的花費40至50萬元也是正常的”。2013年10月16日,北京警方宣布,金吉列出國留學咨詢服務有限公司總裁朱某等人指使下屬出售進京指標,一個應屆畢業生北京戶口最高成交價要價72萬元,朱某等人以涉嫌“買賣國家機關公文罪”被刑拘。“漲姿勢”哈,原來進京指標或北京戶口是“國家機關公文”。
北京將進京指標多分配給國企、政府部門與事業單位,其次是所謂“高科技企業”。這些單位相當于每年獲得了財政補貼,一是可以通過倒賣(涉嫌違反目前的刑法)或掛靠(灰色地帶)套現獲利,二是招人允諾給價值不菲的落戶指標,應聘者愿意在一段時間內承受更低的工資。
大城市戶口值錢,是因為其附著的福利與管制值錢,包括但不限于:(1)一線城市北京與上海的考生有高校招錄優勢,為了進上海的8所部屬高校,江蘇山東的考生可能比上海的難兩到三個數量級。(2)大城市更多更優質的公立教育資源。(3)大城市推出的經濟適用房與“兩限房”等福利保障房,戶籍居民才有購買資格。(4)大城市商品住房限購,對戶籍居民與非戶籍居民實行非對稱監管,例如目前單身非戶籍居民在上海沒有購房資格。(5)大統籌、本地化醫保與養老社保,令大城市市民能廉價享受到本地更多更好的醫療服務。(6)城市政府創造的就業機會,戶籍居民有優先權。
沒有理由懷疑,由內地向東南沿海流動的絕大多數移民,不是沖著上海等長三角、珠三角大城市的上述福利去的,而是沖著那里更多更好的工作機會與商業機會去的;不是為了吃別人的福利,而是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不是為了讓別人為自己的生活負責,而愿意自負其責。但是,總有一部分移民在自己工作與生活的城市,感知著自己與本地人福利之間的巨大落差,追問一個憑什么:自己也在本地納稅了,憑什么不能享受這些福利?為什么不能這樣:一個人搬到一個城市,工作與生活一段時間后就擁有本地的市民權?
大城市政府的苦惱在于:在現行戶籍制度下,如果向外地移民完全放開市民權,那后果要么是為了讓所有人滿意而維持目前的福利水準,本地財政將迅速走向破產,要么是為了確保財政可持續性而聽任福利被迅速稀釋,這會招致本地戶籍居民強烈不滿。
弗里德曼命題
這充分印證了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提出的命題:福利國家與開放的邊界是不兼容的。這話不僅適用于一個國家,也適用于一國內部的一個城市,即:福利城市與開放的邊界是不兼容的。
不過,對一國來說,所謂的邊界主要是指國界線,能把你擋在外面就擋在外面;對越過國界線的非法移民來說,最后的邊界就是公民權。對一國內部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來說,所謂的邊界主要是指市民權。中國自廢除收容遣送制度以后,外地人在本地取得“暫住”或“居住”資格已不成問題,地理意義上的邊界消融了,但法律意義上的邊界即戶籍(將福利與市民權捆綁的政策)仍非常堅韌與牢固。
在自由市場條件下,自由移民當然是有效率的。來自國外(外地)的移民只要能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就能自負其責,此外還能給本國(本地)在經濟與稅收上做貢獻,這詮釋了“人本身是資產”,也根本不會有市民權滯后于城市化率25個百分點的情況。
但是,在這個國家(城市)有豐厚福利的情形下,如果容許自由移民,必然從國外(外地)涌入大量低產出甚至無產出的不能自負其責者,來分食福利。這就解釋了為什么世界各國尤其是福利國家普遍對外來移民有嚴格的限制。投資移民與技術移民是通過設立資產或人力資本的高門檻把高產出人士篩選出來,把低產出人士篩除出去,以最大化生產性努力、最小化分配性努力。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中國的大城市對戶籍人口總量與增量控制仍非常嚴厲,即使在外來移民維權的壓力之下,普遍采取的對策也不過是“積分入戶”。基本模式是:積分由基本分與加分組成。年齡越小、學歷越高、專業技術職稱和技能等級越高、繳個稅與社保年限越長的,基本分總積分越高;緊缺專業或工種有加分,這不是技術移民是什么?投資納稅或帶動本地就業有相應的加分,這是一種創新,是技術兼投資移民,誰能低估國人的創新能力呢?可見,有人調侃說“中國人要移民北京國或上海國難過移民澳洲”,倒有幾分真實的影子。
民權運動Vs因勢利導
不過,同樣是為了維持福利水準的邊界,戶籍相對于國界線在道義上更加虛弱、更加沒有說服力。2012年上海,因女兒占海特沒有上海戶口而不能在上海參加中考,一對父女站出來抗爭,得到了非上海戶籍網友的廣泛同情與聲援。可以想見,在外來移民多的大城市,類似的維權行為甚至維權運動將越來越多、越來越頻繁。
許多同情者將這種戶籍藩籬類比于美國與南非的種族隔離。在某種意義上也對,兩者均為制度性身份歧視。對中國來說,這更是一個極為重要與緊迫的提醒。美國與南非的種族隔離均是在民權運動的持續沖擊下被拆除的。這種以社會運動訴諸道義力量的方式來實現制度變遷的路徑,社會成本巨大,一是由于民權運動的路徑依賴,新管制者奉行“平等”訴求與“道義”原則高于效率原則是大概率事件,分配性努力壓倒生產性努力及反向歧視恐不可避免;二是管制者變更之后,囿于能力與觀念,局部(美國)甚至整體性(南非)的社會治安或公共治理與法治水平倒退將不可避免。上述因素令美國與南非一些城市均出現了黑人與窮人將白人與富人逼出市中心甚至整個城市以致某些城市衰落的情況。
如果中國未來不想承受此種代價的話,應認識到目前嚴控大城市戶籍人口與“積分入戶”只是權宜之計。因為這種在一個國家內部以戶籍維護大城市福利的政策不可能有長期穩定性,與其將來被自下而上的民權運動沖潰,不如自上而下因勢利導,立足早改徹底改,早日將各種福利從市民權中徹底剝離出去。
通過(1)高校招錄改革(詳見《部屬高校:招錄標準面前人人平等》),(2)公立學校入學資格改革(詳見《初等教育:學券將選擇權還給學生》),(3)取消目前給產權的經濟適用房等保障房,搞只保障最低收入者最基本居住條件的少量公租房,(4)退出違逆市場經濟的住房限購,(5)將目前大統籌的醫保與養老社保改為大賬戶或全個人賬戶的新加坡模式,(6)地方/全國公務員等公營機構雇員招考,對所有地方/全國納稅人開放,從實質或法律上廢止戶籍,讓每一個在所在城市有生存能力的人輕松獲得市民權,以促進經濟和諧與社會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