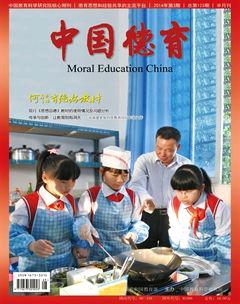“三位一體”的公民—西方公民概念的演變及述評
摘 要 在西方,公民概念的主體成員、權(quán)利內(nèi)涵、地理外延隨著歷史不斷地演變。在主體成員方面,公民由最初的少數(shù)特權(quán)階層逐漸拓展為全體國家成員;在權(quán)利內(nèi)涵方面,公民從單一的政治權(quán)利發(fā)展為多元權(quán)利;在地理外延方面,突破疆界限制出現(xiàn)了超國家的公民概念。這三個(gè)方面構(gòu)成了完整的當(dāng)代公民概念。
關(guān) 鍵 詞公民;主體成員;權(quán)利內(nèi)涵;地理外延
作者簡介 李惠,香港教育學(xué)院管治與公民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公民”一直是一個(gè)充滿爭議的詞匯[1],以致美國學(xué)者史坷拉感嘆道:“再也沒有哪個(gè)詞匯比‘公民這個(gè)概念在政治上更為核心,在歷史上更加多變,在理論上更具爭議。”[2]公民一般被界定為作為一國成員的法律和政治身份,以及所被賦予的權(quán)利與義務(wù)。在這一規(guī)定性概念下,西方公民的主體成員、權(quán)利內(nèi)涵、地理外延隨著時(shí)間、空間不斷拓展,逐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公民(公民身份)理論。本文試圖從公民的這三個(gè)維度出發(fā),探尋西方公民觀念的演變,以便更清晰地認(rèn)識(shí)“公民”的“三位一體”性。
一、公民的主體成員:
從特權(quán)階層到普遍的個(gè)體身份
在古希臘時(shí)期,公民是一個(gè)特權(quán)階層,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有資格成為公民。這部分人必須符合以下條件:首先,父母是城邦自由民的成年男性。如此限制把大量的未成年人、老年人、婦女、外邦人、奴隸工匠排斥在公民范圍之外[3]。其次,擁有一定的財(cái)產(chǎn)。擁有一定的財(cái)產(chǎn)既是成為公民的一個(gè)條件,也是參與公民生活的一種保障。梭倫在改革時(shí)提出按照財(cái)產(chǎn)的多少將雅典城邦的公民分為四個(gè)等級(jí):500蒲式耳階層、武士階層、士兵階層及勞動(dòng)者階層。第一、二、三階層的人可以擔(dān)任國家的主要官職,第四個(gè)階層的人不能擔(dān)任公職。不過,各等級(jí)公民都有權(quán)利參與公民大會(huì),成為陪審員,參與城邦政策的制定及法律審判。最后,參與公共政治生活。亞里士多德認(rèn)為“單純意義上的公民,就是參與法庭審判和行政統(tǒng)治的人,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其他要求”[4]。參與政治生活是公民最大限度地實(shí)現(xiàn)自身,成為一個(gè)好公民的重要途徑。需要指出的是,古希臘的公民概念是以雅典這個(gè)小城邦為前提的,即在這個(gè)地理面積很小、人們彼此了解的小城邦中,具有公民資格的人雖然占總?cè)丝诘拇蟛糠郑傮w數(shù)目還是很少的。他們可以在規(guī)定時(shí)間里很快地聚集在廣場上直接地參與政策的制定或一場審判。[5]這時(shí)的公民對城邦規(guī)模及總體公民數(shù)目有嚴(yán)格的限制,超過一定限制,公民這一身份甚至城邦民主將很難維持。
古羅馬公民與古希臘公民有很大的不同。在羅馬王政時(shí)期,居民分為兩部分:貴族是完全意義上的公民,享有政治權(quán)利,承擔(dān)服兵役和納稅的義務(wù)。平民、被保護(hù)人以及奴隸既不享有政治權(quán)利,也無需承擔(dān)服兵役和納稅的義務(wù)。后經(jīng)改革,無論是貴族還是平民,均按財(cái)產(chǎn)多寡來確定其社會(huì)地位。改革雖然使平民的地位有所改善,但平民仍不能享有與貴族同等的權(quán)利。到了共和國時(shí)期,平民為維護(hù)自身的利益與貴族進(jìn)行了激烈的斗爭,逐漸取得與貴族同等的公民資格。之后,隨著羅馬帝國的擴(kuò)張,羅馬公民不再局限于城邦內(nèi)的居民,而是擴(kuò)展到帝國境內(nèi)的所有自由民。但是,從公民的主體構(gòu)成來看,公民依然是成年自由民男子,婦女和奴隸依然不享有或部分地享有公民資格。[6]
歐洲中世紀(jì)時(shí),教會(huì)和封建君主是國家和人民的主宰,個(gè)體只是上帝的子民、封建君主的臣仆,而不是公民。直到十一世紀(jì)晚期,在新興城市中,一部分從事生產(chǎn)和貿(mào)易的居民,主要包括城市商人、自由民、手工業(yè)者、律師和學(xué)徒,積聚了大量財(cái)富。他們漸漸在國家經(jīng)濟(jì)生活中崛起,成為貴族、僧侶之外的第三種力量,即市民階層。經(jīng)濟(jì)上的優(yōu)勢使市民階層追求更多的自由及政治權(quán)利。他們不斷通過武裝斗爭或贖買等方式取得城市的自治權(quán),開始成為一支獨(dú)立的力量出現(xiàn)在政治舞臺(tái)上。市民階層在一定意義上是一種經(jīng)濟(jì)人,他們對自身權(quán)利的要求源于其商業(yè)的原因。正是這些經(jīng)濟(jì)上的要求促使他們積極地參與到城市的政治活動(dòng)中來,成為國家政治的參與者。現(xiàn)代意義上的公民概念正是在這種市民概念的基礎(chǔ)上出現(xiàn)的。[7]
到了十七、十八世紀(jì),資本主義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迫切需要大量自由、獨(dú)立的雇傭勞動(dòng)力。而以血緣和宗法關(guān)系為基礎(chǔ)的封建制度,只能產(chǎn)生具有依附人格的臣民,而不是公民。于是,西方爆發(fā)了一系列革命,推翻了封建專制制度,建立了資產(chǎn)階級(jí)制度,并以法律的形式將體現(xiàn)資產(chǎn)階級(jí)要求的自由、平等、獨(dú)立等理念確立下來。李榮安和福特把這一階段的公民稱之為“l(fā)iberal citizenship”,人民通過一系列的革命從而獲得權(quán)利成為公民。[8]在這個(gè)階段,公民范圍和數(shù)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法律規(guī)定只要是國家的居民,不論等級(jí)、家庭出身和財(cái)產(chǎn)多寡,原則上都是公民。
到了現(xiàn)代,“公民”作為一種法律概念被確定下來。國家通過法律(一般是憲法)確定其成員的公民身份及其所享受的權(quán)利和應(yīng)承擔(dān)的義務(wù)。這是因?yàn)閺?8世紀(jì)開始,“國家”和“民族”這兩個(gè)詞語開始聯(lián)系在一起,“公民”一詞脫離了城邦的意味,附屬于國家。公民是國家的公民,國家是由公民組成的。國家保護(hù)公民的權(quán)利得以實(shí)現(xiàn),而個(gè)體則要履行作為一個(gè)公民的責(zé)任與義務(wù)。從表面上看,如今公民已經(jīng)失去了它最初的特權(quán)資格本質(zhì),實(shí)現(xiàn)了人人都是公民。但是這種實(shí)現(xiàn)僅僅是法律層面上的,在現(xiàn)實(shí)中是否每個(gè)擁有國籍的國家成員都平等地?fù)碛袡?quán)利和義務(wù),這依然是一個(gè)問題。法律上的規(guī)定更多是一種形式,關(guān)鍵是其內(nèi)涵能否真正實(shí)現(xiàn)。
二、公民的權(quán)利內(nèi)涵:從單一到多元
在西方,公民的權(quán)利內(nèi)涵是隨著時(shí)間推進(jìn)而拓展的。大體來說,公民的權(quán)利可分為三代[9]:
第一代,民事權(quán)利與政治權(quán)利。民事權(quán)利是個(gè)體自由所必需的,包括人身自由、言論自由、思想與信仰自由、個(gè)體財(cái)產(chǎn)權(quán)以及司法訴訟權(quán)。根據(jù)馬歇爾的論述,這兩大權(quán)利發(fā)展主要發(fā)展于十八、十九世紀(jì)。民事權(quán)利是自由主義公民傳統(tǒng)所強(qiáng)調(diào)的中心,其核心是依法治理。一國之內(nèi)所有公民都平等地享受法律所規(guī)定的民事權(quán)利,當(dāng)其權(quán)利受到侵害時(shí),則可訴諸法庭尋求保護(hù)。政治權(quán)利就是個(gè)體參與政治事務(wù)的權(quán)利,如作為政治權(quán)威團(tuán)體的一名成員,或是作為這個(gè)團(tuán)體成員的選舉者。政治權(quán)利既是自由主義公民傳統(tǒng)的核心,也為共和主義公民傳統(tǒng)所強(qiáng)調(diào)。個(gè)體通過參與各種選舉從而參與到國家的政治決策當(dāng)中,真正實(shí)現(xiàn)其權(quán)利。民事權(quán)利與政治權(quán)利互為依賴,民事權(quán)利保障了每個(gè)公民能夠有充分的自由來處理個(gè)人事務(wù),而民事權(quán)利的實(shí)現(xiàn)則依賴于公民有平等的政治權(quán)利,參與到與他的生活直接或間接的關(guān)聯(lián)著的政治事務(wù)中去。[10]
第二代公民的權(quán)利包括社會(huì)權(quán)利與經(jīng)濟(jì)權(quán)利。社會(huì)權(quán)利與經(jīng)濟(jì)權(quán)利組成馬歇爾所謂的公民身份的社會(huì)要素。社會(huì)權(quán)利指賦予個(gè)體的社會(huì)福利,包括教育、住房、健康方面的權(quán)利。經(jīng)濟(jì)權(quán)利則指個(gè)體在市場上的消費(fèi)權(quán)、獲得勞動(dòng)報(bào)酬的權(quán)利、參與勞動(dòng)管理及獲得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福利的權(quán)利。社會(huì)權(quán)利與經(jīng)濟(jì)權(quán)利主要發(fā)展于二十世紀(jì)。二者是物質(zhì)性的權(quán)利,是個(gè)體得以生存的基本保障,是公民民事權(quán)利與政治權(quán)利實(shí)現(xiàn)的前提條件。社會(huì)權(quán)利與經(jīng)濟(jì)權(quán)利的實(shí)現(xiàn)依賴于國家的教育體系和社會(huì)公共服務(wù)體系。法律對社會(huì)權(quán)利與經(jīng)濟(jì)權(quán)力的保護(hù)是有限的,但目前也缺乏一個(gè)非法律的保護(hù)體系來確保公民的社會(huì)權(quán)利與經(jīng)濟(jì)權(quán)利的真正實(shí)現(xiàn)。大多數(shù)社會(huì)權(quán)利與經(jīng)濟(jì)權(quán)利的實(shí)現(xiàn)是與公民個(gè)體聯(lián)系在一起的,即國家賦此權(quán)利于公民個(gè)體,但其具體實(shí)現(xiàn)卻依賴個(gè)體自身。教育權(quán)就是一個(gè)很好的例子。國家法律規(guī)定每個(gè)人都有受教育權(quán),但具體到個(gè)體自身,他或她卻依然可以自我決定是否去實(shí)現(xiàn)這一權(quán)利。在這過程中,國家的法律體系只能為其教育的權(quán)利的實(shí)現(xiàn)提供公平的機(jī)會(huì)與條件,在義務(wù)教育之外不能強(qiáng)迫個(gè)體去接受教育。
第三代公民的權(quán)利包括文化權(quán)利、環(huán)境權(quán)利等。馬歇爾在1949年對第一代和第二代公民的權(quán)利進(jìn)行了經(jīng)典而詳盡論述,但在1949年之后的西方世界,新的移民浪潮、全球環(huán)境等一系列新的問題出現(xiàn),不斷挑戰(zhàn)以往的公民權(quán)利內(nèi)涵。如新移民對傳統(tǒng)文化融合的反對,呼吁尊重民族、文化特色,保持文化的多元性。而在面對全球環(huán)境污染問題時(shí),僅靠一國之力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因?yàn)榄h(huán)境污染的影響范圍往往超過國家界限,需要世界各國通力合作,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這些問題是馬歇爾當(dāng)時(shí)所沒有預(yù)見到的,因而他未將這些問題納入公民權(quán)利的考慮范圍之內(nèi)。因此,到了二十一世紀(jì),公民的文化權(quán)利和環(huán)境權(quán)利開始擴(kuò)展。文化權(quán)利是針對不同的種族、文化、民族和語言的群體提出的,認(rèn)為少數(shù)民族族群有權(quán)利保持特有的文化和語言特色,從而獲得真正的平等。文化與族群權(quán)利的加入既拓展了馬歇爾公民權(quán)利的內(nèi)涵,也體現(xiàn)了公民是一個(gè)漸進(jìn)性概念,它的拓展以促進(jìn)社會(huì)平等為目的思想的體現(xiàn)。[11]此權(quán)利通過《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和《經(jīng)濟(jì)、社會(huì)、文化權(quán)利國際公約》兩個(gè)國際性文件得到了法律上的確認(rèn)。環(huán)境權(quán)利則強(qiáng)調(diào)兩個(gè)方面:一個(gè)方面是當(dāng)個(gè)體因環(huán)境污染而受到傷害時(shí),則有獲得賠償?shù)臋?quán)利;另一方面則強(qiáng)調(diào)各國之間通力合作,保護(hù)地球環(huán)境,為了我們的鄰國,也為了下一代。
三、公民的地理外延:從一國到全球
十八世紀(jì)西方國家開始探討國籍是否為公民的標(biāo)準(zhǔn)。“公民”一詞從此便和民族國家聯(lián)系在了一起,限定在一國的地理疆域之內(nèi)。到了十九、二十世紀(jì),伴隨著全球化,跨國政治經(jīng)濟(jì)組織的出現(xiàn),移民浪潮的興起,公民身份不再受到國家地理疆界的限制,出現(xiàn)了“超國家區(qū)域性公民”與“全球公民”的概念。“超國家公民”概念的提出者M(jìn)ary Rauner認(rèn)為,這個(gè)概念不再將公民作為一國成員,而是把個(gè)體作為一個(gè)獨(dú)立的人而存在。[12]
首先,在歐洲,隨著歐盟的建立,歐洲公民這種全新的超國家區(qū)域性公民出現(xiàn)。這種公民雖然不是法律意義上的,但卻被歐共體和歐盟委員會(huì)所承認(rèn),并在1961年之后經(jīng)常出現(xiàn)于歐盟的文件中。這種公民在歐盟通過四種形式得到發(fā)展:第一,歐洲人權(quán)法庭的建立和《歐洲人權(quán)公約》的通過,使保障歐洲公民人權(quán)成為現(xiàn)實(shí)。《歐洲人權(quán)公約》第25條明確規(guī)定:委員會(huì)可以受理由于締約國一方破壞本公約規(guī)定而致受害的任何個(gè)人、非政府組織或是個(gè)人團(tuán)體向歐洲理事會(huì)秘書長提出的申訴。第二,歐洲議會(huì)成立,歐洲公民可以參與議會(huì)選舉。起初歐盟的公民是通過本國議會(huì)參與選舉,但隨著歐洲通訊委員會(huì)的建立,讓歐盟公民直接參與歐洲議會(huì)的選舉成為可能。第三,《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將歐洲公民這一形式制度化。《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第8條規(guī)定了作為一個(gè)歐洲公民所具有的權(quán)利:歐盟公民無論居住在歐共體的哪個(gè)成員國,在歐洲選舉和市政選舉中都有選舉權(quán)和被選舉權(quán),承認(rèn)任何公民有在歐洲議會(huì)請?jiān)傅臋?quán)利。[13]
其次,世界公民這一觀念由夢想變?yōu)楝F(xiàn)實(shí)。世界公民概念最早見于斯多葛學(xué)派的論述中,但此時(shí)這種公民僅僅是一種烏托邦夢想。到了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新斯多葛學(xué)派論述學(xué)派再次提出世界公民的觀念,其中最有影響的當(dāng)屬Justus Lipsiu,他宣稱“整個(gè)世界是我們的國家”[14]。在啟蒙運(yùn)動(dòng)時(shí)期,世界公民這一夢想受到洛克與康德等大思想家鐘愛。洛克在論自然法則時(shí)提出:“人類是屬于一個(gè)共同體,他們組成了一個(gè)區(qū)別于其他生物的社會(huì)。”[15]康德提出三種類型的法律,其中第三種就是全球法律。這種法律建立在兩個(gè)基本原則基礎(chǔ)之上:第一,隨著人類的遷徙,所有的人類都有權(quán)利受到他所到達(dá)的任何國家的禮遇;第二,因?yàn)榇嬖谝粋€(gè)共同體,世界任何一個(gè)地方的人濫用其權(quán)力都會(huì)被其他地方的人感受到。第二個(gè)原則所強(qiáng)調(diào)的全球公民責(zé)任在今天特別受到關(guān)注。到了十九世紀(jì),兩次世界大戰(zhàn)使世界公民的對立面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受到過度的宣揚(yáng)。國家之間的敵意沖突大增,世界公民的觀念很難找到其發(fā)展的空間。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之后,受到全球利益驅(qū)使以及聯(lián)合國這一全球性政治組織的作用,全球公民的觀念再次被提出。到了二十世紀(jì),世界公民真正從夢想變?yōu)楝F(xiàn)實(shí)。這是因?yàn)椋环矫嫒颦h(huán)境問題成為人們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保護(hù)環(huán)境、可持續(xù)發(fā)展需要全人類的共同努力。共同的實(shí)現(xiàn)責(zé)任,讓世界公民不再是一個(gè)口號(hào)。另一方面,隨著冷戰(zhàn)的結(jié)束,兩大政治陣營對立的局面消失,更多全球性合作組織出現(xiàn),讓國家之間的聯(lián)系更加緊密,一個(gè)世界共同體“地球村”已經(jīng)形成,這讓世界公民有了其存在的客觀條件。在當(dāng)前世界公民的實(shí)踐中,聯(lián)合國這一全球組織發(fā)揮著重要的實(shí)際重要。特別是其1948年通過的《人權(quán)宣言》明確規(guī)定了作為一個(gè)世界公民所具有的基本權(quán)利。在此基礎(chǔ)上,聯(lián)合國人權(quán)組織積極在世界各國發(fā)動(dòng)人權(quán)運(yùn)動(dòng),采取各種措施保護(hù)弱勢群體作為世界公民的基本權(quán)利,這讓“世界公民”一詞真正走入平常人視野,也讓世界公民真正成為一種現(xiàn)實(shí)。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公民概念在西方社會(huì)的發(fā)展基本上是隨著歷史的發(fā)展而發(fā)展的。公民主體成員方面的發(fā)展主要集中于古希臘時(shí)期到十七、十八世紀(jì),在這一漫長的歷史中,公民的主體成員隨著個(gè)體不斷爭取與斗爭不斷擴(kuò)大增加,從最初少數(shù)的特權(quán)階層、貴族,到大量自由民、城市市民的加入,再到所有國家成員都成為公民。到十八世紀(jì),公民的主體成員已經(jīng)基本上確定為所有的國家成員。在此之后,關(guān)于公民的爭論與發(fā)展就開始轉(zhuǎn)移到其權(quán)利的內(nèi)涵及地理外延之上了。公民的權(quán)利從十八世紀(jì)追求個(gè)體自由民主的民事權(quán)利,到十九世紀(jì)拓展到政治權(quán)利。到了二十世紀(jì),公民權(quán)利則由政治領(lǐng)域拓展到經(jīng)濟(jì)社會(huì)領(lǐng)域,把經(jīng)濟(jì)與社會(huì)這類物質(zhì)權(quán)利也包括在內(nèi)。到了二十一世紀(jì),面對新的全球移民和環(huán)境問題,文化權(quán)利與環(huán)境權(quán)利的概念開始出現(xiàn)。在公民的地理外延方面,十八世紀(jì)開始確定以國籍、國界作為公民的地理外延,但到了十九、二十世紀(jì),受全球化的影響,公民的這一地理外延逐漸被打破,超國家的區(qū)域性公民與全球性公民概念開始出現(xiàn)。
由此可見,在西方,公民是一個(gè)不斷發(fā)展的概念,但其發(fā)展卻一直圍繞主體成員、權(quán)利內(nèi)涵、地理外延這三個(gè)方面。這三個(gè)方面構(gòu)成了一個(gè)一體化的公民概念。我們在理解公民這一概念、進(jìn)行公民教育課程的設(shè)計(jì)及教學(xué)時(shí),一定要全面地看待公民的這三個(gè)維度,同時(shí)必須認(rèn)識(shí)到這三個(gè)維度的具體內(nèi)容并非一成不變,而且在不久的將來,其必將出現(xiàn)新的發(fā)展延伸。
參考文獻(xiàn):
[1]Beck.Morality and Citizenship in Education[M].London: Cassell,1998:102-106.
[2]Shklar.American Citizenship: The Quest for Inclusion[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1.
[3]Aristotle.The Politics[M].London:Penguin Books,1962:39-42.
[4]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M].苗力田,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1996:74.
[5]Heater.A Brief History of Citizenship[M].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4:18.
[6]張博穎,陳菊.西方公民觀與公民道德觀的歷史演變:從古希臘羅馬時(shí)期至17、18 世紀(jì)[J].倫理學(xué)研究, 2004(6):88-94.
[7]張鎮(zhèn)鎮(zhèn).公民概念的變遷與人的發(fā)展[J].學(xué)校黨建與思想教育,2010(5):65-67.
[8]Lee,F(xiàn)outs.Education for Social Citizenship:Perception of Teachers in the USA, Australia,England,Russia and China[M].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5:45.
[9]Oliver,Heater.The Foundation of Citizenship[M].New York,London,Toronto,Sydney, and Tokyo,Singapore: Harvester Wheatsheraf,1994: 50-55.
[10]Marshall,Bottomore.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M].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40.
[11]Banks.Diversity,Group Identity,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a Global Age[J].Educational Researcher,2008(37):3.
[12]Rauner.Citizenship in the Curriculum:The Globalization of Civics Education in Anglophone Africa:1955-1995[M].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 1997:104-107.
[13]馬斯特里赫特條約,1991[EB/OL].[2013-01-01].http://baike.baidu.com/view/9909.htm.
[14]Lipsius.Two Books of Constancie[M].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39:96.
[15]Locke.Two Treatises of Civil Government [M].London:Dent,1965:80.
責(zé)任編輯/劉 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