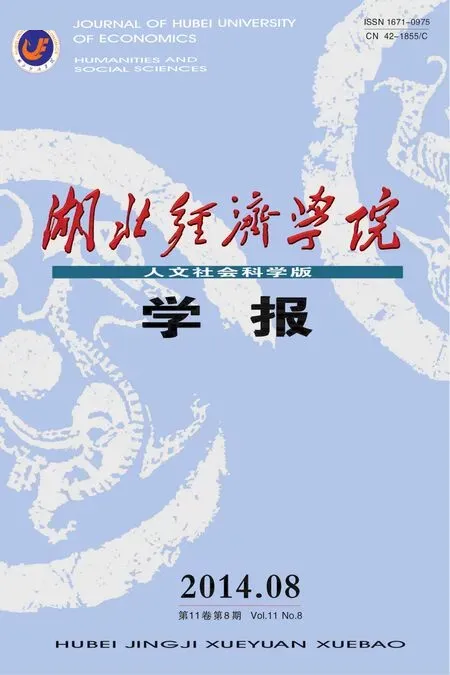關于人民幣幣值變動問題的實證和理論分析
高 峰
(安徽財經大學 金融學院,安徽 蚌埠 233030)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貨幣的價值通常表現為兩種形式,一種是以國內物價反映的對內價值,另一種是用另一國貨幣表示的對外價值。從理論上說,一國貨幣的對內價值和對外價值是統一的。但根據近年來的數據,我們發現人民幣對內和對外幣值表現出不完全一致的現象,而且顯現出強化的趨勢。
一、文獻綜述
關于人民幣幣值變動問題國內外專家學者一直對此非常關注,章昌裕(2012)認為外匯占款促使央行不斷增發人民幣,過大的貨幣供給量導致國內流動性過剩,通貨膨脹壓力增大,人民幣進入“外升內貶”怪圈。[1]張明(2012)提出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依然面臨著升值的內在動力,一旦央行沖銷行為不能持續,中國政府就必須在人民幣名義匯率升值與更高的通貨膨脹之間作出選擇。[2]林苗峰(2013)認為涉外體制不對稱、生產要素價格長期被低估、經濟發展失衡等原因導致了人民幣內外價值偏離。[3]肖文和潘家棟(2013)通過建立國內外利益集團博弈模型,得出外部壓力能促進人民幣升值的結論。[4]
本文在借鑒眾多學者研究的基礎上,運用實證分析法,并從理論上對人民幣幣值變動問題進行討論。
二、人民幣幣值變動問題的實證分析
(一)人民幣幣值變動的經濟表現
第一,人民幣幣值變動的對外表現。2005年7月21日,我國進行了重要的匯率制度改革,開始實行了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同時宣布人民幣升值約2%。從此,人民幣進入了升值的階段。2012年4月,央行決定將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的交易價幅度由5‰提高到1%,浮動區間的擴大進一步增強了人民幣匯率的彈性,也為人民幣升值創造了條件。人民幣名義匯率由匯改之前的100美元兌換827.65元人民幣升值為現在的100美元兌換613.93元人民幣,升值幅度竟然累計達到了25.82%。
第二,人民幣幣值變動的對內表現。關于人民幣的對內價值,其中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在2002年出現小幅下降之后連續出現快速增長的趨勢,并在近幾年保持在3%左右的增長率;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在2001和2002年發生微幅下調后,連續保持上升的態勢,其中出現了兩次超過6%的高速增長率。證券綜合指數和房地產價格指數也出現了增長的趨勢。
(二)人民幣幣值變動內外表現差異的原因
第一,人民幣對外升值主要由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以投資和出口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方式、國內外利差的擴大等因素導致的。
在近十幾年,我國GDP每年保持著較快的增長速度,使外資產生了較高資本回報率的預期從而增大對我國的投資,使得FDI迅速地增長,大量國際資本流入了國內。
此外,我國滯后的投融資體制和不發達的金融體系,導致了利率沒有真正實現市場化,使得利率未能真實反映資金的成本,從而刺激了投資需求的增加。大量的投資由于主要集中在出口加工貿易業和制造業等,所以在促進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在不斷地提高供給水平。不斷增長得供給逐漸超出國內需求,造成了“剩余產出”以出口的方式被國外吸收,從而引起經常項目出現順差。另外,我國在吸引外資方面設立的便利條件,極大得鼓舞了外資對我國的直接投資,也促成了資本和金融賬戶出現了順差現象。總之,在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影響下,我國外匯儲備迅速增長。在現行的結售匯制度和嚴格資本管制情況下,流入我國的外匯增加了對人民幣的需求,人民幣面臨著較大的升值壓力。
央行為了控制貨幣供應量的過快增長以及預防通貨膨脹,連續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國內利率也隨之升高。在國外,以美國為主要代表的西方國家不斷實施量化寬松政策,用美元購買中、長期性金融資產,導致利率降低到極低的水平。利差的存在刺激了大量的美元為了獲得更高的資本回報率而流入中國,人民幣面臨著巨大的升值壓力。
第二,人民幣對內貶值與國內貨幣超發、需求拉動型和輸入型通貨膨脹等因素密切相關。
連續增長的外匯儲備使得央行只好通過增加基礎貨幣的投放來減輕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因此國內的貨幣供應量迅速增大。貨幣供給決定總需求,總需求決定總供給,而貨幣供給的增長速度超過GDP的增長速度,導致了國內消費品市場價格和投資品價格不斷升高。盡管央行采用公開市場操作業務,發行央行票據和運用正回購等,回籠貨幣,但是由于受到規模、成本及其期限的制約,并不能有效得控制貨幣的過快增長和通貨膨脹。
在出現貨幣超發,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率大于經濟實際增長率的時候,閑置的貨幣便流向了房地產、證券等市場,刺激了建筑業、鋼鐵業和運輸業等行業需求的增加,形成了需求拉動型通脹。另外,美國的量化寬松政策使大量美元流向國際市場,推動了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升高。對進口依賴性較強的我國,進口產品價格的提高抬高了國內物價。[5]
三、人民幣幣值變動問題的理論思考
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宏觀政策目標分為內部均衡和外部平衡,能否正確處理內部均衡和外部平衡的關系影響著眾多經濟變量。其中,出現人民幣外升內貶問題恰恰體現了內部均衡與外部平衡存在著矛盾。因此,為了更好地從內外均衡角度分析人民幣外升內貶問題,本文運用蒙代爾-弗萊明模型進行分析。
(一)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的具體內容
蒙代爾—弗萊明模型是蒙代爾和弗萊明在封閉條件下的IS—LM模型基礎上,引入了外部平衡分析而形成的,是宏觀內外均衡分析的重要理論框架。
模型的假定。模型假定商品的價格保持不變,且產出由總需求決定。由此可看出該模型是分析短期內外均衡的工具。
商品市場均衡,即IS曲線。商品市場均衡指的是國內總供給等于總需求, 表示為:Y=(A0-bi)+(ce-ty),b>0,c>0,t>0,其中(A0-bi)表示國內總需求,(ce-ty)表示凈出口。方程可以轉換為:,在i-Y平面中,IS曲線的斜率為負數,IS曲線向右下方傾斜,且隨著匯率的減小(本幣升值)而向左移動。
貨幣市場均衡,即LM曲線。貨幣市場均衡指的是居民對貨幣的名義總需求等于總供給,可以表示為:Ms=p(ky-hi),k>0,h>0,等式左邊表示貨幣總供給,等式右邊代表名義貨幣總需求。其中可設p=1,則方程可以改寫為:,在i-Y平面中,LM曲線斜率為正數,LM曲線向右上方傾斜,且隨著貨幣供給的增加而向右移動。
國際收支平衡,即BP曲線。國際收支平衡是指經常賬戶的資本凈流入等于資本和金融賬戶的資本凈流出,可以表示為:(ce-ty)+w(i-i*)=0,其中 c>0,t>0,w 代表資本自由流動程度,i*代表國外利率。在i-Y平面中,BP曲線的斜率為正,BP曲線向右上方傾斜,且隨著匯率的減小向左移動。另外由于我國實行嚴格的資本管制,資本自由流動程度較低,所以在在同一i-Y平面中,BP曲線比LM曲線更加陡峭。
(二)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的運用

圖1:財政政策調節效果

圖2:貨幣政策調節效果
將IS、LM和BP曲線在i-Y平面內表示出來,如圖1所示。假設經濟開始處于IS曲線、LM曲線和BP曲線的交點A,此時內外均衡同時實現。假定由于國內外因素使得人民幣名義匯率下降,則人民幣實際匯率也會下降,出現升值現象。匯率的減小使BP曲線向左移動到BP’處,凈出口的減小讓IS曲線向左移動到IS’處,國內利率不變則LM曲線保持不變。則新的交點是B點,位于BP’曲線的左下方。此時在B點實現了內部均衡,但由于人民幣升值導致凈出口的減少量,小于國內利率下降引起的資本凈流出的減少量,所以處于國際收支順差中,外部平衡并沒有實現,與我國的現實情況恰好吻合。
第一,運用財政政策解決內外失衡問題。
若使用擴張性財政政策,增加國內需求,使IS’曲線向右移動到曲線IS”處,則新的交點是IS”曲線、LM曲線和BP’曲線交點C。C點與B點相比,利率和產出都較高,國內利率的上升帶來資本凈流出的減少量,遠遠小于產出的增加帶來凈出口的減少量,國際收支差額逐漸變小,從而實現國際收支平衡,內外失衡問題得到了解決。
若運用緊縮性財政政策,減少國內需求,會導致IS’曲線向左移動到IS*處,則此時新的均衡點是D點。D點與B點相比,利率和產出均較小,國內利率的下降導致資本凈流出的增加量,小于產出的減小導致凈出口增加量,則國際收支順差狀況進一步拉大,人民幣有進一步升值的壓力,內外失衡問題沒有解決。
第二,利用貨幣政策解決內外失衡問題。
如果使用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給,使LM曲線右移到LM’處,則新的交點是IS’曲線、LM’曲線和 BP’曲線的交點E點。見圖2。E點與B點相比,利率較低而產出較高,國內利率的下降有利于資本凈流出的增加,產出的升高使得凈出口下降,國際收支逐漸趨于平衡,內外失衡問題得到解決。
如果采用緊縮性貨幣政策,減少貨幣供給,使LM曲線左移到LM”處,則新的均衡點是F點。F點與B點相比,利率較高而產出較低。產出的減少會大大增加凈出口,國內利率的升高會導致資本凈流出的減少,國際收支順差的局面會更加嚴重,內外失衡問題會進一步惡化。
第三,搭配使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解決內外失衡問題。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可以有效解決人民幣升值帶來的內外失衡問題。根據資產組合模型理論,央行在買入外匯,增加本幣貨幣供給量來減輕人民幣升值壓力的時候,可以通過發行央行票據、賣出債券等公開市場操作業務,保持貨幣供給量不變。因此,當搭配使用擴張性財政政策和穩健性的貨幣政策的時候,把經濟狀況調整在有效區間CE內,可以解決內外失衡問題。正如陳靜(2013)所說的量化寬松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也是影響貨幣政策有效性和宏觀調控的重要因素。[6]
四、結論
總之,人民幣幣值內外變現的不統一性是由內部因素占主導、外部因素起加速作用而綜合形成的結果,也是一種累積性的結果。因此,對于人民幣幣值變動問題的解決應該遵循著“短期與長期相結合”、“內因與外因相結合”以及“由具體方法操作與制度機制建設相結合”的原則。
從短期性內因角度來看,既要搭配采用擴張性財政政策和穩健性貨幣政策,將經濟狀態調整到有效區間內,保持經濟在短期內的小幅波動;又要靈活運用宏觀調控的政策工具,強化宏觀調控的數量型和價格型雙重特征,增強調控的有效性和可持續性。從長期性內因角度來說,一方面應通過拉動消費的發展完善經濟發展方式,優化我國經濟的產業結構、需求結構,增強綜合實力;另一方面,應繼續推行利率市場化改革,在現有貸款利率市場定價機制的基礎之上逐步探索存款利率市場定價機制,讓利率真正反映資金的成本,調節資金供求,促進資本得合理配置。
對于短期性的外因,不僅要逐步改善引進外資的政策,傾向于吸引長期資本流入國內,規避套利性和投機性短期資本流動的沖擊;還要積極深化“走出去”戰略,增強資本、勞務以及技術等要素輸出的深度與廣度,擴大國際市場,促進國際收支在數量和質量上的平衡發展。至于長期性的外因,應堅持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增強匯率靈活變化的能力,充分發揮匯率對國際收支的調節作用,促進國際收支長期趨于平衡,實現國民經濟快速穩定發展。
[1]章昌裕.中國入世十年成就回顧與前景展望[J].對外經貿,2012,(1):10-11.
[2]張明.人民幣匯率升值:歷史回顧、動力機制與前景展望[J].金融評論,2012,(2):22-23.
[3]林苗峰.人民幣內外價值偏離的原因及對我國經濟的影響研究[D].浙江大學,2013.
[4]肖文,潘家棟.人民幣升值中外部壓力的沖擊與效應[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3,(8):109-110.
[5]張中華,唐文進,謝海林.我國金融宏觀調控的問題與對策分析[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3,(2):83-84.
[6]陳靜.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與政策效果研究[J].國際金融研究,2013,(2):2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