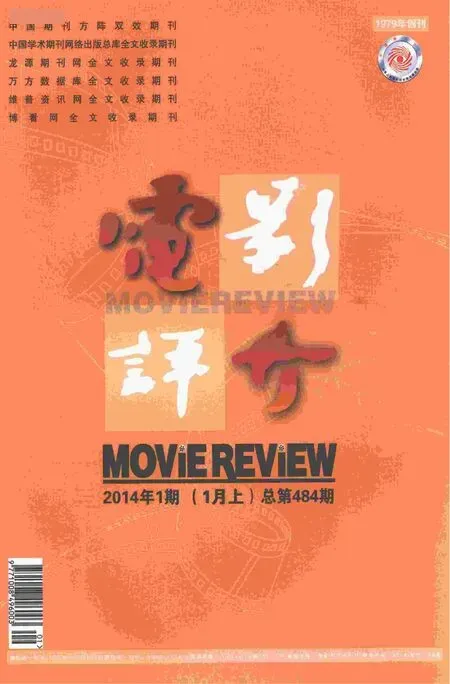論馮小寧戰爭電影中的人性訴求
□文/王偉,山東藝術學院講師

電影《紫日》劇照
戰爭是電影藝術中的一個重要的表現題材。人們對于戰爭題材的影片總是懷著特殊的審美心理。從本質上講,戰爭是反人類的,而電影作為藝術對戰爭的表現卻要遵循著人道主義的方向。人道主義借助電影這種視聽藝術,更強烈地將愛與憎的情感傳達給人們,使觀眾對戰爭的性質有著明確而深刻的判斷,并在情感上激起對善良與無辜者的愛與同情。
戰爭題材的影片在我國當代電影史上是不鮮見的。在這類題材的影片中,對于人性的表現經歷了一個從單純、淺顯到復雜、開放的過程。我國早期的戰爭片如《八百壯士》、《南征北戰》、《紅日》、《平原游擊隊》、《紅色娘子軍》、《地道戰》、《地雷戰》、《鐵道游擊隊》、《敵后武工隊》等,由于囿于特定的時代環境,對于人性的展示表現為一種片面的崇高美,一般著重突出了人物可歌可泣的英雄壯舉,張揚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的激情,歌頌大無畏的獻身精神及宣揚正義必勝的堅定信念。而對于作為生命個體的人則帶有模式化傾向,重在其外部行為的呈現而缺乏一種內心細致情感的刻畫。這種價值取向和判斷的影片,從客觀上講并不能完全反映戰爭時期人的精神狀態。改革開放以后,由于打破了政治意識形態的拘囿,戰爭片中開始表露出一種戰爭背景下的人情與人性。將戰爭與社會、前方與后方的各種千絲萬縷的關系有機地聯系在一起,雖然影片的主調仍然是高昂的英雄主義和愛國主義,但對于戰爭背景下的人性美與人情美的表現已顯露無遺。人物形象的塑造也不僅僅停留在勇敢、無私、機智、果斷等層面上,而是對于人性的多方面進行了初步的探討。如電影《小花》中“妹妹找哥淚花流”的愛情就讓當時的年輕人的心興奮不已。至今仍有不少“過來人”對《小花》留給自己的印象記憶猶新。“《小花》成功的原因也不是所謂電影語言的革新,而是在一部傳統意義上的‘軍事電影’中,將戰爭推到了后景,而將一個更富有人情味的關于真假兄妹悲歡的故事推到了前景。”“這部影片也因對革命的新穎處理和表現及其電影語言的革新而載入了中國當代電影的史冊。”[1]進入90年代以來,對于戰爭背景下人性的表現已日趨復雜和深入。以馮小寧戰爭三部曲《紅河谷》、《黃河絕戀》、《紫日》為代表的戰爭電影已不再是簡單地表現人物心理性格的某一層面,或是簡單地給人物貼上善與惡的標簽,而是盡可能對人物作全方位、立體式的觀照,力圖全面地把握人物性格心理的發展變化,以獨特的視角更為深入地剖析人性的復雜矛盾,從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個體入手,揭示豐富的人性內涵。具體來說,體現在以下幾個不同的側面:
一、人性的復雜及在戰爭環境下的轉變
人性是復雜的,特定的戰爭環境往往為影片展示人性的復雜性提供了有利的條件。馮小寧“新戰爭電影”的成功之處還在于:他通過一些非主流的人物形象,探討并再現了人性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種種不同形態及美與丑、善與惡的相互轉化過程。由此剖析了人類靈魂中美麗、善良、丑陋、殘酷的多重性、復雜性,闡述了真、善、美對于人類存在和發展的重要意義。如影片《黃河絕戀》中的三炮,原本是一個奴顏婢膝、猥瑣下流的潑皮無賴,除了對日本人逢迎拍馬,對村姑唱幾句淫詞濫調外,別無所長。可正是這樣一個讓人厭惡的奴才,在目睹日本人的殘忍與獸性后,勇敢地向八路軍戰士點火示警,并大義凜然地英勇赴死,這種在正義、良知感召下所迸發出的民族氣節,最終使他成為一個大寫的人。影片《紫日》中的秋葉子,原本是一名花季年齡的日本少女,由于接受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教化,其心理被扭曲而異化,變成了軍國主義的殺人工具,在和楊玉福、娜佳共同逃亡的過程中,她曾幾次想置他們于死地。但最終在楊玉福善良、仁愛的感召下,漸漸找回了人性,化敵為友。與三炮、秋葉子不同,楊玉福是一名在日本人的大屠殺中死里逃生的普通中國農民,但是他面對將自己和蘇聯戰士帶進雷區,并炸死了一名蘇軍戰士的日本少女,卻最終沒有忍心將她殺死。作為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在他身上散發出一種可貴的人性光芒,體現了中國傳統文明中善良仁慈的美德。在殘酷的戰爭現實面前,他用實際行動呼喚人類的良知,因為他相信如果人們互相仇視、互相殘殺,戰爭就永遠不會結束。
二、從民族沖突與國家沖突的角度表現人性的沖突
從民族沖突國家沖突的角度出發來表現人性的沖突,探討戰爭與人性的關系在馮小寧的戰爭三部曲中均有所涉及,這也是馮小寧“新戰爭電影”的另一大主題。作為歷史事實,作為一種歷史記憶,馮小寧以另一種方式有感而發,對戰爭背景下民族沖突與國家沖突對人性的改變進行了歷史的拷問和思索。影片《紅河谷》中英國軍官羅克曼上校和西藏地方武裝頭領代本關于西藏獨立問題的對話,幾乎就是一場關于“國家統一與民族獨立”的政治辯論。在影片的最后,當羅克曼通過打火機認出了那位曾經救過他性命的格桑時說道:“我們是朋友”,而此時無論是羅克曼、格桑還是觀眾都有一種心痛的感覺,人與人之間的友誼在民族沖突面前變得如此的脆弱,從而引發人們對戰爭的控訴與對和平的呼喚。在《黃河絕戀》中,安潔以她的悲慘遭遇現身說法:“當刀架在脖子上的時候,什么權利都沒有了。”當人的生存權受到威脅時,根本就談不上其他的人權。在影片《紫日》的結尾,日本少女秋葉子臨死前對楊玉福輕輕地道出的那聲“對不起”,仿佛就是我們現實中等待了多年而沒等到的道歉。
意大利電影導演弗朗西斯科·羅西說“電影無力改變現實,但是有能力促發人們進行思考。”[2]縱觀我國戰爭題材的影片,從早期單一、片面地描寫人性到多樣化、復雜化地揭示人性,代表了當下戰爭電影的發展趨向,體現了一種當代人文戰爭電影的藝術風格。藝術家對于戰爭、暴力的描寫恰恰反映出了人們對和平、人性的永恒追求。它呼吁人類要時刻警醒,防止相互殘殺的悲劇重演。
三、對于死亡內涵的重新解讀與認知

電影《黃河絕戀》劇照
戰爭就意味著死亡。德國著名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在論述戰爭時指出:“戰爭是一種巨大的利害關系的沖突,這種沖突是用流血方式進行的。”[3]在馮小寧的戰爭電影里,同樣描寫了大量的死亡場面。因此,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戰爭三部曲”就是一部流血與死亡的交響曲。然而影片對死亡的大量關注卻是在另一個側面對生命的重新認知和深刻思考。影片《紅河谷》、《黃河絕戀》、《紫日》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人物出發,對死亡進行了重新的探討。比如《黃河絕戀》中八路軍戰士黑子與美國飛行員歐文關于“投降”的認識差異,以及日本軍人在戰爭結束后得知日本投降時的集體自殺,都表明了不同民族對生命和死亡價值的不同認識,以及民族利益、國家利益、生命尊嚴等倫理道德法則在不同民族中的具體體現。
馮小寧的戰爭影片從來沒有正面描寫過傳統意義上的勝利和失敗,他從一定的歷史高度出發把戰爭的本質通過影像藝術表達出來。拋棄了那種世俗的、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功利色彩,在當今的和平環境下,對人類歷史上曾經發生的戰爭進行反思。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在觀看馮氏戰爭影片時往往不能給我們帶來以往那種最終勝利的民族自豪感和正義的滿足感,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沉重的壓迫感和悲劇感的原因。同時也正是通過對死亡的表現,才揭露出戰爭對人性和生命的摧殘與迫害,從而喚起人們對和平的熱愛和對戰爭的憎恨。
縱觀中國當代的戰爭電影,人性表現的發展從兩個維度上體現著其不斷地進步,一是人性表現視野的日益拓展和豐富,這表明藝術家對人性美及人道主義的表現已成為一種自覺。二是在其審美品格上日益豐富與多元,從早期的片面追求理想主義、英雄主義到現在的批判現實主義與以文化反思與浪漫激情相結合的新類型,為人性的表現注入新的美學因素。
展望當今戰爭電影的發展,人性的光輝將始終是電影表現的靈魂,而且將成為每一部戰爭影片的內在底蘊。
[1]陳曉云,陳育新.作為文化的影像[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300-301.
[2]弗蘭切斯柯·羅西.生活就是一場戰爭與下一場戰爭之間的休戰[J].王昶,吳冠平,譯.電影藝術,1999(4):77.
[3]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第1卷[M].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小組,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