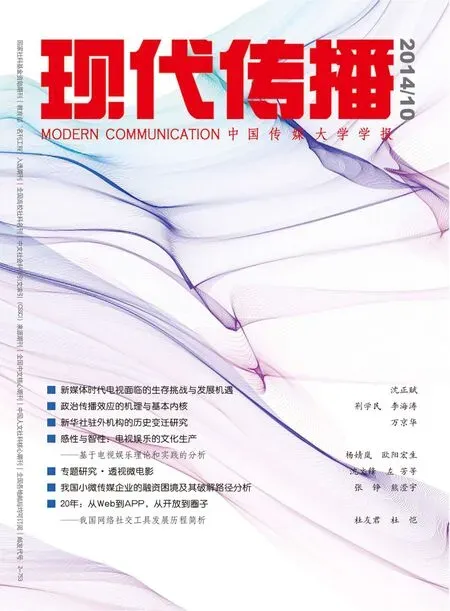影視服飾造型構建與本土文化傳播*
■ 張玲
影視服飾造型構建與本土文化傳播*
■ 張玲
本文從服裝造型設計的角度出發,針砭當下本土古裝歷史題材的影視創作中的突出問題,在深入探尋其潛在影響及內在動因的基礎上,用文化比較的方法對中西服飾審美觀念的差異加以考證,進而從優秀影視案例的實踐出發探討歷史語境下影視服飾造型創作的東方美學之路。
影視創作;服飾造型;審美;奇觀化;廓型
在國際交鋒日趨頻繁的“全球化”時代,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已由政治、經濟、軍事為主導的硬實力逐步轉向以文化、價值觀、影響力、道德準則為內涵的軟實力上來,這些軟要素在國家綜合國力的競技中的作用日益凸顯。面對國際文化格局“西強我弱”的緊迫現實,如何大力提升本土文化軟實力、積極塑造良好的國家形象成為新時期我國文化建設的一項重要戰略目標。
文化的傳播需要良好的載體,影視藝術作為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范本,在現代傳播中表現出極為活躍的媒介特征,作為大眾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公眾影響力輻射本土甚至波及海外。影視藝術所具有的廣泛而活躍的傳播特性使其享有成為“文化使者”的先決優勢。那些承載著鮮明的中華文化特色、深刻的人文思想內涵及獨特藝術品格的影視作品勢必成為一種有效的文化媒介,對本土文化的推廣與傳播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
然而,在甚囂塵上的娛樂文化的浸淫下,本土影視創作似乎喪失了應有的文化擔當,一味與商業利益、世俗趣味妥協同流,在創作形式上片面強調感官的愉悅與刺激,求奇、求異、求怪無所不能;但在創作內容上卻淺薄乏味,缺乏深厚的文化根基和思想內涵。其中,作為影視藝術視覺構成的核心要素——服飾造型,因其直觀可感的外顯特征而成為“視覺狂歡”的最好“推手”,或奢華耀目,或爭奇斗艷,突出表現為一種“只求熱鬧,不論根由,但要出奇,不顧文理”①的“奇觀化”傾向。
一、服飾造型的“奇觀化”癥候
服飾造型的“奇觀化”肇始于本世紀初中國電影“大片時代”的來臨,且伴隨古裝歷史題材創作的持續升溫而愈演愈烈。2000年,李安攜華語巨制《臥虎藏龍》斬獲奧斯卡大獎,迅速引爆了華語電影市場對古裝歷史題材的狂熱追捧,似找到了一條通往成功的捷徑。“大投資、大明星、大營銷”儼然成為國產大片的經典配方。從張藝謀操刀的《英雄》(2002年)、《十面埋伏》(2004年)、《滿城盡帶黃金甲》(2006年),陳凱歌的《無極》(2005年),馮小剛的《夜宴》(2006年)、《趙氏孤兒》(2010年),到新人掌舵的《戰國》(2011年)、《銅雀臺》(2012年),可謂前赴后繼、熱鬧非凡;香港影人亦不示弱,古裝巨制《赤壁》(2008年)、《狄仁杰之通天帝國》(2010年)、《鴻門宴》(2011年)等更是高調搶灘。有若干大導演的身先士卒,眾影視同仁的跟風效法則不足為怪。即便沒有電影制作的雄厚資金,也并不妨礙電視劇作中“尋奇搞怪”的荒誕造型的粉墨登場。影視創作在服飾造型表達上陷入“嘩眾取寵”的審美怪圈,大有“形”不驚人死不休之勢。
1.夸耀外放的廓型結構
為呈現極致炫目的視覺“奇觀”,服飾造型設計不顧東方語境之現實,追求恢弘壯闊的西洋建筑質感,服裝在廓型結構上強調三維立體的畫面感,夸大服裝局部結構的突兀與對比,這種夸張奔放的風格表達與東方傳統服飾的美學精神大相徑庭。在以五代十國為敘事語境的電影《夜宴》中,人物服飾造型呈現出假定的戲劇性,猶如西方舞臺藝術的中國化腳本。章子怡飾演的婉后身著奢華的冊封禮服,廓型結構呈現出西洋史詩般的恢弘力度,其背部夸張的拖裾設計分明是歐洲十八世紀洛可可風格的“瓦托式羅布”的中國翻版,“這種衣服領口開得很大,在背部(后領窩處)有很大的箱型普利茲褶,呈又寬又長的拖裙形式,這種優雅的樣式主要為路易王朝宮廷及其周圍的貴夫人穿用”。②東方宮廷服飾被冠以西洋趣味的標簽,完全喪失了東方服飾文化自身的藝術品格。而古裝巨制《滿城盡帶黃金甲》更是將這股“奇觀化”浪潮推向極致。這部同樣以五代為背景的影片,在服飾語匯上仍滯留于西洋趣味的裹脅中,劇中異常出位的“爆乳裝”,則是對法國宮廷貴族婦女性感著裝的刻意模仿。③為強化性感的立體雙峰,不惜動用緊身胸衣壓擠出突兀的奇觀。這種流于表面化的低俗模仿完全顛覆了中國傳統禮教文化的精神內涵。在電影《趙氏孤兒》中,范冰冰飾演的莊姬服飾造型妖冶艷麗,豐滿圓融的西洋“巴洛克”廓型混搭以唐代風格的高腰設計,即便考慮到有孕的生理因素,也難以讓觀者進入春秋語境下晉國名門的身份聯想。在距內地首部古裝大片誕生十年之際,這一“東方奇觀”的接力賽在新生代導演中繼續上演。電影《銅雀臺》取材于漢末梟雄曹操的傳奇人生,雖置身于漢代特定的歷史語境,但人物服飾造型并未體現出漢代服飾藝術古拙、飛動的美感。由伊能靜飾演的伏皇后其金光燦爛的盛裝呈現出圓融僵硬的體量感,厚重的袍服延伸出夸張的拖裾,恢弘的氣勢堪比十九世紀拿破侖皇后約瑟芬的加冕大典。這種登峰造極的趣味,也同樣肆虐于大量古裝題材的電視劇作中,成為爭奪收視率的吸睛大法。在古裝歷史劇《武則天秘史》中,強悍的飛檐翹肩、高聳的夸張領式和異常突兀的結構細節完全顛覆了東方服飾和諧、雅致的意趣傳統,這樣簡單粗暴的杜撰恐怕只為滿足今人眼中霸氣獨斷的武后風范。
2.雕繢繁復的極致裝飾
“奇觀化”所引爆的視覺震撼力,一方面源于恢弘壯闊的服飾廓型結構的夸耀性表達,另一方面則歸因于雕繢繁復的裝飾趣味。珠繡、緞帶、花卉、羽毛等裝飾要素成為時髦的噱頭,被毫無章法地堆砌拼貼,這種近乎窒息的重工裝飾加速了服裝整體美感的失衡。在備受爭議的電影作品《無極》中,無論是艷光四射的鮮花盔甲,還是美輪美奐的霓裳羽衣,都試圖以浮華的幻象制造出無限的審美沉醉。而《滿城盡帶黃金甲》中,重達40公斤之巨的恢弘帝袍,周身綴滿華麗的金片,厚重刻板的質感將角色屏蔽成僵硬的套中人,阻隔了劇中人物與觀眾的情感交流。為追求空泛的裝飾美感,甚至棄傳統文化的禁忌于不顧,《夜宴》中,婉后吊唁先帝的素白喪服不加回避地被施以文彩裝飾,這種完全無視中國傳統文化禮儀制度的荒誕做法,④可謂“但要出奇,不顧文理”的極端范例。《戰國》中由金喜善飾演的龐妃其袍服上奢華艷麗的皮草飾邊則是現代審美的生硬演繹,這種具有“穿越氣質”的時尚造型實難將演員與觀者帶入兩千年前的歷史想象。而在古裝題材的電視劇創作中,裝飾手段更是天馬行空、無所禁忌。這種以感官享樂為至上追求的荒謬態度,也是當下影視創作在視覺造型上缺乏文化性的重要體現。
“奇觀化”的服飾造型語言與傳統文化語境互生抵觸的事實,嚴重消解了影視作品的藝術價值及美學品位,同時也使廣大非專業的影視觀眾在審美接受中對中國古典服飾的文化內涵及美學格調產生曲解和誤讀,這對民族文化價值觀念的形成將產生負面影響。追本逐源,如果對影視創作中這種“奇觀化”癥候的根源加以深入探究,除去對“好萊塢”視聽文化的狂熱追捧、對現代消費社會大眾娛樂的討巧迎合,恐怕也與影視藝術創作者因對傳統文化精神的荒疏而引發的審美認知上的混沌與彷徨不無關聯。無可否認,傳統文化的傳播斷裂使當代文化陷入“無根”的窘境,而西方文化強大的話語攻勢,讓本土影視創作無可避免地成為西方美學的試驗場。在造型創作上一味地“求奇尚異”,背棄了賴以生存的東方文化的母體,即便形式再過炫耀癲狂,終究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難以獲得獨立的藝術精神和生命活力。電影《無極》《滿城盡帶黃金甲》《夜宴》曾先后逐夢奧斯卡紛紛落敗的事實給予我們深刻的思想啟迪。不難看出,重塑東方文化敘事語境、弘揚中式美學的意蘊精神對本土影視藝術創作的理性回歸具有深刻而積極的現實意義。
二、中西服飾審美旨趣的文化差異
服飾作為文化的表征、觀念的載體,中西方因文化傳統的差異在服飾審美上各異其趣。“中國文化是和諧的隱喻文化,強調均衡、對稱、統一的藝術美感,側重抒情性;而西洋文化則是善于表現矛盾、沖突的明喻文化,強調刺激、極端的形式,以突出個性、表現特異為尚,以視覺享受為第一要義”。⑤正是中西方文化傳統的殊途差異,使二者在服飾審美上表現出“隱性”含蓄與“顯性”張揚的二元對立的矛盾特征。因此深入洞悉和考證中西服飾審美的本質差異,對于不同文化語境下影視服飾美學格調的構建與完善意義顯著。
1.“衣穿人”——西方服飾之顯性張揚
服飾風格的建構與人類精神文化的脈動息息相關。“西方社會自文藝復興以來,人文主義的提出奠定了以個體為軸心的人道主義的框架”,⑥這種“人文主義”的精神內涵折射在西洋服飾文化的血脈中,則表現為超越古希臘式的自然舒展、中世紀的肅穆莊嚴而邁入“愉悅感官”的性感昭彰的新階段。歷史學家布羅代爾曾認為,“歐洲時尚肇始于十四世紀中葉,服裝形式從懸垂型向裁剪型轉化,服裝的功能也從對身體的遮蔽轉為對身體的表現”。文藝復興時期(15世紀中葉——17世紀初)以緊身胸衣和夸張裙撐為“顯性”利器的“西班牙風尚”,開啟了西洋時尚戲劇荒誕的“衣穿人”時代的序幕。人體在服裝的擠壓下重獲“新意”,女裝整體呈現圓融夸張的“A”字廓型,塑造出蜂腰、翹臀、乳房高聳的極端女性形象;而男裝則以雄渾厚重的“V”字廓型與女裝交相輝映,寬肩、收腰的圓融上身,下肢則曲線畢露。為塑造三維立體的“顯性”特征,服裝采用立體剪裁的方式,省道及分割線的運用頻繁多變,尤為注重局部幾何空間的變化,恢弘壯闊的氣勢深得古希臘建筑美學的精髓。這種在服裝立體表現上的夸耀態度即便隨近代“輕裝時代”(緊身胸衣和裙撐消失)的來臨也沒有絲毫的減損,對人體曲線的極致追求仍是西方現代女裝造型創新的至上理想。性感、圓融、雄渾成為西洋服飾審美的風格注腳。
西洋服飾的奇觀化由夸張的立體廓型,延伸到繁復的細節裝飾。經過巴洛克風格(17世紀)、洛可可風格(18世紀)的浸淫,這種矯揉造作的裝飾趣味達到無以復加之地。以下可從對洛可可時期法國宮廷女裝的描述中窺探一斑:“羅布(裙)一般前開,上面露出倒三角形的胸衣,胸衣上自上而下按大小順序排列著一排緞帶蝴蝶結,羅布下面A字形打開,露出里面的襯裙,襯裙和羅布上也都裝飾著曲曲彎彎的褶皺飛邊、麗絲、緞帶蝶結和鮮花,這時還時興用意大利產的人造花裝飾自己,女人被稱作“行走的花園”。⑦繁榮于洛可可時期的珠繡、蕾絲、褶飾等仍成為西方現代女裝重要的裝飾語匯。
2.“人穿衣”——東方服飾之隱性含蓄
“文質彬彬”的儒家學派和以“披褐懷玉”為精神意旨的道家學說在中國傳統服飾美學精神的建構中起到重要的編碼作用。傳統服飾在造型語言上既體現出儒家禮教思想的深刻印痕——“遮蔽與含蓄”,又流露出道家文化所孕育的“氣韻生動”⑧的美感。這種美學“意境”,正如宗白華先生所言既是“由舞蹈動作延伸,展示出來的虛靈的空間,又是構成中國繪畫、書法、戲劇、建筑里的空間感和空間表現的共同特征,而造成中國藝術在世界上的特殊風格,它是和西洋從埃及以來所承受的幾何學的空間感有所不同”⑨。如此而言,華夏服飾藝術不也正蘊含了這種可供“神游”的虛靈的空間嗎?
與西洋服飾不同,中國古典服飾是建立在“T”字廓型基礎上以二維平面化剪裁為主要特征的造型結構。受儒家禮教思想的影響,服裝強調對身體的遮蔽功能,弱化人體自然的“性”特征。男女服裝同款同型、寬松肥大,具有良好的平面封閉性,突出服飾之于人的社會倫理意義。漢代史學家班固在其論著《白虎通義》中對服飾的倫理價值給予了精辟的論述,“衣者,隱也;裳者,障也;所以隱形自障蔽也”,這一隱一障,人體的性別特征自然隱匿不彰了。而褒衣博帶無疑是“隱性文化”的最好載體,它構成中國古典服飾的顯著風格。《詩經·鄭風·淄衣》中即以“淄衣之蓆兮”對寬博之服發出由衷的贊嘆。唐代詩人李白曾形象地以“未行先起塵”,描畫魯國儒生寬袍大袖的雍然之態。清人王夫之更是以“寬博,以示無虔鷙也”詮釋了褒衣博帶的華夏民族“具武備而不害”“文質彬彬”的仁學品格。寬博舒暢的華服依人體自然垂蕩,于衣袖、裙身處堆積出回旋往復的衣紋褶皺,隨著人體的舉步輕揚,更趨靈動飄逸,這種“氣韻生動”的美感構成了中國古典服飾重要的審美特征。“羅衣何飄颻,輕裾隨風還”“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桐布輕衫前后卷,葡萄長帶一邊垂”“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這些意境優美、亙古流傳的古典詩詞滌蕩出生動流暢的服飾美態。
中國古典人物繪畫則從另一個側面再次印證了這一美學特征,衣紋線條折而不滯,顫而不散,“‘曹衣出水’表現出的懸垂感(垂直線),而‘吳帶當風’則表現出服裝的飄逸感(水平運動),二者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中國服飾的獨特文化品位”。⑩
在裝飾趣味上,由魏晉前期的“錯金鏤彩”之美升華為“初發芙蓉”般的清新雅趣,而后者體現出更高的美學境界。(11)追求虛實有致的含蓄之美,不以直白突兀為尚,注重藝術的“留白”處理。《詩經·衛風·碩人》曾較早涉及這一美學命題,“碩人其欣,衣錦絅衣”,六朝劉勰在《文心雕龍·情采》篇對其加以闡釋,“是以衣錦褧衣,惡文之章”,錦衣外罩單衣,因惡彩衣太過華麗,罩衣的隔離功能產生朦朧虛幻的美感。此外,在裝飾趣味上以純凈雅致的色調為尚,追求靜雅恬淡之妙,如古典服飾中的弁服、玄端、深衣皆以白色或黑色為主調,僅在領緣、袖緣、擺緣處施以文彩點綴,主次分明、張弛有度。即便如祭服之屬,雖衣身冠以文彩,但在紋樣的布局上亦注重章法節奏,以單獨紋樣、二方連續或四方連續巧妙構成,虛實生動。裝飾工藝主要以平面化的刺繡、手繪、印染為特色,這與西洋裝飾所追求的立體繽紛的喧鬧效果截然不同,折射出華夏衣冠文化內斂含蓄的精神特質。
綜上所述,中西方的服飾審美觀可謂天壤之別,一個重于外顯、一個傾向內斂;一個極盡愉悅感官之能事,一個盡顯人衣和諧的自然之境。“西方服飾見棱見角見圓見方,中國服飾似水似云似霧似風”(12),從風格對比中不難發現,正是西方“顯性張揚”的服飾審美文化造就了“好萊塢”大片在服飾造型上的奇觀化表現,即在秉承西方審美傳統的基礎上加以藝術化的加工創造。而本土影視創作者卻忽視了這一根本原則,唯“好萊塢”風格馬首是瞻,最終與中國傳統美學精神相背離,喪失了影視藝術所應有的文化根基和立場。
那么以“含蓄雋永”為顯著特征的服飾審美文化將如何在當代影視創作中得以彰顯?歷史之“真”與藝術之“美”如何得以交融?這將成為當下本土影視創作所必須直面和思考的嚴峻課題。
三、東方服飾美學的探索與實踐
在這場聲勢浩蕩的“奇觀化”狂潮中,卻也閃現出敢于逆流而上的“勇士”,他們基于醇厚的人文底蘊及對文化的自覺意識,在歷史題材的影視創作中投入了更多的理性思考,傾注于東方美學精神的探索與實踐,作品洋溢出醇厚的歷史文化質感和藝術張力,為本土影視創作吹來一股清新之風。如陸川執導的電影《王的盛宴》(2012年),鄭曉龍執導的電視劇《后宮甄嬛傳》(2011年)以及丁黑執導的電視劇《大秦帝國之縱橫》(2013年),自問世以來受到業界及廣大觀眾的高度贊譽,社會反響強烈。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電視劇管理司司長李京盛曾對《大秦帝國之縱橫》給予如下評價:“無論是人物、事件,還是服裝、禮儀都參照史料,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實。作品所表達的深刻歷史文化內涵,讓我們對歷史產生了一種由衷的敬意。它讓我們以更直觀的方式走進歷史、了解歷史并反觀現在,傳遞了正能量。”這些獨具文化擔當的影視劇作精品為本土影視創作的理性回歸樹立起光輝的典范。無論是在創作態度還是創作方法上,都值得悉心學習與借鑒。
1.廓型精于歷史考據
廓型結構是構成服裝風格之美的核心要素,其精準與否是古裝造型能否最大限度地接近歷史真實、塑造東方美感的重要前提。強調“T”型框架下舒展自然的平面剪裁效果,以洗練的直線構建出虛靈的服裝內在空間,注重橫向和縱向尺寸松量的協調與統一,領型、袖型等細節特征更應依托考據、精益求精。
以漢王劉邦傳奇人生為敘事語境的《王的盛宴》,對歷史投以敬畏的態度,正如導演陸川所言,“我們的歷史不僅僅可以被肆意消費,被任意篡改,也值得被尊重”。為達到“將攝影機架到古代”的歷史質感,再現楚漢文化古拙生動、澹逸飛揚的藝術特色,(13)該片在戲服設計上,遍考先秦兩漢服飾形象資料,以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曲裾深衣為創作原型,提煉漢服“交領、右衽、曲裾、垂袖”等典型特征貫穿于呂后、戚夫人等戲服結構中,層疊往復的曲裾衣襟盤旋斜下,極具楚漢服飾的美學特征。服裝廓型松量細致考究、局部比例舒暢協調。通過精準的結構語言,漢代服飾所蘊含的質樸雅致、率真浪漫的風格基因被成功解碼。
大型史詩劇作《大秦帝國之縱橫》,同樣以嚴謹、扎實的考據精神完成了秦代服飾的造型風格定位。而古裝劇作《后宮甄嬛傳》以清代文化為依托,堅決摒棄以往清宮服飾“影樓”化的膚淺套路。嚴格考據清代服飾歷史,在關鍵結構處毫不妥協,“圓領、大襟、右衽、直身、闊袖”等細節精準得當,服裝胸、腰部的剪裁松量更是求真于歷史,保持了東方服飾寬松舒暢的自然韻味。絲袍于肩周、腰身、腋下因松量而生的自然褶皺,真實地還原出清代服飾滿漢融合、張弛有度的美學特色。由以上分析不難看出,在歷史題材影視創作中,對古典服飾開展針對性的結構考據是古裝造型設計抵達歷史“真實”的關鍵點,也是成功構建東方服飾美學格調的重要前提。
2.裝飾源于真實融入藝術創造
中國傳統服飾的裝飾工藝以染繪、刺繡見長,側重平面化的裝飾效果,其中以內涵雋永、構圖優美的刺繡紋樣最具藝術特色。影視古裝造型往往借助傳統刺繡工藝以達到回歸歷史、深化主題的目的。在具體創作中,裝飾紋樣題材的選擇要注重歷史文脈感,通過借用特定時代的典型紋樣以真實地還原歷史質感。殷商猙獰的饕鬄紋、楚漢浪漫的鳳鳥紋、唐代祥瑞的對獸紋無不彰顯出各自鮮明的時代特色。
《王的盛宴》中呂后素雅的曲裾袍服花紋取材于馬王堆漢墓服飾,以素雅的泥金銀色火焰紋為裝飾要素。與呂后有所不同,劉邦寵妃戚夫人的服飾則借鑒了馬王堆漢服中輕云舒展、枝蔓綿延的“信期繡”紋,二者服飾花紋皆考據歷史,但又依劇情角色的不同各有側重,呂后的城府理性與戚夫人的青春爛漫,借助潛在的裝飾語言得以有效渲染,歷史之“真”與藝術之“美”在此巧妙融合。這種藝術化的創造手段亦表現在服飾紋樣的布局上。為突出含蓄的美感,藝術化的“留白”被大量使用,服裝主體衣身與領、袖等局部細節在裝飾上力求繁簡交替、主次分明。
為強調具有東方特色的服飾“意境”之美,《后宮甄嬛傳》在深入考據歷史的基礎上,對清代宮廷服飾富麗的鑲滾工藝加以大膽的提煉與加工,并于衣身處渲染簡約蒼潤、意趣盎然的印染花卉,在雍容綺麗中注入一絲清新雅趣。歷史之“真”與藝術之“美”在創作的方法論上達到融合的辯證統一。
對歷史之“真”的探尋源于對自身文化的敬畏與觀照,這是本土影視創作得以回歸東方美學、重塑歷史質感的重要開端。服飾造型在廓型結構、裝飾趣味等方面應最大限度地取材歷史、還原風格、突出歷史之“真”。同時,影視服飾作為藝術化的語言,還應具有揭示劇情、塑造角色的積極意義,因此在造型創作中對繽紛的歷史素材依角色之需加以藝術化的選擇、提煉、概括、抽象等處理,使其成為獨具東方美感的“有意味的形式”。需格外指出的是,這種藝術之“美”的能動性創造必須以歷史之“真”為前提,超越盲目與彷徨,通過探索具有東方美學特色的藝術創新方法與途徑,最終抵達藝術之美的至上境界。
四、結語
服飾造型的“奇觀化”在本土古裝題材的影視創作中泛濫已久,這種與中國傳統文化觀念、服飾美學精神主旨背離的荒謬做法,根源于西方文化價值觀念的強勢沖擊以及創作者對自身文化傳統的漠視與無知。大量有悖歷史真實、穿鑿附會的視覺影像在日益頻繁的大眾傳播中對本土文化價值觀念的構建產生了消極的影響。置身“西強我弱”的國際文化格局,本土影視創作者應樹立起強烈的民族文化自覺意識和歷史使命感,在創作中堅定應有的文化方向,以東方美學精神解構與重塑影視服飾造型藝術,將歷史之“真”與藝術之“美”有機融合,創造出具有醇厚歷史文化底蘊的優秀藝術形象。隨著更多的精品影視劇作的誕生,在大眾傳播中必將形成巨大的文化感召力,從而對本土文化軟實力的提升、國家良好形象的構建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注釋:
① 葉朗:《中國美學史大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7頁。
② 李當岐編著:《西洋服裝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94頁。
③ 資料來源:http://ent.sina.com.cn/x/2007-02-15/08391452419.html。
④ 我國古代喪服制度規定,喪禮五服皆用麻布為之,且不施加文彩,可參見《禮記·士喪禮》,劇中對喪服施以文彩顯然有悖于中國傳統的禮俗文化。
⑤ 蔡子諤:《中國服飾美學史》,湖北美術出版社2001年版,第887頁。
⑥ 金丹元:《中國藝術思維史》,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303頁。
⑦ 李當岐:《西洋服飾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頁。
⑧(13) 李澤厚:《華夏美學》,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78、86頁。
⑨(11) 宗白華:《美學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3、35頁。
⑩(12) 華梅:《服飾與中國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版,第410、388頁。
(作者單位:中國傳媒大學藝術學部戲劇影視學院)
【責任編輯:李 立】
*本文系中國廣播電視協會學術理論研究項目“影視服飾造型傳播對提升本土文化軟實力的研究”(項目編號:2013ZGXH037)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