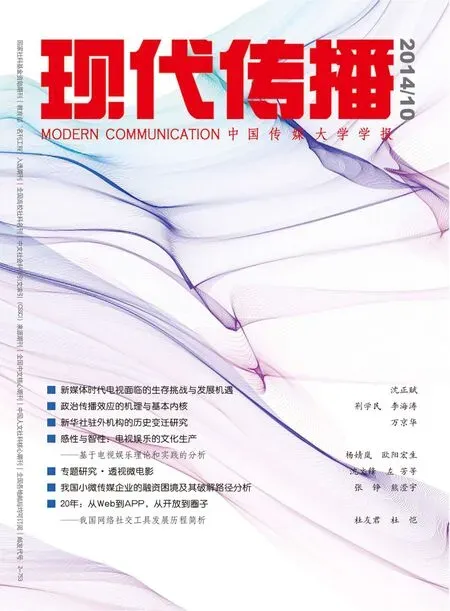網絡科技視角下微電影傳播的文化研究
■ 沈文鋒 吳凱穎
網絡科技視角下微電影傳播的文化研究
■ 沈文鋒 吳凱穎
【編者按】2014年,微電影從一種新型營銷手段日益成為互聯網的“新寵”,“互聯網電影”的概念呼之欲出。繼2013年第7期本刊組織“聚焦微電影”專題之后,本期再次推出“透視微電影”專題,擬從科技、倫理、影像與現代性等多個視角再次給予微電影以深入的透視與解析。
【本欄責編 張國濤】
一
微電影的概念誕生于2006年,流行于2011年。①然而關于什么是微電影卻一直處于爭論之中,至今沒有一個統一的概念。這里存在著四方面的意見:
第一種觀點認為微電影屬于電影范疇,但僅以電影的畫面性、敘事性作為核心,無視電影的其他本體特征和審美特征,直接討論微電影的篇幅長度、制作流程、產生原因及注意問題等,更多的是有關其“微”特征的討論。以百度詞條②最有代表性,也是目前比較通行的一個說法。
另一種觀點堅持微電影并不是電影,不屬于電影的范疇,其重要理由是微電影缺乏適合在影院傳播的特性。如蘇州大學鳳凰傳媒學院倪祥保教授所認為的,“盡管有些被稱為微電影的網絡視頻不乏一些短小精巧的,但從作為藝術作品這個角度上來看,凡稱得上電影的,一般首先應該是為了進入影院放映的那種(專門為電視拍攝的電視電影則具備這樣的條件)。”③
第三種觀點介乎前兩者之間,更加注重其功能價值,認為微電影包含傳統電影的特性,但卻“拘泥于微電影‘微投資、微制作、微時長’的表象”,④是從藝術殿堂里解放出來的具有實用性、不斷區別于傳統電影的某一“類”電影。
此外還一種觀點則把包括專題片、紀錄片等非舞臺記錄類視頻節目在內的短片都統稱為微電影。成為一個廣義上的稱呼。如2013年8月啟動的“全國檢察機關首屆微電影展播活動”,共在收到224部作品,就包括了微電影單元118部和專題片單元106部。⑤
由上可知,關于微電影概念的爭論主要是基于影視藝術學和大眾傳播學的視角。在影視藝術學的視域里,電影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電影的概念天然地成為微電影的參照物,為其設定了標準。在此語境下,要么在僅僅強調電影畫面性的前提下直接討論微電影的“微”形式,要么則因為電影的審美標準而質疑微電影的電影性;在大眾傳播學的視域里,微電影通常被默認歸入電影的范疇,從而其傳播渠道和傳播方式受到了關注。正是這兩個視角,使微電影的研究更側重從審美角度和功能角度去討論其發展前景。因此,在這兩個基礎上的研究,要么容易陷入電影概念的桎梏而難以跳脫,要么過于追求形式而有意無意地弱化其本質。結果是,一方面造成把大量的短片(不論題材和體裁)均歸入微電影的范疇,似乎微電影迎來了一個繁榮的創作期;另一方面,卻因為其藝術性而備受爭議,甚至遭到詬病。
二
事實說明,一個新生事物總是與其發生的社會背景、歷史背景息息相關,背景構成了其名稱、概念的文化原因。如電影,在美國發展成巨大的文化工業,在法國則有更多的藝術電影。電影在不同國家所形成的狀況說明,文化的影響更大,遠超過了照相術的進步對電影發展所起的作用。國外沒有微電影這個說法,而稱之為短片,如法國短片《調音師》。這部13分鐘的短片講述了一個有關“欺騙”的主題,從頭到尾充滿了懸念,在強烈的吸引人的同時又飽含了人生哲理,恰如電影里的臺詞:“當我們在欺騙別人的時候,很容易將自己陷于別人更大的陷阱。”這類短片之所以在國內被稱為微電影,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因為“微”(電影)已經成為網絡時代一個時尚的文化符號。劇作家、影評人橫舟說:“微電影時代,無論是在形式還是內容上,時尚一定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表達方式,一種風格,一種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⑥微電影甚至波及到了臺灣。“優質偶像王力宏和‘小豬’羅志祥分別宣布推出‘微電影’(weifilm/online short films,一個典型的Chinglish[中式英語])來應襯鳥巢演唱會及新專輯的宣傳,一個從文字、影像、網絡接口到在線游戲設計都強調輕薄短小的‘微/小(micro)時代’是否正在成型?是否緊隨大陸腳步,即將迅速開展?”⑦此外,借助于網絡,微電影正在升級為互聯網電影。因此,對于微電影的考察,斷然離不開網絡科技的這個視角,科技發展引起了傳播文化的變化。
首先,這是一個網絡時代。科技的發展使得移動互聯網已經極大地改變了這個世界,人們的生活習慣、交際手段乃至思維方式都因為網絡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新事物產生的同時也意味著對一些東西的顛覆,比如電報、商品零售、金融服務、大眾傳媒等,無論是信息獲得、社會參與還是娛樂,網絡似乎成為虛擬社會和現實社會互相切換的開關。在此意義上,麥克盧漢的名言“媒介即信息”可算是網絡時代的預言。網絡最大的優勢就是提供了渠道,四通八達、左右逢源的互聯互通激發了人們的表達欲望和無窮想象。當網絡帶寬足以傳播流暢高清的音畫數據時,對于普羅大眾來說,叫做視頻還是電影,也許并不重要。所以,網絡改變的是人們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思維方式。比如微電影《冰山》,留學美國學電影的劉忱在樂視網的資助下,大膽觸碰了同性戀題材,試圖通過兩個女人的情感交集而呈現的冰山一角來揭示人性之復雜。這個片子在拍攝制作手法上盡可能地追求電影的聲畫效果以達到專業水平,從而受到廣泛關注。移動互聯時代的到來,使得在手機、iPad這樣的移動終端收看影片變得靈巧的同時,對畫面的審美特征需求也相應發生變化,比如更多的特寫、更少的大景等;同時為滿足移動互聯時代人們利用坐車、等候等大量零碎時間隨時隨地接收信息的特點,對題材的碎片化也提出了要求。并且,以網絡的視角來研究微電影,其針對性是精準傳播,因此還有路徑的問題。
其次,網絡傳播與傳統大眾媒介傳播不同的是,網絡需要網民的圍觀、擴散。仿若病毒式的傳播方式方可產生更大的社會效果,與關鍵節點相對應的類似于輿論領袖的大V的評論、轉發等對于影片的傳播效果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粘度是伴隨著微電影傳播效果的重要考量指標。網絡的開放性,使得對網民的可控性變得渺茫,但也正是因為網民面對海量信息的盲目感,反過來又使網上的輿論控制變得可能,從而發展成為商業炒作。在大眾傳播學的視角中,作品傳播越廣,其在受眾中的影響可能越大。網絡在除了傳統大眾媒介所具有的點到面的傳播方式外,還可以實現點到點的精準傳播。并且,傳統媒介的受眾更加被動,雖然隨著媒介的豐富,受眾的選擇性越來越大,然而與網上的海量信息相比,傳統媒體受眾的選擇性仍非常小;此外,傳統電子媒介如廣播電視的線性編排模式,也限制了受眾的選擇。但是,網絡的互動性在實現精準傳播的同時做到了有效傳播。在科技視角下,對于微電影來說,路徑決定了傳播對象,這才是更重要的問題。如桔子水晶酒店集團的十二星座系列微電影,配合新浪微博的病毒營銷,每集點擊量達到了三四百萬,總播出量超過了4000萬次,微博轉發超過了100萬次,成為2011年最火的病毒營銷視頻。
以網絡視角看待微電影,再次是交叉融合的問題。科技的發展打破了傳統的壁壘。譬如電影最終被認為是綜合藝術,就是把表演、音樂、舞蹈、美術、燈光、攝影等藝術門類綜合在一起,從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形式。可以說電影一開始就具有了交叉融合的能力,在這一點上對應了電影科技的進步。同理,隨著數字技術和放映設備的進一步開發,不再使用膠片拍攝以及不使用拷貝放映電影必將成為一個趨勢。互聯網無處不在的通聯效果,讓影片視、音頻信號同時傳輸到每個影院成為可能。無論是電影還是微電影,在理論上通過數字技術利用網絡進行傳輸是沒有問題的。當影院采用數字放映的時候,當微電影進入影院的時候,對于觀眾來說,區別電影還是微電影已經沒有意義。微電影升級為互聯網電影就是一個證明。這時,網絡的高度融合性使得藝術形態的邊界發生了飄移或者變得模糊。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微電影是一個歷史名詞,是一個時代的產物,它產生的意義在于催生一種新的節目形態,或者說是一種與某種文化息息相關的影視節目形態。所以說,微電影既是網絡從渠道上強力介入影視藝術的表現,又是網絡從形式上定義生活的一種載體。
三
微電影是消費社會里融合性的體現。消費社會使微電影與廣告營銷合二為一。2011年被稱為微電影元年。⑧開山之作被公認為推廣凱迪拉克的廣告影片《一觸即發》。不亞于大片的場面,高超的影視語言和演員的專業化,怎么看都是一部扣人心弦的影片。然而與傳統廣告片不同的是,這部影片有更長的篇幅、更震撼的敘事手段,從而也就賦予其更強烈的傳播效果。而且,超出這個影片的故事之外,人們最終會意識到它所要傳達的價值觀,或者文化理念,通過移情效果,來獲取觀眾以及消費者的文化認同,從而在消費心理上讓商家占領先機。不久前,國內某汽車公司出品、青年實力派演員李晨主演的《致父親》微電影風靡網絡,點擊量近2000萬次。各大門戶網站紛紛轉載,并在央視電影頻道播出,其超高性價比的營銷推廣為媒體所津津樂道。與其他植入汽車廣告的微電影不同的是,《致父親》沒有把影片定位為長廣告,而是以一個溫馨且簡潔的生活故事,來喚醒80后沉睡心底的對父愛的感恩。如上面提到的桔子水晶酒店集團的十二星座系列微電影,把星座、愛情等年輕人喜歡的元素與酒店設計結合起來從而吸引顧客,并進一步將微電影變為盈利項目,植入了奔馳汽車等十幾家公司廣告,且轉發即可獲獎品,有力地推動了微博營銷的力度。這就是在文化的基礎上進行的營銷活動,成為消費社會以文化輸出影響社會的重要方式,也是信息消費在現實社會的一種具體表現和衍生行為。從《一觸即發》到《致父親》說明,微電影一開始就為推廣營銷某種商品而生,然而與商品廣告不同的是,普通廣告要靠在媒體上的不斷重復才有可能達到營銷效果,由于篇幅和預算的限制,微電影不可能在傳統媒體如電視上反復播放。微電影的時間長度比廣告要多得多,在傳統媒體的傳播成本也相應要高得多。在解決了播出渠道的問題即網絡播出后,由受眾在新媒體上觀看,微電影的播出成本便由網民分擔了。廣告是傳統媒體的寵兒,微電影則由新媒體提供播出渠道。微電影可以更豐富地傳達廣告商的意圖,達到影響消費者的目的。雖然從動機和目的看,兩者都是商業推廣的形式,然而與廣告相比,微電影更具文化力量,它是在影片的放映過程中不斷累積產生的,而廣告則是通過播放次數的累積、由量變到質變來達到文化目的的。
微電影依靠網絡進行營銷推廣的傳播方式,促使微電影成為一種新的宣傳方式。營銷推廣是通過在觀念上說服消費者進行消費的傳播方式,而宣傳也是通過傳播在觀念上勸服受眾改變行為的做法。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宣傳也是一種營銷。互聯網是繼電視之后成為受眾最信任的信息來源。微電影借由網絡傳播被應用為宣傳手段,“其社會化媒體的傳播方式和病毒式傳播特點都有利于發揮受眾主體性,實現價值觀的迅速傳播和意義共享,微電影對于主流價值觀的弘揚具有特殊作用”⑨,微電影從而進入主流意識形態領域。還有北京大學圖書館在紀念建館110周年的慶典儀式上,發布并首映了微電影《天堂圖書館》,通過祖孫兩代與北大圖書館的不解情緣,深刻地表現了北京大學圖書館獨特的人文精神及其厚重的歷史感。再如,在2013年閩南文化節期間,主辦方展播了《我在泉州遇見你》《泉城往事》《潤餅》《佛門少年》和《海峽情》等多部微電影,在宣傳閩南文化的同時,最終指向對閩南文化核心城市——泉州的宣傳。
廣告成為影片,文化作為內容,這就是科技進步后帶來的文化融合所產生的微電影現象。因此,微電影作為一種節目形態,其重要意義既不在于豐富了表現手段,也不在于對社會現實的反映,而是其發生的當下性和融合性,即網絡科技的發展對于歷史邊界的消融以及對于傳統觀念的革命。為此,適應網絡科技的發展和消費社會的特點,轉變觀念,以文化消費的方式培養網絡傳播思維是微電影為我們帶來的啟迪。
注釋:
① 何建平、張薇:《中國“微電影”研究現狀綜述》,《當代電影》,2013年第6期。
② 微電影.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4342291.htm。
③ 倪祥保:《“微電影”命名之弊及商榷》,《電影藝術》,2012年第5期。
④ 于麗娜:《微電影:電影抑或類電影?——從〈大雨〉系列看微電影的電影屬性》,《藝術評論》,2012年第11期。
⑤ 賈娜:《微電影·大世界·正能量——全國檢察機關首屆微電影展播活動題內題外話》,《檢察日報》,2014年2月28日第5版。
⑥ 龍平川:《呈現美麗與復雜的世界》,《檢察日報》,2014年2月28日第5版。
⑦ (中國臺灣)鄭秉泓:《微型時代的逆襲——臺灣短片創作狀況》,《當代電影》,2012年第6期。
⑧ 許婭:《微電影廣告的類型研究》,《新聞知識》,2012年第7期。
⑨ 瞿杉:《微電影對弘揚主流價值觀的作用研究》,《新聞知識》,2012年第7期。
(作者系福建泉州廣播電視臺黨委書記、副臺長、高級編輯;吳凱穎系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發展研究院2014級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