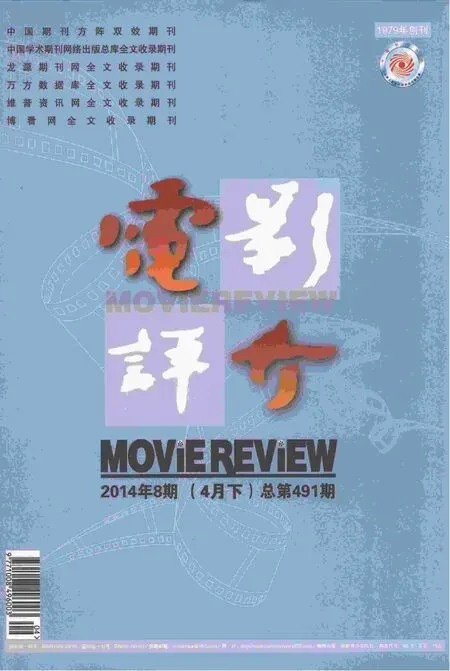論飛散視角下木心的創作:以《溫莎墓園日記》為例
□文/楊 希,杭州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生

著名作家、畫家木心
一
木心1927出生于浙江烏鎮的一個富裕家庭,童年接受傳統的私塾教育,在當時中國南方富裕之家較為開明,木心也從小接觸西方文化,喜愛西洋畫和外國小說。之后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和杭州國立藝專研習中西繪畫。木心總是帶著藝術家的純粹來對待當時紛亂的世事,木心在環境艱苦的條件下始終不放棄寫作,甚至在文革獄中也堅持寫作,似乎藝術是可以改變外在環境的。“我經歷了多次各種‘置之死地而后生’,一切崩潰殆盡的時候,我對自己說:‘在絕望中求永生’。”[1]1982年木心移居紐約,到2006年返回烏鎮故鄉,這期間經歷了二十余年的美國紐約定居生活,大部分作品都是到美國之后完成的。
木心在歷經文化劫難的文化大革命后來到美國,是因為“目前的中國,這流傳兩三千年的精神命脈是斷了,文學的潛流枯涸而消失。”[2]“我可不是理想主義者,我是從急驟墮落的東方文化的絕境中,倉皇脫越而來到西方的,西方文化也在衰頹,然而總要尊嚴些,舒徐有致些。”[3]但這并不是說木心拋棄了中國傳統文化,正相反,木心認為自己是帶根的流浪者,在木心那里,藝術文化原是沒有民族界限的。木心以詩和畫最有盛名,其次是他的散文和小說。本文主要從小說集《溫莎墓園日記》中來分析木心融合中西兩方面的寫作手法和文化意蘊。
二
Diaspora在我國譯為“流散”、“離散”,是我國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的一個術語,“離散”的中文翻譯帶有離開家園的鄉愁,在不同文化環境中身份認同的障礙,漂泊異地的悲情色彩,這也與這個詞含有猶太人流離失所的本意相符合。離散文學的代表作家有嚴歌苓和白先勇,這些作家的特點是深受中西兩種文化熏陶,擁有跨文化,跨民族的世界視野。隨后美國加州大學童明教授提出了飛散的新譯法,對Diaspora不同譯法的變化也體現了這個詞本身意義的變化。從翻譯“離散”轉變為“流散”也體現了原詞在時代變化下意義的變化。
親身經歷過抗戰、內戰,甚至經歷過文革迫害的木心在作品中鮮少提及這段歷史,他的文字沒有抱怨和含沙射影,木心的文筆始終透著淡然,一份貴族的悠閑自得。作品中雖有鄉愁但這鄉愁總是淡淡的,絕不是悲觀的。就木心的小說集《溫莎墓園日記》來說,整個風格是恬淡閑適的。
三
木心熟悉西方古今的思想經典又有中國文化的底蘊,他的作品中必然體現了中西文化的相通性,展示了世界性的特點。而木心對人類在現代社會中面臨的一系列問題的書寫體現出深遠的慈悲關懷。木心對自己所經歷的時代沒有抱怨,而把它看成歷史的必然,以一種超然的姿態審視歷史卻不失慈悲。木心童年時就已經接受西方文學洗禮,學會用中西兩只眼睛觀察世界,他在《魚麗之宴》里寫到:“我的童年少年是在中國古文化的沉淀物中苦苦折騰過來的,而能夠用中國文化給予我的雙眼去看世界是快樂的,因為一只是辯士的眼.另一只是情郎的眼。”[4]木心的作品不是展現了激烈的東西方文化沖突,而是把世界看成一個整體的家園。木心認為現代文化的第一要義是整體性,而不是某一個中心。木心的小說兼具散文和詩的特質,文筆帶著貴族的小資情結。
下面從兩方面以小說集《溫莎墓園日記》為例分析木心在飛散視角下展示的對世界各族文化的體察以及隱含在作品中的人文關懷。
(一)以美國為背景展現了西方現代社會文化
《美國喜劇》記敘了“我”在美國的兩件小事:“我”在窗口總是看見一位穿著精心打扮的少婦,天氣炎熱她卻始終在街邊等待,“我”觀察她的衣著猜想她等待的情郎,為她的癡心感動。終于有一天“我”決定看看她等待的情夫,沒想到迎面而來的是一輛公交巴士。
她蠕動,她舉手,招揮,多稚氣……她朝著來者的方向奔過去……長而且大的巴士駛進,這一段人行道全是車身的投影,她奔過去的地方是巴士站——上車。
上午九時以后,郊區巴士的班次減少,又不準時,每次難免要久等。
這是“我”在美國生活中的一個小笑料,反映了美國女人們對外表禮儀的重視,也反映了現代社會大城市生活的擁擠與不便。
第二件小事講述了美國司法的嚴謹,“我”在高速公路上超速被罰款和違章吸煙被罰款,由此產生對法律過于繁瑣細小的不滿,聯想到對美國宣揚的自由的更深層次的認識。我超速去自首是因為美國警察有雷達波記錄,這點小事卻還需要在法庭辯護,在警察審訊違章吸煙罪時有個小細節,警察打了個噴嚏,隨即說一句文雅的歉詞。作者反映了美國文化法律的嚴謹,卻又認為“文明是愚蠢的復雜化”。而在法律的復雜化下,作者又思考了自由的涵義:
“自由”就是這樣吧。如果再提一項“免于納稅的恐懼的自由”,羅斯福夫人會發愣,再提一項“免于購物付款的恐懼的自由”,可尊敬的夫人要拿起電話喊人了。
《第一個美國朋友》講述了七歲的主人公住在美國福音醫院和院長孟醫生成了忘年交的故事。孟醫生對待病人如親人般,對工作謹慎勤勉,對“我”更是格外照顧,怕“我”寂寞送來一堆畫報雜志,福音醫院里的護士和醫生都是基督教的信仰者,對待病人體貼,既有醫德又有醫術。“我”雖然進行了切除扁桃體的手術但是卻留下一段難忘的美好回憶,二次大戰沖散了他們,但這段友情銘記在心。作者在這篇文章中表達了對美國醫療工作的贊美,以及對西方基督教寬厚愛人品質的欣賞,而木心本人對耶穌也帶有崇敬感,木心受過諸多磨難卻始終擁有平和的心態對待一切,這份慈悲之心正像為人類贖罪上了十字架的耶穌。
《SOS》描寫了輪船海難沉船前的一幕:臨盆的孕婦,外科醫生,即使在即將沉船面對死亡之時,醫生仍然不忘搶救生命,迎接新生命。結局在“海水墻一樣倒進來,灌滿艙房”中結束,但是歌頌了西方文化中對人的尊重,人性在災難前的光輝。木心認為現代中國沒有經歷過西方的文藝復興,啟蒙主義思潮始終是缺欠的,對個人價值的重視不夠,木心在那個時代已經能客觀看待中西方文化了。“到了現代,西方人沒有接受東方文化的影響,是欠缺、遺憾,而東方人沒有接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就不只是欠缺和遺憾”[5],東方和西方是相互對話的關系,現代文化不是“中心論”,而是相互吸收成為整體。
(二)中國現代歷史下對小人物命運的思索
《夏明珠》講述的是“我父親”沒有名分的姨太太夏明珠在父親病故后想回到“我家”,夏明珠深受西方教育影響,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服裝打扮西化,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我”居住的小鎮淪陷于日本法西斯之手,夏明珠遭日本人猜疑、逮捕,嚴刑逼供甚至受侮辱,最終死于日本人之手,女兒也被賣掉下落不明。《芳芳No.4》講述了青春年少、下鄉、文革、嫁為人婦四個時期的芳芳,“文革”只當作一個背景,故事情節看上去一點也不傷感,但芳芳身上的變化卻留下了那段歷史的烙印:
膚色微黑泛紅,三分粗氣正好沖去了她的纖弱,舉止也沒有原來的僵澀,尤其是身段,有了鄉土味的婀娜……本是生得姣好的眉目,幾乎是顧盼嘩然……
她的眉眼口鼻還能辨識,都萎縮了,那高高的起皺的額角,是從前所沒有的……江南三月,她卻像滿臉灰沙,枯瘦得,連那衣褲也是枯瘦的。
年青時的婀娜風韻被風霜粗俗取代,這段前后對比的外貌描寫讓人想起魯迅筆下的少年閏土與成年閏土的差別。夏明珠和芳芳的遭遇都讓人唏噓不已。
《此岸的克利斯朵夫》是木心為了悼念亡友席德進而寫。席德進是木心在杭州藝專的好友,木心用羅曼羅蘭筆下的克利斯朵夫來相比席德進,是因為席德進喜愛唯美主義,是個浪漫主義者,是接受五四后西方思潮的進步青年,而他也是個勤奮努力又有天分的人。但是中國的現實讓他只能是個“浪漫主義在中國的遺腹子”。正如作者的感悟:
中國沒有順序的人的覺醒、啟蒙運動,缺了前提的浪漫主義必然是浮面的騷亂,歷時半個世紀的浩大實驗,人,還是有待覺醒,蒙,亦不知怎樣才啟。
《約翰·克利斯朵夫》被藝專學生奉為經典,但是這遲到的西方思潮與歐洲的時間差距是一百年四百年。
這種本是裨人清醒的“英雄的氣息”,反而弄得我們喝醉了酒似的,將藝術的人物傾在生活中,而把現實所遇者納入藝術里。我們的青春年華是這樣結結巴巴耗完的。
席德進后來去臺灣當了老師,后來成為臺灣著名的畫家,“我”剛得到好消息卻又被告知他患上癌癥,“我”從前寫給他的信始終無法交到他手里。
羅曼羅蘭在其小說的終局,克利斯朵夫渡過了河……席德進是有望渡河,突然折倒在岸邊……
(三)中西結合的寫作技巧和思想內涵
木心的短篇小說中有的背景是中國,人物是中國人但是卻采用了西方短篇小說的寫作技巧;另一種是小說背景是國外但寫作上沒有側重故事情節反而注重氛圍的描寫,營造了朦朧唯美的中國美學意境。正如童明評價木心的寫作具有世界性美學思維,集中體現在他散文和詩的寫作中,在他的短篇小說寫作中也體現了這點。
《一車十八人》講的是“我”研究所里的司機李山和十七個男子開車去參加討論會,李山婚姻不和睦性格變得沉默寡言,除了“我”公司沒有人關心他的生活。因為李山的遲到一車人對他冷嘲熱諷,在他們眼里李山近年不肯動用公車來便利他們的生活,他就沒有可利用的價值了,只有“我”為他說話。開車中途李山怒斥讓“我”下車,車朝著懸崖開去……出人意料細想又合理的結尾方式很有西方短篇小說的特點,還有點偵探小說的懸疑味,展示了人性的自私自利。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沒有說明是這篇小說的改編,但是故事情節完全類似的一部電影《車四十四》,女大巴司機開著滿載乘客的車在公路上遇到兩名在公路上遇到兩名劫匪,女司機被劫匪強暴,全車只有一個男乘客反抗幫助她,最后女司機強迫讓這位男乘客下車,自己開著車駛向懸崖。這部2001年的電影短片獲得58屆威尼斯電影節評委會大獎,電影改編的比木心的小說更合情合理,矛盾沖突更劇烈,更加突出了人性中虛偽冷漠的一面,也充分說明這部電影的原型木心的小說深得西方文化精髓。
中國古代背景的《七日之糧》出自《公羊傳》中《宋人及楚人平》,春秋時期楚莊王圍攻宋國,楚軍只剩下七日的糧食,楚國大夫司馬子反和宋國大夫華元相互刺探情報得知宋國已是“易子而食”的地步,司馬子反說服楚莊王退兵的故事。原故事在中國古代的評價褒貶不一,君子贊揚兩位大夫為百姓著想,而有的人認為大夫私下講和有違國君的權威。在木心的筆下這篇小說以第三人稱司馬子反的視角描寫,側重司馬子反的心理刻畫,心理刻畫正是西方小說的長處。故事以月亮開頭以月亮結尾,全文籠罩在月色下,增添了東方神秘的韻味。木心在原故事的基礎上虛構了司馬子反把一半糧食留給宋城的情節,這體現了西方的人道主義精神和人文關懷,同時這也是中國傳統儒家思想中“仁愛”的思想,正如這個故事中所說的“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的仁者愛人、兼愛非攻思想,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匯就在對人的尊重、關愛上。而木心的這篇小說就把西方的人道與東方的仁愛思想通過運用西方小說技巧表達出來,中西文化是相通的。
同樣是中國古代背景的《五更轉曲》寫的是明末清初清軍南下江陰,在南京已經不戰而降的情況下,江陰駐守官兵和百姓毅然決定赴死一戰,結局是壯烈悲壯的,清兵損失慘重。作者在結尾特意說明“尸體滿街巷,無一投降者”。寫的是中國故事,卻贊頌了人的生命力的頑強,在決戰前官兵醉中唱起了《五更轉曲》,全城百姓引吭高歌。雖然完全是中國的故事,但在木心筆下卻有了荷馬史詩的韻味,以悲劇來贊頌人的偉大。
而《月亮出來了》則是發生在西方都市的一個雨夜,公爵和公爵夫人在大雨中乘坐馬車回家,途中馬車陷進泥坑里,兩人和車夫一起推車,雨停了月亮出來了。月光、夜色下伴隨著馬鳴,這里的景物描寫別有一番情趣:
皓月中天,蒼穹澄澈,幾片杏黃的薄云徐徐飄過曠野……
月色分外清幽,馬嘶,劃破夜的靜空,遠處的林叢絪氳著霧意,月光下的曠野有古戰場的幻覺。
區別于西方的以人為本,中國傳統思想一直很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以莊子思想為代表的道家思想強調“天人合一”,而中國傳統美學的概念“意境”就是對自然景物審美的升華,由景及人,情景交融。在木心的一系列散文中都體現了中國美學含蓄雋永的美學思想,這在小說中也有體現。自然本位的文化下自然都是有著人類情感的,帶上了人的主觀性,而實際上自然又是無知無情的存在。這與西方文化中人本位的觀念完全不同,在西方文化中歌頌人自身的生命創造力,人生的價值在于生命意志,西方美學中悲劇的美就在于人在反抗宿命時顯得偉大而有尊嚴。
結語
木心對中西兩種文化的理解是:“所謂東方,中國才是代表,補給西方,正是對的,因為西方最缺的就是中國的東西:含蓄,以弱制勝。東方西方要是真的相通,文明才開始。可是要喚醒東方,中國,非得西方來理解”[6]木心熟悉西方經典又有中國文化的底蘊,他的作品體現了中西文化的相通性,展示了現代文化的整體性特點。東方和西方是相互對話的關系,現代文化不是“中心論”,不是以一方為尊貴一方卑微,而是相互吸收他人的優點成為世界文化家園。而木心對人類在現代社會中面臨的一系列問題的書寫體現出深遠的慈悲關懷和人文精神。
[1]木心.答臺灣《聯合文學》編者問[M]//魚麗之宴.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27.
[2][3]木心.1983—1998年航程紀要[M]//魚麗之宴.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109,117.
[4][5]木心.答美國加州大學童明問[M]//魚麗之宴.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75,72.
[6]木心.十九世紀德國文學[M]//文學回憶錄.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