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對“三野之地”的教化之功
劉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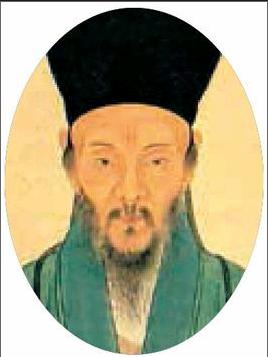

夕貶貴州路八千
明朝正德元年(1505年),戴銑等20余人聯名上疏反映朝廷的弊病,而被欲蒙蔽圣聽的劉瑾下令逮捕。劉瑾是明朝最著名的權閹之一,有“立地皇帝”之稱。
時任兵部主事的王陽明聞此消息,仗義執言寫就《宥言官去權奸以章圣德疏》,不僅痛斥了權傾朝野的大太監劉瑾,而且觸怒了至高無上的皇帝,被廷杖四十大板之后,發往貴州龍場擔任驛棧驛丞。
翻山越嶺,長途跋涉,正德三年(1508年)春,王陽明輾轉來到貴州。
抵達龍場驛站時,王陽明想必十分沮喪和苦悶——龍場驛站破敗不堪,總共有吏一名,馬二十三匹,鋪陳二十三副。不僅辦公條件差,還不提供住宿,王陽明只得在驛站外的草棚或山洞棲身。
王陽明并未怨天尤人,更未就此消沉。龍場百姓的好客與熱情幫助也給予他極大的勇氣,他將所有的時間都投入到學術研究上。他不分日夜,埋首苦苦思索,終有一日,他突然頓悟,首次建立了“知行合一”的學術理論,并以四書五經驗證,“然后嘆圣人之道坦如大路”。
心學建立后,王陽明便移居龍崗山,將一巖洞更名為“陽明小洞天”,在洞內開始傳道授業。當地居民敬佩陽明先生的品德和學識,不忍他居住在潮濕陰冷的洞穴里,自發幫助他修建了木屋,王陽明十分感動,欣然把木屋分別取名為“何陋軒”、“君子亭”,并正式創立了“龍崗書院”。
“龍崗書院”不僅是王陽明本人創辦的第一個書院,更首開貴州書院講學之風,他不顧所謂“華夷之別”,對當地不同族群的學子一視同仁,將腹中學識傾囊相授,更與龍場普通群眾相處融洽。這從王陽明留下的諸多詩篇中便可看出:“宴適豈專予,來者得同憩”;“起來步間謠,晚酌檐下設。盡醉即草鋪,忘與鄰翁別”;“村翁或招飲,洞客偕探幽”。
盡管王陽明在貴州僅僅三年,但這三年對于王陽明的一生至為重要。他不僅初步創立了自己的學說,更從此開始傳播。三年間,上至水西土司,下至普通鄉民都對王陽明極為照顧。貴州淳樸、善良的民風,與權力中樞的勾心斗角、爾虞我詐形成了鮮明對比,更使他明白了“惻隱之心”的可貴,進而創立了陽明心學。可以說,王陽明大大推動了貴州乃至西南土司地區的文化教育發展。
儒學化夷穩邊疆
自元軍繞道西南滅宋之后,西南邊防就備受重視。為維護對西南地區的統治,明朝沿襲了元朝的土司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邊防壓力。但自“土木堡之戰”后,朝政混亂,加上衛所屯軍玩忽職守,安于太平,戰斗力低下,導致當地土司圖謀不軌。當時王陽明雖僅是一個驛丞,卻在穩定西南邊疆上起到巨大的作用。
貴州土司林立,但其中最具威望者當屬水西安氏,時任貴州宣慰使的安貴榮對王陽明的才學十分崇敬,又同情其遭遇,經常派人送來肉、米、金、帛、鞍馬,幫助陽明先生解決生活所需。
當時,安貴榮屢立戰功,見慣了衛所屯軍的不堪一擊,于是心生驕橫,不受節制,還總抱怨獎賞太少,并萌生了妄自尊大的邪念。
王陽明對安貴榮的照顧十分感激,但事關國家大局,他毫不含糊,多次指出安貴榮的不當言行,并加以規勸,并乘著安貴榮重修象祠,邀請他撰文紀念的機會,寫下了名重文壇的《象祠記》。
傳說中,象是舜的弟弟,曾多次在其母慫恿下謀害舜都未成功,最后被舜感化。水西安氏將象視作人文始祖,正是少數民族仰慕和認同中原文化,民族逐漸融合的象征。
安貴榮大肆興建象祠,有炫耀自己權勢的意圖。王陽明識破了他的不軌意圖,在文中指出,其他地區的象祠都早已被損毀,而唯有水西的象祠香火鼎盛,乃是邊疆之民感念其知過能改,更是感念舜對其弟弟的教化之功。王陽明讓安貴榮知道安也如同象一般,是個需要被教化的對象,進而發出了“吾于是蓋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的歷史強音,使安貴榮領悟到居功自傲、貪婪無度的禍患,消除了其妄自尊大的邪念。
之后,安貴榮又上書朝廷要求裁廢水西九驛。水西九驛是安貴榮祖上奢香夫人受令興建的重要驛路。
朝廷既不愿得罪能征善戰、極具威望的安貴榮,又深知驛站對于西南邊防的極端重要性,一時難以決斷。關鍵時刻,王陽明挺身而出,以一封書信對安貴榮提出正面警告和斥責。
在信中,王陽明正面回擊了安貴榮改變驛站舊制的無理要求,還直言安貴榮以地方諸侯的身份要求朝廷修改驛制是犯上作亂的大罪,指出若再提出這樣的無理要求,必會失去朝廷的恩寵,到時候不僅驛站不會減少,安貴榮的宣慰使職位也將被革除,整個家族可能面臨滅頂之災。安貴榮聽從了王陽明的諍言,收回裁廢驛站的要求。
根據明制,水西安氏與水東宋氏共治貴州,其中安氏為宣慰使,宋氏為宣慰同知,一掌印,一掌文書,兩家相互合作又互為牽制,這一規定保證了貴州穩定和驛路的通暢,但由于安貴榮屢立戰功,權勢不斷提升,安氏與宋氏的平衡被打破,安貴榮也產生了吞并宋氏的野心。他拉攏教唆平日里飽受宋氏殘害的民眾作亂,圍攻宋氏土司住宅,宋氏兵敗被困,土司宋然只身幸存。事發后,朝廷下令安貴榮出兵平叛,安貴榮卻托病不出。一時間,貴州大地狼煙四起,百姓飽受折磨。
此時,王陽明再次挺身而出,他致信安貴榮,斥責其謀利重罪的同時,還列舉了安貴榮必敗的原因,并循循善誘地加以開導。安貴榮最終幡然悔悟而出兵平叛。
不費朝廷一兵一卒,王陽明僅靠一封書信就化解了貴州持續多年的亂局。
陽明先生三次成功勸誡安貴榮,不僅因為安貴榮尊崇王的人格及學識,更重要的是王陽明始終在潛移默化中以自己的心學教化著包括安貴榮在內的“夷民”,“儒學化夷”絕不是口號,而是陽明先生在貴州的三年里一以貫之的準則。
了卻君王天下事
正德五年(1510年)初,王陽明謫戍期滿,復官廬陵縣知縣。八月,劉瑾被處死,王陽明被召入京。正德十一年(1516年),升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地,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王陽明前往福建平定叛亂。途經江西時,寧王朱宸濠叛亂,王陽明舉兵勤王,平定了叛亂,也成就了一生最大的軍事功績,但他急流勇退,稱病返鄉,直到正德十六年(1521年)世宗即位才因平叛有功而加官進爵,先升為南京兵部尚書,后加封為新建伯。嘉靖元年(1522年)王陽明的父親王華去世,王陽明返鄉守制,一直到嘉靖六年(1527年),他都在家鄉創辦的書院安心教書,宣講心學大道。
嘉靖六年三月,田州土司岑猛叛亂被總督姚鏌清繳,姚鏌不肯放過岑猛手下部將,于是盧蘇、王受二人起兵叛亂,并先后攻下了田州府和思恩府兩座府城,一時間朝廷震動。姚鏌調集了兩廣和湖廣三省的土、漢官兵八萬人馬,前往征剿,卻久久未能平叛,此時已五十五歲的王守仁再次臨危受命,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總督湖廣、江西、廣東和廣西四省軍務。
思、田二州的叛亂原因比較復雜,既涉及到土司間的恩怨,又與改土為流的國家政策有關,還涉及到民族問題,姚鏌就是因為手段過于強硬,才引發了更大更嚴重的叛亂。王陽明抵達廣西后,厘清了盧蘇、王受叛亂的原因,用計先后撫定了盧、王部眾,繼而對思、田地區采取“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的具體治策,迅速平定了叛亂,維護了地方社會穩定,鞏固了西南邊疆安全。隨后又借助當地土司的力量平定了斷藤峽諸寨的苗民起義,王陽明向朝廷報捷稱消除了兩廣地區百年來的心腹大患,以十分之一的花費達到了數倍的成效。
但立下大功的王陽明再未受到任何封賞,他終于倒在了回家的路上,臨死之前,他用手指心,留下了“我心光明,亦復何言”的遺言。
縱觀王陽明先生的一生,都與土司有著不可分割的緊密聯系,貶謫至貴州,悟道于龍場,傳道于龍崗,授業于貴陽,勸誡安貴榮忠君向善,在岑猛被殺而導致的田、思之亂中最后一次替君王了卻天下事后,駕鶴西去,留給世人的,是無盡的傳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