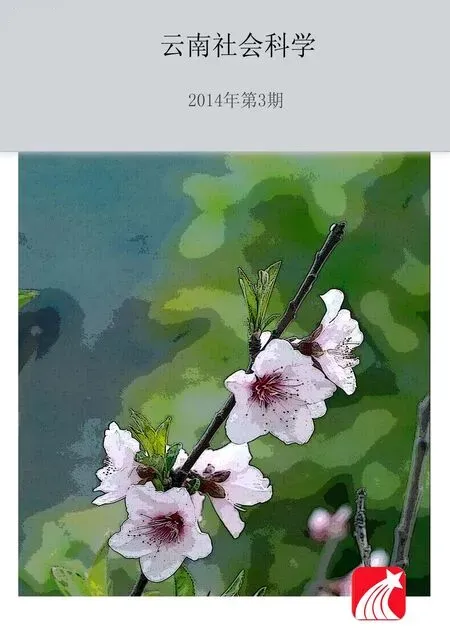民族村寨居民抵制社區旅游的內在機理及對策研究
馬東艷
隨著旅游體驗時代的到來,作為記錄某一歷史時期典型風貌習俗特色,傳承各民族傳統,具有很高歷史認知和審美觀賞價值的民族村寨,成了備受游客青睞的旅游目的地。寨內居民作為民族村寨社區旅游的重要主體,其對社區旅游的態度和行為關系到社區旅游發展的成敗。隨著民族村寨社區旅游的不斷發展,有的社區居民對旅游的抵觸情緒也愈發強烈,當這種負面情緒不斷累計到一定程度又沒有及時釋放的情況下,就會發展成為旅游沖突。在一些地方,旅游沖突有愈演愈烈之勢,甚至出現了嚴重的對抗事件和群體性事件。盡管業界對民族村寨居民抵制社區旅游的關注持續升溫,但學術界就這一議題所開展的理論研究卻相對滯后。基于此,本文擬深入分析民族村寨居民抵制社區旅游的深層次機理,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以促進民族地區社區旅游的健康發展。
一、案例回放
案例1:具有“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遺產地之稱的“云南迪慶藏族自治州”因其擁有哈巴雪山、白馬雪山、梅里雪山和虎跳峽等雄奇自然景觀以及獨特的康巴文化而成為中國西部地區具有極高旅游文化價值和科學價值的重要民俗旅游地區,它也是中國大香格里拉生態旅游區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被學者們譽為中國西部民族村寨社區旅游發展的窗口。但是在迪慶州香格里拉縣崇古村和小街子村,因門票大部分收益被當地政府攫取而引發了村寨居民群體和政府之間的暴力沖突;而在該州的虎跳峽村,因開發商和居民的門票收益之爭引發了村民對開發商的聚眾抗議;在該州德欽縣的明永村,村民在入山空地上自建的賓館、食品店等旅游接待設施被旅游部門認定為非法建筑而予以拆除,而旅游部門卻在此修建了大量的旅游接待設施,此舉雖未引發激烈的社會沖突,卻也引起了居民的極大不滿;在迪慶州吉沙村,因開發商對居民征地補償標準過低以及不容許居民進入開發區從事任何經營活動而引發了居民集體和開發商之間的激烈矛盾沖突,而且這種矛盾沖突一直未能平息。
案例2:云南省西雙版納傣族園因其濃郁的傣族民間歌舞、傣族特有的干欄式建筑等傳統傣族民族風俗以及小乘佛教等宗教文化而具有“人間仙境”和“鮮活的民族歷史博物館”之稱。但是在這里,也因為門票分成不公而造成了村民與旅游開發公司之間的直接沖突,積怨已久的村民甚至自發組成卡車和挖掘機車隊圍堵景區門口,嚴重影響了傣族園的正常運營。同時還因征用村民耕地補償標準過低、開發公司在各村寨招工不均衡、對經營傣家樂的村民征收管理費等問題,導致村民對開發商乃至整個旅游開發極為不滿,矛盾沖突不斷。
案例3:位于四川省甘孜州丹巴縣境內的甲居藏寨是該縣最具特色、知名度最廣、最具有旅游吸引力的景區。甲居藏寨憑借其濃郁的藏族風情、深厚的文化底蘊以及天人合一的獨特生態藏寨景觀,被譽為“中國最美藏寨”、“藏區童話世界”和“康巴風情名片”。甲居藏寨因旅游門票收益完全流向當地政府,以及政府將寨內規模最大的“甲居藏寨賓館”在村民不知情的情況下轉包給外來經營者,對寨內村民旅游接待活動造成沖擊,引發寨內居民極大的不滿。此外,外來經營者由于未采取污染處理措施而使寨內的飲用水源受到了嚴重污染,廣大寨內居民對此極為憤慨,幾乎爆發惡性事件。
類似上述居民與政府或旅游開發商之間的矛盾沖突在中國絕非是一種高度地方化的事件,而是在我國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普遍存在的一種現象,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1]。隨著社區旅游的發展,民族村寨居民普遍感覺自己被旅游發展所排斥和利用,其合法權益在旅游發展中被踐踏,為了發泄內心的強烈不滿,他們憤而采取行動,已經由以往個別村民破壞景區景觀等私人行為演變為一種集體性的靜坐、游行、圍攻、上訪告狀等抗議活動。但這無助于改變居民被不公平對待的現實,于是他們就開始采取打砸搶燒等蠻橫的極端手段進行抗爭。因此,引發了多起居民與當地政府或旅游開發商的惡性暴力沖突事件。這不僅會破壞民族村寨給外界的旅游形象,而且會嚴重阻礙當地社區旅游的可持續發展。因此,民族村寨居民抵制社區旅游的研究開始受到學者們更為廣泛的關注。Gursoy& Rutherford(2004)指出,沒有當地居民對旅游業發展的大力支持,任何民族地區旅游業的發展都不可能取得成功[2]。基于此,本文以新的理論視角對引起民族村寨社區旅游矛盾沖突的機理展開深入的分析,同時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以解決民族村寨社區旅游開發與發展問題。
二、矛盾沖突的內在機理分析
1.政府或開發商對旅游發展擁有絕對控制權
民族村寨旅游資源特有的“稀缺性”造就了其潛在的巨大資本價值。在旅游基礎設施和旅游景觀受“瓶頸”制約時期,無論是資本還是旅游者的可進入性和流動性都十分有限,旅游者的進入給社區旅游帶來的資金非常微薄,也就是說旅游資源因規劃布局而被商品化的空間還相對較小,由利益分配不公引發的矛盾沖突也就不明顯。旅游開發的啟動也就意味著景區可達性和可進入性的空間障礙被破除,民族村寨旅游地理景觀的稀缺性、不可移動性和不可復制性使其成為源源不斷地吸引區域性甚至全球性旅游流的固定場所和獲利工具。隨著大量游客的涌入,民族村寨旅游資源蘊藏的巨大資本價值不但得以展現而且迅速增值,此時旅游資源就是資本,旅游者就是現金。旅游資源的公共池塘屬性以及由此引發的外部性需要政府介入和發揮其職能[3~8],但由于地方政府具有公共利益代表者(制定旅游發展的政策、規則、協調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矛盾、調配旅游資源和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等)和特殊利益集團(為提升政府政績或官員個人升遷,以尋求“租金”為目的,打著公共利益的幌子規避各種法律法規限制,與開發商結成利益同盟,不考慮或較少考慮甚至盤剝社區居民利益)的雙重身份,致使政府為追求自身利益而采取偏離甚至背離公共利益的行動。政府利益的二重性和隱蔽性使其經常巧妙地將政府利益內化為公共利益,因而對明顯有失公平的分配方案視而不見。政府利益對政府行為滲透的結果就是公權力公然對私權利進行侵犯。HohLandTisdelL (1995)指出: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可以通過行政權力控制和限制旅游在時間和空間上的流通性來實現其政治意圖和目標[9]。而作為市場經濟中最重要流動性資源的資本的所有者——開發商憑借其強大資本優勢可以向政府索要政策上的優惠。與擁有絕對權力的政府和擁有雄厚資本的開發商等強勢群體相比,民族村寨社區居民在這場收益分配爭奪的博弈中明顯處于劣勢,導致其利益必然被侵害。Ap(1992)與Sofield(2003)指出:在政府、開發商和社區居民的權力交換中,任何控制著旅游資源并擁有較強權力的一方必然會制造對另一方不利的交換結果,而失利的一方必然會采取反抗行動以改變其不滿意的交換結果。
2. 農民集體法人資格缺失,使集體所有權虛置
由于旅游開發受土地開發的控制,在民族村寨社區旅游開發與發展過程中,對農民集體土地的需求量急劇增加。在我國,農村土地歸農民集體所有,但由于農民集體不是法人組織,只是一個抽象的集合體,因此名義上擁有土地所有權的農民集體對土地不具有真正的處置權,農民集體只有被動接受土地轉變為旅游用地。土地是產生和創造一切財富的來源,而用于旅游開發與發展的民族村寨的土地更因其稀缺性和蘊含的巨大財富價值而在土地使用中產生巨大的利潤空間。由于農民集體對土地話語權的缺失,旅游開發商為獲得巨額利潤,對具有土地實際控制權的集體代理人和社區精英分子進行收買,從而廉價獲取了大量旅游資源的使用權和支配權,而部分集體代理人和社區精英分子為滿足個人利益,不惜損害廣大村民集體利益。
3. 現有條例和法律對居民權益的界定有失公平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規定:旅游用地屬于建設用地,政府在旅游開發中可以通過征收的方式將農業用地轉化為旅游用地,但只能按照土地原有用途對農民進行補償。因旅游開發使土地價值增值,那么對增值的使用權、收益權和處置權被相關法律法規強制性地界定給國家并由政府代為行使。在使用權的規定方面,對開發的范圍、開發利用的強度、項目的布局規劃、項目建設和門票銷售的權利等歸政府,雖然有征求居民意見的要求,但是并沒有可操作性的制度來確定其效力,而且居民只有建議權而沒有否決權。同時規定不得在景區內安排任何有礙風景的農業用地,這就使社區居民不得不放棄原本屬于自己的權利。在構成自然旅游資源產權的一組權利中只有景區服務項目經營權可以合法流轉,但由于目前的法律條例并沒有關于部分經營權必須流向社區的規定,結果是外來投資者獲得了這一權利,當地村民因缺乏資金和經營技巧而被剝奪了這一權利。對景區門票收入,雖然《風景名勝區條例》規定要將這筆收入用于對景區的保護、管理和對景區內財產所有權人和使用權人的損失進行補償,但究竟是否補償和在多大程度上補償又規定得非常籠統,具體由政府視情況而定,在缺乏有效監管的情況下,村寨居民被剝奪了公平分享旅游收益的機會,使巨額旅游收益成為政府的財政收入或被開發商收入囊中。
4. 產權的激勵作用無法發揮
“產權是個人或組織的一組受保護的權利,所有者可以通過收購、使用、抵押和轉讓資產的方式持有(消極的運用)或處理(積極的運用)某些資產,并占有在這些資產運用中所產生的效益”[10]。產權的作用在于,一方面激勵個人運用勞動或財產積極創收;另一方面使個人在與他人交易時形成一種合理預期,并由此促進勞動分工和財富的創造[11]。民族村寨旅游開發的特殊性就在于對旅游者產生強烈吸引力的不僅包括自然旅游資源,還包括民族歷史文化、民族建筑、民族風情習俗等文化旅游資源。民族村寨一旦從事旅游開發,原來由社區集體所有或居民個人所有的在本民族內部不具有稀缺性和經濟價值的民族文化資源就變成了具有稀缺性、排他性和帶來經濟效益的資產。正如科斯所指出的,“市場交易就是產權交易”,一個沒有產權的社會是一個效率絕對低下的社會,也是資源配置絕對無效的社會。只有對旅游資源產權進行清晰的界定,才能實現對資源的最佳配置,才能有效解決外部不經濟的問題(即某項事務或活動對周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而行為人并未因此而付出任何代價)和因旅游收益來源和分配公平性問題而引發的各種糾紛。如果旅游開發和發展不能使當地村寨居民獲得與自身為旅游發展所做貢獻相匹配甚至是足夠的經濟利益,那么產權就很難發揮其應有的激勵作用。
5.合法的利益訴求長期得不到滿足
由于農民自身能力有限以及信息不對稱,其在旅游開發與發展中常常被邊緣化而處于無可奈何的狀態。具體表現在:政治上無權(不能參與旅游決策、旅游規劃、旅游日常管理,無力避免好的旅游工作全部被外來人員占用);經濟上無權(不能公平地分享旅游收益和獲得補償,其收益與貢獻嚴重不符,旅游帶來巨大經濟利益但居民收入不但不能增加反而致貧、對旅游收益分配方案不滿但卻無力改變);心理上無奈(對旅游感到悲觀失望、沮喪、無助、挫敗感);社會上無力(承受旅游帶來的物價上漲、環境污染加劇、鄰里間關系緊張惡化、宗族血親關系淡薄、傳統生產生活方式遭受破壞等負面影響)。民族村寨旅游開發后,大量游客的涌入為村寨帶來了一些先進的思想和理念,居民的民主意識、參與意識和維權意識逐漸增強,但由于目前高昂的訴訟費用、繁瑣的訴訟程序以及基層行政執法人員對居民反映的問題重視不足、解決不力等因素的存在,使居民權益受損問題長期得不到有效解決。于是,他們不再幻想開發商會懷揣一顆慈善的心或政府會給予 “父愛主義”的關懷,而是自發組織起來靠不斷制造麻煩的“梁山泊式的”暴力事件進行維權,以為這樣可以引起媒體和政府的關注,加速問題的解決。有學者指出:如果這種不滿情緒無法通過制度化渠道得以合理合法的宣泄與釋放,積累到一定程度就必然會引發對現行制度、規范和秩序的懷疑、蔑視和敵視等各種危害社會穩定的悖逆式行為的發生。平時不滿卻沉默的大多數則很可能在一個很小的突發事件中成為憤怒的大多數,做出意想不到的破壞性行為,從而危及公共安全和社會穩定[14]。
三、對策建議
1. 完善法律,公平補償
我國現有的法律規定,只有國家才能因公共利益需要依法對土地實施征收,任何單位或個人因建設需要,征用除農村本集體自有土地外的任何農村土地,無論用途是公益性還是商業性都必須通過政府進行征收。由于在我國的憲法和法律中并未對公共利益進行界定,這種規定的模糊性使政府對農村土地征用權力過大、范圍過寬,經常導致侵害村民權益的行為發生,為解決這一問題就需要做到:第一,用新的法律對公共利益的項目或范圍進行清晰而又準確的界定,解決因法律上的模糊界定而賦予政府強制征收權的問題。第二,確立農村居民關于征地的知情權和參與權。土地就是農民的生命,沒有了土地農民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基。政府對與農民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土地進行征收必須保障農民的事先同意權、知情權,事中的參與權、表達權以及事后的申訴權,而且必須保障征地利要大于弊。第三,進行公平的補償。這就需要以市場為依據,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價值、供求關系以及地理區位,進行科學的考察、評估,并制定具體的、富有彈性的、公開、公正、公平的補償標準,取消原來的一次性貨幣補償和機械式倍數的原則。由政府將土地征用補償管理體制、程序、可供選擇的安置方案和補償標準公開告之被征地人并建立相應的審查制度、聽證制度和舉報制度,加強對征地標準和補償情況的監督與制約,同時設立專項基金為失地農民繳納各種社會保險并對因失地使生活窮困的居民給予適當補償。第四,對有失公平的法律和條例進行重新修訂。要減少民族村寨社區居民不斷進行的抵制旅游開發與發展的抗爭行為,就必須對有失公平公正的法律條例進行修改與完善,從而削弱馬太效應的影響,使強勢者不能獨享旅游收益,使弱勢群體獲得應有的補償。
2.進行旅游增權
權力由權利產生并受權利的約束,但如果缺乏制度和法律對權利的保障,一旦出現漏洞或真空,本性偏好膨脹的權力就會在這一漏洞或真空地帶恣意妄為,其結果就是權利被權力剝奪并被迫服從于權力。這種因制度性缺權或無權而造成的居民在主流權力結構中被邊緣化的問題必須通過制度性增權才能解決。制度增權是指國家通過立法或完善現有的政策制度對具有較強權力的政府或開發商等旅游開發機構的權力進行嚴格的規制、約束、控制和監督,同時建立起保障弱勢社區居民參與旅游發展決策、掌控旅游資源、分享旅游收益的權力框架和制度框架。通過正式的制度不僅可以有效遏制政府或開發商因單獨享有旅游控制權而使權力過渡膨脹而進行尋租和設租,而且可以有效防止因公權力對私權利的侵犯而使私權利在法律上成為“真空地帶”,造成權利人利益受損的問題。制度增權的主體必須而且只能是國家,因為只有國家才有能力供給和保障這樣的制度環境。制度增權的實質就是通過國家建立起一套正式的支持性的制度,將強勢的政府或開發商的權利與弱勢的社區居民權利進行重新分配,使社區居民享有與政府或開發商同等強度的權利,避免社區居民因權利缺失而使其利益被外部力量侵犯和剝奪,真正使各利益主體的權利均得以實現,利益均得以保證,實現旅游發展的制度化。
3.建立村民集體法人制度
盡管我國法律明確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均不能以任何借口或手段侵占或破壞農民集體財產,但由于農民集體是一個不具有真正法人資格的虛置主體,不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和民事權利能力,致使集體土地所有權事實上變成了地方政府或集體代理人以及社區精英分子的權利。農民個體基于集體的成員權無法保障農民對集體土地相應的所有權和收益權。因此,必須構建村民集體法人制度,明確規定在將村寨里的集體土地資源納入旅游開發與發展規劃時必須征求全體村民的意見,并將具體內容完全公開,在保障農民集體擁有土地所有權和收益權的基礎上,由全體村民通過投票表決的方式做出集體決定。這樣不但可以有效避免集體代理人或社區精英為追求個人私利而低價租賃或低價轉讓集體土地,而且還可以使農村集體法人化,使其獲得相對公平的收益。
4.用有效的產權制度約束既定的產權關系
這需要國家設計有效的產權制度,明確產權主體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以及產權行使和保護的規則,并對違反產權安排的行為進行懲罰和處理。旅游資源產權的內生困境以及公共資源屬性導致的公地悲劇問題的實質是,因產權沒能起到激勵作用,旅游資源屬于民族村寨社區整體共同擁有,村寨居民既是旅游資源利用主體,同時又是民族傳統文化的“活態”載體,但村寨居民卻未因此而在旅游開發中獲得多少經濟補償或分享到多少經濟收益,旅游創造的巨大價值被政府或開發商所攫取,卻要由居民來承擔旅游開發與發展所造成的所有消極影響,尤其是在政府或政府官員為實現GDP或政績而主動開發以及旅游開發商謀取短期回報的情況下,就不可避免地出現政府或開發商與民爭利,侵犯社區居民權益的行為發生。因此,必須通過建立有效的產權制度,明確政府、開發商和居民的權利與責任。對于任何增進一方利益而使其他利益主體受到損失的行為,都要將相應的成本分攤到從該行為獲益的利益主體身上,通過這樣的約束有效發揮產權的激勵作用并避免外部不經濟行為的發生。
5.健全維穩體制
一方面,要嚴格落實行政執法責任制度。對因漠視、拖延、推諉、不管、不問、不依照法定程序認真答復和解決村民反映的帶有普遍性、突出性的利益訴求問題以及因政府執法工作人員工作失誤、故意刁難而促使矛盾激化的,要堅決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并嚴肅處理。對村寨居民反映的一時解決不了的問題,行政執法人員要耐心細致地做好解釋、說明和疏導工作,防止矛盾的進一步激化。另一方面,要加強司法救濟,引導民間維權。目前高昂的訴訟費用和繁瑣的訴訟程序影響了居民的合法維權,因此要加大對村民等弱勢群體的法律援助和財政保障力度,從而有效彌補因其法律意識淡薄、文化素質低下、訴訟資金缺乏而不能有效利用法律手段和程序合法維權的問題。
總之,我們不但應主動正視民族村寨社區旅游發展中所存在的矛盾和沖突,而且還要理性地對造成矛盾沖突的機理進行深入分析,才能提出具有針對性的合理對策,從而有效解決、治理和防范民族村寨社區旅游中可能出現的各種問題,使民族村寨社區旅游的發展真正造福于當地居民,為維護民族地區的和諧穩定與繁榮做出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