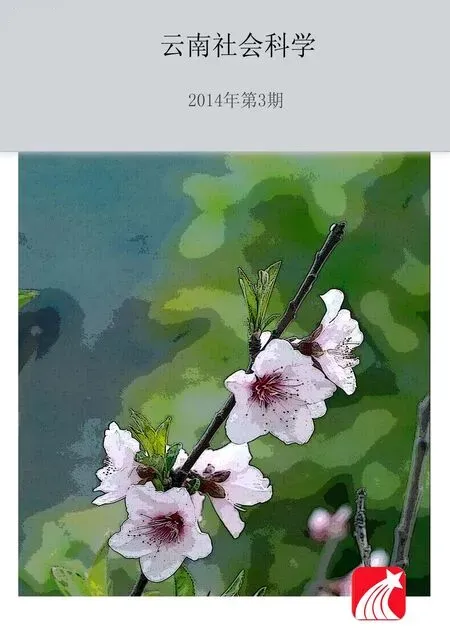秦漢時期南土卑濕環境惡劣觀念考述
李榮華
秦漢時期,隨著全國統一,在南北交往過程中,中原社會形成南方卑濕環境惡劣的觀念。于賡哲先生把“卑濕”視為一種文化符號,從中古時期族群邊界變動的角度對其演變過程進行了研究[1]。本文在此基礎上,試圖從環境—經濟—社會三者的互動探討這一觀念的形成原因,并以此求教于方家。
一、中原社會對黃河中下游部分卑濕之地的認識
根據現代科學研究,黃河中下游地區屬于暖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四季分明,夏季炎熱,冬季寒冷,年平均氣溫8~14℃,一月份氣溫0~-10℃,氣溫日較差、年較差很大,降水分布極不平衡,冬春干旱,夏季多雨。歷史地理學者在研究秦漢時期的氣候時指出,黃河中下游地區的氣候與現今雖然有一些差異,但是并不顯著[2](P70)。當今科學研究成果有助于我們了解歷史時期氣候的演變情況,不過,古人也有他們自己對周圍環境的切身感受。《黃帝內經素問·五常政大論》中載:“西北方,陰也,陰者其精奉于上,故左寒而右涼。”黃河中下游地區天氣以溫涼為主。
在對地貌的認識上,這一時期的人們認為北方土層深厚。《論衡·儒增篇》中說“河北地高,壤靡不干燥”。秦漢以后的人們也持相同的看法。郭義恭《廣志》中說“北方地厚”[3](卷3,P60)。葛洪《抱樸子·登涉》記載“中州高原,土氣清和”。顏之推《顏氏家訓·音辭》則說“北方山川深厚”。北方即黃河中下游地區,包括黃土高原和華北平原。其中,屬于第二地形階梯的黃土高原海拔1500~2000米,地勢較高,覆蓋著深厚的黃土。屬于第三級地形階梯的華北平原,由黃河、海河等河流所攜帶泥沙堆積而成,由于這兩條河流含沙量非常大,使得這一地區土層深厚。
雖然黃河中下游地區從總體上來說土層深厚,但是,這一地區也有地勢卑下的地方。先秦時期,人們就認為這些地方不適宜居住。《左傳》成公六年記載,晉景公打算遷都,征求大臣的意見。諸大夫們認為郇、瑕氏一帶可以居住,“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但是韓獻子以為不可,他說:“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于是乎有沉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郇、瑕氏即今天山西解池一帶,地勢卑下,環境惡劣,疾病流行。相反,新田(今山西侯馬)一帶地勢較高,環境干燥,而且,河水能夠帶走各種污穢雜物,疾病較少,有利于人的身體健康。即使郇、瑕氏一帶資源豐富,可以為國家提供更多的財政支持,但是它不是最佳的居住環境。最終,晉景公同意并采納了韓獻子的意見,遷都新田。《晏子春秋·內篇雜下》中記載:“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在齊景公看來,晏子居住的地方不僅吵鬧,而且低洼狹小、濕氣較重,因此,必須選擇較為高爽的地方居住,只有這樣才有利于晏子的身體健康。
到了秦漢時期,人們依然認為黃河中下游部分地區環境卑濕,不適宜居住。《漢書》卷28上《地理志》中記載秦代襄邑(今河南睢縣)立城的原因,“襄邑宋地,本承匡襄陵鄉也。……秦始皇以承匡卑濕,故徙縣于襄陵,謂之襄邑”。《史記》卷58《梁孝王世家》中《正義》引《括地志》中記載漢文帝封其子于睢陽(今河南商丘)的原因:“漢文帝封子武于大梁,以其卑濕,徙睢陽,故改曰梁也。”賈讓在《治水三策》中指出,冀州應該多修漕渠,“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其中,三害之一就是“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4](卷29,P1695)。水流不暢,致使土地潮濕,人們容易生病。《漢書》卷79《馮立傳》中記載,馮立被遷為東海(今山東郯城)太守后,“下濕病痹”。唐人顏師古在注中指出:“東海土地下濕,故立病痹也。”馮立患痹病的原因在于東海潮濕的環境。《后漢書》卷55《千乘貞王伉傳》中記載劉鴻之子劉纘繼承皇位后,“梁太后下詔,以樂安國土卑濕,租委鮮薄,改鴻渤海王”[5](卷55,P1797)。樂安在今天山東高青縣西北一帶,劉鴻之所以被改封,原因之一恐怕是該地環境卑濕。
潮濕的環境不利于人的身體健康,有可能讓人患上痹病。《黃帝內經素問·痹病論》中記載:“黃帝問曰:痹之安生?岐伯對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痹也。其風氣盛者為行痹,寒氣盛者為痛痹,濕氣盛者為著痹也。”風、寒、濕是痹病形成的三要素,不過,誘發因素不同,痹病的種類也就有所不同,“三氣雜合為以一氣勝者為主病”[6](卷5,P309)。以濕氣為形成原因的為著痹,又稱濕痹,它是由人體正氣不足,感受濕邪,或夾風、夾寒、夾熱,侵襲肌膚、筋骨、關節所導致的,癥狀為肢體關節酸痛、重著、腫脹、屈伸不利等[7](P228)。《黃帝內經素問·異法方宜論》說:“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陽之所盛處也,其地下,水土弱,霧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胕。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攣痹。”居住在南方卑濕環境下的人們更容易患濕痹。總之,在秦漢時期人們的觀念中,黃河中下游地區土層深厚。但是,這一地區也有卑濕之地,它們不適合居住,如果長期生活在此環境中,易患濕痹。
二、中原社會對南方卑濕環境的認識
相對于黃河中下游地區,長江中下游地區屬于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年平均氣溫14~20℃,一月平均氣溫0~8℃,年降雨量在800~1600mm之間。華南屬于熱帶南亞熱帶季風氣候,年平均氣溫20℃以上,一月平均氣溫10℃以上,年降雨量大于1600mm。根據今人的研究,秦漢時期長江中下游地區以暖濕為主,氣溫略高于今,或與現今差別不大[8];華南地區氣候較為溫暖[9]。在時人的認識中,也能看出南方濕熱的環境。《黃帝內經素問·五常政大論》中說,“東南方,陽也,陽者其精降于下,故右熱而左溫。”《淮南子·地形訓》中說:“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論衡·言毒》中記載楚越為“太陽之地”。
與北方相比,南方土地卑下。《史記》卷129《貨殖列傳》以及《漢書》卷28下《地理志》均提及“江南卑濕”。《論衡·言毒》中也記載,“江南地濕”。長江中下游地區及以南地區位于巫山、雪峰山以東,屬于第三級地形階梯,以平原、丘陵、低山為主。先秦秦漢時期,這一地區平原地帶以湖泊沼澤濕地為主。《禹貢》中記載揚州和荊州“厥土惟涂泥”,涂泥主要為湖沼相沉積物[10]。其中,江漢平原云夢澤呈現平原—湖沼形態的地貌景觀,洞庭湖和鄱陽湖地區以河網切割的地貌為主,長江下游一帶湖泊眾多,濕地廣布[11]。嶺南北部以山地丘陵為主,南部一帶為海洋,珠江三角洲平原此時沒有形成,處于水下發育階段,海岸線位于黃埔、廣州、佛山、九江一帶[12]。從總體看,南方水資源豐富,土地卑濕。
在中原社會傳統觀念中,卑濕之地是不適宜居住的。當他們面對著卑濕的南方時,認為此地更加不適宜居住。當賈誼被貶長沙時,“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濕,自以為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13](卷85,P2492)。在賈誼看來,長沙卑濕,居住在此生命恐怕不能長久。當袁盎被徙為吳相時,袁種告訴他“南方卑濕”,不過,他認為袁盎“能日飲,毋何”[13](卷101,P2741)。吳國的封域有三郡五十三城,三郡為東陽、鄣以及吳。其中,東陽位于江淮之間,鄣、吳位于江南[14](P34~37)。袁種強調南方卑濕,言外之意該地環境惡劣,不適宜居住。七國之亂被平叛后,衡山王劉勃未參加叛亂,漢景帝“以為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濕。’徙衡山王王濟北,所以褒之”[13](P3081)。衡山國位于江淮之間,東界當在《漢志》酉陽、潛縣、居巢一線以東,西界當在下雉、邾縣一線以西[14](P47~48)。漢景帝獎賞衡山王劉勃的辦法是把他從卑濕之地遷出,說明南方卑濕環境惡劣的觀念深入人心。東漢時期,考侯劉仁要求減邑內徙,原因在于舂陵(今湖南寧遠)環境潮濕,“仁以舂陵地埶下濕,山林毒氣,上書求減邑內徙”[5](卷114,P560)。馬援之子馬防因犯法被徙丹陽(今安徽宣城),他認為“江南下濕”,上書和帝乞歸,“和帝聽之”[5](卷24,P858)。章和元年(公元87),漢章帝認為阜陵(今安徽全椒)土地下濕,將阜陵國的都城遷到壽春,“以阜陵下濕,徙都壽春”[5](卷42,P1445)。阜陵位于歷陽縣(今安徽和縣)以西,壽春(今安徽壽春)位于九江郡西北,淮水之濱,二地相距較遠[15](P221)。相對于阜陵,壽春的環境比較干爽,這恐怕是漢章帝遷徙阜陵國都城的原因。
更有甚者,中原社會認為居住在南方卑濕環境下的人們容易夭折。《黃帝內經素問·五常政大論》中記載:“帝曰: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右熱而左溫,其故何也?岐伯曰:陰陽之氣,高下之理,太少之異也。東南方,陽也,陽者其精降于下,故右熱而左溫。西北方,陰也,陰者其精奉于上,故左寒而右涼。是以地有高下,氣有溫涼,高者氣寒,下者氣熱,故適寒涼者脹,之溫熱者瘡,下之則脹已,汗之則瘡已,此腠理開閉之常,太少之異耳。帝曰:其于壽夭何如?岐伯曰:陰精所奉其人壽,陽精所降其人夭。”東南方氣候炎熱,人們壽命比較短暫。唐人王冰認為,“陽方之地,陽氣耗散,發泄無度,風濕數中,真氣傾竭,故夭折。即事驗之,今中原之境,西北方眾人壽,東南方眾人夭,其中猶各有微甚爾,此壽夭之大異也,方者審之乎!”[16](卷20,P128)清人張志聰也指出:“陰精所奉之處,則元氣固藏,故人多壽。陽精所降之方,則元陽外泄,故人多夭。”[6](卷8上,P523)由于氣候的原因,南方之人陽氣不能固守于身體中,容易耗散,致使其壽命遠不如北方之人。《淮南子·地形訓》中說,“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人修形兌上,大口決眥,竅通于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史記》卷129《貨殖列傳》中記載:“江南卑濕,丈夫早夭。”班固《漢書》卷28下《地理志》中亦載:“江南卑濕,丈夫多夭。”雖然此種觀念受五行思想的影響,但它是建立在中原人士對南方生態環境認識的基礎之上的[1]。
三、南方社會發展水平與中原社會的地域歧視
眾所周知,秦漢時期,黃河中下游地區是整個國家的基本經濟區,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包括涇水、渭水和汾水流域,以及黃河的河南—河北部分在內的這一整個地區,卻構成了一個基本經濟區,這一基本經濟區,是從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整個兩漢時期的主要供應基地和政權所在地”[17](P78)。廣大南方地區經濟比較落后,《史記》卷129《貨殖列傳》中載:“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贏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蓏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
南方經濟落后,一方面,使得這一地區生態環境保持原始面貌,沼澤濕地廣布。這在前面已經談到。另一方面,使得這一地區醫療衛生條件較差。建立在一定社會生產方式基礎上的經濟發展程度,直接決定了人們的社會保障和物質醫療保障,奠定了人們是否健康長壽的客觀物質基礎。也就是說,經濟發展水平越高,人們的平均壽命較高;經濟發展水平越低,人們的平均壽命較低[18]。南方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了當地居民的醫療水平和平均壽命。而且,這一地區濕熱的環境,有利于病原體的孳生、繁殖,人們以水為中心的生產生活方式,為各種病原體的入侵提供了大量的機會,致使他們易感染各種疾病[19](P231)。
既然南方醫療衛生條件較差,人們又易感染各種疾病,那么,他們如何應對疾病呢?秦漢時期,南方十分盛行“信巫鬼、重淫祀”的社會風俗。《漢書》卷28下《地理志》中記載,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史記》卷28《封禪書》中說:“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后漢書》卷41《第五倫傳》中記載,會稽(今浙江紹興)一帶“俗多淫祀”。當地人通過祭拜鬼神應對疾病,解除病痛。王符在《潛夫論》卷3《浮侈》中指出:“今多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或棄醫藥,更往事神,故至于死亡不自知為巫所欺誤,乃反恨事巫之晚,此熒惑細民之甚者也。”棄醫藥,事鬼神,只能延誤疾病治療的最佳時機,提高疾病的死亡率。
從客觀事實的角度,南方地區經濟落后、環境濕熱、疫病流行,直接影響到當地居民的醫療衛生水平和平均壽命,必然會對南下的中原人士產生種種不良的影響。但是,中原社會強調南方環境的卑濕,目的在于顯示南北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突出北方社會的區位優勢,展現出對南方社會的地域歧視。所謂地域歧視,是以一定的文化中心為本位,對其他地區進行形象扭曲和地域文化貶低,包括地理感知的不良評價與對地域人群(或族群)的貶低,其原因在于地區間地理環境、經濟文化的差異[20](P400)。可見,南北環境的差異、南方經濟的落后,是中原社會歧視南方地區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原人士不愿前往南方的主要原因。而秦漢帝國在經營南方過程的種種遭遇,更加深了中原社會對南方卑濕環境的印象。
秦漢帝國為了統一南方,不得不派大量士兵南下。由于南方生態環境完全不同于中原地區,南下的士兵短時期內難以適應這種環境,他們中的大部分命喪黃泉。呂后時期,西漢政府禁止向南越供應鐵器。趙佗獨立,并侵犯長沙,為此呂后派兵南下,“會暑濕,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13](卷113,P2969)。士兵還沒有到達嶺南,已經傷亡過半。在《漢書》卷49《晁錯傳》中,有晁錯指出秦朝時期前往南方的戍卒不能適應當地水土大量死亡的事實。“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邊,輸者僨于道”。漢武帝時期,閩越攻打南越,南越向西漢政府求助,淮南王劉安認為南下的軍隊不能適應當地的環境,“南方暑濕,近夏癉熱,暴漏水居,蝮蛇蠚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4](卷64上,P2781)。由于湖南江西一帶與嶺南的交通險阻,極其艱難,“南粵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余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漢武帝著力經營西南地區,想通過這一地區,出其不意,占領嶺南。不過,在經營西南地區的過程中,軍隊同樣遭遇重創,“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餉。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暑濕死者甚眾”[13](卷116,P2995)。東漢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武陵蠻反叛,光武帝劉秀派馬援前去鎮壓,結果“馬援卒于師,軍士多溫濕疾病,死者太半”[5](卷41,P1412)。總之,秦漢政府在經營南方的過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也使得中原社會對南方卑濕的環境記憶猶深。
總之,秦漢時期,中原社會形成南土卑濕環境惡劣的觀念。這一觀念的形成,與南北環境、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差異密不可分。相對于中原地區,南方地區經濟落后,醫療衛生條件較差,環境濕熱,沼澤濕地廣布,疫病流行。中原社會受卑濕之地不適宜居住傳統觀念的影響,在認識南方生態環境的過程中,過分強調南方環境的卑濕問題,并將其無限夸大,目的在于顯示南北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突出北方社會的區位優勢,展現出對南方社會的地域歧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