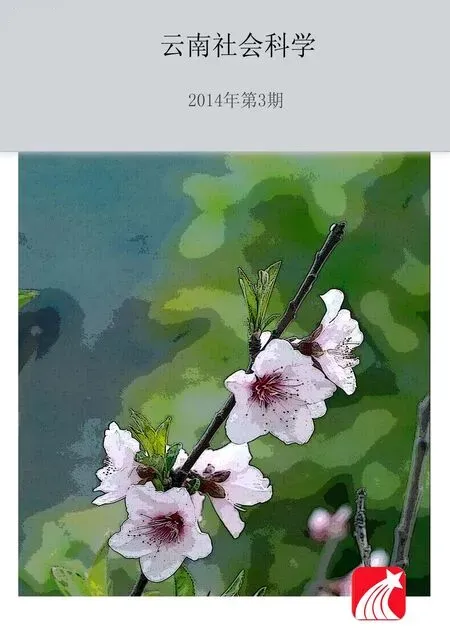論西部邊地文化小說(shuō)敘事的現(xiàn)代性焦慮
金春平
現(xiàn)代性一詞自產(chǎn)生之日起,就是一個(gè)鬼魅四射而撲朔迷離的概念,它不僅是20世紀(jì)中國(guó)文學(xué)發(fā)展的價(jià)值訴求,也是中國(guó)社會(huì)轉(zhuǎn)型的歷史準(zhǔn)則。按照福柯的說(shuō)法,現(xiàn)代性是一種文化理念和思維方式,是“一種態(tài)度”,“一種由特定人民所作的自愿的選擇”。[1](P430)正因?yàn)楝F(xiàn)代性是一種集體認(rèn)知態(tài)度,決定了無(wú)論是不同民族、不同國(guó)家還是不同個(gè)體,都可以對(duì)現(xiàn)代性做出自己的理解和實(shí)踐。但總體而言,“現(xiàn)代性作為一種推動(dòng)現(xiàn)代化的精神力量,具有三個(gè)層面,即感性層面、理性層面和反思超越層面”,“現(xiàn)代性不是其中某一個(gè)層面,而是三個(gè)層面的整體結(jié)構(gòu)。”[2](P1)與此類似,馬泰·卡林內(nèi)斯庫(kù)則將現(xiàn)代性分為社會(huì)現(xiàn)代性和審美現(xiàn)代性,并對(duì)二者進(jìn)行了區(qū)分:“一方面是社會(huì)領(lǐng)域的現(xiàn)代性,源于工業(yè)與科學(xué)革命,以及資本主義在歐洲的勝利;另一方面是本質(zhì)屬于論戰(zhàn)式的美學(xué)現(xiàn)代性,它的起源可追溯到波德萊爾。”[3](P254)而中國(guó)西部“邊地”,是一個(gè)相對(duì)于“中心”的命名,它包含著地理、經(jīng)濟(jì)、政治、文化的邊緣性。從地理上考察,西部邊地的自然地理與氣候條件相對(duì)惡劣,在其影響下的西部邊地民眾也孕育出獨(dú)特的生存方式和生命觀念。從經(jīng)濟(jì)角度考察,西部邊地又是與“東部繁華中心”相對(duì)而言的經(jīng)濟(jì)欠發(fā)達(dá)地區(qū),而且由于物質(zhì)生活的匱乏,民眾的精神狀態(tài)和民族性格也呈現(xiàn)出了封閉卻堅(jiān)韌的特點(diǎn)。從文化的角度考察,西部邊地是與漢民族中原文化而言的異質(zhì)性和邊緣性文化體系[4]。在縱向性的自成體系和橫向性的文化互補(bǔ)當(dāng)中,西部“邊地文化”就成為一個(gè)形態(tài)不斷演進(jìn)、內(nèi)涵不斷充實(shí)的帶有歷史性和時(shí)間性的概念。對(duì)于身處多重文化空間的西部作家而言,他們既可能表現(xiàn)出對(duì)物質(zhì)現(xiàn)代性(都市文明)的向往,將感性解放作為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旨?xì)w;也可能表現(xiàn)出對(duì)鄉(xiāng)土封閉形態(tài)的啟蒙批判,將文化改造作為西部轉(zhuǎn)型的理想;還可能表現(xiàn)出對(duì)現(xiàn)代文明諸多弊端的反思與批判,將理念層面的互相制衡作為理想王國(guó),即現(xiàn)代性本身的多維向度,最終導(dǎo)致了西部作家在現(xiàn)代性問(wèn)題上的分化,以及多元敘事形態(tài),從而在思想發(fā)展上形成了“前現(xiàn)代”、“現(xiàn)代”和“后現(xiàn)代”之間的繼承又沖突的共存局面[5]。多元文明的并存,使敘事主體能置身于不同的文明形態(tài)視閾,對(duì)最具話語(yǔ)霸權(quán)的現(xiàn)代性理念和實(shí)踐效果進(jìn)行多元角度的觀照和反思,但差異化的理解,也使西部小說(shuō)的敘事主體認(rèn)知呈現(xiàn)出普遍的“現(xiàn)代性焦慮”,在折射出中國(guó)作家主體性建設(shè)困境的同時(shí),也讓“文學(xué)何為”這一基本命題得以深化和反思。
一、個(gè)體與群體:“人文主義”與“革命主義”
現(xiàn)代性的基本內(nèi)涵,毫無(wú)疑問(wèn)包含了“民主”與“科學(xué)”兩大主題。而對(duì)“民主”的理解,要么滑向?qū)Α皞€(gè)體”價(jià)值的強(qiáng)調(diào),其潛在的參照價(jià)值體系是“非現(xiàn)代性”的封建“專制”體系;但也可能滑向在民族公意的基礎(chǔ)上,建立民族共同體,其潛在的參照價(jià)值體系則是中國(guó)封建社會(huì)的“家姓天下”。因此,以民主為核心基點(diǎn),強(qiáng)調(diào)個(gè)體價(jià)值的“人文主義”與強(qiáng)調(diào)民族價(jià)值的“革命主義”之間就必然產(chǎn)生內(nèi)在裂隙,并常表現(xiàn)為“個(gè)體自由”與“政治統(tǒng)攝”之間的內(nèi)在矛盾。“文化大革命”結(jié)束之后的西部作家構(gòu)成,主要是外來(lái)的“右派”流寓知識(shí)分子,這些作家集體性地對(duì)“文化大革命”這場(chǎng)政治苦難進(jìn)行咀嚼與回味。反觀歷史政治、反省人生歷程、質(zhì)疑政治災(zāi)難等是他們這一時(shí)期創(chuàng)作的主要內(nèi)容。而在一系列的歷史記憶與政治回顧中,最重要的莫過(guò)于受難者對(duì)自身曾經(jīng)的歷史身份與階級(jí)身份的認(rèn)定,甚至可以說(shuō),回歸歷史情境與政治記憶的首要任務(wù)就是確認(rèn)自身的群體歸屬。雖然政治身份的認(rèn)同焦慮不僅僅是西部作家的獨(dú)有困惑,但當(dāng)中所貫穿的強(qiáng)烈的對(duì)階級(jí)性生存和政治性歸屬的基本訴求,卻由于身處“西部邊地”這樣一個(gè)有著政治重負(fù)與歷史因襲的文化環(huán)境而顯得相當(dāng)?shù)湫汀?/p>
政治體驗(yàn)的生存焦慮表現(xiàn)在小說(shuō)中,就是當(dāng)那些“歸來(lái)者”以回憶的方式反思那段歷史噩夢(mèng)時(shí),對(duì)自己在受難期間的身份歸屬進(jìn)行的自我辯駁與體驗(yàn)思考,其典型體現(xiàn)就是“人文主義與革命主義”、“個(gè)體自由與政治統(tǒng)攝”之間的身份困惑。人文主義在文本中化身為知識(shí)分子精英,革命主義在文本中化身為西部底層民眾,二者之間是“民間愚昧與知識(shí)文化”的教育與反教育,是“政治馴化和思想個(gè)體獨(dú)立”的置換與反置換。這種共存于同一個(gè)體的精英與大眾之間的身份焦慮,不僅包含著“右派”知識(shí)分子歸來(lái)之后對(duì)“文革”造成人的身份失落的歷史荒謬的批判,也包含著在特定歷史時(shí)期政治信仰不斷侵入人的原有思想獨(dú)立體系時(shí),人的無(wú)意識(shí)反抗的精神生存困境。而通過(guò)這樣的身份焦慮的曲折表達(dá),西部作家不僅實(shí)現(xiàn)了對(duì)歷史的反思,而且傳達(dá)了對(duì)完美人性的堅(jiān)守。這種身份焦慮的表達(dá),其“機(jī)智”之處在于:它在“右派”改造的文化認(rèn)同、政治認(rèn)同和信仰認(rèn)同的服膺之下,在貌似迎合意識(shí)形態(tài)和“左翼”話語(yǔ)的表象下,利用自身的人格分裂困惑和身份焦慮表達(dá),策略而潛隱的將批判的鋒芒指向了那段荒謬歷史的制造者。而身份焦慮突破過(guò)程中的精神洗禮、思想改造、人性辯駁,都是傳達(dá)歷史荒誕給人帶來(lái)的精神劇痛的隱晦表征。其中對(duì)個(gè)體自由的束縛與向“低級(jí)”文化的被迫學(xué)習(xí)的心靈傷害,都是這種身份焦慮表達(dá)的最終指向,這在張賢亮、王蒙、董立勃等作家的文學(xué)世界尤為明顯。在他們的作品中,政治身份的焦慮主要體現(xiàn)為啟蒙者與大眾化、個(gè)體性與一統(tǒng)化、批判性與合法化之間難以逾越的鴻溝。啟蒙者的基本原則是對(duì)現(xiàn)存社會(huì)的否定性,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背叛與超越,“按其先進(jìn)的主張,它是大拒絕——對(duì)現(xiàn)狀的抗議”。[6](P54)但是中國(guó)社會(huì)對(duì)啟蒙現(xiàn)代性的追求,由于過(guò)于急切的現(xiàn)實(shí)功利性,放棄了對(duì)哲學(xué)、宗教和藝術(shù)形而上層面的關(guān)注,卻將希望寄托于政治權(quán)力和意識(shí)形態(tài),認(rèn)為唯有它們才能實(shí)現(xiàn)民族的復(fù)興。那么在這種感召之下,作家和文學(xué)也理所應(yīng)當(dāng)?shù)某蔀榱藝?guó)家意識(shí)形態(tài)的維護(hù)工具。這樣,啟蒙者的個(gè)體性就要讓位于政治意識(shí)的群體性,啟蒙者的批判性就要讓位于政治體制的合法性。于是,政治意識(shí)形態(tài)的整合性與個(gè)性啟蒙身份的獨(dú)立性就試圖尋求一種新的整合,“在通常的情況下,只要一訴諸言談,作為‘小我’的他就悄然隱去,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的則是‘大我’——意識(shí)形態(tài)”。[7](P345)西部小說(shuō)就在這種艱難的文本整合中呈現(xiàn)出了明顯的裂隙,以國(guó)家化的合法外衣隱藏了個(gè)體化的批判質(zhì)疑。
張賢亮小說(shuō)的敘事立場(chǎng),在政治合法化的外衣下面,隱藏的卻是知識(shí)分子的優(yōu)越感與對(duì)這場(chǎng)改造運(yùn)動(dòng)的“質(zhì)疑”。體現(xiàn)在作品中就是知識(shí)階層與底層大眾之間的錯(cuò)位,由此造成的是西部底層大眾的“貶抑化”和知識(shí)分子受難者的“神圣化”。在《綠化樹(shù)》當(dāng)中,作為“右派”分子的章永璘,本應(yīng)是一個(gè)政治意義上的需要被教育者,但在“崇尚文化”意識(shí)的馬纓花看來(lái),他卻是一個(gè)擁有文化知識(shí)的精神優(yōu)越者,“你是個(gè)念書(shū)人,就得念書(shū)。只要你念書(shū),哪怕我苦得頭上長(zhǎng)草也心甘”。政治優(yōu)越者身份的馬纓花與政治遺落者身份的章永璘,通過(guò)知識(shí)這一中介,完成了“愚昧”的“大眾”與“文化”的“圣人”之間不平等地位的置換。同樣,《土牢情話》中的喬安萍與石在之間源于知識(shí)魅力的愛(ài)情,《河的子孫》當(dāng)中的韓玉梅因文明之物——手表而許身于科長(zhǎng)等等,都表明了張賢亮在政治改造的合法性外衣下,隱藏的卻是知識(shí)分子身份優(yōu)越于底層大眾的自信。而作品中所謂的正面人物,特別是女性人物雖然由于西部地域的封閉和傳統(tǒng)道德的束縛而呈現(xiàn)出善良淳樸等優(yōu)秀品質(zhì),卻因?yàn)樵谖幕瘜用娴拿つ慷鵁o(wú)法與知識(shí)精英達(dá)成精神交流,“政治的導(dǎo)師”最終淪為了知識(shí)精英落難的“異化”對(duì)象。
董立勃的《白豆》在政治合法化的外衣下,隱藏著對(duì)政治“合法”性的質(zhì)疑,體現(xiàn)出“幾乎所有的政治,都要把自己的欲望、利益和理想普泛為大眾所共有的,而且是永恒的。……它們的這種‘打扮’帶有明顯的‘遮蔽性’,即政治愚弄和欺騙”的深刻批判性,[8]在小說(shuō)中主要體現(xiàn)為政治理性對(duì)自然人性的扼殺。當(dāng)女主人公白豆被迫與人結(jié)婚時(shí),“戀愛(ài)自由與婚姻自主”可以成為組織營(yíng)救她的理由;而當(dāng)馬營(yíng)長(zhǎng)看上了已訂婚的白豆時(shí),卻對(duì)吳大姐說(shuō):“戀愛(ài)自由,婚姻自由,這個(gè)道理,你這個(gè)婦女干部不會(huì)不懂吧。吳大姐說(shuō),這我懂,我懂了。馬營(yíng)長(zhǎng)說(shuō),懂了就好。”[9](P52)作品中老楊因他人威脅而不得不放棄白豆時(shí),“共產(chǎn)黨員”這一屬于政治正面色彩的身份,卻可以成為掩蓋自身無(wú)奈失敗境地的擋箭牌:“我盡管很喜歡白豆,可我是一個(gè)共產(chǎn)黨員,我應(yīng)該做到毫不利己專門利人……”[9](P32)。相反,當(dāng)馬營(yíng)長(zhǎng)試圖強(qiáng)奸白豆時(shí),他同樣用這個(gè)正面身份作為掩蓋非人性的理由:“干部工作很緊張,有時(shí)候見(jiàn)到女同志,也會(huì)開(kāi)開(kāi)玩笑。”[9](P157)此外,作品中的楊來(lái)順就具有“革命者”與“小農(nóng)”雙重身份。他雖經(jīng)歷了革命思想的洗禮,但卻難以擺脫小農(nóng)意識(shí)的束縛,他沒(méi)有因?yàn)檎蔚耐⑵鹨粋€(gè)革命者應(yīng)有的思想觀念和革命素質(zhì),卻在世俗斗爭(zhēng)中失去了農(nóng)民本應(yīng)具備的諸多優(yōu)秀品質(zhì),最終成為一個(gè)無(wú)賴式的怪胎,這是一個(gè)典型的政治同化與小農(nóng)個(gè)性無(wú)法彌合的異化人物。
因此,對(duì)于歷經(jīng)政治煉獄的西部作家而言,政治意識(shí)形態(tài)以它的強(qiáng)制性和神圣性為現(xiàn)實(shí)抹上了一層溫情的外衣,成為作家在特定歷史時(shí)期意識(shí)形態(tài)領(lǐng)域無(wú)可辯駁的強(qiáng)大話語(yǔ)權(quán)威,一切行為與事件在“政治”與“人民”的宣言下變得合理而合法;但作為個(gè)體的知識(shí)分子卻由于啟蒙思想與批判思想而不斷的質(zhì)疑著政治行為的合理性,不斷揭示著諸多虛假表象下的不真實(shí)領(lǐng)域,于是國(guó)家意識(shí)形態(tài)的統(tǒng)攝對(duì)個(gè)性言說(shuō)自由的束縛,以及個(gè)體自由對(duì)國(guó)家意識(shí)形態(tài)的反抗,最終造就的不僅是“無(wú)形的話語(yǔ)權(quán)力壟斷產(chǎn)生的隱性統(tǒng)治權(quán)才是今天政治權(quán)力施展的主要手段,……話語(yǔ)權(quán)力的壟斷已經(jīng)成為政治權(quán)力特別是一元政治權(quán)力體制不可或缺的前提”,[10](P280)還有西部作家在小說(shuō)中所表現(xiàn)出的特殊政治環(huán)境下知識(shí)分子個(gè)體化的政治現(xiàn)代性焦慮。
二、理性與感性:“啟蒙批判”與“世俗狂歡”
現(xiàn)代性的內(nèi)涵,包含了“感性的解放”與“理性的制約”。但由于中國(guó)的現(xiàn)代性帶有“外迫性”,而非出于中國(guó)社會(huì)發(fā)展的“內(nèi)源性”,即西方現(xiàn)代性的入侵,才將中國(guó)的現(xiàn)代化進(jìn)程推向歷史軌跡。因此,現(xiàn)代性在中國(guó)本土呈現(xiàn)出了較為矛盾的狀態(tài):一方面,出于物質(zhì)現(xiàn)代性的全民訴求,改革開(kāi)放以來(lái),發(fā)展經(jīng)濟(jì)成為國(guó)家和社會(huì)發(fā)展的唯一價(jià)值,物質(zhì)感官的解放,終于從政治為綱的桎梏中解放出來(lái),物質(zhì)感官享受獲得了國(guó)家甚至是法律層面的合法保障;但另一方面,中國(guó)文學(xué)的價(jià)值資源普遍來(lái)自于傳統(tǒng)的道德倫理,包括儒家的“重義輕利”的價(jià)值體系,因此,對(duì)于物欲泛濫甚至是物役的束縛,中國(guó)作家普遍采取了以道德倫理為核心的中國(guó)式“啟蒙理性”批判的立場(chǎng)。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lái),西部中青年小說(shuō)家所面對(duì)的是一個(gè)全新的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和消費(fèi)主義的社會(huì)語(yǔ)境,最能引起他們關(guān)注的,則是在此背景下西部城鄉(xiāng)世界不斷演繹的諸多人生的悲歡離合。西部鄉(xiāng)土世界的沉滯與動(dòng)蕩,西部人在社會(huì)轉(zhuǎn)型當(dāng)中心靈的安守、人性的制衡和物欲的誘惑等等現(xiàn)實(shí)情境,都使西部作家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介入的姿態(tài)進(jìn)行著審視與思考。雖然他們?cè)诓粩嗟奶剿骱统C正,但不得不遺憾地說(shuō),西部小說(shuō)作家直到新世紀(jì),其創(chuàng)作的整體價(jià)值立場(chǎng)依然是模糊的,甚至在個(gè)體作家筆下,價(jià)值立場(chǎng)表現(xiàn)出前后矛盾和背離(如石舒清、陳繼明等)。現(xiàn)代性焦慮在中國(guó)當(dāng)下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非西部作家所獨(dú)有,但能夠像西部小說(shuō)這樣,將不同的文化體系,諸如農(nóng)業(yè)文明、都市文明和后現(xiàn)代文化等不同文化因子,將現(xiàn)代性的感性、理性和反思—超越等不同層面同時(shí)吸納并被不同的作家所演繹,這在中國(guó)當(dāng)下文壇格局中是鮮有的,而這種文化的多元與焦慮在西部中青年作家中,具體表現(xiàn)為“啟蒙批判”與“世俗狂歡”之間的焦慮緩釋和抉擇。
世紀(jì)之交以來(lái),封閉已久的西部邊地同整個(gè)中國(guó)大地一樣,經(jīng)受著文化開(kāi)放的沖擊,其中對(duì)西部鄉(xiāng)土沖擊最大的當(dāng)屬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蔓延,它所激發(fā)出的是長(zhǎng)期被政治話語(yǔ)所壓抑的對(duì)物質(zhì)欲望和消費(fèi)欲望的釋放。這一以物質(zhì)解放即感性解放為主導(dǎo)的文化潮流,沖擊著深處邊遠(yuǎn)西部傳統(tǒng)的鄉(xiāng)土文化聯(lián)接的人倫關(guān)系和鄉(xiāng)土倫理,最終給西部中青年作家?guī)?lái)的是文化混亂和價(jià)值迷失的焦慮困惑:傳統(tǒng)的鄉(xiāng)土倫理被人遺棄背離,寧?kù)o沉滯的鄉(xiāng)土生活開(kāi)始動(dòng)蕩,而如潮水般涌來(lái)的所謂都市文化和現(xiàn)代文化也并未帶來(lái)預(yù)想的實(shí)踐效果,甚至他們一度懷疑在西部以農(nóng)業(yè)文明和游牧文明為根系的文化機(jī)體上,新興文化能否生根發(fā)芽,這些新興文化是否是一場(chǎng)喧囂鬧劇和虛幻蜃樓。西部中青年作家在面對(duì)這一措手不及的文化侵襲時(shí),陷入了難以明晰的價(jià)值認(rèn)知和文化焦慮當(dāng)中,由此也形成西部作家價(jià)值立場(chǎng)與文學(xué)敘述的分化與動(dòng)蕩。對(duì)于這樣的身份焦慮與價(jià)值混亂,一些西部作家也試圖進(jìn)行文化精神的重建和心靈家園的尋覓,“那些文化上災(zāi)變性的大動(dòng)亂,亦即人類創(chuàng)造精神的基本震動(dòng),這些震動(dòng)似乎顛覆了我們最堅(jiān)實(shí)、最主要的信念和設(shè)想,把過(guò)去時(shí)代的廣大領(lǐng)域化為一片廢墟(我們很有把握地說(shuō),這是宏偉的廢墟),使整個(gè)文明或文化受到懷疑,同時(shí)也激勵(lì)人們進(jìn)行瘋狂的重建工作”。[11](P3)
多元文化的夾擊,迫使成長(zhǎng)中的西部中青年作家最終以理性的姿態(tài)來(lái)定位和確立自身的生存處境和身份歸屬。面對(duì)現(xiàn)代消費(fèi)語(yǔ)境下精神堅(jiān)守的脆弱與崩潰,擺在西部作家面前的選擇,要么融入市場(chǎng)潮流,要么堅(jiān)持鄉(xiāng)土倫理,要么反思鄉(xiāng)村與都市的正負(fù)效應(yīng),“如何在多元文化構(gòu)建進(jìn)程中發(fā)出自己的聲音,如何在‘現(xiàn)代化演進(jìn)’與‘民族性自守’之間定位好自身的敘事指向平衡點(diǎn),是許多民族作家所面臨但又不得不解決的文化難題”。[12]然而,“清醒地選擇、確立自身的某一‘位置’,又使另一些作家從惶惑、緊張中走出”。[13](P236-237)也就是說(shuō),焦慮的身份必然引導(dǎo)作家尋找自己的身份歸屬,盡管充滿了游移與不確定性。但邊地文化空間的多元性所提供的價(jià)值選擇,畢竟讓西部作家在當(dāng)代文學(xué)大環(huán)境的混亂與西部文學(xué)小環(huán)境的駁雜中,不斷逼近和切近了自己文化身份的位置,這種傾向性在西部小說(shuō)創(chuàng)作中,自20世紀(jì)90年代中期開(kāi)始,便逐步顯露出一種“保守主義”的敘事傾向——回歸鄉(xiāng)土傳統(tǒng),貼近西部底層,挖掘西部風(fēng)情,吟詠心靈詩(shī)意,將對(duì)激進(jìn)時(shí)代的疲憊跟蹤轉(zhuǎn)為放慢腳步固守大地。
如果說(shuō)固守鄉(xiāng)土的立場(chǎng)剛剛確立,那么,當(dāng)西部作家將審美視野重歸于生長(zhǎng)于斯的西部大地時(shí),他們對(duì)西部現(xiàn)實(shí)的困惑顯得更為焦灼。因?yàn)椋谖幕顺钡臎_擊下,西部傳統(tǒng)的價(jià)值體系已經(jīng)分化和崩潰,繼續(xù)堅(jiān)持農(nóng)業(yè)文明時(shí)代鄉(xiāng)土的“靜”與“美”已經(jīng)成為一個(gè)奢侈的理想,尤其是中東部地區(qū)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高歌猛進(jìn),也使西部作家在內(nèi)心質(zhì)疑著精神的堅(jiān)守與物質(zhì)的進(jìn)步到底孰重孰輕。最終他們從自身的敘事經(jīng)驗(yàn)出發(fā),認(rèn)識(shí)到文學(xué)的獨(dú)立與批判精神對(duì)社會(huì)的警醒,仍然可以起到一定的文化啟示作用,他們有責(zé)任和使命對(duì)生長(zhǎng)于斯的西部大地所日日發(fā)生的現(xiàn)實(shí)巨變與西部人在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的靈魂變遷發(fā)出自己聲音:“一切有能力思考的人,都應(yīng)該對(duì)社會(huì)發(fā)言,何況作家”,[14]“關(guān)于土地和苦難——誰(shuí)也不能否認(rèn),這兩樣,是文學(xué)的基本母題。生活在西部的作家,距離土地和苦難更切近,因而寫得更多,這不應(yīng)該受到非議。對(duì)于他們來(lái)說(shuō),這樣的情形更是命運(yùn),而非策略”,[14]“作為作家,我們是沒(méi)有能力幫助他們?cè)趺礃訒?huì)好一點(diǎn),或變成什么樣就更好了。作家的本事就是寫出能引起讀者共鳴,甚至震撼的作品來(lái)。”[15]這些作家自述都表明,他們選擇了不為“什么”而寫,只為“寫”而寫。在這樣的創(chuàng)作理念下,西部中青年作家將文化熱情、民間話語(yǔ)和人道主義情懷作為自己安身立命的三個(gè)資本,以消費(fèi)主義時(shí)代罕見(jiàn)的群體精神去審視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西部人在多重文化形態(tài)共時(shí)共存的境遇下的精神震蕩與人性變遷。其中既包括了書(shū)寫西部人對(duì)詩(shī)意生活的追求,也審視了西部人群人性弱點(diǎn)的根源,以及西部鄉(xiāng)土民眾進(jìn)入城市之后的文化沖突與心理震蕩,他們孜孜以求地構(gòu)建著一片純凈而豐富的西部文學(xué)世界。由此,西部小說(shuō)也實(shí)現(xiàn)了一次文學(xué)性的“換血”:即從80年代西部文學(xué)在急躁與刻意的“發(fā)現(xiàn)”與“標(biāo)榜”邊地特征,到90年代以較為平靜和自然的姿態(tài)“表現(xiàn)”與“咀嚼”著西部世界,西部文學(xué)由此從“刻意化”的地域性特色構(gòu)建,逐漸呈現(xiàn)出“自然化”的本土化自然特色。
從典型性來(lái)看,西部小說(shuō)就是當(dāng)下中國(guó)文學(xué)格局的一個(gè)縮影與標(biāo)本;從示范性來(lái)看,西部作家在面對(duì)西部本土人世方面,在立場(chǎng)的模糊中,也無(wú)意或有意地形成了一些個(gè)性獨(dú)特而深有寓意的審美特征與價(jià)值傾向,這不僅標(biāo)志著西部小說(shuō)家在一度的身份焦慮中,對(duì)自身身份屬性的逐漸明朗,即回歸大地、回歸底層。而且這種價(jià)值立場(chǎng)是對(duì)現(xiàn)代文學(xué)傳統(tǒng)的一種有意識(shí)的承繼,其對(duì)西部人在當(dāng)下多重文化擠壓下的人性變異與靈魂動(dòng)蕩所進(jìn)行的形而上思考,使西部小說(shuō)在緊貼西部鄉(xiāng)土大地的表象之下,內(nèi)蘊(yùn)著對(duì)現(xiàn)代文化反省的批判光芒,這在當(dāng)下文壇各種思潮紛紜迭起但卻價(jià)值含混的境遇中,顯示出一種獨(dú)特而堅(jiān)韌的內(nèi)斂式品質(zhì)。
三、守望與突圍:“邊緣敘事”與“主流話語(yǔ)”
現(xiàn)代性在中國(guó)的發(fā)生,常與“前現(xiàn)代”和“后現(xiàn)代”交織在一起,并在彼此的沖突和纏繞中,逐漸凸顯和展示出現(xiàn)代性的話語(yǔ)權(quán)威。現(xiàn)代性在中國(guó)社會(huì),表現(xiàn)為農(nóng)業(yè)文明向工業(yè)文明的轉(zhuǎn)型;在文化領(lǐng)域,化身為鄉(xiāng)村文化向都市文化的轉(zhuǎn)型;在地理領(lǐng)域,呈現(xiàn)為中西部地區(qū)向東部沿海地區(qū)的跨越;在文學(xué)領(lǐng)域,表現(xiàn)為“邊緣寫作”向中東部地區(qū)的“主流寫作”靠攏、逼近和融合。因?yàn)椋ㄓ腥绱耍拍堋芭嘀裁癖姷某志谜J(rèn)同,占領(lǐng)文化領(lǐng)導(dǎo)權(quán)的制高點(diǎn)。而能否得到民眾廣泛和主動(dòng)的認(rèn)同,是決定特定文化主體當(dāng)下生存權(quán)利和未來(lái)處境的關(guān)鍵因素”。[16]對(duì)于作家而言,文化演進(jìn)和地理分布的不均衡,使中東部地區(qū)作家能較早關(guān)注、涉獵和思索現(xiàn)代性在中國(guó)社會(huì)和中國(guó)文學(xué)中的命運(yùn)和走向,并通過(guò)自身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形成較為穩(wěn)定的文學(xué)理念,產(chǎn)生持久的文學(xué)影響力。而對(duì)于那些嶄露頭腳、身處大陸腹地的后起作家而言,能否躋身于文壇中心,不僅涉及到了自己的寫作命運(yùn),也涉及到了自身寫作能否被主流文壇認(rèn)同的問(wèn)題。這一問(wèn)題對(duì)于西部作家而言,關(guān)聯(lián)著他們?cè)诋?dāng)代文壇的話語(yǔ)聲音;對(duì)于當(dāng)代文學(xué)格局而言,則涉及到了文壇力量的互相牽制和力量均衡,甚至牽涉到中國(guó)文學(xué)版圖重繪的史學(xué)命題。“話語(yǔ)總是某一制度或者組織利益的代言,大眾媒介作為最發(fā)達(dá)的意義表達(dá)體系和社會(huì)話語(yǔ)的組織者,自然成為社會(huì)各種力量角逐的戰(zhàn)場(chǎng)”。[17](P138)而西部與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中心權(quán)力的疏遠(yuǎn),自然使他們?cè)诋?dāng)下以媒介主導(dǎo)的“新型意識(shí)形態(tài)”的權(quán)力格局下被拋擲于一個(gè)尷尬的位置。當(dāng)大多數(shù)中東部作家在本地區(qū)以積極努力的姿態(tài)介入文學(xué)圈的時(shí)候,對(duì)于廣大的西部作家而言,他們躋身文壇主流的道路卻異常艱難。無(wú)論是從西部省份行政體制對(duì)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有意扶持,種種地域文學(xué)口號(hào)的樹(shù)立與標(biāo)榜,還是作家自身對(duì)主流獎(jiǎng)項(xiàng)和榮譽(yù)的珍視,都可以看出西部作家發(fā)自內(nèi)心的渴望自身創(chuàng)作和作品價(jià)值被主流文學(xué)認(rèn)可的急切與焦灼。
西部中青年作家的小說(shuō)類型主要是鄉(xiāng)土小說(shuō),而鄉(xiāng)土題材的集體傾向卻又與當(dāng)前的“新新中國(guó)”的“城市喧嘩”與“現(xiàn)代演進(jìn)”相異,這同樣是西部作家除卻地域偏遠(yuǎn)之外備受冷落的文學(xué)成因。在中東部地區(qū)作家急切的表現(xiàn)和描繪著“現(xiàn)代化”和“大都市”的社會(huì)景觀之時(shí),對(duì)于西部作家而言,他們依然生活在鄉(xiāng)村人口占據(jù)絕對(duì)多數(shù)的農(nóng)業(yè)文明和游牧文明包圍的邊地鄉(xiāng)土世界。西部的城市盡管有了很多的現(xiàn)代都市符號(hào),但由于西部邊地文化的封閉性與悠久性,鄉(xiāng)土文化在西部邊地仍然有著一定的話語(yǔ)權(quán)力和文化份額,西部的現(xiàn)實(shí)情形仍以鄉(xiāng)村文明為主導(dǎo)。因此,對(duì)于西部作家而言,他們不僅要面臨如此情狀的一個(gè)文化事實(shí)與生存現(xiàn)實(shí),而且作為一種體制內(nèi)的精神創(chuàng)作活動(dòng),又不得不考慮自身價(jià)值的被認(rèn)可。但從西部作家本身的文化儲(chǔ)備和理論資源來(lái)看,與中東部地區(qū)的作家相比,他們對(duì)曖昧模糊的后現(xiàn)代文明有著天然的隔膜,因此,他們只能將視野轉(zhuǎn)向?qū)Ρ就潦澜绲纳钊胨伎肌S谑撬麄儗ⅰ拔鞑苦l(xiāng)土”特有的文化傳統(tǒng)、人文精神、鄉(xiāng)土情懷和審美理想等融合在一起,構(gòu)成起了一個(gè)獨(dú)特的西部文學(xué)世界,以此作為走向主流文壇和躋身文學(xué)中心的敘事特色和實(shí)踐籌碼。盡管他們以策略的敘事方式提供著異質(zhì)的文化要素,作為自己安身立命的文學(xué)資本,但在幅員遼闊的中國(guó),尤其在中東部與西部地區(qū)的政治制度、經(jīng)濟(jì)發(fā)展和文化權(quán)力發(fā)展存在巨大步伐錯(cuò)位的“中國(guó)國(guó)情”之下,西部作家無(wú)論是從自身的文壇話語(yǔ)權(quán),還是自身作品的受眾群體廣度,都普遍性的有著渴望躋身但卻被拒之門外的身份焦慮。尤其是當(dāng)中東部已經(jīng)在向全面小康社會(huì)邁進(jìn)的勢(shì)頭之下,西部作家仍然以遙遠(yuǎn)西北人為了基本的生存而苦斗的內(nèi)容為主題,這樣的文學(xué)表現(xiàn)自然容易受到冷落。但這個(gè)真實(shí)聲音的表達(dá),卻也恰恰構(gòu)成了西部文學(xué)得以存在和具有發(fā)展?jié)摿Φ膬?nèi)在價(jià)值所在:首先,它充分顯示出西部作家與鄉(xiāng)土大地的文學(xué)傳承與精神聯(lián)系,這是他們的文化母體與精神家園;其次,西部鄉(xiāng)土小說(shuō)的美學(xué)資源與文學(xué)思考在當(dāng)下的城市喧囂中可以提供復(fù)歸人性的文化能量;再次,西部鄉(xiāng)土小說(shuō)在當(dāng)下普遍低迷而下滑的精神維度中,卻表現(xiàn)出關(guān)注現(xiàn)實(shí)與凝望本土的文學(xué)品質(zhì),這既是西部作家在邊緣與中心的焦慮中,始終不改的文學(xué)命題,同時(shí)也是其可貴之處。盡管時(shí)至今日他們的這種邊緣與中心的焦慮仍然存在,但其立足本土、追求精神純粹的文學(xué)品質(zhì)正逐步得到主流文壇的認(rèn)可。西部作家在當(dāng)前的文學(xué)格局中,更多面臨的是如何在本土題材中實(shí)現(xiàn)普泛性的價(jià)值觀照,而且已經(jīng)有相當(dāng)一部分作家提供了這種價(jià)值理念成功實(shí)踐的范式。
從新時(shí)期到新世紀(jì),由于政治體制與意識(shí)形態(tài)的逐步開(kāi)放與革新,全球性的不同文化也在中國(guó)這個(gè)剛剛復(fù)蘇的古老土地上開(kāi)始了自己的文化表演與生存競(jìng)爭(zhēng)。面對(duì)政治記憶、鄉(xiāng)土轉(zhuǎn)型與邊緣處境的審視,不同作家筆下之所以會(huì)出現(xiàn)截然不同的結(jié)論和判斷,之所以他們對(duì)政治、文化、地域的現(xiàn)代性轉(zhuǎn)型充滿著決絕與猶疑混雜的曖昧態(tài)度,歸根結(jié)底,還是源于創(chuàng)作主體對(duì)現(xiàn)代性的認(rèn)知差異,對(duì)“現(xiàn)代性”本身概念的多重性的理解差異。對(duì)于西部小說(shuō)而言,這種對(duì)現(xiàn)代性問(wèn)題的不同認(rèn)知所帶來(lái)的現(xiàn)代性焦慮,不僅體現(xiàn)在西部作家在當(dāng)前文壇格局中的思想觀念認(rèn)同與文化身份認(rèn)同的焦慮,而且體現(xiàn)在西部作家面對(duì)西部鄉(xiāng)土世界和萌芽期的西部城鎮(zhèn)等文化象征物時(shí),所構(gòu)建出的不同內(nèi)涵的文學(xué)審美世界的價(jià)值判斷。同時(shí),在新時(shí)期以來(lái)中國(guó)文壇思潮迭起的文學(xué)演進(jìn)中,西部文學(xué)逐漸呈現(xiàn)出繼承鄉(xiāng)土文學(xué)對(duì)現(xiàn)代性探索的這一傳統(tǒng)主題的典型文本意義的同時(shí),始終保持著對(duì)西部鄉(xiāng)土世界的現(xiàn)代性進(jìn)程的弊端進(jìn)行獨(dú)有的遠(yuǎn)觀性與警惕性審視的立場(chǎng),呈現(xiàn)出與東部各種以“新”和“后”命名的文學(xué)思潮演進(jìn)相異的整體固守性姿態(tài),構(gòu)建著對(duì)現(xiàn)代性進(jìn)行“反思和超越”的“論戰(zhàn)式美學(xué)”的實(shí)踐典范。從這一意義上考察,西部小說(shuō)的邊緣敘事,恰恰體現(xiàn)出對(duì)現(xiàn)代性的感性發(fā)展和理性發(fā)展進(jìn)行藝術(shù)、哲學(xué)和文化制衡的最前衛(wèi)的“審美批判”價(jià)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