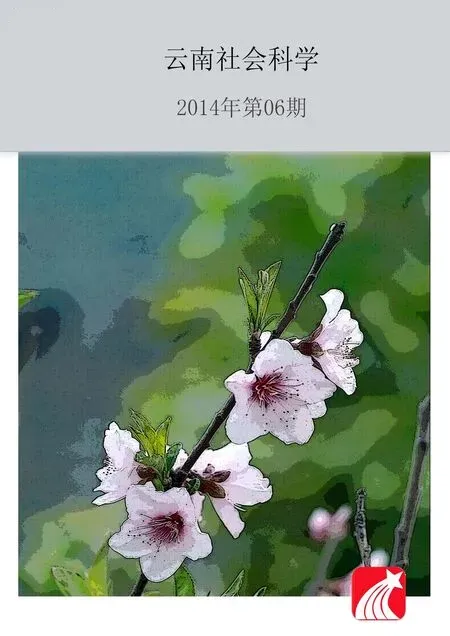記憶論:民俗學研究的重要方法
邵卉芳
尼采早就指出:“每個人和每個國家都需要對過去有一定了解……只有為了服務于現在和將來,而不是削弱現在或是損壞一個有生氣的將來,才有了解過去的欲望。”[1]可見,社會學、歷史學、民俗學、人類學等人文社會學科對于記憶的研究非常迫切。但對社會記憶進行理論化和全球化的研究,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成為熱點,這些研究加深了人類對自己歷史的了解與反思。
較早對社會記憶進行研究的主要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學者,有愛彌兒·涂爾干(émile Durkheim)、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ismund Schlomo Freud)、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阿比·沃伯格(Aby Warburg)、弗雷德里克·沃爾特雷特(Frederick C Bartlett)、沃阿諾爾德·茨威格(Arnold Zweig)、爾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等,最為杰出的當推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他是社會記憶研究的鼻祖。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法國、德國和北美分別出現了一批較為出色的研究者,但他們都在兩大范疇展開研究,即:民族國家的記憶——對個人以及個人所屬的集團或國家記憶的研究;全球記憶——對他國、他民族的記憶。
傳統記憶研究者認為記憶是跟過去緊密相連的概念,人們通過記憶直接或間接地了解和認知個人和集體的過去。但隨著研究的深入,新的研究者顛覆了以上看法,認為記憶包括現在的、未來的和動態的內容,記憶是一個帶有可塑性的動態系統。因為“記憶中把過去和將來兩個維度的聯系表現為一個人、一個群體或一個社會對將來的期待。沒有對自己的過去的把握,則很難對自己的未來有一個充滿意義的期待。所謂的希望也就是產生在這樣一個‘期待的空間’(evwartungsraum),而這期待的空間的大小是由記憶的內容以及容量來決定的”[2](P2)。
一、民俗學的記憶研究
在明確地提出“記憶”和“社會記憶”概念之前,民俗學界就已有學者進行記憶的研究,只是沒有把記憶明確提出來作為理論思考的對象,更沒有把它上升到“記憶論”的高度來看待。當社會學、歷史學等人文社會科學加深了對社會記憶的研究力度后,民俗學者對記憶論的關注才逐漸自覺起來。在民俗學界,對記憶進行研究最多的要數日本民俗學者,主要研究有:
阿部安成、小關隆的《コメモレイションの文化史·記憶のかたち》是日本記憶論研究的先驅,作者在記憶的概念、戰爭記憶的形成、文化遺產等方面的考察都做出了開拓性貢獻。羽賀祥的《史蹟論———19世紀日本の地域社會と歴史意識》調查分析了日本近世以來的紀念碑和紀念物的建造過程,揭示了建造過程背后的相關因素。名古屋大學出版會出版的《記録と記憶の比較文化史》對歐美、日本以及中國的社會記憶做了比較研究。小關隆《記念日の創造》對近代各國的紀念日的起源和意義作了分析。其中小關隆在1999年對人文學領域的記憶概念下的定義比較有代表性:
記憶是人們對過去的知識和情感的集合體,記憶的形成是一個表象化的行為。……記憶不單純是過去事件的儲藏庫,它是記憶主體針對自身所處狀況喚起特定的過去事件并賦予意義的主體行為。因此,記憶和記憶的主體,即生活在當下現實的人們所屬的社會集團的自我認同有著本質的聯系。……由于個人、集團的自我認同是不斷變化的,與此對應,記憶也不斷地被重新建構,“值得記憶的”在不斷被選擇、喚起的同時,相反的事件則被排除、隱瞞。從這個意義上說,忘卻也是構成記憶的一部分。任何一個記憶的表象的背后,都有無數被忘卻的事象[3]。
根據該定義,記憶的特點為:(1)記憶形成于人們對過去事件的表象化過程中。記憶與記憶主體的當下狀態直接相關。(2)記憶本身包含著忘卻的機能,記憶不僅代表過去的靜態的內容,而且是關聯現在與未來的動態的概念。
如今,記憶論在民俗學界的應用與研究逐漸增多,民俗學者對記憶論之于民俗學研究的看法也各具特色。巖本通彌指出:“記憶作為一個有效的分析性概念,在分析社會、政治現象時得到廣泛運用。在民俗學領域,記憶論的研究也開始成為矚目的焦點,……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民俗學的最本質性的存在就是記憶。”[4](P109~115)巖本通彌極為肯定記憶論研究的重要性,但筆者認為這一論點不太合適,說“記憶是民俗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法”或者是“民俗學的最本質的存在是‘研究記憶’或‘用記憶方法研究民俗’”似乎更為恰當。另外,針對傳統民俗學的研究取向*即追求民俗資料的“真實性”,口述訪談資料被當作文獻資料的補充,民俗學變成了歷史學的輔助學科。,巖本提出記憶論在民俗學研究方面的幾個相關事項。
(1)民俗學不是以文獻記錄,而是以記憶為素材的學問。它主要以沒有被文獻記錄下來的事項作為研究對象。(2)在研究中,它的基本方法是對直接性的口述、對話進行訪談記錄。(3)通過以言語為媒介的記憶提取信息,原生態地把握當地人們的生活世界。 (4)同時,把非言語的如身體行為、感覺、思維方式、價值觀、感情、身體技能作為研究對象。(5)這些知識系統以身體作為媒介,在不同的個體、群體之間發生的保持、傳承、傳播。力圖去把握這個傳承的過程和特征。(6)將使這樣的記憶可視化、有形化的行為,通過訪談記錄、民俗語匯化、民俗志等方法加以記錄,(主要是文字化)[4](P109~115)。
巖本還認為,訪談記錄法是民俗學區別于人類學參與觀察法的重要指標,在方法論上,巖本總結了千葉德爾的訪談方法論,指出:訪談記錄“既是民俗學發揮本領的領域,也是未來文化研究必須解決的重大難題”[5](P274)。為了強調記憶論與訪談方法研究,巖本使用了比較絕對的說法,實際上,除了人類學,民俗學和社會學也同樣在非常廣泛地使用參與觀察法,且參與觀察與訪談記錄兩種方法相得益彰地運用才是民俗學研究的題中之義。
關于記憶論對民俗學研究的意義,王曉葵認為,記憶論在民俗學研究中的一個嘗試是用口述史的方法,分析民俗現象在現代社會多元化結構中潛在的多種變體。這些變體依據傳統的研究方法往往會被簡單地作為例外加以排除。但通過對口述史材料的分析,可了解具體的民俗傳承人的生活經歷和傳承行為的關系,敏銳地把握現代社會的民俗變遷[5](P276~277)。另外,王曉葵還舉川森博司的例子指出,新的民俗志的書寫將基本上完全依靠記憶,因為有很多現實中不存在但是依然存活在人們記憶之中的“潛在民俗”。王曉葵認為現代民俗學的研究離不開記憶論,但筆者認為若單純依賴記憶則必然會使研究走入死胡同,因為現代民俗學有很多內容是當下發生的,不需要過多地憑借記憶,而現時的參與觀察顯得更為重要。
筆者贊同日本民俗學者對記憶論之于民俗學研究重要性的論述,其中需要注意的問題下文有詳述。
二、記憶論之于民俗學研究
記憶論應如何引入民俗學研究?民俗學可在記憶論研究方面發揮什么作用?這些都是民俗學者理應深入思考的問題。
首先,除了上文中提到的口述史研究以及戰爭與災害記憶的研究,民俗志的書寫也離不開記憶論。對此,王曉葵認為:“民俗學的主要方法之一是民俗志的方法,而傳統的民俗志的撰寫工作,往往是直接對口頭傳承的訪談記錄,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有很多民俗事象隨著生活方式的變遷,已經喪失了其存在的外在形態。比如很多地方已經不再使用耕牛,相關的農具等也不復存在。但是,這并不意味者相應的民俗已經消失。……如有需要,他們(老農)是可以回復這個民俗事象的。這種現象,日本民俗學家櫻田勝德稱之為‘潛在民俗’。所謂潛在民俗,就是保存在人的記憶之中的、失去了外在形態,但是經過記憶的重構,是可以恢復原來的形態的。因此,民俗志的書寫,開始越來越依據記憶的材料。”[5](P278)記憶的材料固然是民俗志研究與書寫中的重要材料,但僅將記憶看作關于過去事情的回憶,確有片面性。因為如前所述,記憶研究的不僅是過去,更重要的是當下。小關認為:對過去事件的記憶和“記憶的主體,即生活在當下的人們所屬集團的自我認同的本質,復雜地交織在一起。”[6](P5~22)因為“‘民俗’及與‘民俗’關系密切的‘文化遺產’的承擔者是當今的民眾,他們本身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民俗學現在不斷地對那種變了形的現場進行調查并盡量地把它們記錄下來,可問題是與‘文化遺產’關系密切的亙古的‘記憶’里沒有包括當今的民眾。在這種情況下,民俗學正試圖刻畫現在承擔著‘文化遺產’的民眾的生活,作者也認為應當這樣做。本文所論及的正是這樣的‘現在’的記憶。”[7](P302)過去的記憶與現在的記憶應有機地統合在民俗志的研究與書寫中。
其次,“非遺”項目中保護的其實就是“記憶”,既有“物質上的記憶”也有“身體上的記憶”。王曉葵指出:“人們往往認為,文化遺產是為了保存或者喚起過去的‘記憶’。……其實‘文化遺產’保存的‘記憶’不是原本就有的,而是在人們回顧過去時產生的。”[7](P299~301)筆者贊同王曉葵的說法,記憶不是生來就有的,而是在與人的回憶行為發生關系之后的特殊產物。民俗學的記憶研究不只是記錄與整理。因為,僅僅將記憶存檔并不等同于文化記憶,只堆積資料而不進行甄別篩選,便缺乏感情與歷史的投入,也不能表明其與當下的聯系。記憶研究指的不僅是記錄訪談錄音,記錄的前提是訪談,訪談的視角、如何訪談等本來就極為重要,這些也值得探究;如何記錄也很關鍵,按照學界多數學者的觀點,民俗學的記錄不但要記錄談話內容,而且要注意觀察和記錄訪談現場的氣氛、環境以及被訪談者的表情、動作等細節,這些是連視頻都無法“完整記錄”的重要內容,更不用說錄音和筆錄了。更重要的還有“記錄何為”的問題。退一萬步講,按照理想狀態,我們把發生在訪談現場的“所有”內容一應俱全地完整記錄了下來,但記錄的目的是什么?記錄的內容作何用途?難道僅僅把民俗學研究看作資料搜集的手段嗎?因此,要解決上述問題,在進入田野之前就應弄清訪談目的、田野作業的旨歸、民俗學研究的追求等問題。
再次,民俗學目前還面臨著一個與大眾傳媒緊密糾纏的問題——即媒體與記憶的關系。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民眾包括“非遺”傳承人都深受媒體的影響。較早注意“文化記憶”與媒體之間關系的是陽·阿斯曼(Jan Assmann)和愛蕾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夫婦,他們的貢獻是突破了哈布瓦赫的視野,將媒體引入記憶研究領域。他們認為“文化記憶”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走過了三個歷史階段:口頭敘述階段、筆錄階段與印刷階段。阿斯曼夫婦非常反感印刷技術發展以后文化記憶的發展狀態,他們指出,正是由于“文化民主化”,才使得“文化傳統不是得到了保護,而是得到了(不必要的或是別有用心的)更新,回憶也就變成了編造,‘文化民主化’必然使傳統變成了無家可歸的流浪漢”[8](P114~140)。客觀而言,阿斯曼夫婦的這種觀點顯得片面,事實是,逐漸發展的大眾媒體使得人們的回憶意識慢慢地變成了生產消費品與消費人為編造“歷史”的狀態[8](P114~140)。當消費欲望超過文化傳統保護理念的時候,記憶文化便會為“眼球文化”所代替,從這個角度來看,阿斯曼夫婦大聲疾呼“記憶的危機”也就理所當然了。筆者以為,阿斯曼夫婦的這種批判實際上是對那些利用媒體制造社會記憶的權威勢力的批判,也就是說,他們的批判對象不是媒體本身,而是制定記憶政策的威權者,可以肯定地說,他們的這種批判在當下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現如今的事實是,越來越多的人依靠媒體形成自己的社會記憶,在大眾傳媒的強烈沖擊之下,口頭敘述顯得如此稀缺與無力。因此,媒體與社會記憶的關系問題依然是一個值得探討的深遠話題。概括而言,主要有兩個方面值得思索:一是大眾傳媒如何幫助人們建立社會記憶?二是不同階層的社會記憶如何反過來影響媒體的敘述,從而在媒體上表現出來?這一點在朱仙鎮木版年畫傳承人的身上表現得極為明顯,一方面傳承人的身體記憶為媒體的言說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另一方面媒體的言說又影響了傳承人的言說與身體記憶,二者之間的這種互動關系值得考察。
另外,筆者認為民俗學的記憶研究還需要注意以下幾點:
1.記憶的選擇性
記憶都是有選擇的,記憶或忘卻的標準分別是什么?為何記憶這個而忘卻那個?記憶的標準與原則是什么?不論是個人記憶、集體記憶、社會記憶還是文化記憶,都是選擇的結果,這里就存在選擇的原則與標準的問題,而這也就是需要著力探討的內容。
選擇的原則與標準并不是客觀地存在于那里的,而是受到各種外界因素影響的。“從技藝規定身份這個角度看,應該記住什么,忘卻什么,就不僅僅是一個純技術性的問題,也不僅僅是‘記憶的策略’的問題,而更是反映了這個人或這個民族現實的需求,也反映了該人或該民族面對過去的道德責任和勇氣。這種記憶的需求和面對過去的道德責任,以及在此基礎上產生的記憶,規定了這個人或這個民族怎么看自己以及希望他人怎么對待他/它。”[2](P2)社會學家哈布瓦赫區分了“記憶”與“回憶”,認為回憶是過程,記憶是結果,并且指出:“既然個人回憶的前提是社會需要,記憶是回憶的結果,那記憶也必然充滿瑕疵。記憶是社會回憶過程中的重新建構,是一種社會行為。換言之,記憶本身和它所涵蓋的事件本身之間有很大差異。也就是說,在記憶的構建過程中,事件有所丟失,也有所補充,但作為回憶的結果即記憶和曾經發生過的事件之間絕對不是等同的。回憶是有策略的,社會的忘卻和記憶有一部分是迎合了當權者或者是社會勢力強大的利益集團的某種需要。”[9](P66)如上文談到的媒體與記憶的關系,其中隱藏的威權勢力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
2.記憶建構身份
“在現實社會,一個人的身份,一個民族的自我認同,無不與這個人、這個民族對自己過去的記憶有關。”[2](P2)可見,不論是個人記憶、集體記憶還是社會記憶,均不同程度地具有建構身份的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說,建構身份是記憶存在的最本質特征之一。“在塑造自己的身份時必然要求我們找出能說明我們認為這是我們的一連串事件。在這樣做的過程中,我們從無數的經驗中篩選一些我們認為可面對今天的事實,同時我們又根據事實的重要性來決定我們的篩選。記憶就是這個篩選作業的產物。沒有忘卻就沒有記憶。”[10](P170)記憶建構身份的過程實際就是把過去與現在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過程,是一個賦予過去事件以一定意義的主體行為,其中含有充分的主體性。
回到田野個案,朱仙鎮木版年畫藝人郭太運的身體記憶有助于他現在的“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身份的塑造,因此,探究身體記憶(包括郭太運本人的身體記憶以及其他相關人員的身體記憶,包括政府相關資料的記憶即記載或記錄)是如何塑造的以及塑造的過程等,搞清楚身體記憶在其中發揮的作用,都是非常有意義的話題。
3.記憶的對峙性
不同主體對同一件事情的記憶也會有所不同,因此便出現了不同記憶的對峙與共存。例如,在上述朱仙鎮木版年畫傳承人郭太運的身體記憶與朱仙鎮木版年畫的身體記憶中,存在著官方的記憶與民間的記憶、公共的記憶與私人的記憶、正式的記憶與非正式的記憶、“正確的”記憶與“錯誤的”記憶的對峙與共存。上述現象在現代通信技術高度發展之后,在非政府組織大量出現之后,更加凸顯出來。
“不同的群體對似乎是同樣的 ‘過去’,明顯有著不同的‘故事’,而這不同的故事,則限定著這些群體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甚至限定了他們對未來的設想。”[2](P6)面對不同的記憶與敘述,民俗學者究竟應持何種態度?筆者以為,最先明確的便是不同的記憶是如何進行敘述的?諸如此類的不同的敘述方式因何得以存在?在分析這些不同記憶與不同敘事時,關鍵不在于探討其合情合理性,而在于探討它們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另外,還存在一種比較特殊的“對峙”,即同一個人的“不同的記憶”。在郭太運的“身體記憶”中也包含著這種“對峙”,也就是說郭太運的對自己記憶的講述以及對朱仙鎮木版年畫等民俗的講述,都不完全是他關于記憶與民俗的最本源的“知識”,而是通過與外邊世界“比較”之后的“知識”。簡單地說,就是針對同樣一件事情,在不同的時間段或在不同的場合,傳承人也會有不同的記憶與言說。究竟哪一種記憶與言說是正確的?這不是筆者著重討論的話題,不同記憶與言說的形成原因與過程才是最值得思考的問題所在。不可否認的是,傳承人在受到媒體影響的過程中主觀上認可威權勢力的話語權,而對自己的本來記憶產生了疑惑甚至是背離。
4.個人記憶與社會
法國社會學家哈布瓦赫,是社會記憶研究的鼻祖。在他之前,學界對社會記憶的研究重點幾乎都放在了生理遺傳條件或心理條件方面。哈布瓦赫對社會記憶的研究具有名副其實的顛覆性。他認為,個人記憶由社會來決定,集體記憶與個人記憶不可分割,集體記憶可以共享并且可以傳遞給后代,并且指出集體記憶存在于現代社會和一些社會團體中。哈布瓦赫非常關心個體記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只有在社會里人們才能獲取他們的記憶。也只有在社會里人們才能回憶,認同其回憶以及使記憶找到自己的位置。”[11](P38)按照其觀點,個人記憶只有在社會化的過程中才能形成,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相對,個人記憶具有社會性并受社會的制約。因此,民俗學對個人記憶的研究意義重大,例如對傳承人等人口述史的研究便顯得格外緊迫,因為這些看起來屬于個人記憶的內容其實與集體記憶和社會記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集體與社會的某些內容與動向。透過個人記憶,來審視集體和社會的某些變化與特征,才是研究的關鍵所在。
三、身體記憶與民俗學研究
在民俗學記憶研究中身體記憶占據重要位置,因此筆者把身體記憶作為獨立的一個小節進行論述。首先來對 “身體記憶”的概念進行界定,界定之前有必要對以往學術界的相關概念進行回顧。社會記憶研究的鼻祖莫里斯·哈布瓦赫使用的概念是“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德國的古埃及學家陽·阿斯曼(Jan Assmann)則用“文化記憶”(cultural memory)的概念,其后的學者也有使用“公共記憶”(public memory)和“社會記憶”(social memory)這兩個概念的。但以上概念均沒有明確其“身體性”。而之后的學者也沒有對之作出明確的定義。只有劉鐵梁才真正強調了身體記憶的重要性,他的觀念深深影響了弟子們,張青仁在2009年發表的《身體性:民俗學的基本特性》便是例證。筆者對劉教授“身體記憶”的理解是:“身體記憶”一方面包括“頭腦中的記憶”,另一方面包括“身體實踐”或曰“身體技藝”,因此筆者在做朱仙鎮木版年畫的田野調查時,比較注意收集記憶與技藝這兩方面的資料信息,實際上,二者緊密雜糅在一起,藝人按照師傅傳下來的方法制作木版年畫這個身體實踐過程本身,既有技藝的成分,又有記憶的成分,可以說記憶包含在技藝中——通過大腦的記憶來記住師傅傳授的年畫制作技藝;同時技藝也包含在記憶中——大腦中記住的不僅有木版年畫其他方面的知識,而且還有其傳統的制作工藝即技藝知識,這里的記憶將為年畫制作技藝的實施助一臂之力[12](P111~133)。需要指出的是,筆者這里談到的身體記憶不局限于某一個體的身體范圍之內,也可以指兩個個體或者是多個個體之間的身體記憶,即身體記憶具有主體間性,它存在于互動的主體間的范圍內。因此可以說,身體記憶概念的提出與在民俗學研究中的運用將是一個不小的突破,同時也拓展了民俗學身體研究的路徑。
筆者認為,身體記憶概念在民俗學研究中的引入,與劉鐵梁的“感受民俗學”關系十分密切,可以說,只要提到身體,就不可回避感受。這里的感受既包括研究者主體的感受。劉鐵梁說:“民俗學直接面對的卻是有主人在場的生活文化。”[13](P24)在這里,他強調不要忽視生活的整體性,并且指出“應該說,只有通過人的行動,才能呈現出生活的整體性,而不是靠民俗事象的排列組合”[13](P24)。根據劉教授的觀點,筆者認為民俗學研究應該重視人、人的生活與感受,其中包括對人身體記憶的思考與研究。劉鐵梁還在《中國社會科學報》中指出:“地方社會保護民俗文化就是在保護其共同的歷史記憶”,“對于一個地方社會來說,保護民俗文化就是在保護地方社會共同的歷史記憶,即一個集體對于共同經歷的生活變化的記憶。既要求改變生活,又要求記住自己的過去,這兩方面的要求構成了當代人的文化心態”[14]。另外劉鐵梁還強調:“民俗學的……根本性的價值是對于生活整體的關照。”[13](P2)而關照生活整體,最需要關注的則是生活中的人,因此對人的身體記憶的關照與研究就顯得如此迫切。
筆者認為,除了上述之主體間性,身體記憶還具有復合性。即身體記憶這一概念的使用并不僅僅局限于個人記憶的范疇之內,它同時還適用于集體記憶、社會記憶與國家記憶等范疇。因為身體雖然首先是個人的身體(包括身與心),但同時也是集體、社會和國家的身體。盡管集體、社會和國家沒有具像的身體存在,但這并不影響身體記憶的研究,因為筆者所談論的身體記憶從根本上來講,與其說是一種研究對象或研究內容,倒不如說是一種研究方法。這種觀點深受劉鐵梁教授的影響,之所以強調身體記憶在民俗學學科范圍內的重要性,實際上依然還是在回應與踐行劉鐵梁的“感受生活的民俗學”的理論觀點。因此,不論是“通過民俗”還是“通過身體”,方法論的凸顯才是關鍵所在。
四、結 語
目前,記憶研究還未成為主流的考察方法,依然處于邊緣學科或跨學科的研究境地。盡管如此,與記憶論有著天然聯系的民俗學,依舊需要深入思考記憶論作為一種重要研究視角在民俗學研究中的應用,該研究視角的可能性與現實性均應成為民俗學者探索的重要話題。
1.民俗學應該建立本學科的記憶研究理論
“鑒于社會記憶研究在學科領域的多樣性(政治學、哲學、文化學、人類學、民族學等),同時又鑒于這些領域在社會記憶研究中本身的界限的模糊性,要很清晰地把社會記憶研究歸入某一學科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便如此,仍然有必要從某一學科出發,努力地勾畫出不同的記憶方式,以及它們會如何引起不同程度的‘社會忘卻’(social amnesia)。”[2](P5)因此,民俗學應當發揮出本學科的優勢,牢牢抓住民俗學“體驗、感悟、理解、認識”生活的學術指向[15](P5),扎實地做好田野工作以及個人生活史和民俗志的研究,在實際中建立本學科的記憶研究理論,逐步完善民俗學記憶研究的理論體系。
2.身體記憶包括理論和實證兩個層面
民俗學的身體記憶研究,包括理論層面和實證層面的研究,理論研究為實證研究提供指導與方法,實證研究為理論研究提供支持與檢驗,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通過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的結合,需要明確的問題是:誰是身體記憶的主體?記憶的內容是什么?主體是如何記憶的?記憶的手段或媒介是什么?什么原因促使記憶的發生?為何這樣記而不是那樣記?此外,關于身體記憶的理論還處于未成熟階段,有待于進一步地思考與完善,相關的個案研究也為數不多,同樣具有巨大的研究空間,民俗學者大有施展之處。
3.記憶的難題
記憶(包括身體記憶)存在兩大難題:一是記憶的多義性,二是記憶被誤解。記憶的多義性本質上就是記憶概念的模糊性,不同學科不同學者在使用記憶這一概念時均有所側重,都有一套自己的解釋模式,局限于自己的模式之內進行演繹,很容易讓讀者產生一種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的感覺。因此,記憶的多義性問題亟待解決。記憶被誤解主要是伴隨著記憶問題的國際化而出現的問題,具體而言,主要是不同民族或國家對歷史的不同記憶甚至是誤解。例如對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看法,亞洲國家與歐洲國家的看法不盡相同,中國人與日本人的看法很不相同,德國人與日本人的看法也不完全相同,在同樣的歷史事件上,甚至還會出現不同民族有著完全相反觀點的現象,這便是記憶被誤解。面對這一問題逐漸擴大化的現實,民俗學者理應做出自己的回應與貢獻,對相關記憶問題進行著力研究方是可行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