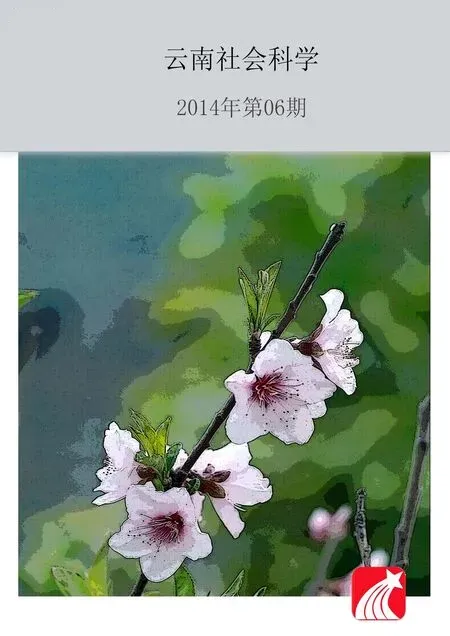傣族村社政治關系的變遷
——以云南省孟連縣和雙江縣為例
周俊華 刀麗鳳
村社是中國農村社會最基層的組織,處于農村社會組織結構的末梢。“從民族政治學的角度,少數民族地區的政治體系可劃分為國家政治體系、民族自治政治體系和民族村社政治體系三種形式。”[1](P107)研究民族村社政治關系是了解和理解民族村社政治的重要途徑與方式。對云南邊疆地區民族村社政治關系的探究,有利于構建和諧民族政治關系,促進邊疆各民族的團結、繁榮和共同發展。本文試圖描述云南傣族地區最基層政治關系的變遷及其當下特征,為學界了解云南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村社政治關系的發展變化提供個案。
筆者對歷史上傣族村社政治關系主要采取文獻研究的方法,對當下傣族村社政治關系則運用實證研究的方法。選取云南省孟連縣勐馬鎮和雙江縣沙河鄉各一個傣族村社作為田野調查點,采用民族學的慣例,將兩個傣族村社化名為勐混村和勐滾村。筆者于2013年12月上旬,前往兩地做入戶問卷調查和訪談,歷時8天。受訪者包括當地鄉鎮公務員、村干部以及村民。調查問卷內容包括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個人信息,第二部分是關于傣族村社政治關系的相關問題,共40個問題。在兩個調查點各隨機發放200份問卷,共發放400份問卷,回收398份。其中,傣族受訪者370人,其他民族受訪者28人,本文以370份傣族受訪者的問卷為樣本進行統計分析。
一、傣族村社政治形態的沿革
1.1949年以前傣族村社的政治形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傣族社會形態經歷過原始社會、家長奴隸制社會、封建領主(部分為封建地主)制社會的演變。據《泐史》記載,傣歷五百四十二年,即宋淳熙七年(1180),叭真在今云南西雙版納建立了著名的景龍金殿國,其政權內部有嚴密的組織體系,層層銜接,環環緊扣。至元代,中央王朝在云南傣族各聚居區原有政權機構的基礎上設立了土司,如西雙版納地區的徹里路軍民總管府(明后改為車里宣慰司)、德宏地區的平緬宣撫司(后因勢力過大被撤銷)、木連路軍民府(明后改為孟璉長官司、孟連宣撫司)等。此后,除個別傣族地區的土司被廢除外,在云南大多數傣族地區,土司統治一直延續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據史料記載,云南省雙江縣和孟連縣的傣族先民是在南宋寶祐元年(1253,傣歷615年)從勐卯弄(今德宏瑞麗一帶)遷徙而來。孟連土司的主要轄區是孟連壩子,統治達660年之久,共歷28代,勐勐土司的主要轄區是雙江壩子,前后統治共306年。[2](P79~81)孟連土司和勐勐土司的政權組織系統均由土司衙署、地方派出機構、村寨三級組成,具體又略有差異。孟連土司最高統治機構為宣撫司署,宣撫司使(傣語稱“召賀罕”)為其最高統治者。其中,土司署保留了傣族社會長期沿襲下來的由各個小土司、山官組成的“司廊”(即議事庭),由三個資歷最老的世襲的召根(貴族家臣)輪流擔任“薩地龍”(議事庭庭長),他們統率所有官員,總理土司署內一切政務。[3](P183)每個召根管理著數個村寨,村寨頭人則由土司或召根任命。召根之下又設有召郎作為聯絡官,職責是監視和制約各級頭人。村寨頭人執行土司的命令,行使村寨權力,但在決定重大事務如分配土地資源等,仍需召開村民大會征詢意見,獲得村民的認可。
土司衙署是勐勐土司轄區內的最高統治機構。土司任命若干大小“太爺”、“宣爺”為其助手。一般而言,太爺由土司的直系血親擔任,依據其能力和資歷的不同,所掌權力也不同,但各自都擁有轄地和私莊,享有各種特權。土司處理重大事務時,一般先召集太爺商議后作出決定,再令有關宣爺執行。宣爺由貴族擔任,在土司衙門或下級管事機構擔任一定的職務,經土司加封后可以世襲,否則雖有宣爺頭銜,卻無特權。太爺、宣爺還固定統轄某些圈官和村寨頭人,代表土司分別掌管轄區的軍政大權,處理訴訟案件,為土司征收賦稅,分派兵役等。[4](P55~56)勐勐土司政治廢棄了原始民主制形式,土司的統治和管理更為垂直。
綜觀孟連土司和勐勐土司政治統治結構,土司統治下的傣族社會內部形成三個階層,即土司統治階層、農民階層以及佛教僧人階層。出于統治的需要,傣族土司還將轄區內的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土地劃分為領主地段、農民地段和佛寺地段,這種傣族封建領主制下土地制度使傣族社會三個階層的區分凝固化。
這一統治模式延續至傣族村社中,形成了土司統治下傣族村社的政治關系及其特征:(1)整體上而言,土司階層擁有對其屬民的絕對控制權,農民依附于土司階層。(2)橫向上而言,在傣族傳統社會結構中,佛寺相對獨立于土司階層與農民,同時,因傣族全民信奉南傳上座部佛教,通過信仰對世俗生活的滲透、融合,佛寺與土司階層和農民發生聯結,從而形成傣族社會內部土司階層、佛寺、人民之間穩定的“三角式”政治關系,對傣族社會政治秩序的維系和穩定產生重要作用。(3)縱向上而言,傣族土司統治下的村社政治關系自上而下,從土司到召根或太爺,再到召郎或圈官直至村寨頭人,具有垂直多層、環環緊扣、職能明晰等特征。
2.1949年至改革開放前傣族地區的政治形態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確立了新的政治體制,影響包括傣族在內的中國各少數民族政治形態的發展。1949年至1950年間,孟連縣和雙江縣先后解放,成立了孟連縣臨時人民政府和雙江縣人民政府。新的政治體系的建立,為少數民族基層社會的一系列改革提供了強有力的政治保障,也促使原有的村社政治關系發生了巨大轉型。國家權力直接深入到傣族鄉村社會,實現對傣族鄉村社會的直接控制,傣族地區與內地一樣實行縣、鄉、村這樣的行政層級,村社被直接納入到國家基層政權的控制之下。原有的傣族社會自成一體的政治組織形式和政治關系完全被打破、革除,實現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少數民族村社政治關系的新建構。
至人民公社化時期,國家權力對鄉村社會實現了全面控制。此時,村社內構成了以大隊黨支部為領導核心的村社黨政組織體系,人民公社全面掌控了傣族鄉村社會內部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力量,每一個成員個體都對人民公社全面依附,從而建構起人民公社—大隊—村—村民這樣一種垂直的、自上而下單維度的政治關系。這種村社政治關系的優點是簡單、垂直、明晰,確實強化了當地各民族的國家認同意識,增強了各少數民族對黨和政府的絕對支持。但這種整齊劃一的體制嚴重削減了鄉村生活的自我生存空間,剝奪了村這一級中國鄉村社會最末端組織的自主管理權力以及村民個體的主體性和自由性,鉗制了基層社會的生機和活力。地處西南邊陲的少數民族鄉村社會本身具有特殊性、差異性和離散性等特征,這種單向度的村社政治關系與之不匹配,因而也缺乏良性發展的社會根基。與傳統傣族社會中原生型、多向度、具體的村社政治關系相比,這種村社政治關系是抽象的、外嵌型的,因而在一定意義上而言是畸形的。
3.改革開放以后傣族地區政治形態的變化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村民自治施行后,國家權力逐漸下放,開始給予村社一定的自治權力,使村社有了較大的自主管理和發展空間,傣族村社政治關系再次發生轉型,逐漸形成了以國家政權為依托的體制內政治權力主體和以傳統文化習俗為支撐的體制外政治權力主體并存的局面。在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社會環境復雜化、經濟現代化等多種因素的交織互動下,傣族村社政治關系走向復雜化、多維化。依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云南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孟連縣和雙江縣于2000年將村公所、辦事處改為村民委員會,村民自治制度方正式施行。現在的孟連縣共轄3個鎮、3個鄉、3個居委會、39個村委會,雙江縣轄四鄉兩鎮、3個居委會、72個村委會。
二、目前傣族村社政治體系的基本情況
傣族村社的政治關系總的來說可分內、外部兩大類。
(一)傣族村社內部的政治關系
目前,傣族村社內部的政治關系主要是掌握權力的政治權力主體之間、政治權力主體與村民之間的關系。根據權力的獲得方式,傣族村社內部政治關系可分為以下三大類:
1.體制內政治權力主體內部的政治關系
(1)村民委員會與村黨支部的政治關系。傣族村社村黨支部與村委會的政治關系通常是圍繞村社公共權力的運行空間而展開的,主要表現為競爭、合作兩種關系。第一,合作關系。一般而言,在傣族村社中,村支書主要負責主持村黨總支全面工作,負責黨建、組織、人事、民族團結、武裝、思想政治等工作;村主任則主要協助村支書工作,處理本村的各項公共事務,調解村民糾紛,協助維護本村社會治安,向上級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見和要求并提出建議等。由于二者的許多工作會有交叉,為了更好地完成工作,就不免相互幫助、支持與合作。例如潑水節慶祝等民俗活動以及鄉鎮政府下達任務時,都需要村兩委共同完成。第二,競爭關系。從雙江縣勐滾村和孟連勐混村的情況來看,村黨支部和村委會之間的競爭并不明顯,主要表現在村黨支部對村委會產生和運作過程的隱性影響。首先,村黨支部會通過一定鄉土社會人際關系影響村主任的產生。針對“跟書記關系好的人是否更容易當選村主任”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約5.6%的受訪者表示認同,38.5%的受訪者認為有時候是這樣,55.9%的受訪者則認為沒有任何影響。其次,村黨支部書記會因其人格魅力影響村社事務及決策。例如,在勐混村的問卷調查中,約有41.1%受訪者表示村支書對村里的事務更有決定權,比選擇村主任的人數多近10%。此外,48.2%的受訪者表示如有事情需要找村領導會先找村支書,而僅24.1%的受訪者會首先去找村主任。可見,傣族村社中,村黨支部與村委會存在競爭的政治關系,但卻是以一種較溫和的、隱性的方式存在。
(2)村民委員會與村民小組的政治關系。村民小組是民族村社中的另一體制內政治權力主體,是鄉村社會組織的最末梢,也是國家權力滲入村民社會最后的媒介和渠道。從法律意義上看,村民小組在縱向上隸屬于村委會,受村委會的領導。但從傣族村社的實際情況來看并非完全如此,村委會與村民小組之間更多是一種互動的關系,表現為博弈與調適。因自然地理環境、村民小組集體經濟實力以及村民自我利益等因素的影響,村民小組事實上享有相對獨立的政治空間,并常常導致村委會在一些事務上對村民小組心有余而力不足。“村主任是否指揮得動隊長”*隊長,實為村民小組組長。人民公社時期,云南一些少數民族地區的自然村被編為生產隊,負責人為生產隊隊長,現被沿用來稱呼村民小組組長。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73.9%的受訪者認為偶爾可以,前提是村主任有理,8.8%的受訪者認為由于村民小組長比村主任更有能力而致使村主任難以支配村民小組長,僅17.3的受訪者認為村主任可以完全支配村民小組長。但這種博弈沖突,通常雙方都會因實際情況做適當的妥協、讓步。其原因在于,村委會掌握相較于村民小組更多的資源,包括便捷的信息資源和對整個村社資源的配置權等,而村民小組的治理是村委會政績考核的一部分。因此,雙方的讓步將是必然。此外,村委會領導與村民小組干部的私交情感也為二者的政治關系提供了更多的默契與調適,為博弈帶來許多緩和。
2.體制內政治權力主體與體制外政治權力主體的政治關系
在傣族村社中,除了村委會等正式的政治權力外,還有一些村寨自然內生的政治權力,即體制外政治權力,他們在民族村社的治理過程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
(1)村委會與家族的政治關系。傣族個人脫離不了與家族的關系。雖然傣族家族內部沒有像漢族那樣森嚴的家規,普通傣族人家沒有家譜,甚至沒有姓氏,主要以家族、血緣和鄉土情感以及傳統禮儀實現家族秩序的規約,但傣族依然具有較強的家族意識。從學理上分析,家族認同及其家族的支持對一個家族成員獲取公共政治權力有一定的影響。調查中也有案例支持這一分析,如雙江縣勐滾村A組的村干部中有兩位就是來自同一家族,而其家族在全村寨約占1/3的人口,多數為村中大戶。然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57.2%的受訪者表示并非親戚較多的人在村委會選舉時更容易當選村委會主任,73.8%的受訪者表示村委會決策時并不會特意征求家族勢力較大者的意見。這組數據說明,村寨中的大戶要競選村主任憑借的并非是親戚力量,家族勢力不會直接或更多影響村委會權力的運行,至多是有一些潛在影響。這表明村民自治制度自2000年在雙江縣和孟連縣實施以來,經過14年的推行,已經能夠依法按照正常的軌道運行,鄉村家族力量的政治參與基本被納入村民自治的合法秩序化軌道。
(2)村民小組與布干、介么和佛寺的政治關系。傣族傳統社會中,村寨最高領導者為“布干”(有的地方稱“布先”或“布介”),由村民代表大會選舉德高望重的長者擔任,總管村寨內部事務,并為領主征收各種賦稅等。目前,布干一職仍然保留,但其職責已發生巨大改變,僅帶領安贊*有的地方又稱布贊,是村社里懂傣文和經文的男性長者。和召色*或稱竜色,是代表村社前去敬奉“竜色曼”的男性。傣族建寨時,把該寨背靠大山的水源林敬奉為“竜色曼”,即氏族祖先靈魂居住的神林,簡稱“竜林”,是傣族祖先崇拜的象征。負責村寨內的宗教儀式以及節日的主持活動,其原來的公共事務管理職能則由村民小組全部接手。布干僅作為一種儀式象征存在,布干在宗教祭祀等活動中的工作需要村民小組的協助和支持。
“介么”,在傣族傳統社會又被稱作“總理”,每個傣族村寨均有設立,一般由三至四人共同擔任。介么原來主要協助布干管理村寨公共事務,現在他們主要負責村寨各種民俗活動的策劃與安排,如婚喪嫁娶、賧佛等,參與村社的管理。有的村寨的集體財政由介么管理,會計僅負責填寫具體賬目,導致村民小組的活動有時也因此而受到掣肘。
云南大部分傣族聚居區的幾乎每一村寨都建有佛寺,但佛寺和佛爺又游離于村社政治生活之外。佛教全面滲透進傣族的民俗生活,如賀新房、婚喪嫁娶以及村寨里其他祭祀儀式都會請佛爺前去做法事,而村民的許多重大活動也經常在佛寺舉行,佛爺卻不參與村社的管理活動,不參加村民會議,僅作為宗教權力的象征而存在。尤其現在一些傣族村寨的佛爺是從別的村寨或縣市請過來的,甚至孟連縣有從緬甸請過來的28位大佛爺。國籍身份的限制使這些佛爺更不可能參與村社的管理活動。
3.傣族村社政治權力主體與村民的政治關系
(1)村委會與村民。村民是整個民族村社形成的基礎。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村委會作為村民選舉產生的自治的管理組織,管理全村的各項公共事務,掌握著村社的共同資源,尤其是公共權力資源,并為村社的所有村民服務。而村民作為村社的一員,就必然承擔相應的義務,受村社自治組織的管理和約束。因此,村委會與村民的關系是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然而,在傣族村社中,由于村委會與村民的直接接觸較少,往往是通過村民小組來與村民溝通,因此在提及村委會時,受訪者評價為“一般”和“沒感覺”的比例較大,占比87.6%,評價“值得敬重,為村民做了不少好事”的受訪者只占10.4%。因此,村委會有必要加強與村民的直接溝通,多為村民辦實事辦好事,以密切村委會與村民的關系。
(2)家族、布干、介么、佛寺與村民。如前文所述,傣族村社中雖然以個體家庭為基本的社會和經濟單位,但始終與家族保持密切聯系,以家族為生產生活和情感的依靠。現在的傣族村社中,布干和佛寺已經成為傣族傳統文化傳承的象征,他們掌握著本民族的文化內容以及文化傳承工具——文字,基于此,布干和佛寺里的佛爺得到全村社村民的極高尊重,尤其是老人,年輕人很多時候只是因老人的吩咐而遵從,內心將其看作是一種風俗習慣。而由于介么在傣族村社中仍參與村社的管理活動,村民們在許多場合仍需要他們出面總理事務。因此,在一定的場合,介么與村民是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其余時間與普通村民是平等身份。
(3)民族精英與村民。傣族傳統社會中,土司和村寨頭人掌握著轄區內的公共權力和經濟資源,他們既是政治精英也是經濟精英,傣族的文化精英則集中在高級別的佛爺以及懂傣文和熟悉傣族歷史文化的長者之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黨和政府重視培養民族干部,傣族村社優秀人才多被吸納到黨政部門中,成為傣族地區民族精英的主要代表。目前,勐滾村和勐混村在政府部門任職的人數不過四五人,在村內的影響力有限。“村委會決策是否會征求本村在政府機關工作的人的意見”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僅有2%的受訪者表示村委會商議要事時經常征求他們的意見,19%的受訪者表示“偶爾會”,其余79%的受訪者則認為從來沒有這樣的事情。改革開放后,傣族村社逐漸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如今還建立各種產業合作社,如勐混村的惠民蔬菜專業合作社等,同時也不斷涌現出經濟能人,成為村中的經濟精英。而這些經濟精英很多時候則成為村社政治權力的有力競爭者。在對“是否很會做生意、家庭經濟好的人更容易當選村主任”問卷調查中,就有63.4%的受訪者認為經濟實力對競選村主任有重要的影響,其中,11.8%的受訪者選擇“都是這樣”,51.6%的受訪者選擇“有時候是這樣”,36.6%的受訪者則選擇了“一點影響都沒有”。
(二)傣族村社政治體系與外部政治體系的政治關系
作為一個政治體系,民族村社不僅要處理好自身內部的各種問題和關系,還要面對其他政治體系,并與之產生政治關系。筆者主要從兩個方面考察傣族村社政治體系與外部政治體系的政治關系。
1.傣族村社政治體系與國家政治體系的政治關系
“在民族的政治體系中,國家政治體系處于首要的地位,是極為重要的民族政治形式,不僅充分地體現著民族政治的內涵,同時也體現了民族政治的功能特征。”[1](P46)為了更有效地實現政治統治和社會管理,國家政權建設始終是歷代中央政權關注的焦點,在某些歷史時期,為了不產生權力的真空或者為了更好地調配資源,國家政權直接下沉至村社這一級,但民族村社總要力圖保持自己一定的地盤和空間。這樣,國家政治體系與民族村社政治體系就會在宏觀的國家背景和村社的微觀環境下產生排斥、對抗與共處、協調互動的政治關系。但是,基于國家政權的強制性與至上性,傣族村社的村民們面對國家政權時更多的是習慣性服從,并在心理上保持對于國家政體的強烈認同。對“鄉鎮府執行中央下達的精神與本人和民族產生矛盾時采取的措施”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約40.5%的受訪者認為“既然是中央政府的精神,我們老百姓哪怕吃虧也要服從”,其理由是“人家是召,是混,我們能怎么辦”*“召”、“混”,傣語,是王、君主的意思。。而選擇“我才不管什么文件呢,只要我吃虧,我就不服從規定”的受訪者僅占18%。這也表明傣族長期以來具有一種順從的文化,這與佛教長期對傣族的濡染塑造是分不開的。
2.傣族村社政治體系與民族自治體系的政治關系
民族自治體系是多民族國家特有的政治體系,是少數民族參與國家政治的一種形式。中國歷史上少數民族曾建立過類型多樣的民族政治體系,有的還采取國家政治體系的形態,如前述傣族建立的“景龍金殿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基于我國民族發展和民族問題的實際情況,創立并施行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目前我國共建立了155個民族自治地方,其中,以傣族為主體民族建立的自治地方有西雙版納、德宏、耿馬、雙江、孟連、景谷、新平、元江、金平等州縣。民族自治政治體系是介于國家政治體系與民族村社政治體系之間的,民族村社是民族自治體系的一部分,因而受到民族自治體系的管理,形成管理與被管理的政治關系。在實際政治生活中,由于民族村社很多時候可以直接面對民族自治體系,因此對民族自治體系的要求和態度不同于對國家政治體系,他們會直接向民族自治體系表達自身的利益訴求。
三、當下傣族村社政治關系的特征
政治關系是影響政治生活的一個重要因素,民族村社政治關系的結構和發展變遷,既反映了民族村社政治權力的運行狀態,又決定著民族村社政治生活的基本格局和走勢,同時也是認識和把握當下民族地區農村基層政治生活核心特征的一個視窗。通過對云南省孟連縣和雙江縣的傣族村社政治關系的調查和分析,筆者發現,當下傣族村社政治關系具有以下特征:
1.傣族村社政治權力的微觀性和隱蔽性
福柯認為,現代權力既無處不在,又無時不有,工廠、學校、監獄、精神病院等都隱藏著權力的影子,教養、規訓、監控都是權力的表現,現代社會是座“環形敞景監控監獄”(Panoption)。權力是各種力量關系的、多形態的、流動的場域,似水瀉般滲入社會每個角落,“權力從未確定位置,它從不在某些人手中,從不像財產或財富那樣被據為己有”[5](P27)。現實的權力是微觀的、具體的、沒有中心的網絡關系,個體是權力的主體的同時又是權力的對象,而權力的目的也不只是壓抑,而是生產出各種各樣的規范效應。
以福柯權力政治學的微觀分析視角來剖析傣族鄉村社會的權力關系,傣族鄉村社會更多的是一種人情社會、熟人社會,加之佛教溫良的面紗,使傣族村社政治權力的運作細致而隱蔽。在傣族村社中,每一個政治主體都是村社公共權力的主體,同時又是其他政治主體權力運行的對象,它們行使權力和被權力影響的過程形成了一個復雜的、沒有中心的關系網絡。權力關系互動的過程中,除了制度性的規定以外,還有許多顯態或隱態的因素滲入,使得權力的顯性和丑陋的一面被溫情脈脈的親情、錯綜復雜的熟人關系、世俗生活的質樸與親切、信仰生活的神圣與良善等所隱藏、遮蔽。
2.“權力—知識”貫穿傣族村社政治關系的發展變化
在權力關系過程中,“權力與知識是直接相互連帶的,不相應地建構一種知識領域不可能有權力關系,不同時預設和建構權力關系就不會有任何知識”[5](P29)。民族村社的政治過程也呈現出權力、主體、知識三者的互動。
由于農業生產的灌溉系統管理、社會生產生活秩序維持等的需要,傳統傣族社會中部落聯盟首領或家族長逐漸發展成為高踞于民眾之上的統治者。他們運用所掌握的權力頒布各種政令和規范,甚至書寫自己以及本民族的歷史和文化。這是一個“權力創造知識”[5](P29)的過程。而后,這種由權力灌輸的知識就成為社會生活中的真理,反之又為權力提供一種正當的合法性權威。此外,隨著佛教在傣族地區的傳播,僧侶們也因掌握傣文和傣族歷史文化知識得到眾人的尊敬,從而獲得權威。通過政令的頒布、佛教文化的傳播和形塑等途徑,傣族村民的思維和行為受到一定的規約,形成固定的模式,即對佛主無比崇敬、對領主絕對服從等溫順的生活態度,甚至于成為傣族的性格特征之一。
新中國政治體制的變革,經濟社會的發展,民族政策的長期施行,教育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使傣族地區得以普及九年義務教育,接受高等教育的傣族青年也越來越多。今天,自主地接受教育、獲取知識已經由傣族貴族階層走向傣族民眾。今天傣族村社的政治主體主要是因知識而獲得權力,但擁有一定的權力也將為其獲取更高的知識創造條件。因此,權力、主體、知識的互動邏輯仍繼續影響傣族村社政治關系的發展變化。
3.傣族村社村民自治組織一定的內卷化現象
“內卷化”是美國人類學家克利弗德·吉爾茨(Clifford Geerez)在研究爪哇的水稻農業時首先提出的概念。之后杜贊奇在其1996年出版的《文化、權力與國家》一書中借用此概念提出了“國家政權的內卷化”的觀點。“國家政權內卷化是指國家機構不是靠提高舊有或新增(此處指人際或其他行政資源)機構的效益,而是靠復制或擴大舊有的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如中國舊有的贏利型經紀體制——來擴大其行政職能。”[6](P67)
村民自治施行后,農村成為“一個具有內部公共事務和外部權限邊界的公共社會”[7](P166),國家政權從制度構建上退至鄉鎮一級。然而現實政治生活中,國家政權并沒有完全退出農村社會,也不曾停止或改變它對民族村社權力的整合。現實中,國家政權主要通過協助村社經濟發展、指導村社治理工作等方式影響民族村社的政治生活。例如,雙江縣曾由縣政府撥款聯合縣農科站在勐滾村A組建立了冬季馬鈴薯科普示范基地、設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工作隊、派遣村官等措施。雖然村民自治的初衷是讓村民自我管理村社社會事務,但現實中的村民自治組織往往成為上級政府貫徹黨和國家意志、完成上級下達的行政任務的工具,促進了國家權力對民族村社的滲入和控制。黨和政府領導的原則和村民自治的原則使村民自治組織在實踐中產生一定的內在緊張,導致自治組織的行政化,云南傣族村社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