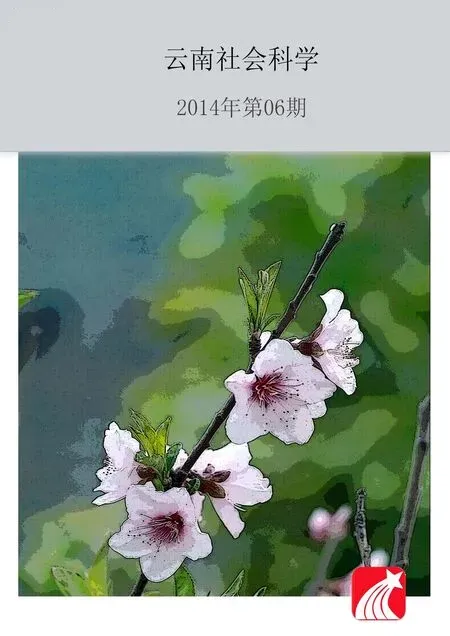美國私人非法獲取證據之證據能力研究
——以美國法為基礎的考察
李 黎
在我國的刑事訴訟程序中,隨著新《刑事訴訟法》的頒布實施,進一步明確了偵查機關負有收集證據的責任,但是,由于我國司法資源的有限性、偵查機關取證手段的欠缺,以及偵查人員在辦理具體案件中不同程度存在的惰怠情緒等原因,偵查機關的取證行為并不能達到完美的程度,所以,私人所收集的本案證據,對于司法機關查明案件事實具有查漏補缺、完善證據鏈的作用。這種現象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屢見不鮮,并且在有的案件中,私人收集的證據對于案件的定罪量刑還能夠成為關鍵性的證據。因此,不論學界贊同或者反對私人的獲取證據行為,在司法實踐中,該行為已經成為偵查機關取證行為的必要補充。當然,對于私人獲取證據的性質,還應當進行深入探討。從實踐的角度來看,在私人獲取證據的行為之中,最重要的是如果私人非法獲取證據時,該證據的證據能力問題,也就是證據的可采性問題。目前學界探討最多的是偵查機關違法取證問題,私人也有可能通過非法手段獲取證據。這個問題不可避免地涉及刑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范圍問題,即該規則的排除范圍是指僅僅排除偵查機關非法獲取的證據,還是不論證據提供主體為何人,凡是以非法方式獲取的證據都要被統統排除?本文結合我國的實際,以美國法為借鑒,探討私人非法獲取證據的證據能力問題,以供立法與司法參考。
一、我國私人非法獲取證據證明力的立法與司法現狀
在我國,對于私人非法獲取證據是否應當排除的問題,不論是立法上,還是司法實踐與學術研究中均比較混亂,亟待對此進行厘清,以此為立法和司法實踐提供參考。隨著我國刑事法治建設的逐步完善,以及新刑事訴訟法的全面實施,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已經成為我國學術界與實務界所普遍關注的問題。但是,該規則僅僅是指在庭審階段中法院排除偵查機關所非法獲取的證據,私人非法獲取證據的證據能力問題在我國的學術界與實務界并沒有受到普遍的關注,也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然而,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該問題的發生頻率較高,主要表現為該證據由私人非法獲取后,主動交給司法機關使用,或者司法機關在發現私人非法獲取的證據之后,將該證據的證據能力依法進行認定,以此作為查明案件事實的依據,在個別案件中,私人所非法獲取的證據還能夠成為查明案件事實的關鍵證據。
隨著控辯雙方對抗式訴訟模式的逐漸加強,各方當事人在訴訟程序中提供證據更加積極主動,并且《律師法》也對此做出了相應的配套性規定,例如,保障并加強辯護律師在刑事案件中的調查取證權,使得作為私人這一稱謂的多種表現主體——被害人、自訴人、律師、私家偵探等的取證行為更加常見,在這些取證行為中,自然也會存在非法獲取證據的情形。對于這些大量的非法取證行為,庭審時法官又應當如何處理呢?筆者認為,在我國司法現狀下,這些非法取證行為所導致的后果無非有兩個,一是由于相關法律在此問題上存在真空地帶,導致法官在認定與適用時存在疑慮與困惑,最終無法認定;二是法律規定的空白導致在司法實踐中,法官對于該問題的自由裁量權不受限制,對該爭議可以隨意進行認定,使得被告人的相關權益得不到保障。
當然,就這一問題,理論界至今沒有達成一致意見。部分學者認為,大多數關于證據能力的證據規則所規制的對象是偵查人員,所以,私人非法獲取的證據則不應當排除。但是,反對者認為,如果法院允許并認定了私人非法獲取的證據,那么國家公權力機關則成為違法證據產生并使用的“共犯”。依據法理,排除非法證據的重點是排除違法行為所產生的證據,因此,私人非法獲取的證據也應當適用排除規則的規制,并進行自動排除。與此同時,另一些學者認為,私人非法獲取的證據,由于其危害程度較低,并且只是零星發生,所以通常不應當排除,對于該非法行為,可納入民事與刑事制裁的軌道。但是,如果私人實施了非法拘禁或者刑訊逼供等手段來獲取證據時,則應當自動排除[1]。還有部分學者指出,私人非法獲取的證據可以分為違反憲法的非法證據、一般的非法證據,以及技術性非法證據,對這三種證據的效力應區別對待:違憲證據應當絕對排除,一般非法證據的排除應當根據法官自由裁量而定,技術性非法證據通常不應當排除[2]。
二、美國“私人取證的認同模式”的適用范圍
美國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發源地,美國法最先確認了這一規則,但并未規定該規則適用于私人的取證行為,私人根據非法行為所獲取的證據將能夠被法庭采信,所以,該模式可以叫做“私人取證的認同模式”。對此,可以用以下三個主要問題作為分析視角,來對該規則的適用范圍進行仔細審視。即:第一,除了偵查機關之外,該規則的適用主體是否包含私人在內?第二,對于偵查機關獲取證據與私人獲取證據這兩種方式而言,在非法證據的證據能力方面,是否需要進行區別對待?第三,對于私人非法獲取證據的證據效力進行判別時,是否涉及利益權衡原則?詳述如下。
1.除了偵查機關之外,該規則的適用主體是否包含私人在內?
在美國法律中,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可以追溯到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的相關規定,并且有明確的闡釋,“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由政府使用的任何違反第四修正案有關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免于受到不合理的搜查扣押方式所獲取的證據,不能被作為認定該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根據”[3]。 隨后,聯邦最高法院在一系列判決的制作中確立了各種原則,逐步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適用到憲法第5、6、14修正案所確立的反對自我歸罪權、獲得律師幫助權、以及正當法律程序權。追溯該規則的歷史,私人非法獲取的證據是否屬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主體這個問題,是聯邦最高法院在Burdeau v.McDowell案中所確立的[4]。在該案中,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本案不應當適用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私人非法獲取的證據并不應當在庭審程序中被排除。隨后,聯邦最高法院又通過一系列判例表達了自身立場[5]。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筆者認為,聯邦最高法院制定、發展、完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依據是聯邦憲法的規定,而憲法的制定前提是限制政府的行為以及公權力的運行方式,所以,只有在政府實施了某種行為時,才能產生憲法的限制與適用,也才有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存在價值。所以該規則的適用主體只有司法人員,并不包括公民私人在內。
2.對于偵查機關獲取證據與私人獲取證據這兩種方式而言,在非法證據的證據能力方面,是否需要進行區別對待?
由于私人非法獲取證據與偵查機關非法獲取證據的規制方式并不相同,所以,只要美國公民私人沒有被政府所雇傭或者出于為政府服務的目的,即使其在取證時使用了非法方式,其非法行為即便違反了刑法,也并不存在違反憲法規定的情形,其非法取證行為所獲取的證據依然具有證據能力,并不能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所以,私人的非法獲取證據行為即使違反了相關法律的規定,具有民事侵權性與刑事違法性,但該證據也不會被排除于法庭之外。因此,私人非法獲取證據的證據效力問題是被法官無條件進行適用的。
3.對于私人非法獲取證據的證據效力進行判別時,是否涉及利益權衡原則?
在美國,私人非法獲取證據的證據效力問題是被法官無條件進行適用的,并沒有利益權衡原則的存在空間。也就是說,對于私人非法獲取的證據,只要不存在政府權力的介入,都不會被法官根據利益權衡原則進行排除。其實法官在處理涉及私人非法獲取證據的證據能力問題時并沒有自由裁量權,即不論非法行為的情節、后果、以及造成的損害程度如何,該證據的證據能力都將不受限制,這樣更加有利于法官綜合所有全案證據,正確認定案件事實。然而,雖然法官對于私人非法獲取的證據進行了采信,但并不是對于該違法行為進行了認同,該行為也應當受到制裁。作為程序性制裁方式之一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雖然只能夠規制政府的非法獲取證據行為,但私人非法獲取證據行為則需要受到實體性制裁方式的規制與限定,即非法取證的私人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以及刑事責任。即使在涉及該規制方式起源的Burdeau v.McDowell案中,聯邦最高法院也指出:“根據該案具體情形,我們毫無疑問的認為,上訴人有權向非法獲取證據的那些人取得相關的救濟。”美國的司法實踐表明,雖然民事賠償責任與刑事追訴責任對于限制政府非法獲取證據的行為而言,通常是行不通的,但這些措施在應用于限制私人非法獲取證據的行為時,通常都是卓有成效的。作為制裁措施的兩種方式,實體性制裁與程序性制裁在限制不同的取證主體在非法獲取證據的行為時,都是有效的制裁方式,并發揮了積極的效果。多數美國學者認為,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雖然能達到制裁偵查人員違法行為的發生,但該規則的實施也將不可避免地帶來妨礙并限制案件真實發現的效果,在這個意義上來說,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作為程序性制裁方式的一種,其運作的成本較高。在同等情況下,當民事賠償行為與刑事追訴行為都可以達到制裁違法主體的違法行為、救濟權利受侵害者的目的時,司法實踐中就不存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空間。
三、美國立法規定“私人取證的認同模式”的法理基礎及正義性
在美國法中,圍繞私人非法獲取證據的相關規定比較明確,在立法、司法以及理論界較少進行爭議。筆者認為,造成這種狀況的深層原因主要是兩個方面:即刑事訴訟構造的差異以及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理論依據,闡釋如下。首先,美國刑事訴訟采用對抗式訴訟模式,強化當事人在舉證、質證、認證等方面的訴訟主體地位,法官被動中立,并不主動進行查明案件事實真相的活動,只是居中裁斷。因此,雙方當事人在地位、權利方面較為相等,應當對兩者進行平等對待,并且當事人主義的訴訟模式信奉“政府權力有限”與“公民權利至上”,應有之義即是對于政府權力的限制,以及公民權利的保障。與辯護方相比,由于控訴方具有天然的優勢地位,所以在立法上就會擴大辯護方的權利,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也就成為了實現控辯雙方實質平等的重要制約與保障機制。如前所述,該規則只是針對國家權力運行中政府的不當行為而設定,并不能規制私人非法獲取證據,所以這時適用該規則并不具有正當性。其次,就該規則的理論依據而言,雖然聯邦最高法院在各種場合論證了其正當性,但在Berg法院與Rainquist法院的任期內,該規則的適用范圍僅僅被限制在警察的非法取證行為上。雖然美國相關法律也建立了刑事追訴機制、內部紀律懲戒、民事侵權訴訟等各種實體性制裁方式,但司法實踐一再證明,對于遏制警察違法取證來說,讓犯法的警察承擔實體性制裁責任并不具有實質性效力,所以只有適用該規則并消除警察違法取證的動機才是治本之道。就私人非法獲取證據而言,私人權利的行使不具有公權力的行使身份,非法取證通常具有特殊原因,基本都是在通過正常途徑無法取證,或者證據不及時獲取就有滅失之可能的情況下不得已而為之,不具有反復實施的可能,所以不需要通過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來嚇阻違法行為。由此可見,對于非法獲取證據的私人而言,民事侵權訴訟與刑事追訴機制完全能夠防止并制裁私人非法獲取證據行為。為什么會這樣呢?其目的就是為了滿足發現案件實質真實的需要。其實,對于發現案件事實而言,最大的障礙就是排除具有相關性的證據。十九世紀末,英國著名法學家邊沁指出,證據是正義的基石,排除證據就等于排除正義[6]。由此可見,除非絕對必要,否則不能夠排除相關證據。如果排除了私人非法獲取的證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就會顯得過于嚴苛,也妨礙了案件事實真相的發現。在私人非法獲取證據方面,程序正義讓位于實體公正,這也是法律的價值考量與利益權衡的結局。另外,私人非法獲取證據可采性的自動適用,要求法官在處理此類問題時不具有行使自由裁量權的余地。這樣的制度構建具有兩大優勢:一是避免法官運用自由裁量權限時,所產生的案件判決結果的不確定性;二是避免了法官在處理相類似案件時,會同案同判,不會出現相同情形不同判罰的情況,某種程度而言,既體現了司法權威,又維護和保障了司法公信力。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美國法所秉持的“私人取證的認同模式”也不是完美無缺的,存在著明顯的瑕疵,尤其備受學者詬病的是,該模式如何維護司法正義?對此,筆者認為,該模式完全能夠實現維護司法正義的立法目的,述之如下。
1.取證主體獲取證據的方式違法,是否就應當排除該證據?
根據取證主體的不同,刑事訴訟中的取證主體可以分為私人主體與國家主體兩類。私人在取證時不具有國家公權力的背景,與國家相關工作人員相比,所造成的損害后果相對較為有限。私人違法獲取證據時也不會像偵查人員一樣,對公民的人身安全、財產安全等構成嚴重侵害。私人獲取證據的行為往往具有一次性、隨機性與偶然性,并不具有重復性,也沒有必要以預防再犯為目的,對私人的違法行為進行懲罰。另外,我國目前的司法實踐一再證明,對于國家機關的程序性違法行為而言,現行法律所規定的實體性制裁機制在適用范圍上非常有限,即使相關人員實施了違法行為,其懲處效果也不盡人意,以至于不能讓受害者得到安慰與補償[7]。但對于實施非法獲取證據的私人而言,正當權利受到非法取證行為侵害的人都可以根據民事法或者刑事法的相關規定,要求國家對其權利進行保障。根據《刑法》的規定,當行為人通過暴力行為獲取證據,或者通過對于被搜查人實施非法搜查等各種行為時,行為人將會根據其違法程度的輕重,受到罪責追究。根據相關民事法律的規定,當私人非法獲取證據的行為侵害到他人的合法權益時,權益受到侵害的人可以向法院提起如民事侵權損害賠償之訴的救濟。由此可見,不論是追究相關侵權人的民事責任,還是追究相關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責任,對于私人的責任追究都將更加便利。另外,如果被排除的私人非法獲取的證據是辦案中的關鍵證據時,會導致事實無法查清以至于無法定案。
2.肯定私人非法獲取證據的證據能力時,是否就表示對于該違法行為的認定?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只是針對國家權力運行中政府的不當行為而設定,并不能規制私人非法獲取證據,所以這時適用該規則并不具有正當性。但對于實施非法獲取證據的私人而言,正當權利受到非法取證行為侵害的人都可以根據民事法或者刑事法的相關規定,要求國家對其權利進行保障,并且在制裁私人非法取證方面更為有效。所以,針對私人非法獲取證據行為的處罰,應當是實體性制裁方式的處罰。比如,我國刑法規定,行為人非法搜查他人身體以及住宅的,構成非法搜查罪;行為人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構成非法侵入住宅罪。這些規定都是為了制裁私人的非法獲取證據行為,也都表明了立法對這類行為的明確否定。自從人類進入近代社會以來,當公民的正當權利受到侵害時,以暴力、血腥、野蠻為標簽的自力救濟的方式已經逐漸被社會所淘汰,而由國家公訴機關所主導的刑事追訴,逐漸成為當公民的正當權利受到侵害時,公力救濟的主要途徑。筆者認為,當司法機關肯定私人非法獲取證據的證據能力時,并不表示對于該違法行為的認定。當法庭采信該非法證據時,應當視行為人違法程度的輕重,分別追究其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
3.法官對于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與不利于被告人的證據是否應當做出相同認定?
在美國的司法實踐中,私人非法獲取的證據是否應予排除?學界與實務界主張不予以排除的理由都是“不能讓案件真實無法查明,進而致使有罪者逃脫應有的制裁”。但經過仔細分析可以發現,此處所謂的證據是指不利于被告人的證據。我們知道,特定案件中的證據都分為兩種: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與不利于被告人的證據。那么,如果該證據屬于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呢?是否應當像對待不利于被告人的證據一樣,做出相同的認定?其實,這樣的情形并不只存在于私人非法獲取證據這一種情形之中,在偵查人員通過非法手段獲取證據時,也會產生這樣的疑慮。對于該情況,西方各主要法治國家都進行過激烈爭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德國學界的主張,按照德國學界的公認劃分方式,將非法證據所導致的證據禁止劃分為證據取得禁止與證據使用禁止,與此處有關的是證據使用禁止。針對這種情況,一部分學者認為,證據使用禁止僅僅適用于不利于被告人的證據,而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則不應當禁止使用。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不應當將非法證據進一步區分為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與不利于被告人的證據,只要屬于證據使用禁止的適用范圍之內,都應當統一適用,對其做出效力相同的認定[8]。由此可見,這種劃分的關鍵就是對于將無辜之人錯判有罪與使有罪之人逃脫法網這兩種情形,孰重孰輕,如何取舍的問題。筆者認為,根據當代西方各主要法治國家的司法理念可見,將無辜之人錯判有罪,比使有罪之人逃脫法網,就所導致的后果而言,要嚴重得多。在錯案中,所謂的程序正義是沒有意義的,非但如此,與程序正義相比較,錯案中的實體正義將更為重要。這種思想不但當代如此,自古以來就流傳著類似的司法審判理念,如在民間就廣為流傳類似于“寧可錯放,但絕不可錯殺”等側重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合法權益的說法,正是這種相對樸素的司法價值理念,構成了“遇到疑義時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的民眾基礎與信仰。所以,根據上述分析,不論是在當代法制先進國家還是在我國目前的司法現實之下,面對取證違法性相同的非法證據時,不利于被告人的證據的認定標準應當比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更為寬松。因此,當法官在具體案件中面臨對于非法獲取證據的證據能力進行認定時,首先應當將該證據做出是否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的劃分。這時可以借鑒美國法中的“私人取證的認同模式”,即只要法官認定該證據屬于無罪證據、罪輕證據等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時,該證據就可以被法官認定為定案的根據之一。當該證據被法官認定為有罪證據、罪重證據等不利于被告人的證據時,可以由法官根據利益衡量原則的認定標準,對該非法證據所侵犯的社會利益以及該非法證據的證明價值之間進行權衡,也就是說,將該證據獲取時的非法手段所侵害的法益與國家的追訴利益進行權衡,進而認定該證據是否應當予以排除。經過認定,當該非法證據所侵犯的社會利益大于該非法證據的證明價值時,非法獲取的證據應當予以排除,否則就不應當進行排除。通常來說,私人根據收買證人、盜取證據、誘騙相關知情人、對相關知情人的言談記錄進行竊聽、竊錄的等相對緩和的手段所獲取證據的各種情形時,應當承認這些證據具備證據能力;如果私人根據暴力、脅迫、強制等相對激烈的手段所獲取證據的各種情形時,因為公民的合法權益遭受到私人非法取證行為的過度侵犯,所以該非法證據應當被排除于法庭之外,不得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
四、美國“私人取證的認同模式”對我國立法的啟示
美國“私人取證的認同模式”是庭審對抗主義的產物,保護私權及重視抗辯雙方的平衡是其立法的法理基礎,能夠實現維護司法正義的立法目的,對于我國的立法與司法實踐均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隨著我國《兩個證據規定》與新《刑事訴訟法》的頒布實施,以及當事人人權保障意識的大幅提升和舉證能力的顯著增強。對于查明案件事實而言,作為偵查機關調查取證的有益補充,私人收集獲取證據的方式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這些證據不但具有查漏補缺、完善特定案件中證據鏈的作用,并且在部分案件中對于案件的正確定性與定罪量刑還具有重要價值。當然,在司法實踐中,基于特定案件中證據的稀缺性,即使私人獲取證據方式違法,也不應當排除該證據,并且還應該肯定該證據的證據能力。與此同時,對于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即使取證方式違法,只要查證屬實,就應當作為定罪量刑的根據。當然,針對私人取證行為違法性的不同程度,還可以判處其承擔相應的民事侵權責任與刑事責任。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達到刑事訴訟中控制犯罪與保障人權的根本目的,最終實現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的有機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