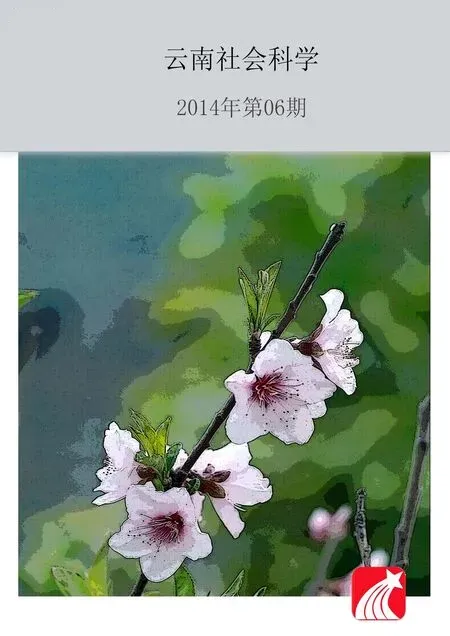論《莊子》與早期禪宗在演變理路上的契合性
周黃琴
在自述宗派的傳承中,禪宗不僅以世尊的拈花一笑來論證其傳承的合法性,而且還建構了歷史久遠的宗派傳承譜系。然不容忽視的事實是,禪宗在中國化的歷程中,卻不斷卸去原始佛教的色彩,而與中國傳統思想交織在一起,特別是與《莊子》的關系,一直成為歷代儒者批駁之點,以致史上存有“莊禪”之說。如早在唐宋時期,傅奕與朱熹就曾認為禪宗乃是早期高僧剽竊老莊思想之產物。而本文試圖對《莊子》與早期禪宗在演變理路上的契合性作一定的探究,以揭示其內在的關聯性。
一、祛魅化
無論從馬克斯·韋伯對宗教的分析來看,還是從雅斯貝爾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所指而言,其皆展示出了人類文明在發展道路上的祛魅化走向,即不斷剝離神秘,走向理性。以此觀念去觀照《莊子》與禪宗思想時,其祛魅化色彩亦非常清晰。雖然相比于上古文化而言,整個先秦文化就具有強烈的祛魅化傾向,如莊子對中國傳統中的一些神秘觀念作了進一步的祛魅化。首先,對于傳統的神秘之天與鬼神之說,莊子在承繼老子思想的基礎上,認為“道”不僅誕生萬物,而且“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道”本論思想的觀照下,傳統之“天”與鬼神之說的神秘面紗被剝離掉,并被還原到自然性上,與萬物等同。此舉無疑還在某種程度上消解了祭祀與卜筮的價值與神秘性。
盡管《莊子》篇中充滿了大量的神話,但此時的“神話則變成語言的材料,成為用以表達與原意極為不同的含義的寓言”[1](P9)。確切地說,《莊子》借用了神話的形式,來展示其內在深刻的哲理思想。因而,任繼愈認為,《大宗師》中“神鬼神帝,生天生地”的思想,是對“古代宗教迷信思想的挑戰”[2](P171)。侯外廬亦指出,莊子“更托于古帝,否定了西周以來原始的宗教神,批判了孔、墨的理論的宗教神”[2](P142)。而在張松輝先生看來,莊子“把道置于神鬼之先”,無疑“極大消弱了神鬼的地位”,對古代神學構成了“一次沉重的打擊”[3](P71)。
其次,在生死問題上,莊子立足于宇宙大自然的層面,重新審視生死,以破除傳統上的生死觀。據資料記載,仰韶文化的葬具上存有“孔”,齊家文化的死者周邊撒有赤紅色鐵礦粉,這些現象無不折射出早在上古時代人們就認為人的靈魂具有永恒性,以致形成了一系列的占卜、祭祀等神秘活動。而且,在歷史的潮流中,后人又不斷給“死”后世界累加了一些陰暗與殘酷的可怕色彩,致使世人形成了強烈的“悅生惡死”之觀念。
但在莊子看來,“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4](P348)。即是說,人的生死就是一個氣聚、氣散的自然過程,期間沒有任何神秘性。而且,人的肉身不過是一種外在形式而已,是宇宙大道假借外在質料的一個瞬間展現而已,即“生者,假借也”,而“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至樂》)。故一切短暫的假借,就如同“塵垢”一樣不值得留戀,其最終必然都要回歸于“道”中,就像一個游玩的孩子該回家一樣自然。所以,當莊子從宇宙大化的角度去看待生死時,人的死亡就不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而是一種拋棄“塵垢”而回到本真狀態的快樂。
莊子消解了對死的恐懼。在《至樂》篇,莊子以空髑髏之夢的寓言來展現死后世界的美好性,即“死,無君于上,無臣于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這不僅消解了人生中最大的困惑,即對死的恐懼,而且還使人重新認識自身與定位周邊的一切。
而在祛魅化方面,禪宗亦有清晰的表現。首先,從高僧們的神通術方面來看,就有一個不斷祛魅化的過程。慧皎的《高僧傳》,素有反空疏、務求信實之特征,而被譽“永為龜鏡”。然其中卻記載著大量的神通術,甚至卷九與卷十都是以神異性為主題而編寫的。然令人驚異的是,此后為禪宗宗派的法統性所建構的《祖堂集》,卻把以往僧傳中的神異性逐漸剝離掉,取而代之的是意蘊深遠的偈。如文中在描寫弘忍大師夜送慧能過江時,并非像《高僧傳》所載的耆域者式的神通過江,而是“自把櫓”。本來,《祖堂集》就是為禪宗的合法性尋找依據,故出于護宗之考慮,其理應更會通過有意塑造各祖師的神異術,來強化或抬高禪宗。然而,《祖堂集》并沒有用神通性來強化禪宗的價值,反而流露出了強烈的祛魅化傾向。
其次,從歷代禪宗所奉行的經典來看,亦有一定程度上的祛魅化傾向。眾所周知,禪宗所奉行的經典并不是一成不變,而是隨著歷史的變遷不斷發生著演化,如《楞伽經》《大乘起信論》《金剛經》《壇經》等。據《續高僧傳》的記載,達摩曾以四卷本的《楞伽經》授予慧可,并云:“我觀漢地,惟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得度世。”[5](P552)然而,從宏觀上看,《楞伽經》卻有著眾多的關于佛力的神奇性描述[6](P2)。然而,《楞伽經》中的神話性的描述方式,并沒有在日后禪宗所信奉的《起信論》《金剛經》《壇經》中得以再現。雖然,《起信論》是“《楞伽》思想更加明朗和具體化的發展”[7](P231)。然而,《起信論》不僅剝離掉了《楞伽經》里的大量神奇性的語言,而代之以理性的義理闡述,甚至在“勸修利益分”中,亦沒有《楞伽經》原有所彰顯的修法開悟的奇異狀態,而僅為理性地加以勸示。對于《壇經》來說,其不僅破除了修行的神通性,而且還撕開了成佛的神秘帷幕,把佛凡的距離拉到了咫尺之間,即“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8](P155)。
最后,從因果報應的思想演變來看,禪宗亦存有祛魅化色彩。印度佛教素有“業報說”,認為人的生活狀態與業力有關,惡有惡報,善有善報。此理論在中國早期佛教的傳播階段中亦得到了廣泛的流傳,如在《弘明集》中就有大量的學人支持報應說與神不滅論。然而,不論因果報應說,還是靈魂不滅思想,卻在日后禪宗的思想中被逐步剝離出去。實際上,從達摩對梁武帝企圖通過造寺、寫經、度僧等來建立功德之舉的否定來看,就蘊含了對神秘報應的祛魅,而把修行拉向了人內在的心靈世界。而到慧能時代,這種面向更為突出。據《壇經》的記載,“慧能不僅反對把‘造寺度僧’、‘布施設齋’之行等同于‘功德’,而且還認為佛教‘六道輪回’中的‘地獄’與‘畜生’亦沒有什么神秘與可怕之處,其實它們就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即‘貪嗔是地獄,愚癡是畜生。’因而,原始佛教中的因果報應思想在《壇經》中已經完全褪去了其原有的意蘊與色彩,而直接化為人的不同心境。”[9](P153)
盡管《莊子》與禪宗都存在著祛魅化傾向,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們之間一定存有必然的聯系,或許這是人類理性思維發展的必然結果。然而,有意味的是,它們在祛魅化之后,都沒有像西方思想那樣,朝著理性化方向發展,最終卻走向了反知性思維,并尋求一種神秘的感悟。因而,《莊子》與禪宗在祛魅化的背后目的上存有一致性,即祛魅化并不是為了凸顯理性,而是為了更大的“破”,來掃除前人所構建的障礙,以求新的發展。確切點說,《莊子》與禪宗都是通過“破”來求得出路。
二、反智主義
當現代西方哲學把研究方向轉向對工具理性反思的角度上,其后卻在西方史上產生了巨大效應。然而,事實上,相對于二千多年前中國傳統中的反智思想來說,那是一種多么滯后的反思思潮。其實,對于工具理性的反思,中國傳統中的老莊早就意識到這個問題,并從多個角度加以揭露,但由于言簡意賅,沒有構成一個體系,而顯得非常的孤寂,并不被人理解,乃至出現后人的歪曲。然有意味的是,老莊對知性的懷疑精神并沒有在中國傳統思想中產生較大的反應,而巧合的是,卻在近千年后的禪宗思想里重現光輝。
首先,對語言文字的訶毀。《老子》開篇就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其實,此句之本意不僅展示了“道”的永恒性,而且也揭示了語言的有限性。實質上,此句話已經向人展現了一個不可調和的無限與有限的矛盾。然而,老子這種格言式的表述,難以使人從語言缺陷層面上加以理解,而是把側重點放在對“道”的感悟上。
莊子不僅承繼了此思想,而且還對語言文字之缺陷做了深入揭露,即“其所言者特未定也”與“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因而,若從視、聽的角度來理解語言文字的話,則只能獲得形、色、名、聲,而非意。甚至在《天道》篇中,莊子還通過匠人嘲笑桓公讀書之舉來佐證以上之論點。事實上,《莊子》中不僅發展了老子的“行不言之教”思想,而且在展示該思想時亦盡量避免語言文字對意的束縛,故而文中采用了寓言、重言、卮言等多種不同的表達方式,來打破語言文字之束縛。
然對于禪宗“不立文字”之教旨,教界雖一直追溯到佛陀的捏花一笑上,以求尋得法統傳承上的支撐。可令人質疑的是,禪宗在為自己的合法性尋找理論依據的過程中,是否存在著有意的構想呢?據資料記載,湯用彤先生早在《隋唐佛教史稿》中就曾質疑禪宗“秘密相傳,不立文字”思想與曇林所記的“入道四行”,以及達摩以《楞伽經》授慧可之事存有相悖之處。[10](P187)而且,雖然《法沖傳》亦認為從達摩一直到玉法師都是“口說玄理,不出文字”。然其后卻曰:“可師后,善老師(出抄四卷),豐禪師(出疏五卷),明禪師(出疏五卷),胡明師(出疏五卷)。”[11](P24)同時,從資料的記載來看,早期佛教在譯經過程中還存在著“會意”與執守文本的激烈沖突。只是“會意”者在當時佛教界處于弱勢之方,從而遭到“守文者”之攻擊,并被視為異端而得不到大范圍的推廣。這種現象恰好可以佐證,當時佛經中并沒有明顯的會意或悟的價值取向,否則的話,竺道生就不會遭到如此大的打擊。或許早期佛教的會意路向與執守經教的矛盾,為日后禪宗在語言文字上的革新埋下了種子。
在龔雋先生看來,雖然不能“否認印度佛教傳統中具有‘無概念性的’和‘不可言述的’般若智”,可“分別智”在“印度禪”中有比較充分的發展空間,如《俱舍論》《瑜伽師地論》《阿毗達摩俱舍釋論》《阿毗達摩俱舍論本頌》都明確地提到“得分別慧”,但“在中國禪的發展中,分別智并沒有獲得相應的空間,而消解于‘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主流話語之內,則也是應當承認的事實。而這一反智主義的傳統,并非發源于學者們樂以道之的7世紀末到8世紀初中國禪的分化,特別是弘忍門下的倡導,而是有著更為悠遠的歷史。”然而,當龔雋先生作進一步分析的時候,他卻認為“從道安的用語”和“意義分析”來看,道安“受到道家關于言意論辯的深刻影響”。而且“ 6至7世紀中國禪學的演化,又鮮明地表示出不拘文字經教而崇尚玄遠虛寂的一流”[7](P66~67)。
而且,即使從禪宗的早期經典內容來看,《楞伽經》亦沒有完全排斥語言文字,反而將其視為修行的一個重要手段,只是擔心后人“墮于文字”,執著文字,故而倡導脫離文字,悟得佛法。然《壇經》盡管提到不同根器之人應有不同之方便法門,但其更為凸顯上根之人的修行,即“心開悟解”、“不假文字”。甚至為了凸顯這一思想,《壇經》《別傳》以及日后禪宗的資料都極力強化慧能之不識字但卻能悟得佛法之事件。
其次,《莊子》與禪宗皆有破除原有觀念系統與經教之意向。據《莊子》的記載,莊子不僅時而對孔子進行批判,還對儒學所彰顯的觀念與人類原來所建構的一切觀念作了質疑與批判。在莊子看來,人類的認知是有著自身類種所限定的界限,因而在人的認知區域之外還存在著廣闊的人類所無法認知的境域,致使“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圣人論而不議”(《齊物論》)。確切點說,“六合之外”是人無法認知的領域,故只能“存而不論”,保持沉默。但“六合之內”雖為人的生活世界,但其中之論又皆是相對的,故而只能“論而不議”。
由此可見,莊子窺視到了人的觀念世界與世界的本來狀態所存在的矛盾,即世界瞬息萬變,但又息息相通,圓融無礙,而人卻在各自的觀念世界里自限一隅,然又一廂情愿地把這一隅想象為世界的整體或唯一正確的認知,并以之作為萬世的標準。而莊子想通過“破”的方式來消解人為所設定的各種觀念障礙,以達世界的融通之境。
對于禪宗來說,破除經教的束縛,有著一個漫長的演化過程。實際上,在佛教初傳時期,國人就對佛典的繁雜性表現出了厭煩與精簡之意向,即“今佛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非一人力所能堪也,仆以為煩而不要矣。……佛經眾多,欲得其要,而棄其余。直說其實,而除其華”[12](P18~20)。
從禪宗的演變史來看,不僅達摩放棄十卷本的《楞伽經》,而把四卷本的《楞伽經》傳給慧可,而且據呂澂先生所考證,慧可甚至用“四卷本《楞伽經》”來對抗當時的“十卷本《楞伽經》”[13](P306)。同時,即使在傳授《楞伽經》的過程中,慧可仍感受到了名相化走向的危險境地,即“此(楞伽)經四世之后,變成名相,一何可悲”,以致他在傳教中采取“行無軌跡”、“動無彰記”的傳授方式來消解各種印痕與束縛。期間無疑蘊含了強烈的破除經教繁瑣性之趨向。
到慧能時代,這種意向更為凸顯,其不僅表現在《壇經》中有大量的理論論說,而且還有自身經歷上的佐證。在他看來,“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求善知識,指示方見。若自悟者,不假外求”[8](P164)。同時,《壇經》還配有慧能自身“悟得佛道”的實例,來強化自悟成佛的思想。這個實例不僅徹底打破了世人的固有觀念,而且還對經教的權威性產生了巨大沖擊與破壞,即既然一個目不識丁之人,能勝過一個“博學多聞”的“教授師”,提前悟得佛法,傳得衣缽,那么成佛不是靠讀經,而是內心上的感悟。這與其說是一種宗教上的革新,還不如說是佛教史上的一種破“繁”趨簡意向的最后歸宿。
然而,在實際的修行中,慧能還沒有徹底拋棄一切經教與善知識。如他認為不能自悟者還需借助經教,“開導見性”,甚至到神會時仍強調“般若波羅蜜”的經教價值。直到洪州宗、石頭宗時,則把破經教之意向全面落實到了實踐的修行層面。[14](P6)南宗禪為了破除執著,應變無窮,不僅運用了大量的隨機公案,而且還以棒喝、搊鼻、打人等方式,以期使人頓悟。
最后,破除繁雜的儀式規范與戒律。就《莊子》而言,從其所記載的魯哀公與莊子爭辯魯國儒者多少的故事來看,一方面說明了后儒內在本質的喪失和外在形式的走向;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內在本質與外在形式的分離性。正是基于此因,莊子在文中不僅批判儒學背棄人性,賣弄名聲,而且還揭露出了儒學規范化的走向所導致人性的迷失與失真,甚至儒學所建構的仁義道德規范反而演化為“大盜”之工具。更為可怕的是,統治者只知執守各種規范,以致本末混淆,更不知“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天運》),從而導致把世人演化為規范的奴隸與工具。致而,為了保存人的本真狀態,莊子不僅對各種破壞本性之舉進行了大肆批判,而且還反對各種人為設定的外在儀式,以致對儒家所倡導的喪禮都敢直接進行蔑視與批判。
可對佛教來說,戒律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佛陀所云:“有戒則有慧,有慧則有戒;戒能凈慧,慧能凈戒。”[15](P265)因此,禪宗思想的演變無疑對戒律構成了巨大沖擊。早在唐朝,作為律師的道宣就對達摩禪有所批評,即達摩禪“誦語難窮,歷精蓋少”,存有“遣蕩之志”,而慧可是“情事無寄,謂是魔語”[16](P2060)。其實,早期南方禪師也并沒有完全拋棄戒律。如達摩在修行方面,仍注重“二入四行”,并九年面壁修行禪定。慧可不僅在永和寺受戒,而且為求佛法“自斷左臂”,后“兼奉頭陀”。即使到道信時代,其仍常勸門人,“努力勤坐”,并傳“菩薩戒法一本”。到弘忍時期,則法門大啟,不擇根機,“齊速念佛名,令凈心”。乃至東山門下的北宗、凈眾宗、宣什宗皆把“念佛凈心”作為最通用的禪法。
然發展到慧能及其弟子時代,則不僅反對枯坐,而且還對終日口念佛名之修行提出了質疑。在他們看來,“坐”不是“枯坐”,也不是“著心”或“著凈”,而是“無障無礙,外于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而“禪”為“內外自性不動”。故修行只需“心行”,“不在口念”。也就是說,不論“坐禪”還是“禪定”等各種修行,不是一種外在儀式規定下的簡單遵循之行,而是只要能達到其內質上的“外離相”、“內不亂”的要求,其具體用什么外在方式都是無所謂的。實質上,這種思想無疑無形地消解了佛教原有的清規戒律。
上述觀念被無住、道一、石頭等門下,淋淋盡致地展現出來。大珠慧海禪師對律師法明曰:“經論是紙墨文字,紙墨文字者,俱是空寂,于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非是空。座主執滯教體,豈不落空?”“法身無象”,“應物現形”,“是以解道者,行住坐臥,無非是道。悟法者,縱橫自在,無非是法。”所以,當法明問“如何是佛”?大師卻曰:“清譚對面,非佛而誰?”[17](P155~157)而青原系的德山宣鑒禪師本是“精究律藏”,后悟得佛法,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焚之”。他認為“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瘡疣紙。四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古塚鬼,自救不了”,并在日后開示弟子的教行中有著大量的棒喝與呵佛罵祖之行。如曰:“這里無祖無佛,達摩是老臊胡,釋迦老子是乾屎橛,文殊普賢是擔屎漢。”[18](P372~374)更為甚者,馬祖的弟子丹霞,燒佛像來取暖。由此可見,南宗后系把慧能的“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的思想發展到了極致,并用大量看似荒誕的“機緣問答”與棍棒交加的極為粗俗之肢體語言來啟示弟子。
可見,破一直貫穿于整個禪宗的發展過程之中。而這種“旋立旋破”的方式又恰好為禪師們打破一切人為設定的障礙,達到“無念”、“無住”、“無相”的解脫狀態提供了出路。因而,《莊子》與禪宗的反智主義背后實質上又都蘊含了一種對靈魂出路的探尋。
三、世間解脫
眾所周知,無論是佛教,還是莊子,都不僅對人的生存境遇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而且還積極探尋出路,以求解脫。
一提到《莊子》,或許我們腦中浮現更多的是大鵬高飛的自由情狀與那些無所不能的“神人”、“真人”和“至人”,以及神秘莫測的“道”。對于這些畫面,人們也許更多的是從文學的主觀面向去理解,甚至認為莊子以徹底拋棄人世間之方式,來建構神秘的逍遙世界。然實際上,《莊子》中的大鵬高飛不僅蘊含了一種“化”,即由鯤變為鵬,而且還預示著人要獲得自由的話,就必然要破除舊視域,并通過自我的提升或高飛來重新獲得全新的“道”之視域。即借助于超越之眼來徹底摧毀或消解原有的束縛,從而在現世中就可獲得解脫。所以,《莊子》中并沒有建構出一個脫離人世間的純粹的彼岸世界,即使對于本源之“道”而言,其雖不為感性、理性所能把握與認識,具有超時空性,但它亦不是高懸的,而是“無乎逃物”,即蘊含在宇宙萬物之中,甚至在極為骯臟的屎溺中都存在。確切點說,莊子恰是通過超時空的永恒本體之“道”的建構,不僅可以反思與批判人類社會的迷失走向,而且還為人類建造出了“生命之根”,并破除掉人為后天所建構的“成心”,即偏執之心,從而在現實世界中就能獲得與“道”同在的逍遙之境。
對于佛教而言,為了擺脫人世間的眾苦,佛陀力圖通過“八正道”等一系列的修行方式,以達快樂的涅槃世界。對于涅槃,盡管學界存有不同的理解,但毫無疑問的是,在原始佛教的思想里,涅槃世界乃是對現實世界的否定后所構設的理想世界。然有意思的是,禪宗在歷史的流變中,卻把神圣的涅槃世界拉回到了人世間。如據《壇經》的記載,由于“本性是佛”,因而不僅“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而且佛與眾生或凡夫之別亦在悟迷之間,即“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確切點說,在《壇經》里,佛的神秘面紗已被徹底卸去,致而成佛亦非在遙遠的未來與高懸的彼岸世界,而是就在當下的迷悟之間,所以彼岸與此岸亦非遙不可及,而是在轉瞬之間,即“著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即名為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通流,即名為彼岸,故號波羅密”[8](P155)。換言之,人雖生活在人世間,但只要能“離境無生滅,如水常通流”,就能達到涅槃的境界。所以,當韋刺史詢問慧能念佛能否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時,慧能則曰:“迷人念佛求生于彼;悟人自凈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凈即佛土凈。使君東方人,但心凈即無罪。雖西方人,心不凈亦有愆。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凈土,愿東愿西;悟人在處一般。所以佛言:隨所住處恒安樂。”[8](P176)
在日后南宗各支派的思想中,世間解脫思想亦得到了進一步的實施與發展。如大珠慧海禪師認為和尚用功修行就在于“饑來吃飯,困來即眠”的日常行為之中。而希運禪師則云:“終日不離一切事,不被諸境惑,方名‘自在人’。”[14](P54)因而,中國的禪宗,“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向思想方面的延伸,不是思想的體系,而是滲入到日常生活世界個體化的內在生命中”[7](P37)。
四、余 論
《莊子》思想與禪宗內在演變理路上所存有的契合性到底是學術上的“家族類似性”現象,還是存有一定程度上的承繼性,亦或是兩者兼而有之呢?盡管對于《莊子》與禪宗的關系,歷代都有不同的論說。如早在唐代,傅奕就認為佛教“模寫莊老玄言”。而僧界的吉藏、澄觀、宗密等高僧則認為老莊思想在深度上不能與佛教相媲美,特別是老莊在本體論方面的論說,若以佛教思想來觀照的話,其乃犯了“邪因”與“無因”之錯誤。確切點說,唐朝儒者與高僧都執于一方,以維護各自之目的。
然有意思的是,吉藏、釋法琳、澄觀、宗密等高僧的作品中還存在著援引《莊子》思想來闡釋佛理之現象。即使到了宋朝,高僧們的作品中仍存有大量援引《莊子》思想之現象。而宋代的儒者們亦沒有停止從模寫莊老的面向來批佛。如朱熹不僅在《雜學辨》《四書或問》等眾多文中存有批佛之舉,而且還撰寫了一篇《釋氏》之文專門對佛教進行批判。在《釋氏》篇,朱熹甚至把佛教竊取莊老思想之舉作為批判佛教的重要支點,并認為禪宗皆“自莊老來”。林希逸在《莊子口義·發題》中認為“《大藏經》五百四十函”皆是從《莊子》中“抽繹”而出。
即使到近現代,學界與僧界仍有兩派不同的聲音,即一為禪宗是佛陀精神的回歸,二禪宗乃為莊老思想的承繼之物。如鈴木大拙認為禪宗雖然“拋去了佛教一切歷史的和教理的外衣”,但卻“把握了使人產生創造力的佛陀根本精神”[19](P33)。印順則認為,雖然慧能時期的禪宗仍“保持了印度如來禪的特性”,但發展到“牛頭禪”時,則在吸取老莊思想的基礎上使“印度禪蛻變為中國禪宗——中華禪”,更為甚者,日后遺則的“佛窟學”則無論是形式還是內容都“更與玄學相融合”。[11](P103~323)在蕭萐父看來,如若說慧能通過心境的清凈而從達摩禪中突破出來,那“后來的洪州禪、臨濟禪注入了莊子的‘逍遙游’精神,主要在于追求幻想中的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理想人格”[14](前言P21)。崔大華則指出,構成禪宗“頓悟本心”的兩大“基本的方法論因素”,即“整體直觀”與“實踐體驗”,其“觀念背景”與“觀念淵源”皆“存在于莊子思想中”[20](P536~537)。
由上觀之,學界的主流觀念認為禪宗在演變的過程中由于承繼了《莊子》某些思想,以致出現一定學理上的相似性。但不得不承認,禪宗的演變理路與《莊子》思想的契合性,并不是禪宗對《莊子》思想的簡單模寫,而是佛教在中國化的過程中為了破解各種生存困境,并為了更好地符合中國人之性情所做的一些演變。如為何禪宗會走向祛魅化與世間解脫的道路?其不僅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趨勢,而且還是中國文化理性化的產物與中國人的性情使然。從中國傳統儒、道家的修行面向來看,其既側重于人內在的心靈世界,而不是外在的神秘世界,而且對于修行的出路與結果,亦沒有寄托在遙遠的來世或神秘境地,而是把修行安放在世間日常當下的所有生活中,并期以獲得快樂,致而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就有一些文人對佛教中的神不滅論與神秘的因果報應持批判之論。所以,為了能在中國扎根下來,其必然要針對中國文化的主流而做出一些演變,即卸去原始佛教所建構的神秘帷幕而轉向人的心性與世間解脫,以求更好地迎合中國人之需求。
同時,從反智主義面向來看,盡管禪宗把“不立文字”之旨追溯到了佛陀的拈花一笑上,但實際上,在佛教初傳中國時,既出現了文人大肆批判佛經繁瑣性之現象,而且“執守”與“意會”取向的矛盾亦得到了凸顯。更為甚者,禪宗在傳播的過程中就被名相化所困。破除該問題乃是一大重要問題。然有意思的是,自魏晉以來,老莊的反智主義思想恰好為禪宗破解名相化困境提供了重要的催化作用。[21](P196)
而且,從深層次上看,不論是祛魅化、反智主義,還是世間解脫之追尋,其實《莊子》與禪宗演變理路上的契合性折射出了一個重要哲理,即無論對一個學派或宗派而言,還是對個人與國家來說,若要得以發展的話,就必然要一直貫穿著破與立,即破解阻礙發展的一切束縛,并因時制宜地立些新內容。確切點說,只有破繭才能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