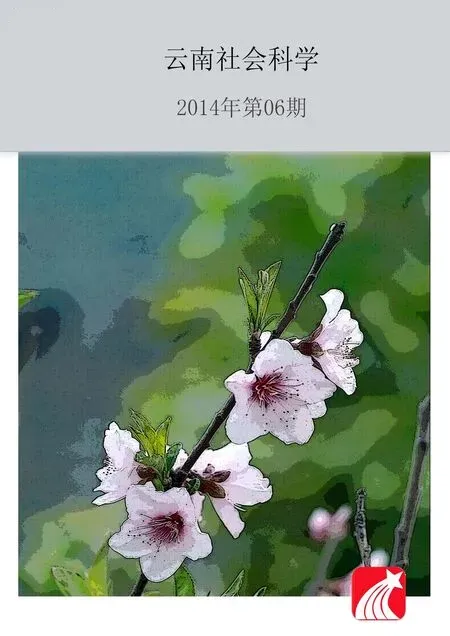中國民族史學史芻議
史金波
中國民族史學史是中國民族史和中國史學史共有的重要課題。筆者不揣淺陋,芻議概說,以引玉之磚,就教于方家。
一、中國民族史學史的任務和意義
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漢族和各少數民族為祖國的締造與發展都作出了重要貢獻。中國的歷史是中國各民族,包括歷史上存在后來已經消亡的民族形成、發展、共同前進的歷史。中國民族史研究領域相當廣泛,內容十分豐富,它研究中國各民族的歷史,包括現在中國境內各民族和歷史上古代民族興衰、變遷的族別史,各民族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專史,以及各民族之間的關系史等。中國民族史學史是研究中國民族史學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各時期特點以及人們對它的認識、史學成果的社會影響的學問,著重研究民族歷史編纂學的發展史,探究歷史學家、政治家等對民族史學的評論,也包括對民族史學自身的反思、總結和前瞻。
中國民族史學史可以幫助我們認識中國民族史,告訴我們中國的史學家怎樣記錄民族史,怎樣認識、評價、研究、總結民族史,怎樣從民族的發展、興衰中借鑒經驗。研究中國民族史學史可以更準確地認識、總結中國民族史研究,從而更有力地促進和發展中國民族史研究,為繁榮中國史學、維護祖國統一和中華民族的團結做出積極貢獻。
中國民族史學是一門既古老又年輕的學科。說它古老,是因為源遠流長的、傳統的中國史學從來就是記錄和研究漢族和各少數民族及其先民歷史的。說它年輕,是因為專家們自覺地從民族歷史的角度進行研究,并取得有影響的成果,使民族史學成為一個專門的學科,還是近百年的事。近代意義的史學史是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的。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民族歷史研究受到重視,進入嶄新的階段。然而歷史學家擺脫舊史學的影響,樹立唯物史觀指導下民族平等的觀點,需要一個過程。而培養一代民族歷史學家,撰寫出有豐富內容的民族史學著述,再在此基礎上研究中國民族史學史,那就需要更長的時期和更豐厚的基礎。近幾十年來,民族史研究有了長足的發展,有關中國民族史的專著不斷推出。先后出版了各民族專史、地方民族史、民族關系史和全國性的民族史。中國民族史學形成了蓬勃發展的局面。然而作為其中一個分支的中國民族史學史的研究卻顯得滯后,系統的研究似乎仍是一項空白。
20世紀90年代在民族史研究蓬勃發展的形勢下,我們曾提出編寫《中國民族史學史》的意向,并著手搜集基本資料,搭建書稿框架,但終未能完成。然而對這一課題的思考和準備并未停止。用科學的觀點考量中國歷史上的民族問題,是民族史和民族史學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問題。我們不斷從民族的角度審視歷史和現實。1990年我提出了“民族史觀”的概念[1],此后一些專家進一步詮釋“民族史觀”[2]、[3]。
我們高興地看到中國史學史的研究近些年在老一輩專家的基礎上又取得了顯著成就,特別是瞿林東先生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做出了新的重要貢獻[4]、[5]。十年前我與瞿先生交談時曾提出希望他關注民族史學史,他提到民族史研究專家們對民族史比較熟悉,希望他們更多地研究民族史學史問題。后來瞿先生專門組織過有關中國少數民族史的學術研討會議,會上還發表了《中國少數民族史學發展的幾個階段》的重要論文[6]。近幾年“中國民族史學史”已列入研究規劃,希望在各位同仁的關心和幫助下,完成這一課題。
二、中國民族史學發展的幾個階段
中原王朝對少數民族歷史有決定性影響。中國民族史發展階段與中原王朝基本吻合。
1.先秦時期
在中國古代原始社會,尚未有民族之分,但關于后來民族的先民早就有了歷史傳說。傳說中的黃帝和炎帝被視為中原地區的部落首領,是后來漢族的祖先,在部落聯盟階段,又融入了來自羌、夷、苗、黎等氏族集團的人。蚩尤則被視為九黎部落的首領。傳說蚩尤是主兵之神。黃帝和蚩尤在涿鹿(今河北涿鹿之南)的關鍵大戰,奠定了后來漢族和部分少數民族的政治和地理格局。《史記》記載:“蚩尤作亂,不用帝命。于是黃帝乃征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7](卷1《五帝本紀》)其后九黎的一部分融合于華夏族,一部分回到江漢流域,建立三苗部落聯盟,被認為是后來苗族的祖先。中國古代的史書載有“五帝”,而蚩尤未被列入,這或許反映當時以中原為主體的歷史記載和傳說對周邊部族的輕視和排斥。但從不多的歷史記載中仍能看到蚩尤的重要影響。秦始皇時祠八神,“三曰兵主,祠蚩尤”[7](卷28《封禪書》)。秦末在沛縣響應陳涉起義的劉邦被立為沛公后,就“祠黃帝,祭蚩尤于沛廷”,漢高祖初年“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長安”[7](卷8《高祖本紀》、卷28《封禪書》)。后來蚩尤在史籍中成了兇神惡煞的代表。
商、周時期已進入階級社會,關于民族史的記載也漸增多。在殷商的甲骨文和周代的銘文中都有關于民族史的記錄。如認為商王的祖先是東夷,周王的先民是夏人的一支,雜居戎、狄之間,與羌人關系密切。這種資料反映出在民族形成前其先民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當時人們對這樣的歷史現象有一定的認識。華夏族發展較快,力量強大,而周邊的“四夷”則較為落后。華夏族統治者已有“內中華、外夷狄”的觀念,對“四夷”采取歧視和壓迫的政策。
春秋戰國時期,群雄割據,華夏族從黃河中下游向東北、西北、西南延伸,少數民族先民在中國歷史舞臺上也顯露出實力。在先秦史籍中,這一時期有更豐富的民族活動記錄,華、夷尊卑貴賤的觀念已很明顯,中原王朝如何對待四夷已是當時統治者的重要研判內容。在中國民族史上《左傳》樹立了重視民族史的先例。它記載了華族及其以外各民族的分布和互相之間的關系,以及他們互相接近甚至融匯的過程。該書記載晉悼公和大臣魏絳討論如何對待山戎時,魏絳堅持“請和諸戎”,認為“和戎有五利”[8](《襄公四年》)。晉悼公接受了魏絳的建議,達到了“和諸戎狄以正諸華”的效果。魏絳提出恰當的和戎政策在當時很有見地,當時也有與此相反的論調,認為四夷不可信,提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8](《成公四年》)的大民族主義觀點。
2.秦漢時期
在公元前兩個世紀和公元后兩個世紀的秦漢時期,漢族逐漸形成。秦朝統一中原后,東北的扶余、北部的匈奴、西北的月氏、西部的羌,都是有較大勢力的少數民族。漢朝更替秦朝后版圖擴大,它溝通西域,屯田湟中,設西域都護府,管轄西北少數民族地區。秦漢時期與北方匈奴民族的關系是影響當時歷史的重大事件,或征戰,或和談,或和親,都表現出少數民族在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地位越加重要。漢朝征服了西南夷,設立郡縣。這一時期多民族中國的統一有了新的發展,奠定了各民族密切交往、相互依存的主流。
司馬遷的《史記》開中國“正史”之先河。其中在記載皇帝編年的《本紀》中,就有關于中原政府與少數民族關系的重要史料。而人物傳記中那些少數民族人物以及涉及少數民族治理、少數民族關系、少數民族地區的人物傳記,也有很豐富的民族歷史資料。特別是《匈奴列傳》《南越列傳》《東越列傳》《西南夷列傳》《大宛列傳》,為各民族撰寫專門的傳記,這種體例開創了中國史學的一個良好先例。通過《史記》可以看到司馬遷進步的民族史觀,他把所謂“四夷”都看成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且往往追根尋源,論說少數民族和中原華夏的關系,如“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后也”[7](卷110《匈奴列傳》、卷114《東越列傳》)。司馬遷能站在大一統的高度看待當時的民族問題,主要是他所在的西漢形成了大一統的國家。當然這種歷史認識和司馬遷本人曾深入到少數民族地區也有重要關系[7](卷130《太史公自序》)。
《漢書》繼承了《史記》的傳統,有《匈奴傳》《西南夷兩粵朝鮮傳》《西域傳》等,其中有很多民族史的精彩內容。《后漢書》中把少數民族列傳集中在一起,擴大了內容,有《東夷列傳》《南蠻西南夷列傳》《西羌傳》《西域傳》《南匈奴列傳》《烏桓鮮卑列傳》。在有些《志》中,也記載了不少少數民族資料,如在《地理志》中不乏少數民族地區地理的記錄。這反映了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的現實,少數民族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也反映出史學家們對民族問題重要性的認識。
3.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
東漢末年群雄割據,開始了近3個世紀動亂紛爭的時期。三國時期魏居北方,與烏桓、鮮卑關系密切。蜀踞巴蜀,爨、蠻為其南鄰。諸葛亮為鞏固后方,率兵南征,對少數民族首領孟獲七擒七縱,撤兵后用當地渠帥治理,采用羈縻之法,使“綱紀粗定,夷、漢粗安”。史學家對諸葛亮的舉措給予高度評價。
三國統一于晉。晉代匈奴內遷,鮮卑南進,吐谷渾西移,形成了少數民族大遷徙的局面。短暫的晉朝中后期又發生了新的分裂。這一時期少數民族在中國政治舞臺上的影響擴大,地位提高,進入所謂十六國時期。十六國中有13個是少數民族政權,其中有匈奴3,巴氐1,羯1,鮮卑5,氐2,羌1。有的已進入中原建立政權,如匈奴建立的前趙,羯族建立的后趙,鮮卑建立的前燕、后燕和西燕,氐族建立的前秦等。這些王朝時間短暫,但他們在中國民族史上有重大意義。南北朝時期漢族和少數民族政權對峙。南朝的轄地為南方,北朝則建立了影響很大的以鮮卑族為統治民族的北魏王朝,存在近一個半世紀。這一時期雖然國家處于分裂局面,但修史的意識很強烈。少數民族長期管領北方,占據長安、洛陽兩京,以正統自居,這種格局對歷史的認識和史書的撰述起了決定作用。當時少數民族和漢族一樣尊崇儒學,重視自己的歷史,中國最早設起居之官的是北魏。少數民族政權撰述歷史已蔚成風氣,有《漢趙書》《后燕書》《南燕錄》《秦書》《涼書》《十六國春秋》等近30種,對后世把十六國史列為正史有重要影響。十六國中多數在“正史”中有豐富的少數民族史內容。特別是魏收撰寫的《魏書》,詳細記錄了鮮卑族拓拔氏的興起、統一北方、建立政權、由盛至衰的過程,以及與周邊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從中可見鮮卑族在發揮本民族優勢的同時,逐漸吸收其他民族特別是漢族的政治制度、文化傳統,反映出民族之間的相互交往、融合的發展趨勢。
這一時期地方民族史的著作也很豐富。晉常璩撰寫的《華陽國志》是當時有代表性的、綜合性的地方史著作,所記主要是西南地區的地理、民俗、文化等,包括了豐富的民族史資料,特別是作者實地考察搜集的資料,為其他著作所缺,是研究西南民族歷史不可多得的史料。
4.隋唐五代時期
自6世紀末中國又走上隋唐3個多世紀統一的發展路程,再一次反映出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強大的凝聚力。大一統的政治局面促進了“天下一家”思想的發展。這時雖也是以武力為后盾實行民族壓迫政策,但總的來說,民族政策比較和緩,特別是唐朝對少數民族的羈縻政策已經系統、成熟,和親政策也行之有效。當時回鶻、吐蕃、南詔、渤海都是有影響的少數民族政權。鮮卑、吐谷渾在西北地區逐步融入漢族和藏族。黨項羌受吐蕃的壓迫,北遷至今甘肅、寧夏與陜北一帶。唐朝北制突厥,西聯回紇,開絲綢之路;回鶻助唐平定安史之亂,收復兩京,后分別建立河西回鶻、甘州回鶻、西州回鶻。東北地區的契丹和奚日益強大。西面吐蕃崛起,統一了青藏高原;唐朝與吐蕃來往密切,實行和親。西南以烏蠻為主體建立南詔。
這一時期中原對少數民族了解增多,認識加深。唐太宗的曾提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9](卷3《太宗本紀》)。 這種最高統治者進步的民族史觀影響到一個時代,包括史學家的認識。史學家們對少數民族的記錄、研究著作更加豐厚。唐初正式設立史館,在“禁中”修史,纂修梁、陳、齊、周、隋五代史,后又下詔新修《晉書》。房玄齡等人撰著的《晉書》包含了十六國的歷史,以《載記》的方式記錄。對少數民族政權的記載認識上有了新的發展,不再像過去撰寫南北朝歷史那樣記本朝為“本紀”,稱他朝為“傳”,北朝稱南朝為“島夷”,南朝稱北朝為“索虜”,而是比較客觀地按編年敘述。李大師、李延壽父子撰成《南史》80卷、《北史》100卷。他們認識到過去寫少數民族歷史的偏頗與失實,撰述思想很有創見,比如將少數民族王朝魏列入“本紀”,對南北朝的交往記載也較他史為詳[10](卷100《序傳》)。
唐代劉知幾所撰《史通》雖未專門論述民族歷史,但其史學思想和史學理論影響著包括民族史在內的整個中國史學史。他認為:“戎羯稱制,各有國家,實同王者。”[11](內篇《稱謂第十四》)承認少數民族政權的實際歷史地位。唐代開創了典制體史書的編撰,杜佑撰寫的《通典》分門立目,以類相從,在“邊防”類中記錄了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共190 多種,其中也有境外民族和國家,這為研究當時的民族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他提出“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12](卷185《邊防一》)。滲透著樸素的進化論和民族平等的思想,是難能可貴的進步民族史觀。
隋唐時期的民族史著作有裴矩撰寫的《西域圖志》,記西域40多國的史地、風俗。唐朝后期有李德裕著的《異域歸忠傳》《西南備邊錄》,高少逸著的《四夷朝貢錄》《云南行記》,竇滂著的《云南別錄》《云南行記》。特別是樊綽著的《蠻書》(又名《云南志》)10卷,詳細記載云南的交通、山川、六詔、民族、州城、物產、蠻夷和相鄰諸番夷國,以及與唐朝的經濟文化交流,內容極為豐富。
唐代安史之亂以后,社會動蕩,民族關系緊張,后形成藩鎮割據的局面,藩鎮中不乏少數民族政權。五代時期朝代更替頻繁,先后建立了十國政權,中國又一次處于分裂狀態。五代時期編撰了200卷的《唐書》,內有大量民族史資料,其中突厥2卷,回紇1卷,吐蕃2卷,此外南蠻、西南蠻15族1卷、西戎14族1卷、東夷5族1卷、北狄8族1卷,有的屬域外。
唐代少數民族自己撰寫史書尚未成熟,然而有文字的民族也開始記錄本民族的重要史實,如西藏拉薩的藏文、漢文合璧的《唐蕃會盟碑》,記載了唐朝和吐蕃和親會盟友好事件。又如突厥文、漢文合璧的《闕特勤碑》《毗迦可汗碑》敘述了突厥汗國歷史、首領的功績以及和唐朝的關系。敦煌發現的藏文卷子中有關于吐蕃歷史和社會的史料[13]。
5.遼宋夏金時期
遼、宋、夏、金約370年的時間是漢族和少數民族王朝分立時期。契丹族首領耶律阿保機建立了遼朝;黨項族首領元昊建立了西夏;女真族首領完顏阿骨打建立了金朝。前期遼、北宋、西夏鼎立,后期南宋、金和西夏并立,加之西北的回鶻、西部的吐蕃唃廝羅政權、西南的大理政權,形成了多民族政權并立的新格局。這對民族歷史的認識產生了深刻影響。
宋朝未能統一中國,與遼成為兄弟之國,后又不得不承認西夏的實際地位,這對長期以大民族主義為主導的漢族統治階級是難以接受的現實,統治者和史學家有強烈的屈辱感和憂患意識。當時雖然國力孱弱,但史書的撰著熱情高漲,大型史書不斷問世,如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范祖禹的《唐鑒》、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等。北宋史學家樂史仿《元和郡縣志》編著《太平寰宇記》200卷,依北宋初的建制敘述地理,其中有很多民族史資料系于各地,特別是四夷地區。南宋史學家鄭樵撰著紀傳體通史《通志》200卷,其中《年譜》記自三皇五帝以下諸帝王,也包括少數民族王朝的帝王。《二十略》中氏族6卷,有代北復姓230余,很多是少數民族姓氏。特別是以15卷的篇幅為《載記》,多記少數民族王朝始末,頗為詳盡。
《續資治通鑒長編》長達980卷,是一部翔實的北宋編年史,內有大量宋朝和遼、西夏、金、吐蕃、回鶻的民族關系史料,十分珍貴,為后世治史者所重。《建炎以來系年要錄》200卷,其中有很多與金朝的關系史料。南宋王稱著《東都事略》130卷,以紀傳體記宋朝史實,后有附錄8卷,專記遼、金、西夏等國事,常為后世史家所引用。
宋朝重視少數民族歷史和現狀的記載。范成大撰《桂海虞衡志》3卷,其中有“蠻”一門,對宋代廣南瑤、僚、黎以及西南白、彝等民族的社會、生產、習俗有較詳細敘述,為研究南方民族史留下了寶貴資料。《三朝北盟會編》250卷,專輯宋、金交往史實,引書近200種,其中包括金國實錄10種。南宋趙拱撰《蒙韃備錄》1卷、彭大雅撰《黑韃事略》1卷,都是最早敘述蒙古立國、社會、政治、軍事狀況的著作,所記多為親身見聞,至為珍貴。
宋朝也遵循歷代傳統編寫前朝正史。薛居正奉詔修《五代史》150卷,成梁、唐、晉、漢、周五代史書,內中不少與少數民族有關的史料,又記世襲、僭偽列傳5卷,記包括少數民族王朝的“十國”史實,外國列傳2卷記契丹、吐蕃、回鶻等少數民族歷史。后歐陽修又自修《新五代史》74卷,少數民族史實集中在《四夷附錄》3卷。他認為少數民族“惟其服叛去來,能為中國利害者,此不可以不知也。自古夷狄之于中國,有道未必服,無道未必不來,蓋自因其盛衰。”[14](卷72《四夷附錄第一》)宋徽宗被金俘虜后,曹勛隨侍,歸國后撰寫《北狩見聞錄》。洪皓使金,撰寫《松漠紀聞》。兩書皆親聞親見遼金事,有補史實。
遼、西夏、金朝和中原王朝一樣對修史十分重視,都設專門修史機構記史、修史,延續中國修史傳統。遼設起居舍人院,掌修起居注;翰林院下設國史院,任命女真人、漢人、契丹人為史官。遼朝創制契丹文,耶律儼、耶律成、蕭韓家奴等都是本民族史學家。遼代史學撰著不少,今多已亡佚,據后人搜尋知有正史、編年、起居注、載記、雜史等。如耶律儼有70卷的《皇朝實錄》,蕭韓家奴與耶律成合編有遼先祖事跡20卷,翻譯漢文史籍多種。
西夏創民族文字,后世稱為西夏文。近代出土有西夏文王朝法典《天盛律令》、西夏文類書《圣立義海》和歷史雜記等。西夏設秘書監修史書,設翰林院修實錄。西夏末期大臣羅世昌辭官后撰《夏國世次》20卷,修《金史》時尚存,后亡佚[15](134《外國傳上·西夏》)。蒙古軍隊進攻西夏時,“諸將爭取子女金帛,(耶律)楚材獨收遺書及藥材大黃”[16](卷146《耶律楚材傳》),可見耶律楚材還收集到一些書籍。
金朝尚書省下右司“兼帶修注官”。金朝也創制民族文字女真文,科舉中設立“女真學”。考試中史書內容占很大比重,推動了史學的發展。史官中有譯史者,譯《史記》《西漢書》《新唐書》等。金朝修史以實錄為主。如完顏勖撰寫《太祖實錄》20卷,紇石烈良弼成《太宗實錄》《睿宗實錄》等,后實錄的編寫持續不斷,這在中國封建王朝中十分突出。金朝佚名作者撰《大金吊伐錄》4卷,依年次編錄金國破宋、滅遼、立偽楚的國書、誓詔、冊表、文狀、指揮、諜檄等文書161件,資料珍稀,為世人所重。蕭永琪撰成《遼史》30卷,后又成第二部《遼史》。金末國運衰微,史學家更以“亡國作史”為己任,以為后世修史用。元好問作《野史》和《壬辰雜編》,以親歷為實錄,記金末喪亂事,帶有搶救史料意圖,惜已散失;又作《中州集》,匯集當時詩人200余人,每位詩作者都有小傳,不啻一部紀傳體金史[15](卷126《元好問傳》)。劉祁撰《歸潛志》14卷,據見聞所及記當時金末、元初事,在《辨亡》一篇中認為金朝民族壓迫政策導致國家短命,部分地道出了金朝滅亡的原因。這時期有葉隆禮奉敕撰寫《契丹國志》(一說元人偽托)27卷。宇文懋昭撰寫《大金國志》(一說宋元人偽托)40卷。兩書保存了很多契丹史和女真史原始資料,可補其他文獻之所無,但體系蕪雜,舛誤較多。
遼、西夏、金都不自外于中國,推行儒學,以中國正統自居。這一時期少數民族以新的姿態出現,雖政權分據,“中國”意識并未削弱。
6.元朝時期
以蒙古族首領成吉思汗及其繼承者建立的蒙、元朝,結束了中國的分立,建立了龐大的統一王朝,前后180多年。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由少數民族掌握全國政權的局面,這大大影響了人們對民族關系的認識,大漢族主義受到極大沖擊。由于元朝分為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等,民族壓迫以新的形式出現。元朝在少數民族地區確立土司制度,對后世影響頗深。
元代少數民族史學家編纂的著作有突出的成就。第一部全面反映蒙古族歷史的著作《蒙古秘史》問世,共12卷,作者不詳,應是蒙古族史學家。該書記述了13世紀中期以前成吉思汗和窩闊臺時期蒙古族的歷史和相關的民族交往情況,描繪出以武力見長的蒙古族軍事活動。該書顯示出少數民族史書的特點,寫史事時常加入詩歌,是研究蒙古族前期最重要的資料。原書以老蒙文撰寫,后譯成漢文,后世僅存漢譯本。
藏族的史學家蔡巴·袞噶多吉用藏文撰《紅史》記印度王統、釋迦世系漢地王朝帝系、蒙古王統、吐蕃王統,突出漢藏關系。回鶻人馬赫木德·喀什噶里編纂的《突厥語大詞典》用阿拉伯文記錄了很多操突厥語民族的歷史,保存了很多珍貴史料。
佚名作者的《圣武親征錄》和蘇天爵撰寫的《元朝名臣事略》,也是有關蒙、元前期、中期的有重要學術價值的著作。元人撰寫的游記性著作有很高的史學價值,如道人李志常撰寫的《長春真人西游記》(多記蒙古、畏吾爾族)、契丹人耶律楚材撰寫的《西游錄》(多記西域各地民俗)、劉郁撰寫的《西使記》(多記中亞風土人情)等。
虞集等編撰《元經世大典》880卷,取材檔案,涉及元代各種典章制度,民族史材料很多,現只存輯錄本。元朝還編撰了各代實錄共15部。由蒙古人札馬剌丁和漢人虞應龍共編《元一統志》1300卷,包括漢族和少數民族地區,內容十分豐富,可惜現僅存部分篇章。
元代也產生了稽考中國過去朝代史實的宏篇巨作,其中有馬端臨撰寫的《文獻通考》348卷,其中宋代資料過半,有關民族史的資料很豐富,特別是輿地、四夷部分。
元朝繼承中國編寫“正史”傳統,編寫宋、遼、金三史,不僅工程浩大,也具有突出的史學史意義。其體例確定為“各國稱號等事,準《南北史》”,“金、宋死節之臣,皆合立傳,不須避忌”[17](《附錄·進遼史表》)。把宋、遼、金視為平等的王朝,正式確立了少數民族王朝的歷史地位。這種民族史觀的確立,與歷史上同為“夷狄”的蒙古族執政有重大關系。《遼史》《金史》都有少數民族和漢族史學家參與纂修,保存了大量契丹、女真和他們建立王朝的史料,具有突出的民族史特點。《遼史》的部族、屬國表有關于少數民族和鄰國的資料,列傳中的“外記”分記高麗、西夏二國事。《金史》的“交聘表”記載了與宋、西夏、高麗關系。這些資料反映了各民族交往,有的民族走向融合的歷史進程,推進了民族史學的發展。
元朝編寫三朝史時,未同時編撰西夏史。其原因可能是西夏比宋、遼、金三朝勢力小,為三朝屬國,元初首議修史時就未提及西夏;元滅西夏時首都中興府破壞很大,典章圖籍散失殆盡,當時雖有《夏國世次》等史書,但資料仍顯缺乏;西夏很多典籍以西夏文書寫,即便有遺留書籍,翻譯使用困難。還可能是元朝把黨項族(唐兀人)列為色目人,民族地位較高,入元后多用蒙古族名字,元朝不把西夏視為獨立的國家。進入中原、或接近中原的契丹族、女真族、黨項族逐漸走上民族消亡和同化的道路,現存的史書成為了解這些民族的重要載體。
7.明朝時期
元末農民起義推翻了元朝,建立了明朝。明朝并未完全統一中國,北方仍由勢力頗大的蒙古族統治。明代對南部、西部少數民族地區仍實行土司制度。
明代官修《明實錄》內容豐富,卷帙浩繁,2909卷,為前所未有。官修《大明會典》417卷。兩書保存了很多民族歷史資料,是研究明代民族歷史和民族關系的重要史書。
明初太祖攻占北京不久,即下詔修《元史》,僅歷10個月修成。這是明朝統治者急于總結、汲取元朝興亡成敗的經驗教訓。過去往往把治內的少數民族和境外鄰近的民族、國家都列入四夷傳,《元史》僅將境外的國家列為“外夷”,這明確了修史區分境內外民族的觀念。
元滅明興是朝代的嬗替,但相當一部分漢族人認為是從中原驅逐了“夷狄”,這種認識反映在有些史書中,便扭曲為無視歷史事實的大漢族主義。如王洙的《宋史質》中把遼、金王朝列在“外國”,并上推明太祖的先祖直接“繼承”宋朝,抹殺元朝的存在,被后世史家貶為“荒唐悖謬”。 柯維騏編著《宋史新編》雖具史料價值,但把遼、金、西夏列入“外國”。這種民族史觀的倒退,引起史學界的異議,認為是“迂闊之見”、“殊涉偏見”[18]。
明代李賢領銜編撰的《大明一統志》,在一些州郡記錄中保存了很多少數民族分布、沿革、風俗、土產等珍貴資料。當時因防御北邊少數民族的需要而編著的北方地方志顯著增多,成為研究當時民族和民族關系有價值的文獻。
隨著明朝與少數民族關系密切,明太祖敕撰《華夷譯語》,成祖設四夷館,接續敕編,始有八館:蒙古、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緬甸,其中雖兼及外國,但以少數民族為主。書中除各民族語常用詞與漢語對照外,還有詔書和文件,保存了很多重要民族史料。
此外還有不少有關少數民族的史書,如金幼孜撰《北征錄》記明成祖北征韃靼事,楊榮撰《后北征記》記作者隨成祖征韃靼事,蕭大亨撰《北虜風俗》記明代蒙古族風俗和社會制度,元劉佶、明鄭曉撰《皇明北虜》記元明時期蒙古族活動,鄭曉又撰《皇明四夷考》記明中葉邊疆少數民族的歷史、文化、民俗、交通等,高拱撰《邊略》記明朝與蒙古族、苗族關系及廣東剿倭事實,陳誠撰《西域番國志》記出使阿富汗途徑西域各民族地區事,馬文升撰《復興哈密記》記哈密部分蒙古叛亂及政府平叛事,他又撰《撫安東夷記》記女真與明朝關系,張洪撰《南夷書》記洪武初至永樂初平定云南各土司事,朱孟震撰《西南夷風土記》記四川、云南少數民族地區情況,倪輅撰《南詔野史》記云南各民族世系史料,茅瑞徵撰《皇明象胥錄》雜記邊疆四夷及周邊外國情狀,楊慎著《滇載記》以白文史籍雜以調查資料記云南少數民族事。錢古訓撰《百夷傳》記云南地區多種少數民族情況。
王圻作《續文獻通考》是《文獻通考》的續作,補充了有關遼金的典制,十分重要。 晚明史學家王世貞編撰100卷的《弇山堂別集》,其中記載了很多明朝與少數民族關系的史料。王世貞編撰《弇州史料》100卷,內中也有很多民族史資料。
明初藏族學者薩迦派僧人索南堅贊以藏文撰寫《西藏王統記》記述吐蕃王統傳承,對吐蕃前期三位贊普的事跡記載尤詳,對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嫁吐蕃和唐朝、吐蕃的文化交流也有翔實的描寫。明成化年間藏族學者噶舉派僧人桂洛·宣奴貝以藏文撰寫《青史》,記述藏族歷代王統傳承和藏傳佛教各教派的創建、發展歷史,尤詳于噶舉派。嘉靖年間藏族學者班欽索南查巴用藏文撰寫《新紅史》,記吐蕃王統,著重記宋、元、明時期藏族20個割據政權的情況,還記載了漢地朝代更替,蒙古、西夏王統,表明作者已把藏族史和中國各民族史視為一體,這是元代將西藏正式納入行政管轄的結果。嘉靖年間藏族噶舉派噶瑪支系活佛芭臥·祖拉陳哇用藏文撰寫史書《智者喜宴》,不少內容為漢文文獻,甚至是其他藏文文獻所缺載的。
明末撰有蒙古文《蒙古黃金史》,一為作者不詳的《小黃金史》,一為羅卜藏丹津撰著的《大黃金史》,包括從成吉思汗至元朝滅亡以及明代蒙古族共270年的歷史。它們與《蒙古秘史》《蒙古源流》合稱蒙古文三大歷史著作。
8.清朝時期
明末滿族首領奴爾哈赤統一各部,后其繼承者入關統一中國,再次建立了少數民族統治的大一統王朝。清朝繼承中華傳統文化,重視史學,反對輕視夷狄,沖擊了大漢族主義觀念。但其對夷狄的忌諱,特別是對滿族的回護造成民族主義的高壓政策,影響了史學的發展。
滿族進關前創制了滿文,以滿文記錄了很多珍貴歷史資料。最早的官修編年體史書《滿文老檔》記錄了后金、清初在東北30年的史實和民族關系史料。可見滿族統治者在東北時便注重記錄本民族的歷史,有明確的修史意識。
官修《清實錄》4000余卷,分別以漢、滿、蒙三種文字繕寫,民族歷史資料是其重要部分。此外有大量清代檔案傳世,約有1000余萬件,多方面地記載了清代歷史,其中有大量滿文檔案,十分珍貴。官修史書中還有續“三通”和清“三通”,即《續通典》《續通志》《續文獻通考》《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獻通考》,其中保存了大量民族史資料,如《續文獻通考》在明《續文獻通考》的基礎上又有很多新的增益,四夷部分就有14卷。
清朝也重視修撰前代史。《明史》纂修歷經百年,其中關于民族史的內容很豐富,在《本紀》《兵志》中都有很多記載,特別是第310~319卷為湖廣、四川、云南、貴州、廣西土司傳,詳細記載了西南部地區少數民族的歷史和現狀。其外國傳所列大部分是外國,但把韃靼、瓦剌也列入外國,頗為不妥。卷330~332為《西域傳》,包括新疆等地及藏族地區,也集中記錄少數民族地區史料。《明史》對滿族入關前與明朝的從屬關系,以及南明抗擊清朝的事實抹殺不記,反映出當時滿族統治者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明末清初王夫之作史論著作《讀通鑒論》,多有卓見,因貫穿反清立場,強調“華夷”之辨,清朝將其排斥于《四庫全書》之外,因此可見王夫之和清朝統治者民族史觀的對立。
清代編纂了多種與民族地區有關的《方略》,如《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平定金川方略》《平定準格爾方略》《平定兩金川方略》等,都記載了對少數民族地區的重大軍事行動和民族關系。趙翼編撰《皇朝武功紀盛》記康熙、乾隆平定三藩、朔漠、準噶爾、兩金川、臺灣、廓爾喀等地事跡,有重要史料價值。清設理藩院管理少數民族事務,有《理藩院則例》64卷,也是研究清代少數民族歷史的重要資料。乾隆時官修《皇清職貢圖》繪記300余民族、部族男女形象及部長屬眾衣冠,并附錄說明習俗、衣食。
額爾泰等纂《八旗通志》全面記述滿族特有的社會組織形式八旗制度,對八旗的建立、發展、更定、重要人物的事跡均予詳細記載,很有特色和價值。另一部官修史籍《滿洲源流考》記滿族先世及有關東北各民族的歷史,書中多用滿語詞語,十分珍貴。但書中對女真各部與明王朝的隸屬關系隱諱不載,造成史料的缺漏。鄒應龍、李元陽編纂的《云南通志》有很多當地史料,其中羈縻等部分尤為集中。清初還編纂《衛藏通志》記述西藏歷史、地理、寺院、習俗以及清朝在西藏實行的各種制度,于西藏前期的重大歷史事件記載更為詳細。特別是著名史學家錢大昕著有《補元史藝文志》《元史考異》《遼金元史拾遺》等。《元史氏族表》介紹蒙古、色目人的起源、發展及其區別,考證精確。
清高宗敕撰《平定羅剎方略》,記述清朝康熙年間中國東北各族抗擊沙俄的史事,其中記載沙俄對達呼爾、鄂倫春、鄂溫克、赫哲、滿、漢等族人民燒殺擄掠的罪行,清廷調集各地各族兵丁與東北各族人民共同抵御沙俄的事跡,表現了中華民族共同抗擊外敵的愛國主義情操。
龔自珍高瞻遠矚,首倡新疆建省,撰寫《西域置行省議》,后王樹枏等撰《新疆圖志》,內容豐富,是新疆建省后的第一部通志。一些在少數民族地區任職的官員撰寫民族地區史志,記錄民族情況,總結治理經驗。如滿族人七十一(尼瑪查氏)撰寫《西域聞見錄》,詳記新疆少數民族情況,他還著有《回疆風土記》。蒙古人松筠著《西招圖略》專記西藏事務,他又主持纂修《西陲總統事略》,詳記清初新疆地區事務,包羅宏富。蒙古人和寧撰《回疆通志》,是一部全面反映新疆的著作。黃沛翹撰《西藏圖考》,繪西藏地圖,并有西藏源流及地理、風俗考證。蕭騰麟撰寫《西藏見聞錄》,記載很多珍貴的西藏史料。佚名作者的《番僧源流考》,記述了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等大小藏傳佛教派系44支,詳盡記載了西藏的風習、文化和佛教傳承。滿族人額恒撰《伊爾根覺羅氏家傳》,敘其先祖生活、征戰以及到西藏、云貴、兩廣任職情況,內有西南少數民族起義資料。有關少數民族史地著作還有嚴如煜的《苗防備覽》,記錄了作者親歷和查閱檔案、志書的資料,特別是湘西苗族、土家族、仡佬族、瑤族及附近漢族的第一手資料。清朝后期有人撰寫鎮壓少數民族起義的著作,如奕訢領銜修撰的《平定云南回匪方略》,盡管書中歪曲、污蔑回族農民起義,但對起義所敘甚詳,是重要民族史資料。
清代蒙古族薩岡徹辰洪臺吉編纂的蒙文史書《蒙古源流》利用多種蒙、藏文獻,結合親見親聞,敘述了蒙古族歷史以及蒙古與各族的關系,先后譯成滿文、漢文,為史家所重。藏族在清朝又有新的史書問世,如五世達賴喇嘛作《西藏王臣記》,詳載西藏從傳說時代至清初顧實汗歷代王統和王朝事跡,于藏族史貢獻很大。彝族很早就創制彝文。用彝文撰寫的《西南彝志》約成書于清朝前期,除記載彝族對宇宙和人類、萬物起源的認識,特別記錄了彝族來源、發展、風俗習慣,以及彝族內部六大支系之間的關系,內容豐富,史料價值巨大。
1840年中國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新史學在孕育、形成,但中國古代傳統史學仍然延續。這時期對歷史上少數民族歷史撰述頗豐。如謝啟昆的《西魏書》、吳任臣的《十國春秋》、邵遠平的《元史類編》等。對蒙、元史的紀傳體撰著還有魏源的《元史新編》、屠寄的《蒙兀兒史記》、柯紹忞的《新元史》、洪鈞的《元史譯文證補》。后者首次利用外文資料考中國歷史,更為可貴。紀事本末體有李銘漢著《續資治通鑒紀事本末》《遼史紀事本末》《金史紀事本末》。云生修撰《打牲烏拉志典全書》,記述滿族社會歷史。魏源撰寫的《圣武記》不僅記載滿洲的興起、發展和統一中國,還記載了各族抗俄戰爭,特別是記載苗族、回族起義事,有很多新資料*因篇幅原因,關于中國近現代民族史學史將另文討論。。
三、中國民族史學的特點
中國民族史學是中國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有中國史學的一般特征,也有自己的特點。
1.中國民族史學的發展與歷史上各民族的發展、所處地位相契合,與民族實力的消長、政權的存廢相關聯
民族史學在先秦時期隨著民族先民的活動中而顯露萌芽,漸被重視;秦漢時期在漢族形成過程中,少數民族也登上舞臺,民族史學逐步形成;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少數民族紛紛建立王朝,特別是鮮卑族所建魏影響很大,促進了民族史學的發展;隋唐時期的大一統局面和統治者較為和緩的民族政策,使民族史學活躍并穩步發展;遼宋夏金時期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與宋朝并立,皆承中國德運,以中國正統自居,各自修史,民族史學進一步發展;元代以少數民族為主體,實行民族等級壓迫,沖擊了大漢族主義史觀,不僅自修歷史,還將前代多民族王朝分撰“正史”,推動民族史學新的繁榮發展;明代統一了中國大部,北部仍是蒙古政權,史學家關注民族地區,因此有不少民族史書問世,蒙古、藏族史學家紛紛著書立說,民族史學呈現繁榮局面;清代中國一統,少數民族又一次成為主體,雖有對少數民族的回護,但民族史學著述豐碩,特別是滿、蒙、藏文史籍大幅度增加,民族史學進一步繁榮。可見,民族史學隨著時代的進步、各民族不斷發展、民族間交往增多而逐步發展、成熟、繁榮。
2.從民族史觀角度看,不同時代、不同階層、不同民族、不同學養對歷史會有多種多樣的觀點
不同的民族史觀構成人們認識上的差異,相互交織出民族關系上的矛盾、仇視、包容、和解和融通。在階級社會,大民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的民族史觀表現突出。隨著社會的發展也形成了進步的民族史觀。社會的發展,民族關系的走向不以哪一階層、哪一個人的觀點為轉移。其實,中國歷史上各王朝都是多民族的。中國歷史上民族關系的主流“是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經過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愈來愈密切的接觸,形成一股強大的內聚力,盡管歷史上各民族間有友好交往,也有兵戎相見,歷史上也曾不斷出現過統一或分裂的局面,但各族間還是互相吸收、互相依存、逐步接近,共同締造和發展了統一的多民族偉大祖國,促進了中國的發展,這才是歷史上民族關系的主流”[19]。中國各民族向心力越來越強,共性越來越多。
3.民族史學資料十分豐富,但也十分分散
過去中國歷史記載的主要是漢族歷史或中原地區的王朝歷史,但有關少數民族歷史的記載也摻雜其中,內容豐富。不僅在“正史”中有大量民族史資料,在其他很多典籍中如政書、類書、志書、別史、雜史等都有豐富的史料,在各民族的口碑資料中也有重要的歷史資料,近代考古發現的資料中也包含著不少有關民族史的實物。其中有些資料比較集中,但大部分資料支離分散。因此需要在各種類型的史籍中爬梳揀選,有的還需要在少數民族地區調查搜尋,有的則需要在少數民族生活過的地區進行考古發掘。此外,過去史書中不少是官方或漢族學者編撰的間接資料,需要認真地核對和甄別。
4.用少數民族文字記載民族歷史資料,是民族史學的一大特點
中國古代各少數民族中有的創制、使用過民族文字,形成了數量不等的民族文字文獻。以本民族文字撰寫本民族歷史,多是第一手資料。如敦煌石室發現的藏文歷史文書、黑水城發現的西夏王朝法典,都是真實反映當時歷史的珍貴史料。很多民族還有豐富的民間傳說,也是極富價值的資料。過去由于對少數民族文字史料缺乏重視,不少民族文字史書遺失,如用契丹文、女真文撰寫的文獻多未傳世。存世的少數民族文字史料需要翻譯、注釋,特別是有些死文字的解讀需要漫長時日,利用這些資料困難重重。近代史學家對民族文字史料逐漸加以重視,特別是新中國建立后,民族文字史料的開發、利用有了長足的進展,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大量民族文字史料的解讀和利用還需要史學家做出更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