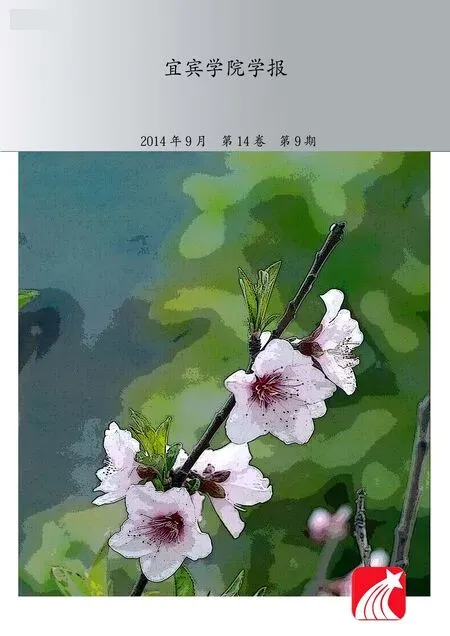唐君毅先生詮釋二程學“性理”義之方法探源(上)
鄧秀梅
(環球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臺灣)
唐君毅先生分判周、張、二程與朱子五人之思想內涵,將其分成兩大類,周敦頤、張載是從天道論下貫至人性論的思路,二程乃是先從內在生命開始致思,由人性論而上升至天道論,朱子亦循此路徑以入。從解釋程顥的人性觀開始,唐先生提出“生之理”這一概念,此概念貫徹于程顥、程頤二兄弟之學說,是唐先生詮釋儒家“性理”之重要解析,若能掌握唐氏所解繹的“生之理”之涵義,則對其所詮解的二程學之方法,將有莫大的幫助。
所謂“生之理”者,即是使萬物得以生生不息之理,為萬物化生之終極根源,亦稱“生生之理”。這個詞匯的由來,遠本于《易傳》言“生生之易”,《中庸》言天之生物之道,亦遙契孟子之言“生則惡可已”之旨,它是為說明萬物之所以生生不已的原故而提出。唐先生認為,在中國思想中,特重此宇宙萬物之創造、生化,或流行之歷程之未濟而未已,此不已,乃悠久無疆而永純一不已,由此乃特重此道之永遠在前為導之義。[1]439-440以宇宙生化的角度觀之,生之理與儒學中所謂的天道、天理、太極等稱謂相當;當其落實在一一個體之中,生之理即為人物之性。以人物之性而言,此性如何又可為生生之理?此需回歸唐氏對“性”之最初洞見。他認為此性“乃一將人向上提升,以達高明,自內開拓,以致廣大之一理想原則,而非一說明人生之現實之因果之一現實原則。”[2]336緣于有此性,人遂可超拔自己以及于他人與天地萬物,躋升圣境而與天地合德。按此解釋,內在于人之性,是一可以改變人之現實生命狀態,使人得以從原始的、只知追求滿足生活需求的生命狀態漸漸蛻變演化而成為一理想的、有意義的生命型態,依唐先生自己的解說則是:
此中之性,只是一生命之上升而擴大之性,即一生而又生,以成其生之充實之性。故此性,亦只是生生之理、生生之道。然人有此生生之理、生生之道以為其性,則其生命之沿其心思之所及,以求上升擴大,即可至于對此心思所及之天地萬物之所在,亦皆視為我之生命之所在。而此性、此理、此道,遂為一使我之生命,通于天地萬物之生命,而見其為一體,使我之生命成圣人之生命者。[2]337
此觀點若從二程學的學脈以觀,更加豁顯。生之理落實而成為人性之理,循唐氏之解,它應是具有改變人之現實生命形態的能力,人唯有賴此性理,生命才得以不斷充實提升。因之,最直接的解法便是此性理內在于人,具有主動的作用力使人能夠改正自己的心地言行,若取另一當代新儒學大師牟宗三先生的術語而言,即此性理不僅是存有之理,它尚具活動性,是“即存有即活動”的創生之理。然而此未必是唐氏的解法。在唐氏的詮解下,性理之活動性其實并不顯豁,但是他不斷重復一個論點:此性此理即以“向于與之相應之情之生、氣之生”為其本質之意義。由此而肯定此理即是生理,此性亦是一生性。雖則性理的活動性不突出,可是它有一清楚無疑的“方向”,這方向對準與它相應的情氣而隨時使彼相應之情氣生發出來。就性理有一昭然清晰的方向而言,唐氏認為此性此理“非只是靜,而是靜中有動義者”。種種論述皆顯示唐先生欲把二程(特別是伊川)所言之“性理”活化成一有作用力的理,而非止于靜態的萬物所以存在的存有之理。
如是豐富而曲折的義理內涵,其原初的思維意念是怎么樣?有無一脈相續的理念主導之?本文意欲探解唐氏“生之理”一義之義涵及其思維脈絡,以昭顯他詮釋二子之學的宗旨源流。至于唐先生所詮釋的內容是否切合二程學,以及與其他學者詮解內容的比較,則非本文之重心。
一 生之理具體化為人之性
儒家論人性之源,從《中庸》《易傳》乃至周濂溪、張橫渠,是謹守著“天命之謂性”這一傳統脈絡立論。以濂溪而言,濂溪視誠為一天道,而此天之誠道,是一立體性的貫注于天地萬物,使之由生而成,而樹立于其中之道。[2]332橫渠的思想則是先將天地中之人與萬物齊等平觀,視為同原于一本之太和以生,太和既是一一個體物化生之本,也是一一個體物受天命而生成之本。因此,雖然周、張二子是從天道論下貫至人性論,但人性之本源自天道之下貫降命,則是每一位儒者必須肯認的理念,即使二程與朱子,唐先生綜論他們是由人性論而上升至天道論,其義亦然,人物之性畢竟要上源于天。前言曾引唐氏之說,北宋諸子所言之人性,并非是一說明現實人生之因果的現實原則,而是一使人超拔其個體,向上提升以達高明的理想原則,也就是從這個觀點來說生生之理、生生之道。
(一)性為在前為導之理想原則
此性既是一理想性原則,其中之豐富意涵,得透過人之不止息的盡性功夫,方能彰顯性之價值與意義。唐氏給予此性一擬喻,就性之使人超拔其生命,譬如一道路,此道路可以導人由卑下狹小而向上提升以達高明廣大,人若有所成,而回顧此性之何所是,則可不見其豐富的內容,此中若為空蕩蕩,似是一空虛之原則;但唯有緣此道路以前行遙望,然后見此道路乃可引人以無遠弗屆,而瞻顧四方者。因之,此性是自盡于人之功夫中,方能見其價值與意義。就此點而論,唐氏說道:
此性亦即恒顯為在前為導之一道、一理。而克就一道、一理之在前為導,而尚未為我所行踐言,此道、此理,即為純形而上,亦尚未全實現于我之生命之氣之中者,而凡吾人未能盡之性,亦皆可說為尚未全實現于我之生命之氣中者。由此即開出明道伊川之以性即理、性即道,而不以此性此道皆屬于已成之氣之一新路之思想。[1]337
此喻甚能把天命之性之莊嚴與無限期的實踐歷程彰明出來,使人曉喻性不僅止于人物之所以存在之理,它同時也是人所以能開拓提升自家生命境界的生生之理,而且依儒家的一貫共識,后者之意義較之前者更能適切表達人性之意涵。由此道路之喻也暗示唐先生對于生之理、亦即天命之性的認知:
第一,性之豐富意涵必得透過人之盡性之功夫,方能一點一滴的領悟。這不表示性需經由人的踐履來增進它的豐富性,而是性自身本即具有完整而豐富的內容,只不過人之領悟其中的內容得須經過盡性的功夫。
第二,以道路為喻,此道路是無遠弗屆的,人踐行其上固然可以循序躋升圣賢之域,但人因應外境、當下體現此性之意涵是有限的。天命之性卻是無窮無盡的,人勢必無法悉數實踐朗現性之內涵,此處即拉開了理(天命之性)、氣(人之踐履)的距離,程伊川、朱子的理氣觀實乃鑒于此而立論的。
道路之喻暗藏上述兩種涵義,這對唐先生思繹二程學有相當大的影響,左右了他對二人哲學體系的詮釋方法。
(二)程明道論生之謂性
按唐先生對二程學的理解,明道、伊川初非視此人性為一客觀的天道之一表現,如周、張二子所為;“而是自始直就人生命之所以能由卑下而高明,由狹小而廣大,此中應有一道一理,內在此生命之中,而引導之以上升,而使其內部日趨于擴大者,為其生命之性。”[1]337唐子以為這是一種新思路,從人之自覺自己生命之實往上升即能證實此性之必有,而且此理、此道,亦即此性必然已先在于此,譬如一道路已先在此,而為我所能行;我既能行,即見我有能行之性,是以前面“道路”之喻實也隱含人有能力遵循性之理想原則而改變生命狀態。
以明道論性而言,“生之謂性”是他常說的一句話。所謂“生之謂性”者,明道的解釋如下: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卻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卻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①
“生之謂性”原出于告子,告子的原意是就著各種物類的生之狀態或生之本質上說性,此種性僅能歸類在“人生氣稟”這一層次,人生氣稟理當有善、惡相對之兩類,至于“性”則無此兩物相對。此言依唐氏之解,第一,他判斷明道之言與告子之意完全不同,所謂“生”之謂性之“生”,是指“已成之一生命之個體,如佛家眾生之生。此為一名辭,乃與性之名義無關者。”[2]338告子說性,是就生之狀態或生之質上言,但明道所言“生之謂性”卻不如是,可見唐先生也把性和氣區別開來,并不以為性“即是”氣,氣“即是”性。第二,唐先生判定明道此言乃是即就人物之生,而謂之為性。“即此‘生’之自身而謂之曰性。亦即就將此‘生’之自身,當做‘人物之存在所循之道路、或一道、一理’看,而謂之曰性。”[2]339此道、此理不離已成之事物或氣,并且為此氣“去生”之理,換言之,已成之事物或氣之能去生他物,全依憑此“去生”之理,此“去生”只是一創造原理,其實就是一生之理。此生之理雖不離已成之事物或氣,但也不能說此“去生”之理即在已成之事物或氣之中,而為附屬于此已成之事物或氣者。[3]339這段分辨十分重要,后來唐氏詮釋朱子的“太極者本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機”即以此為準則,強力蘇活朱子太極之理為一活理而非死理。
(三)性理表現為生之事的方式
依上文所述,生之理即是物或氣“去生”之理,此意非是理直接生氣,而是氣憑依此生之理而去生新的氣,物也是如此。生之理之為宇宙生生之理,其故在于物物皆依理而生,即依理而去然、去生的意思。此為生之理表現為宇宙生化的方式,落實在一一個體物中而為人物之性,則此理此性之表現于去生去然,“非只孤立表現為一抽象普遍而浮現于物之上層的生相;而是表現于其具體特殊,而落實地與天地中其他之物相感而有應之事中。”[2]341如是,此性的進一步內涵即是感應之理。所謂去生去然,即在感應的模式下而有所生、有所然;此感應之事,即此性此理之表現為生之事。我與其他萬物相感應之實況,唐先生陳論如下:
而吾人與其他天地萬物之感應,乃一方有吾人自己之心之生而內感,同時有此所感之天地萬物之生于吾人之心,及緣“吾人對天地萬物之所為之事”之“生”,而亦有之“天地萬物變化”或“生”。此中所見者,正是己之去感去應,與所感所應之天地萬物之一種“生則一時生”之關系。[2]342
此處又涉及明道另一重要理論——合內外、徹上下之一本之教。
從我與萬物之感應,唐先生析釋其中之義,乃是我之心生而內感,所感之物同一時也生于吾之心;由此可推演出當吾人順著去生去然之性而去感去應時,與所感應之萬物非一先一后之關系,而是“生則一時生”之關系。此生之理、生之性固然在我,也在物;在內,亦在外,它是一方合內外之物我,一方徹上之天命與下之人性者。就人物相感應而一齊生言,即見渾然與物同體,不見物我之別,就此而言名曰“仁”②;反之,若認為天地萬物自與己不相干,正如醫書所言手足痿痹之不仁狀態。手足痿痹乃氣不通貫全身,故無法感受手足之觸感;人之待其他萬物若也是這種態度,則亦同如醫書所云“不仁”也。③這是要在于己與人物氣不相貫不相感處,隨處使一己之氣與之相感通,而隨處見此仁所貫注之體,于吾人之生命心靈之中。[3]137此為唐先生的詮釋。
此中應當留心的是能感能應的是我之心,當我之心生而內感,所感之物也于同一時生于我之心,不分內、外、心、物,一起同時生起。然則何謂“內感”?為何當我之心生而內感時,同時就有所感之物生于我之心?有無可能吾之心僅是單純的內感而無所感之物?或者人可以略過內感而直接外感于物?在此唐氏并無特別解義,不過“內感”之義在他疏解伊川“性即理”時,倒有詳細的說明:
所謂內感者,乃自家之“能感”自相感,而生生不息。能感不息,方能外通,以有通外之感。若非先有此性理之內具,使內感不息,亦無“內感”以通外,亦無“更升起呈顯自覺的理想,于心目之前”之事也。[2]353
簡要來說,內感即是自家(此處指的是心)能感而有自相感之事,吾心之所以能自相感,所感者即是性理,亦即“生之理”,心憑依著生之理而有自相感之事,蓋性理即內具于心,不在心外,故云“內感”。心之內感必然通外之感,所以唐先生才會說:“吾人與其他天地萬物之感應,乃一方有吾人自己之心之生而內感,同時有此所感之天地萬物之生于吾人之心。”是故吾心與物有“生則一時生”之關系。若無依憑此生之理而內感,是無所謂外通,亦無生生之事,所云感應者皆僅是被動地感于外物,是散漫、淆亂之物感,不具生生不息之能。
此自家能感而自相感的心,在上文的陳論過程中,很清楚的,此心并非“即是理、即是道”之心,而是隸屬于氣的心,此點在他詮釋明道“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一理念時便可知。唐氏疏解此理念的大意是:當仁者以己之氣與人相感,也就是以己之仁心仁情行于此相感之事中,此仁自是貫于一切所感之事中。是故仁固然是一道、一理,非只是一事、一氣,但必須于一一以己之氣去貫通所感,以仁心仁情成此相感之事中,識此仁之理之道,而不可望空懷想此仁之體、仁之道。明道從同氣相貫、疾痛相感言仁,即是直接從心之能感通之道之理說仁。心固然可以外知有天地萬物,但不表示天地即在我心之上;透過我心之感通,則萬物即在我心所感之中,于此可言“天地之用為我之用”,我已不限于我,我已不自私。此大公之境界,必須有真情實感以實之,否則易流于一藝術性之觀照境界,而非仁者之道德生活的真實境界。[3]137-138
統理以上之論述,可得出幾條重要眉目:其一,生之理即是“去生、去然”之創造原理;其二,生之理落實于人物之中乃為性之理,性理表現為生生之事是依“感應”之模式,能感者是自家之心,心依憑生之理(亦即性理)而內感外通于外物,當我之心生而內感,所感之物也同時生于我之心,是所謂“生則一時生”;其三,此中能感之心為實然之氣心,非與道、與理為一之心;其四,真正與萬物相感相通的是仁心、仁情之“氣”,仁道、仁理是在前為導的生之理,欲與物感通仍得一一以己之氣去貫通所感才行。此為唐氏詮解明道言性的幾項結論,這些結論也被用在解疏伊川學上,可視它們為分解二程學的綱領原則。
(四)伊川論“性理”義
按唐氏對二程的見解,他認為明道、伊川二兄弟之思想乃同出一脈、理徑一致,皆是就人之生活中事,性情心身上事,以展示盡性至命、窮神知化之境。因之,明道言性的一些原則,譬如性之為生之理、性乃是開拓提升生命的理想原則等,皆可應用在伊川學。當然兩兄弟仍有些許差異:伊川更能于當然之理與行為實踐之距離特別反省,而將理、氣之差距拉開來,彰顯理之超越而尊嚴、恒常而貞定;此外,伊川于此學中之種種名義,更有分別肯斷之論述,不同于明道之多指點啟發語。[3]163唐先生論二程之差異大體就此兩點立論。
1.“性即理”之重要意義
伊川言性與明道之將道、理、性,連于吾人生命之氣、神等,以相即而說不同,伊川乃是別理于生命之氣,使理氣如相懸隔,而更要說此理之即吾人生命之性,以見此懸隔之統一,則學者非有一思想上之自下至上之躍起者,未易悟此義。[2]348-349因為理、道、性、氣諸名互相比較,理之客觀意味最重,性則是主觀意味最濃。明道善合內外而立說,論“性”是通貫著氣、道來說,因之明道言性,道、性即天理,此結論均可自然推演而出。伊川則不然,伊川偏在即理以言道,又并不如明道之即神以言性,于是通內外主客之懸距,乃全賴性即理一義之建立。[2]349在一般人的觀念里,理是客觀的,是天下所共知之大公而普遍者,性則為主觀,乃一人之內具私有而特殊者。
人既視理為客觀、性為主觀,而凡人之離性以言理者,其所謂理,乃外在而非內在,恒傾向于說所知之自然之理、或超越之玄理。至于離理以言性者,則其所謂性,乃或私曲而幽隱,恒傾向于個人內具之氣質。在人之道德生活中,凡不知此性之即理,而以理制性者,則其理,恒只尊而不親,其性亦卷曲而不伸,人乃恒疑于其性之善;凡不知理之即性,而任性以為道者,則其性,乃雖親而不可尊,于理則悖之而遠離,人乃更違善而近惡。唯知性即理,乃能知天下之大公之理,即一人之所自有,而客觀普遍者,即在此主觀特殊者之中。[2]305
程頤“性即理”一說之重要貢獻在此。將性和理連結起來,可使人性之論不再止于卷曲之氣質,而是凡理想之所在、大公之理之所在,皆不出我之外,為我所固有。此無疑把人性升舉至形而上層次,更能證明人性為善非泛泛之空言。誠如唐氏所云:
此中之理,如吾人之客觀而超越之理想,性如吾人今日之所謂生命之性。人孰不知其所向之客觀而超越之理想為善?今謂此人之所向之此理想之所在,即此性之所在,或此理想原為內具于吾人之生命中,以為其性,亦由此生命而發出者;人尚孰能疑于其生命之性之善,而不以此理想之實現,即吾之生命之性之實現乎?[2]350
順此引申,凡吾人之理想或所肯定之理之所在,無論所及者如何高明廣大,乃至無限量,其為吾人生命之所向往,即無非吾人之性之所在。天下實無性外之理。若落實在個體的現實生命中,現實生命是一有限量的氣之流行,縱是有限量,但此氣可通以理,以擴大超升,由凡而入圣;氣之可通以理,即已見其具“能有所向之理,而已通于理”。[2]352此為唐氏特別指出的重點。生命之氣所以能流行不已,端賴此具理而通于理之生命之性,故不可以氣為性,唯可即氣之所以流行之理以言性,故曰性即理。生命之性既在理不在氣,人遂可知以氣從理,以理率氣,如是,理高明氣亦高明,理廣大而氣亦廣大。吾人即可率有限之生命之氣,由通之以理之無限量,而擴大超升,超凡入圣于是乎在。
此中,唐氏明顯表達兩個重點:一是凡為性者皆我所固有,因為“性”之一詞即是生之理具體落實在個體生命當中,性自身若即是理,即可導引出此理必在我之內,為我先天所具有。然而伊川嚴峻區分理、氣之別,縱使性理原具于吾生命之內,若性理無活動性以致對吾之生命有興發鼓舞之作用,又如何保證必能朗現此性理呢?因此重點之二“氣可通以理”便為一句至關重要的樞圜。氣不是單純的生而化、化而生之流,或是形成個別物體的材質,它早已具備“能有所向之理,而已通于理”之能,此能具于氣之靈覺、精爽的那一部分,若依后來朱子之論,氣之靈覺唯獨人之“心”有之,心就是性理能夠內感外通的關鍵。
2.性理具內感外通之能
從上之義,凡吾人所可能發出之真理想,皆是內在于我之生命之性,理想縱未一一呈顯,但必然先在,均是吾人未顯之性;而已呈顯之理想皆為此本原,亦即生命之性之用之一端耳。當未有此用之一端時,人亦當知此時此心之沖漠無朕,而實萬象森然已備,寂然不動之性理之體之全,自在其中矣。[2]353此是心未感性理之情形,由此唐先生續推論道:
因其感而應,亦只是依此內具之寂然不動之理之感而遂通,未嘗外于此理,以有此感通之能也。凡此感通,皆是“內感”以外通。[2]353
前文述及“內感”義時已討論到心、性之關系,乃是心憑依性理而自相感、而生生不息,性理之全實已在心之中,當心有所感于性理而發出真理想時,即是感而遂通。是以能感者在心,所感者為性,如此看來,性理是無感通之能可言的。不過這樣的分解可能超過唐先生的本意,他特別強調“若非先有此性理之內具,使內感不息,亦無內感以通外,亦無更升起呈顯自覺的理想,于心目之前之事也”一事,也許就是提醒讀者,縱使能感者在心,但性理之引發心之能感也不可輕忽,若無性理內具于心,心亦不存內感之事。可見心之內感是受到性理的影響或吸引,所以才引發內感。此即是性理之作用。
3.由性情論推衍至理氣論
唐先生的理路很清楚,所有應當發出之理則或理想,俱已蘊于吾人之生命而為我之性,既云“當然之理”,可見此理應當有表現于外在之情的能力,在其論述生之理為去然、去生之理時,唐氏特別標出生之理之“四義”,此四義分別是能然、當然、必然與自然④,生之理內在為我之性,則此理除具當然之義外,也同時涵蘊“能然、自然與必然”,亦即當然之性理自有主動顯發的能力,故唐氏斷言:“言性即理,即謂性之未表現于情,在情上未然者,當表現于情之實然上之謂。”[3]173此當然之性理雖一時未發未表現,但它必然具有一能動之動向義,永遠朝著形于外之方向而發動。
當然之理是否一定實現而成就實然之存在?依唐先生的理解,這是不成問題的,當然者即向在成為實然,若不向在成為實然,則當然也就不成其為當然之義。且當然不僅向在成為實然,當然之理尚蘊含成為實然的動能,循此以論性、情,則是“依性有情,情表現性”之關系;就此延伸出去,性即理,情依氣,所謂性情之關系,實則也是理氣之關系。“依性有情,情表現性”推演為理氣模式,即是“依理有氣,氣表現理”。性一時未表現于情,然性“當”表現于情之實然;同樣的,理一時未表現于氣,然理“當”表現于氣之實然。所有關于性和情的陳論皆可移至理、氣之關系,唐先生甚而認為伊川思想之重點,當是先有此性情之辨,后方及理氣之論。重理氣之相對,喜以理氣言天地、以及于人物之性情,那是朱子所為,非伊川之理徑。[3]173-174
唐氏提出此觀點,確有他人未及之獨到處,蓋伊川、朱子的理氣之辨一出,人或已忘伊川思想之本原在性情之辨,理氣之辨乃后來之派生。緣于此,人或只以此中之“理”之觀念之立唯在說明氣化之所以然,而“性”之觀念之所以立,則是為了說明情之所以然。于是,人或以為伊川立“性理”一觀念乃為說明人之現有的惻隱、羞惡之情、或事物之氣之流行的可能之形上根據。綜觀目前學界論述伊川學之學者,譬如牟宗三先生,即是以此觀念剖析伊川之學術。⑤此處唐氏企圖扭轉這類普遍的想法,重新提出一套新理論:
然此中吾人以性為情之根據,理為氣之根據,乃意在說明未有當有之情之氣,所以有、所以可能之根據,亦即意在說明此我所將創生之情氣,所以可能之根據,而非意在說所已有,現有之情氣所以可能之根據。[3]176
將性理作為“所已有,現有之情氣所以可能之根據”,與作為“未有當有之情之氣,所以有、所以可能之根據”似乎無甚差異,總是指向“性理為情氣之根據”一途,可是唐先生就從此細微處把伊川的性情論導向情為性所生發。其理論是若欲對人已有現有之情氣追溯其所以之根源,而以性理為根據者,“此仍是由吾人之思及此現有已有者,初原是未有非實有,或只為一當有;而后覺其由未有當有而實有,須有一說明。此仍是求一根據,非對已有現有者,求其根據。”[2]176
對已有現有者求一所以可能之根據,不正是哲學思維所以興起之因嗎?但如今唐氏把人對已有現有者求一根據之思考,轉向為實際上乃是對未有當有者之所以可能有求其根據;這一轉向,即是唐氏為確立“性”為當有未有之情之可能的根據,“理”則是當有未有之氣的可能根據,如是一來。
此性此理,即以“向于與之相應之情之生、氣之生”,為其本質之意義。故此理即是生理,此性亦是一生性。此性此理,乃是即在其未表現于氣、見于情時,已有此向于生此情、生此氣之意義者,然后得為此情此氣所根之以生者。[2]177
此處理之所以為生理,性之所以為生性,不是全然由于氣依憑著理而有新生之氣發生,故此理為生理,而是因為此理本即傾向生發與其相應之氣,故為生理,性之為生性同樣也是這個緣故。進一步,此理、此性之傾向,最終化而為靜中有動義,而實表現一動,以顯此性理于情氣。
如只即情即氣而觀,當情氣之未生,則于此性理可說之為靜。然即此性理而觀其向于此情氣之生,為此情氣所根以生,則非只是靜,而為靜中有動義者。依此性理之有此動義,而實表現一動,以顯此性理于情氣,是為此心之“感而遂通”。若自此心未實表現一動,只有此具動義之性理之存于心說,則為此心之寂然不動。[2]177
在唐先生的詮解下,伊川之性理被賦予能動義了。不過觀唐氏解性理之動義,并非顯著地就著性理而論其能動與否,乃是透過“心”之寂然感通而說性理具有動義,如此說之“動義”十分隱微,它不似心之活動一樣明顯,可是它仍然有動,此動義,本文判斷應是性理有潛在影響心之作用,由此說性之能動義。如是解析方能與前文論述一致。
單就著性理而言,是無所謂動靜;必連著心說,性理才有動義可言。此即涉及伊川“心主性情”之義理,待下篇詳論之。
注釋:
①參見宋代程顥、程頤所著《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一中《端伯傳師說》,中華書局2004年版本,第10頁。關于《二程集》之《遺書》部分,以下簡稱《程氏遺書》。
② 明道《識仁篇》曾云:“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即為表達此意。載于程顥、程頤所著《程氏遺書》卷二上,第16頁。
③明道原文是:“醫書言手足痿痹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見程顥、程頤所著《程氏遺書》卷二上,第15頁。
④唐先生對此四義的解釋是:“自然”似本體論之自己如此如此地去然;“當然”似道德論上之當如此如此去然;“能然”似宇宙論上之就存在事物,而言其能如此如此地去然;“必然”似就理之自然、當然、能然者,而更就其反面之不可能處,說其只可如此如此地去然,而不得不如此如此地去然,以成為實然者。參見唐君毅所著《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第340頁。
⑤牟先生評論伊川之學術風格乃是一質實者,多偏于分解表示。質實者即直線分解思考之謂。依其直線分解的思考方式,遂將太極真體、太虛神體、乃至于穆不已之體,只分解地體會為只是理,將性體亦清楚割截地直說為只是理。性與廣泛的存有之理合流,而復與格物窮理之理接頭而以格物窮理之方式把握之,則原初講性體以為道德實踐所以可能之超越根據之義意見泯失而不見。源于此,牟先生判斷伊川所言之性理,實與存有之理淆混一處了,總用“以然推其所以然”的方式說道德行為。有關牟先生解析評論伊川之學,請參閱其所著《心體與性體》第二冊第三部分論二“明道、伊川與胡五峯”,正中書局1985年版。
參考文獻:
[1]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M].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9.
[2]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M].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9.
[3]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上[M].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