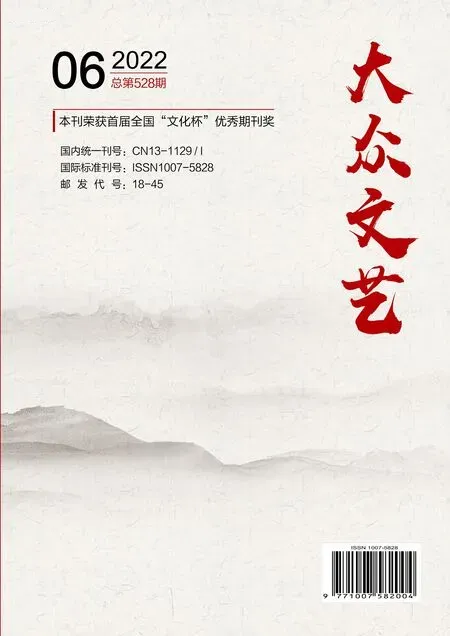文化詩學視角下的詩經《采葛》篇解讀流變
崔 璨 (安徽大學文典學院 安徽合肥 230000)
文化詩學視角下的詩經《采葛》篇解讀流變
崔 璨 (安徽大學文典學院 安徽合肥 230000)
在中國詩歌數千年的發展歷史中,有關詩經《采葛》篇的主旨解讀先后出現了“懼饞說”、“淫奔說”、“男女慕情說”等不同的解釋。詩歌的解讀總是帶著深刻的時代烙印,從文化詩學的視角來探討詩經《采葛》篇解讀背后所蘊含的文化語境對于我們正確地把握詩歌主旨具有重要意義。詩經《采葛》篇的解讀流變在某種程度上昭示著人性的常態化回歸,這也為我們真切地理解和關照古人的生存狀態和心路發展歷程提供了可能的途徑。
詩經《采葛》;文化詩學;解讀流變;人性
一、詩經《采葛》篇的文本初探與文化語境重構
詩經《采葛》篇出自《詩經?國風?王風》,共三章,章三句,短小精悍,膾炙人口。“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1
清人皮錫瑞強調了對于詩歌的把握必須要回到詩歌原有的語境中去。詩經《采葛》篇的文本理解其實并不難,但是由于本詩只是表現出一種急切的相思情緒而沒有具體內容,因此關于此詩的主題思想就眾說紛紜。不同時代對于此詩的不同解讀其實并非文字、音韻等訓詁學意義上的分歧,也非詞句、語法等語言學意義上爭論,真正推動詩經《采葛》篇解讀流變運動的是加之于歷代文人身上的文化思想印痕。
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講究詩旨解讀、千人異面,理通圓賅的自當勝出。這種解讀方法強調了讀者主體在面對文本時的獨立性,面對同樣的詩歌文本,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解讀會有不同的閱讀體驗。但強調詩歌解讀的千人異面,卻不能忽視歷代詩歌解讀的共性歸納背后所蘊含的深層次文化思考。一首詩歌在一定時間段內的解讀為什么會帶著同樣的解讀痕跡?這點值得我們去揣摩和玩味。畢竟,一首優秀的詩歌作品是不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日漸暗淡的,我們對于詩歌的把握也不能因為得出了看似公允的結論就放棄了對于詩歌王國的藝境求索。保持持久和穩定的藝術追求是我們歷代詩家的責任。本文將以詩經《采葛》為例,仔細梳理從漢代的《毛詩序》到錢鐘書的《管錐編》這兩千多年的時間跨度里,中國文人對于此詩主旨的解答演變并運用文化詩學的有關理論來分析歷代的這些解讀背后所呈現的“中國式問題”。
二、詩經《采葛》篇的解讀流變梳理與分析
有關本詩主旨的理解,首估《毛詩序》。《詩序》有言:“《采葛》,懼讒也”。鄭《箋》云:“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大小,使出者則為饞人所毀,故懼之。”2毛瑞辰在《毛詩傳箋通釋》中說道:“《傳》《箋》并以采葛、采蕭、采艾為懼讒者托所采以自況。”3王逸《注》:“葛藟惡草,乃緣于桂樹,以言小人進在顯位。”4
凡此種種詩評,皆可歸類為一類:那就是將詩歌的文化語境放在了封建君臣之間,將遙望撿拾艾草的人生硬地比作君王。對于此,錢鐘書先生在《管錐編毛詩正義》中提出了明確地懷疑態度,他認為這是穿鑿附會的解釋,把情侶之間的想念的情感錯誤地解釋為舊日官場上朝士的心理狀態,不符合詩歌的主旨,但是這種解釋卻反應了古代社會官場上的一種普遍心態。5
后世對此解讀一直到了朱熹之時有所改變,他提出了“淫奔說”。朱熹在《詩集傳》中云:“采葛所以為絺綌,蓋淫奔者托以行也。故因以指其人,而言思念之深,未久而似久也。”6這種詩意解釋有利地攻擊了“懼讒說”,將詩歌的文化語境從高高在上的王臣之間拉回到了普通人的生產生活之中。然而朱熹詩評中的淫邪之意是從何處看出的?后世學人對此多有疑義。究其原因也似乎不難理解:朱熹是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是中國哲學史上的一代宗師,其部分思想在后世逐漸演變成為壓抑人性的三綱五常等具有教條性質的封建官方哲學。在那樣一種文化背景下,人們是無法祝福那些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男女愛情的。個人對于愛情的自由追求終究敵不過人倫天理包裹著宗法觀念。李易安的晚年改嫁令時人對其詩詞才華和人品多有微詞,而陸放翁的一首千古絕唱《釵頭鳳》則成了對此的最好注解和深沉抗爭!
朱熹將此詩的主旨從君王臣子之間拉回到了普通人的生產生活之中,開始關注普通人的生活,這在一定程度上宣告著從王性到人性的回歸,但是卻將男女之情解讀成為男女淫奔之事,足見當時以朱熹為代表的宋代理學思想對于人倫常理的禁錮的抹殺。
關于詩經《采葛》的解讀到了清代以和許多詩家的觀點趨于一致,如姚際恒在《詩經通論》中,并駁《毛詩序》、朱熹《詩集傳》,將詩意解讀為思慕親朋。7聞一多在《風類詩鈔》里所言:“懷人也。采集皆女子事,此所懷女者,則懷之者男。”8傅斯年在《詩經講義稿》里稱本首詩為“男女相思之歌”。9錢鐘書在《管錐編之毛詩正義》中也認為本詩的主旨是反應男女之情而非君王臣子懼饞之事。
總而論之,本首詩的主旨可以概括為男女極言相思、懷遠之作。
三、詩經《采葛》解讀流變的人性回歸論思考
詩經《采葛》篇的解讀流變史是一部人性回歸史。
首先,古人對于此詩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把詩歌所要表達的主體放在了君王和臣子之間,這說明在專制社會中,普通人的情感是很少被人提及的。在古代社會,每一個獨立個體都被綁在了所謂的“家國”這樣一個概念之上。在那個時候,每個人的生產生活都必須圍繞在忠君愛國這樣一個大的前提下,所以也就不難理解為何“懼饞”說能夠持續如此之久,并且得到如此眾多的附和之語。當公共的關注對象始終是某一個人或者是某一個集團時,那么每個人的主體性作用就會被消解掉。在中國古代的士大夫文化里,我們能找到的要么是“處廟堂之上則憂其君,處江湖之遠則憂其民”這樣具有自我安慰性質的失意者,抑或者是隱居山野、著書立說的避世哲學家。但無論是哪一類人,都始終沒有擺脫掉群體的種概念加在每個人身上的枷鎖,而屬于個人的類屬性總是被顯性或隱性的群體運動所遮蔽!原有秦火,中有梁武,近有文革,在那種狂飆突進的氛圍內,每一個人都幾乎已經停止了思考,理性認知被體內分泌旺盛的荷爾蒙所取代,所造成的結果必然是毀滅性的。于是乎,朱熹的“淫奔說”便有了存在的市場和空間。因為封建倫理的種概念是統制于個體的追求自由的類概念之上,所以男女情愛如果沒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可將其定義為淫邪。
人之所以為人,正是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氣質,獨特的靈性,一旦這種靈性被掏空,那么恐怕我們人就不能稱之為人了。所以,詩經《采葛》的人性回歸解讀流變給我們樹立了一種觀點:我們對于詩歌的解讀不能用群體的種概念去抹殺掉每個人的類概念,每一種獨立而自適的生存方式都是值得我們尊敬的。采葛的可以是王孫貴族,也可以為蕓蕓眾生,面對那采葛的男女,我們應摒棄心中的那些偏見,用包容的心去接受所有的可能。
詩經《采葛》篇的主旨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中有不同的解讀,而這些解讀背后所蘊含的文化內涵值得后世學人不斷去思索。以古典詩文為切入點、運用文化詩學的理論方法加以研究為我們理解和把握古代社會的思想文化和民族的心理狀態提供了一個新的途徑。一部詩經《采葛》的解讀流變史是一部人性回歸史,透過其解讀流變,我們能探析到中國文學逐漸向人本化和常態化發展的傾向特征。
[1]程俊英.詩經譯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標點本)[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3]馬瑞成.毛詩傳箋通釋[M].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1992
[4]許子濱,王逸楚辭章句發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5]錢鐘書,管錐編[M].北京:中華書局,1978.
[6]朱熹,詩集傳[M].北京:中華書局,1958.
[7]張海宴,姚際恒《詩經通論》研究[J].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02期.
[8]聞一多.聞一全集[M].上海:三聯書店,1982.
[9]傅斯年,詩經講義稿[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崔璨(1992-),男,漢族,安徽淮南人,安徽大學文典學院,研究方向為中國文學批評史和文化詩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