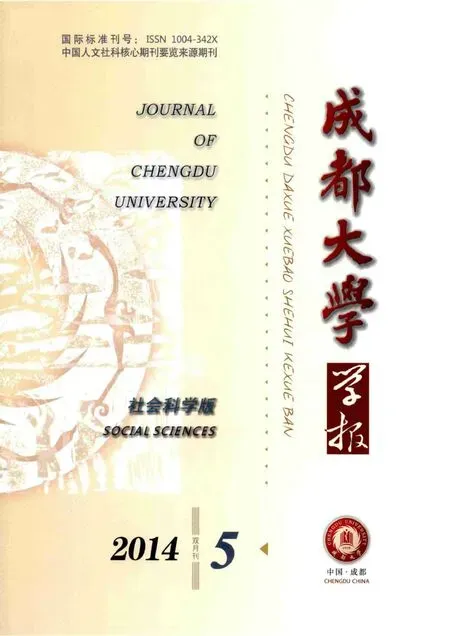農民工的社會信任狀況研究*
何麗 許傳新
(成都理工大學,四川成都610059)
農民工的社會信任狀況研究*
何麗 許傳新
(成都理工大學,四川成都610059)
本文采用中國西部經濟社會變遷問卷調查數據,探討了農民工的社會信任狀況及其相關因素。并采用因子分析法,把農民工的信任狀況分為制度信任、特殊信任、普遍信任三個方面。研究發現,農民工的社會信任狀況為典型的差序格局,性別、年齡、文化程度、收入狀況、流出經歷都和農民工的信任狀況有一定程度的相關。
農民工;社會信任;相關因素
一 研究背景
當代信任研究始于20世紀50年代心理學關于人際信任的實驗研究,20世紀70年代之后,信任問題的研究逐漸走出純粹的心理學范疇,成為社會學、經濟學、管理學等領域探討的重要課題。[1]20世紀初,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Simmel)首次將信任引入社會科學研究范疇,他認為,社會信任代表著一種力量,通過個人并為個人服務,通過人類的交往并為人類交往服務,是一種最重要的社會整合力量。[2]信任對于維護社會交往、社會秩序、社會團結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處在社會主義轉型時期的中國,在社會結構深刻變動,改革進入深水區的關鍵時期,良好的社會信任對于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構建和諧社會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推進,農民工這一龐大的群體已經成為我國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龐大的農民工隊伍促進了農村社會結構的轉型,并在很大程度上型塑著中國的社會結構與走向。[1]目前學術界有很多學者針對不同的群體進行信任問題的研究,如農村居民的信任研究、城市居民的信任研究、中國居民整體信任研究等,但對于改革開放條件下農民工這一特殊利益群體的信任研究數量較少,程度尚淺。本文通過較大規模問卷調查收集資料,對農民工的社會信任狀況進行描述與分析,研究農民工的社會信任狀況及其相關因素。
二 研究設計
(一)概念界定與測量
社會信任。目前學術界對信任的內涵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是把信任當作個體行為,梅西克和克雷默認為信任是個體基于對他人行為是否會遵守或破壞道德標準所做的一種反饋行為。[3]第二種是把信任當成預期,認為信任是施信者對他人可能行為的一種積極性預期。[3]本項研究中,我們把信任的內涵界定為第二種,即把信任當成一種積極性預期。盧曼在齊美爾的基礎上,認為信任是一種簡化復雜性的機制,并區分了人際信任與制度信任。[4]鄒宇春指出信任通常被分為人際信任和制度信任,人際信任又被分為兩種主要子類信任: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3]前者指個體對自己熟悉的、親密的人的積極性預期,后者指個體對那些自己不熟悉的、較少互動的人所持有的積極性預期。
在本項研究中,我們設計了以下8項指標來測量農民工的信任狀況:(1)對社會上大多數人的信任;(2)對家人的信任;(3)對朋友的信任;(4)對鄰居的信任;(5)對地方政府的信任;(6)對地方法院的信任;(7)對醫院的信任;(8)對陌生人的信任。采用李克特量表的測量分為5個等級,即“根本不信任”、“不太信任”、“說不清”、“比較信任”、“完全信任”,分別賦予1~5分,得分越高,信任程度越高。
為了綜合分析農民工的社會信任狀況,筆者首先采用主成分法對農民工信任狀況的具體指標進行因子分析,并采用方差極大化原則對因子負荷進行正交變換,以便對本次研究中有關農民工社會信任狀況的具體指標進行綜合,從而提取出概括多個具體指標的新因子(因子分析的結果見表1)。

表1 農民工社會信任的因子摘要表
我們對這八個指標進行KMO檢驗,這八個指標的KMO值為0.748,巴特利特球狀檢驗的卡方值為1522.010,自由度為28,在0.000的水平上顯著,表明這八個指標適合進行因子分析。表1的結果表明,八個指標被概括為三個公因子,根據每個因子所包含的指標內容,分別命名為制度信任因子,特殊信任因子和普遍信任因子。累計方差貢獻率為62.786%,基本達到因子分析的要求。在提取了新的公共因子后,我們計算出各個因子得分,即制度信任得分、特殊信任得分、普遍信任得分,制度信任得分均值為3.44,標準差為0.96;特殊信任得分均值為4.18,標準差為0.61;普遍信任得分均值為2.34,標準差為0.77,表明農民工的特殊信任水平最高,制度信任水平次之,普遍信任水平最低。
(二)資料與方法
本研究的數據來自于2010年“中國西部經濟社會變遷”的問卷調查,“中國西部經濟社會變遷”問卷中包含了測量社會信任的部分。調查于2010年9 -10月份進行,調查對象為西部12省市年齡在18歲以上的成年人。采用pps法抽取60個居委會樣本,在抽中的居委會內隨機抽取20戶,每戶隨機選取1人作為被訪者,每個省市的樣本總數為1200戶,所有省市都遵循一樣的抽樣程序和步驟。根據研究需要,我們對調查原始數據重新開發,從原始數據中抽出961名農民工樣本,并對農民工的社會信任狀況進行描述統計分析。
三 結果與分析
(一)農民工社會信任狀況
我們將測量農民工信任程度的8項指標進行描述統計分析(見表2),可以看到:(1)農民工對家人的信任程度最高,均值得分為4.73,標準差最小,為0.57,對家人持完全信任的農民工所占百分比為77.8%。對陌生人的信任程度最低,均值得分為1.74,對陌生人持完全信任的農民工所占比例僅為0.2%,而持根本不信任的占到48.6%。(2)農民工的信任程度存在強弱差異,信任程度從強到弱的順序如下:家人>朋友>鄰居>醫院>法院>政府>社會上大多數人>陌生人。對家人、朋友、鄰居的信任程度分值為3.5~5分之間,信任程度很高;對地方政府、地方法院、醫院的信任程度分值在3~3.5分之間,信任程度中等,但是信任得分的標準差比較大,表明農民工對政府、法院、醫院的信任程度有較大的個體差異性;而對社會上大多數人和陌生人的信任程度分值則在1~3分之間,信任程度比較低。

表2 農民工的社會信任狀況(%)
(二)農民工群體內部社會信任狀況的比較分析
1不同個體特征農民工的社會信任狀況比較
(1)不同性別農民工的社會信任狀況比較
對男女農民工信任狀況的比較分析發現(見表3):在制度信任方面,男性和女性無顯著差異,但是在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方面,男性和女性存在顯著性差異,男性的信任程度要高于女性。現階段,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時期,社會結構的變革時期,社會問題、社會矛盾比較突出。而女性相對于男性來說更加感性的心理特征使得他們在社會中上當受騙的可能性增大,從而導致了她們的特殊信任水平和普遍信任水平相對男性而言要低一些。

表3 男女農民工社會信任狀況比較分析
(2)不同年齡農民工的社會信任狀況比較
對不同年齡農民工信任狀況(見表4)的比較發現:不同年齡的農民工在普遍信任方面不存在顯著性差異,在制度信任和特殊信任方面存在顯著性差異,年齡越大,制度信任和特殊信任程度越高。原因可能在于:第一,年齡較小的農民工進城務工的時間還比較短,社會經驗不夠豐富,對有關農民工的政策、法律保護及制度保障了解不夠深入,相對于年長一點的農民工而言還不知道如何合法、有效地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因此對制度的信任程度相對較低。所以,針對年齡較小、進城務工經驗比較少的農民工,更應加強對其自身權益維護的宣傳教育活動,從而增強其制度信任水平。第二,年齡較小的農民工自身心智還不很成熟,對家人、朋友的叛逆情緒比較強,從而影響其信任程度,而年長一點的農民工更能夠感受到家庭角色在整個社會角色中的重要性,對家人、朋友、鄰居給予更多信任。

表4 不同年齡農民工社會信任狀況比較分析
(3)不同文化程度農民工的社會信任狀況比較
對不同文化程度農民工的信任狀況(表五)比較分析發現:在制度信任方面,不同文化程度農民工的信任程度差異較大,農民工對制度的信任水平隨著文化程度的提高呈“U”型變化趨勢,表現為小學>初中>大專>高中,即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農民工的制度信任水平最高,初中文化程度的農民工次之,高中文化程度農民工的制度信任水平最低,到大專文化程度農民工的制度信任水平又有所回升。在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方面,不同文化程度農民工不存在顯著性差異。很多學者都認為,受教育程度越高,社會信任水平也就越高。教育程度會影響人們的理性思維和理性判斷能力,受教育水平越高,人們對事物的認識就不再是盲目地信任或不信任,更多的是基于理性的思考判斷,不會對社會上大多數人、陌生人盲目地排斥、不信任。但是我國農民工的文化水平普遍較低,受教育程度不高,在本次調查中,高中文化程度農民工所占比例為14.5%,大專文化程度的農民工僅占3.8%,農民工文化水平層次的普遍偏低使得農民工在脫離農村鄉土社會、熟人關系信任模式進入城市社會后,很難對他人產生較高的信任水平。

表5 不同文化程度農民工的社會信任狀況比較分析
2不同收入狀況農民工的社會信任狀況比較
對不同收入水平農民工的信任狀況(見表6)比較分析發現:不同收入狀況農民工的社會信任狀況不存在顯著性差異。有很多學者認為,社會信任同物質富裕程度有著緊密的關系。吉登斯認為,占有大量資源可以使人具有一種更加開放、更自在的人生態度,而這種人生態度可以增強對他人的信任。[5]在本項研究中,通過比較分析發現,收入差異對農民工的社會信任狀況并沒有顯著性的影響。原因主要在于目前我國農民工這一特殊群體的收入水平普遍較低,普遍處在收入分配的底層。農民工收入水平的低下,物質財富的缺乏使得農民工進入城市社會后缺乏安全感、融入感、開放感,他們沒有多的資源來承擔因信任他人失敗而帶來的風險與損失,從而很難對他人產生較高程度的信任,導致農民工的普遍信任水平普遍較低。

表6 不同收入狀況農民工的社會信任狀況比較分析(單位:元/年)
3流出經歷對農民工社會信任狀況的影響
(1)不同流出時間農民工社會信任狀況的比較通過對不同流出時間農民工的信任狀況(見表7)比較分析發現:在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方面,不同流出時間農民工不存在顯著性差異,在制度信任方面,存在顯著性差異。一般而言,外出時間越長,農民工的城市閱歷越豐富,城市適應能力也會越強,因此理論上來說流動有利于提高農民工對城市居民和陌生人的信任度。[6]但是在本項研究中發現流動時間的長短對普遍信任不存在顯著性的影響。關鍵在于目前我國農民工的城市融入狀況不太樂觀,城市融入程度低,不能享有與市民同等的權利,從而導致其普遍信任水平并未隨著外出務工時間的增加而提高。在制度信任方面,外出務工的時間越長,制度信任水平越低。剛剛進城務工或進城務工時間還沒有多長的農民工,對于融入城市生活、實現自我具有較高期望,而隨著外出務工時間的增長,他們會經常感受到自身的權益被侵害,得不到保障,無法真正地融入城市生活,從而導致他們對制度的信任程度降低。處在社會主義轉型時期的中國,對于農民工這一特殊群體的利益保護方面,還存在很多制度上的缺陷和不完善,這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農民工對制度的信任程度。

表7 不同流出時間農民工社會信任狀況的比較分析
(2)不同流出地點農民工社會信任狀況的比較
通過對不同流出地點農民工信任狀況(見表8)的比較分析發現:在普遍信任方面,不同流出地點的農民工不存在顯著性差異,在制度信任和特殊信任方面,存在顯著性差異。在制度信任方面,在本鄉、本縣、本地區務工的農民工的信任程度要高于在本省、外省務工的農民工。農民工對政府、法院等的信任程度與其對農民工的支持與幫助程度緊密相關。有學者研究表明,政府幫助程度對提高農民工對政府的信任有顯著的正面影響,即政府對農民工的支持與幫助越多,則會獲得農民工更高程度的信任。[6]在本鄉、本縣、本地區務工,農民工獲得的政府的幫助與支持會相對較高,因此他們對制度的信任程度也會相對越高。特殊信任方面;在本鄉、本縣務工農民工的信任程度要高于在本地區、本省、外省務工的農民工;在本鄉、本縣務工的農民工其鄉土性更強,信任模式仍更傾向于農村社會的熟人關系信任模式,對家人、朋友、鄰居的信任程度更高。

表8 不同流出地點農民工社會信任狀況的比較分析
(3)不同流出行業農民工社會信任狀況的比較
對不同行業的農民工信任狀況(見表9)的比較分析發現:在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方面,不同行業農民工不存在顯著性差異,在特殊信任方面,不同行業農民工存在顯著性差異,信任程度具體表現為,農業>建筑裝修業>其他行業>商業服務>制造行業。原因可能在于在農業和建筑裝修業務工的農民工由于其行業特征、接觸對象范圍的局限性使其保留了比較強的鄉土性,其信任模式主要還是熟人信任模式,對家人、朋友、鄰居的信任程度比較高,而在制造行業和商品服務行業務工的農民工由于其行業特征、接觸對象范圍的寬廣性使其保留的鄉土性相對較弱,其信任模式發生轉變,對家人、朋友、鄰居的信任程度相對減弱。

表9 不同流出行業農民工社會信任狀況的比較分析
四 結論與討論
本項研究通過對西部12省市成年人的抽樣調查,分析探討農民工這一特殊群體的信任狀況及其相關因素。通過研究,得出以下結論:
其一,總體來看,農民工的社會信任水平處于中等水平。具體而言,農民工信任平均得分最高的是特殊信任(4.18)處于較高水平,其次是制度信任(3.44)處于中等水平,最后是普遍信任(2.34)處于較低水平。農民工對政府、法院、社會上大多數人的信任水平還有待提高,尤其是對于社會上大多數人、陌生人的信任狀況很不理想,這對于農民工的城市融入、現代化建設以及和諧社會的構建都非常不利。農民工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入,工業化、城鎮化的不斷發展,農民工已經成為我國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在推動中國工業化、城鎮化、經濟的快速增長方面起著重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型塑著中國社會的未來走向。所以其信任水平對于其城市融入、現代化建設的不斷向前發展、和諧社會的構建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亟需提高其社會信任水平。
其二,通過對八項指標的測量分析,本項研究發現,農民工的信任狀況存在著差序格局,即以家為核心向外波及的圈狀特征。這和費孝通描述的中國傳統社會的差序格局是吻合的。農民工對家人的信任程度最高,對陌生人的信任程度最低。信任程度從強到弱的具體順序如下:家人>朋友>鄰居>醫院>法院>政府>社會上大多數人>陌生人。具體的,在人際信任方面,存在著差序格局,家人>朋友>鄰居>社會上大多數人>陌生人,以自己為中心,按照交情深淺、熟悉程度、由近至遠呈現強弱差異。個人與家人、鄰居、陌生人等自然人的關系親疏不同,意味著個體對與他們相關的信息的熟悉程度不同,個體對這些不同對象的信任也因而會有程度差異。[3]在制度信任方面也存在差序格局,醫院>法院>政府。信任程度的差異,在于個體對制度承諾的相關信息的了解程度以及對這些承諾實現程度的判斷,個體對不同制度的信任程度理應會因個體對制度承諾內容、制度承諾實現情況等信息的掌握程度而出現類似人際信任一樣的差序格局。[3]
其三,通過本項調查研究,我們發現農民工流出經歷越豐富,其社會信任狀況水平越低。我國農村社會相對于城市社會而言鄉土性還比較濃,受鄉土文化的影響更為深刻,信任狀況也有所差異。在中國農村社會事實上存在著兩種秩序與力量:一種是官制秩序與國家力量;一種是鄉土秩序與民間力量。[7]我國農村社會的信任模式相對于城市社會而言更多的是一種熟人社會信任模式,對家人、朋友、鄰居的信任程度較高,受鄉土文化的影響,農村居民對政府等制度的信任程度也比較高。離開農村進城務工之后,農民工身上的鄉土性隨著其流出經歷的豐富性而發生改變,流出經歷越豐富,其鄉土性會慢慢減弱,城市性增強,受城市文化的影響加深,其信任模式也會發生明顯改變。正如本項調查研究所得出的,如農民工流出時間越長,閱歷經驗越豐富,對政府、法院等制度的了解與理解就越多元,對制度的信任水平也會越低;流出地點范圍越廣,鄉土性越弱,受城市文化的影響越強,制度信任水平和特殊信任水平越低;流出行業所接觸對象范圍越廣,鄉土性越弱,特殊信任水平越低。
提高農民工的社會信任水平,需要政府、社會、市民、農民工自身的共同努力。其一,政府必須要加強相關制度、法律法規的建設,完善、健全農民工社會保障體系,為提高農民工的社會信任水平提供制度與法律保障。政府應重點建設社會福利保險,在農民工養老、醫療、住房、子女教育等民生方面逐步實現農民工與市民的銜接與整合,加強養老保險、醫療保障、保障房建設、農民工子女享受平等教育等,讓農民工享受市民待遇。同時加強農民工權益保護的立法、執法工作,如對于拖欠農民工工資的行為,堅決予以法律制裁,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為農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提供法律、制度上的保障。其二,企業需要加強社會責任建設,提升農民工的組織歸屬感,提升農民工的組織信任、社會信任水平。其三,建立和諧的社會互動,市民也要消除對農民工的排斥,更多地和農民工互動,消除對他們的偏見,讓農民工更好地融入當地社會,更加信任他人,推動和諧社會的構建。其四,對于農民工自身而言,在脫離農村社會的熟人信任模式后,必須不斷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質水平,理性地鑒別和判斷周圍的人和事,哪些能信,哪些不能信,必須予以理性分析、鑒別,而不是盲目地信任抑或不信任,從而真正地建立起農民工人際信任體系。
[1]劉愛玉,劉明利.城市融入、組織信任與農民工的社會信任[J].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2(2):78-79.
[2]張連德.農民工社會信任危機及其思考[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1(3):62.
[3]鄒宇春,敖丹,李建棟.中國城市居民的信任格局及社會資本影響——以廣州為例[J].中國社會科學,2012(5) 132-133.
[4]Luhmann,Niklas.Trust and Power[M].John Wiley&Sons Ltd,1979.
[5]Giddens,Anthony.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J]Stan 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79.
[6]符平.中國農民工的信任結構:基本現狀與影響因素[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2):38.
[7]胡鳴鐸,牟永福.權力與信任:基于中國鄉村社會的考察[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6):22.
B84
A
1004-342(2014)05-01-05
2014-06-30
本文為2011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新生代農民工婚戀問題研究》(項目批準號:11BSH033)和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2010年度一般項目《工作壓力與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適應研究》(項目批準號:SC10B062)的階段性成果。
何麗(1990-)女,成都理工大學碩士研究生;許傳新(1975-)男,成都理工大學文法學院教授,社會學博士,碩士研究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