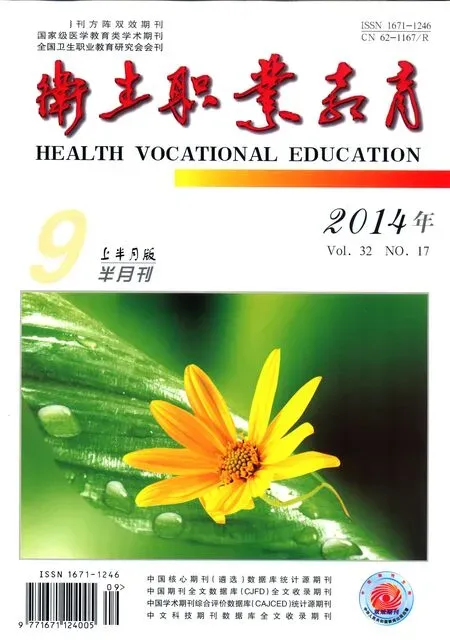借鑒澳大利亞職業教育經驗找準職業院校在辦學中的角色定位
蘇緒林,蔡興東,秦建設,劉 洋,張訓浩
(重慶三峽醫藥高等專科學校,重慶 404120)
借鑒澳大利亞職業教育經驗找準職業院校在辦學中的角色定位
蘇緒林,蔡興東,秦建設,劉 洋,張訓浩
(重慶三峽醫藥高等專科學校,重慶 404120)
借鑒澳大利亞職業教育經驗,認為構建職業教育立交橋主要是政府的職責,制定專業人才培養標準主要是行業協會的職責。職業院校應在辦學中找準角色定位,把主要精力放在以學生為中心、以能力為本的教育教學改革中,切實提高人才培養質量。
澳大利亞;職業教育;角色定位
筆者曾兩次赴澳參加職業教育學習,對澳大利亞職業教育的培訓包、職業資格框架體系、以能力為本的教學模式有一定認識。在建設示范院校過程中,筆者曾先后與十余所高職示范院校教師進行了深入交流,先后受教于姜大源、趙志群等多名職業教育專家,深感我國高職示范院校在建設和改革中承擔了太多職責。筆者不禁思考其原因,并試從澳大利亞職業教育中尋找答案。
1 借鑒澳大利亞的職業教育體系,找準在構建職業教育立交橋中的角色
1.1 澳大利亞職業教育體系
澳大利亞建立了職業資格框架體系,實現了中學教育、職業教育(包括職業學歷教育、繼續教育和短期培訓)、高等教育的對接與互通,相互間學分可互認,畢業文憑可分級對接。
澳大利亞職業教育建立了立交橋,經2013年修訂,TAFE(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學院或其他認證機構可頒發1~4級證書、文憑、高級文憑、研究生證書、研究生文憑共8級文憑[1]。同時制定了職業教育能力標準體系——培訓包,規定了從業者在工作崗位上有效工作所必需的技能和知識標準。培訓包是澳大利亞職業教育與培訓的一個主要特色,是統領整個澳大利亞職業教育與培訓的綱領性文件,它對各級文憑間能力培養的要求進行了統一和對接。培訓包公開透明,可通過國家專門的培訓網站查詢[2]。
1.2 我國職業院校在構建職業教育立交橋中的角色
我國成人教育、職業教育、普通高等教育之間有一定聯系,但尚未建立職業教育立交橋,沒有成為相對獨立的體系。《國家“十二五”教育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建立“學歷教育與非學歷教育協調發展,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相互溝通,職前教育與職后教育有效銜接……終身教育體系”。
借鑒澳大利亞職業教育體系,我國一是應建立自己的職業資格框架體系,完善中學教育、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體系框架,建立各類教育立交橋,實現各類教育的銜接;二是完善職業教育體系,建立中職教育、高職教育、繼續教育和各類培訓的立交橋,實現各級職業教育的對接;三是應組織建立培訓包,將職業教育與國家職業資格認證有機融合,實現畢業證與職業資格證統一,實現教育與就業的對接。
建立職業教育體系是一項系統、復雜且艱巨的任務,需由政府組織制定并權威發布。在示范院校建設過程中,許多學校做了諸如中職與高職的對接[3]、職業資格證書與畢業證書的對接[4]等工作,這些探索提供了一定的借鑒,但作用極其有限。筆者認為構建職業教育立交橋,關鍵看政府。只有教育部門、各行業主管部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等部門強有力地組織,實現各級政府部門的對接,方能取得較好的效果。所以,在構建職業教育立交橋中,政府是主角,只要建立了學歷資格證書體系,中職與高職的銜接通道就自然打開,職業院校就無需“上下探索”,只需做好本層次人才培養即可。
2 借鑒澳大利亞行業企業參與體制,找準在制定人才培養標準中的角色定位
2.1 澳大利亞行業企業參與職業教育體制
澳大利亞行業技能委員會在職業教育中起主導作用[5],主要體現在培訓包的開發和更新過程中,行業技能委員會是主導者和制定者。培訓包由政府牽頭,具體由行業技能委員會主導開發設計,由行業專家顧問、學校、政府、社會專家(有行業經濟導向分析能力)組建團隊進行開發。行業技能委員會能把握行業發展狀況,了解行業人才需求,能將職業崗位能力要求進行一定程度的細化,以能力單元形式確定下來。它將制定的人才培養標準交由國家培訓質量委員會進行質量認證,認證合格后經政府權威發布,自然能被廣泛認可,成為學校培養人才的統一標準。
澳大利亞勞動力匱乏,企業一方面需要大量聘用職業教育畢業生,另一方面也積極主動地承擔培訓任務。只要經過國家培訓局認可,任何機構、企業和個人都可以承擔培訓任務,政府一視同仁地給予經費支持[6]。許多學生一邊學習一邊工作,其在T A F E學院學習時,部分課程可在工作單位學習,并可在工作單位考核。所以,澳大利亞企業既有巨大的內在動力參與職業教育,也有相關法規等外在因素促使其重視職業教育。
2.2 我國職業院校在制定人才培養標準中的角色
我國行業學會也參與到職業教育中,但是行業企業對職業教育的認識、參與主動性及發揮的作用都不夠。我國也建立了職業分類及基本的行業規范,但無系統的職業教育培訓包,無專業能力標準。
在示范院校建設過程中,各學校積極探索校企合作機制,部分學校組建職業教育理事會,由學校牽頭邀請行業專家、教育專家、學校教師等成立專業建設委員會,按照工作過程系統化的要求,從工作領域、行動領域、學習領域分析構建專業課程體系和能力標準[7]。面對跨界的職業教育[8],這樣做存在較多問題,一是針對同一個專業,多個學校重復做,浪費人力、物力和財力;二是制定的標準不權威,得不到行業企業的認可,也得不到相關院校的認同。
筆者認為,在制定專業人才培養標準中,行業學會應是主角,應該由政府牽頭,行業執筆,教育部門參與,建立中國的培訓包,完善職業資格證書的標準體系、質量認證體系和應用體系,尤其要明確各職業崗位能力要求,細化能力單元。學校的主要任務是根據行業制定的標準培養人才。實際上,我國相關部門已經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如當前國家組織了43個職業教育教學指導委員會[9],正在研究制定全國統一的專業教學標準。遺憾的是,雖然吸引了不少行業人員參加,但是組織者還是教育部門,政府部門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如果由政府建立綜合協調機構,組織各行業主管部門制定標準,其效果會更好。更關鍵的是,我國應完善職業教育法規,明晰政府、行業企業、學校在職業教育中的權利與義務,從體制上解決行業參與不足、校企合作只是學校“一頭熱”等問題,建立長效運行機制。
3 借鑒澳大利亞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找準在人才培養中的角色定位
3.1 澳大利亞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
澳大利亞的培訓包只規定應該達到什么目標要求,但對具體培訓和教學模式沒有做強制性要求,各教育培訓機構可根據學生情況和相應證書的能力要求,靈活開展教學。
澳大利亞接受職業教育的學生多為有從業經驗者,學習目標明確,入學時學校會對學生進行多項評估和分析,教學安排最大限度地為學生考慮。學生生活基本獨立,學校基本不考慮學習外的管理。對學生實施先前能力評估,即學生先前所學的知識和技能,不論是通過何種方式、在何時何地學到的,均可在入學時通過相關考核得到認定并折算為學分,以免修相應的模塊課程[10]。
教學以能力為本,以學生為中心[11],教師是引導者和幫助者,教學目標是幫助學生掌握各能力單元。為達成能力培養目標,各學校采用和開發的教學資源非常豐富,實訓操作時每人均有操作工位,如調制雞尾酒時,不論用料多貴,均使用真材實料。
3.2 我國職業院校在人才培養中的角色
我國也在大力倡導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但仍存在以下問題:一是傳統教學模式根深蒂固,以學生為中心教學“形似”多于“神似”。二是教學資源相對不足,班級規模較大,不能很好地滿足每個學生的學習要求。三是基本上未實施學生先前能力評估,在一定程度上浪費了人力、物力和財力,也浪費了部分學生的時間。四是面向專業和課程等過程性評價多,但未真正建立以學生為中心、以能力為本的評價機制。
筆者認為,在人才培養中,職業院校是主角。借鑒澳大利亞經驗,職業院校應從4方面深化教育教學改革:一是以學生為中心,將教學焦點對準學生,因材施教,在培養學生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同時,應注重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學習方法,增強學生的社會適應能力。二是著力提升教師能力,轉變教學觀念,從說教者轉變為引導者,讓學生成為課堂的主角,實現有效課堂。三是大力開發教學資源,尤其要注重整合市場教學資源和數字教學資源建設,為學生學習提供有力的條件支撐。四是改變評價方式[12],建立以學生為中心的評價體系,注重學生職業能力測評,注重第三方評價,讓評價更加客觀真實并能促進人才培養質量的提升。
[1]The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Council.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Second Edition January 2013[DB/OL].http://www.aqf.edu.au/wp-content/uploads/2013/05/AQF_Issuance_Jan2013.pdf,2013-11-25.
[2]Australian Government.Training Package Search[DB/OL].http://training. gov.au/,2013-11-25.
[3]付海濤,段玉明.中職高職教育銜接新探[J].時代教育,2013(15):227.
[4]申慧林.高職院校學生職業資格準入路徑研究[D].楊凌:西北農林科技大學,2012.
[5]魏體麗.澳大利亞行業技能委員會研究[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13.
[6]易燁,石偉平.澳大利亞新學徒制的改革[J].職教論壇,2013(16):89-92.
[7]姜大源.論工作過程系統化的課程開發[J].新課程研究(中旬刊),2012(9):5-7.
[8]姜大源,王澤榮,吳全全,等.當代世界職業教育發展趨勢研究[J].中國職業技術教育,2012(18):5-14,16.
[9]43個行業職業教育教學指導委員會成立大會在上海召開[J].教育與職業,2011(1):116.
[10]王紅玲.澳大利亞先前學習認定制度探析[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2(11):78-83.
[11]劉培林.以學生為本促進中國職業教育的發展[J].遼寧高職學報,2010(3):1-3.
[12]趙志群,莊榕霞.職業院校學生職業能力測評研究[J].職教論壇,2013(3):4-7.
G420
A
1671-1246(2014)17-0016-02
注:本文系重慶市教委高等教育教學改革研究項目(133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