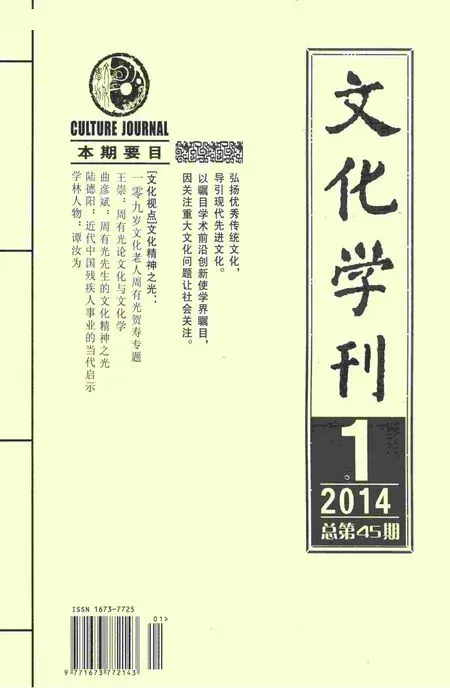啟蒙問題和信仰問題
吳 思
(《炎黃春秋》雜志社,北京 100045)
首先祝賀周有光老先生的生日。
周老師幾次參加《炎黃春秋》的會,這是我們的榮幸。我們每次開會,先向蔣彥永大夫請教一下,問周老先生的身體怎么樣,如果身體很好我們就敢請,如果身體不太好,我們就等下一次。
今天會議的題目是“新啟蒙與當代知識分子的責任”。我看到這個題目,先愣了一下。新啟蒙已經說過好幾次,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就在搞新啟蒙,“五四”的時候也在搞啟蒙,后來我們改革開放、解放思想,還是啟蒙。什么時候啟蒙是個頭?什么蒙住了我們,我們要啟什么蒙?我愣就愣在這兒。
我是這么想通的:每個話語體系,每個思想體系,每個觀念體系,都揭示了一些真相,也蒙蔽了一些東西。無論選擇哪個視角,看到的東西都難免有缺陷。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經常被語言和觀念體系約束,被蒙住了眼睛。至少,存在某一個盲點,有看不見的東西。這樣來看,啟蒙的價值是長期存在的。事實上,中國歷史上也有幾次大的啟蒙,也就是重大的觀念變遷和話語變遷。
史上可見的第一次啟蒙,是儒家對商代神鬼觀念的啟蒙。我們看《尚書》,滿篇都是上帝,天命,那個時代有大規模的祭祀,人殉,動輒向鬼神占卜。在儒家看起來,這就是蒙。子不語怪力亂神,子罕言命,用常識和人心解釋世界,這就是一次啟蒙。從儒家派生的法家大講利害,那就更不用說了。
“五四”時代又來了一次啟蒙,用民主科學啟儒家三綱五常之蒙。伴隨著白話文運動,民主科學的話語迅速普及。
到了上世紀三十年代,馬列主義者搞起了新啟蒙,就是陳伯達他們倡導推動的那場運動。這次啟蒙怎么評價?我有點犯糊涂。一方面叫新啟蒙,另一方面又有人說,這是救亡壓倒了啟蒙,但從后往前看,改革開放初期,大張旗鼓地解放思想,發動真理標準的大討論,這個事實至少給出一個暗示:三十年代的新啟蒙不是合格的啟蒙。至少,新啟蒙留下來的蒙很多,比起“五四”時代的科學民主話語來,還有倒退之嫌,所以需要再一次解放思想。當然,新啟蒙也引進了許多重要觀念,例如階級斗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發展生產力如何重要,等等,如今回顧起來,確實具有啟蒙的意義。
再往后就是改革開放、解放思想。這是第四次啟蒙,啟個人迷信之蒙。
現在我們面對著第五次啟蒙。我們現在談的啟蒙是什么東西?什么在蒙我們?這就是周有光老師所處的歷史方位。他大聲疾呼,我們看他的文章,就能找到問題的答案,我這里不重復了。
什么時候啟蒙是個頭?我猜想,什么時候世界上的主流觀念成了“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多元化了,各種觀點可以互相批評證偽了,百花齊放了,那時候,就不用大談啟蒙了,因為沒有某種強大的勢力及觀念體系成心蒙你。這時候,在基本制度方面,啟蒙的任務就算完成了。這是從反面下定義。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就了解真相,我們還要繼續往前走,不斷有新的發現。
借今天這個機會,我向周老先生請教一個問題。
會議剛開始,資中筠先生說到,周有光老先生有一個信仰,就是信仰“規律”——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我聽了這句話很受觸動,因為這也是我的一個困惑。周曉平說,希望會上對周有光先生的觀點提出不同意見。我有沒有不同意見?我有自己的困惑和對我自己的意見,也就是資中筠先生說的,我們是不是信仰規律?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這個科學能不能成為我們的信仰?周老先生似乎把“道”也看作一種規律,所以有《朝聞道集》。“朝聞道,夕死可矣”,正是信仰的地位。這些規律,能夠成為我們的信仰嗎?我不太明白。我想請教周有光老先生,也請教在座的各位。
按照儒家經典的說法,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這個“道”是人性的展開,跟歷史規律還不是一回事。當然,也可以把人性當作科學研究的對象來看,看它怎樣形成,如何展開,可是,科學到了人性面前,恐怕應該止步。我們的人性,我們自己創造出來的自己的人性,難道是可以預定的嗎?一旦人有了充分的自由,沒有衣食溫飽的束縛,超越了生理學的領域,人類精神和人性的發展就進入了一個我們難以預知的境界。在這個境界里,我們到底是什么,我們將把自己創造成什么樣,科學無法回答,我們自己都無法回答。我們不知道能夠創造出哪些新觀念和新興趣。比如,有的人著迷于圍棋和橋牌,有的人信奉某種宗教,無論進入哪方面的精神世界,都有無窮的發展前景。面對這種復雜豐富和未知,科學有什么辦法?甚至,連科學本身,也是這種精神自由創造的產物。
我們信仰什么?信仰科學規律,恐怕還是一個讓人質疑的答案。應該信仰的是什么呢?我不太清楚。我覺得當代知識分子有很多任務,不光是有啟蒙的任務,還有探索人性的任務,探索可以安頓身心的根基的任務。比如率性,人性到底是什么?哪里是我們的安身立命之處?除了啟蒙,這也是當代知識分子的任務之一。
我向周老先生請教的就是這些。這是我個人的問題,可能也是許多朋友的問題。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