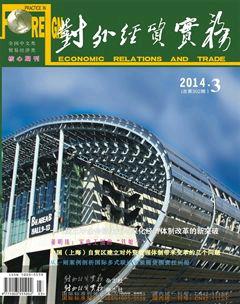WTOSPS“特別貿易關注”對我國食品安全標準的影響
周桂榮 程震

為規范各國技術貿易措施的使用,(WTO)通過了衛生和動植物檢疫(SPS)措施,SPS措施作為國際貿易中廣泛采用的一種非關稅措施,近年來所提出的“特別貿易關注”也呈現出新的特點和發展趨向,并對中國食品安全標準化體系的構建有著截然不同效應的影響。其正面效應的影響集中體現在有助于完善我國“十二五”規劃的食品安全標準化體系構建與國際接軌,以及食品安全管制的規范化管理;而負面效應則體現在SPS措施涉及領域的擴大化,可能會成為貿易保護主義更為隱蔽的手段。基于此,本文提出了要積極適應新的國際貿易特別關注的變化,整合我國食品安全標準不一的狀況,構建與國際標準接軌的食品安全標準體系。
一、 SPS“特別貿易關注”的主要特點與現實
(一) WTO/SPS特別貿易關注的定義及特點
成立于1995年的世界貿易組織(WTO),就食品貿易的《實施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協定》(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SPS)在(法律、法規、規章、標準等)和《貿易技術壁壘協定》(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TBT)(包括技術法規、標準和合格評定程序)作出了詳細的規定。關于WTO/SPS“特別貿易關注”的定義,世貿組織并未給出特別明確的定義。筆者認為SPS協定是為了保護食品安全、動物和植物生命健康而對進口商品設立的強制性法規、標準、檢驗和檢疫要求,而“特別貿易關注”是世貿組織構成的成員國對貿易關注的相關議題給予平等的開放性的磋商,從而為各成員國表達貿易關注和解決貿易紛爭提供的一個平臺。其主要的特點是:
1.以科學依據為前提的原則。按照SPS協定中的規定,科學依據是“各成員的動植物檢疫措施應以國際標準、指南或建議為依據……”,“各成員可以實施或維持比有關國際標準、指南或建議為依據的措施所提供的保護水平更高的動植物檢疫措施,但要有科學依據……”。在食品安全領域涉及的國際標準即為國際法典標準(CAC),風險分析和關鍵控制點制度(HACCP)來進行風險預警管理成為食品安全法規標準的核心內容。
2.問題的通報與解決都是基于自愿的原則。成員方無論是提出關注或是報告關注的解決結果,都是基于自愿的原則。也就是說在SPS委員會上,完全是由成員自己選擇是否提出關注,即便有關成員的SPS措施與《SPS協定》的規定不一致,是否向委員會通報解決的結果,也是自愿性的。盡管參加委員會例會的成員構成呈現出了多邊性的特點。不僅有發達國家,亦有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國家參加這一多邊場合的磋商,但自愿化的原則體現了公平化的特征。
3.非裁決性賦予了關注結果的不確定性。與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不同,在委員會磋商的關注,委員會不會對任何關注做出裁決,或提出任何傾向性的意見。即使在委員會上提出的特別貿易關注,有些明顯與協定不一致,委員會也不會對具體關注做出裁決。但即便如此,關注結果的不確定性其后續的影響也是難以估量的。因為,無論是交流性質的還是關注性質的信息披露,都會提高市場和消費者的敏感度。
4.農獸藥殘留限量標準成為重點關注的領域。近年來,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農獸藥殘留量限量問題關注已成為焦點。一些成員國逐漸完善了農藥的法規標準體系,但同時這些標準體系的變化也成為了其他成員國出口農產品的技術性貿易壁壘而備受關注。從1995-2010年間,各成員國在SPS委員會上對歐盟有關農藥的法規提出了10項“特別貿易關注”。
5.與食品安全相關的關注領域擴大化趨勢明顯。包括轉基因食品標簽、輻照食品等新興食品安全問題也成為了“特別貿易關注”的重要內容,除了農獸藥殘留、污染物、微生物等重要的食品安全問題外,轉基因食品標簽問題也備受關注。美國對轉基因食品標簽采取的是自愿標識的政策,美國的食品與藥品管理局(FDA)負責轉基因作物的食用安全性評估;歐盟采取的是限制規定和標簽要求;日本采取的是強制性標簽和自愿標簽相結合的原則;而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采取的是強制性標識政策,要求凡含有轉基因成分超過1%的食品必須標識。中國亦對農業轉基因生物采取了嚴格標識制度,未經標識和不按規定標識的,不得進口和銷售。不僅如此,有關關注還涉及到對轉基因飼料進行標識,并將追溯性要求貫穿于飼料產品的所有階段。
(二) SPS“特別貿易關注”的現狀
1. “特別貿易關注”的數量呈現出不規律的變化,食品安全仍是關注的重點領域。從圖1可以看出,自1995年至2013年間,成員國向SPS委員會提出的“特別貿易關注”共計344項,其中與食品相關的貿易關注為110項,占“特別貿易關注”的32%,但數量的變化并無規律性可言。1995年和1997年提出的貿易關注項目最少,均為1項 ,2002年提出的貿易關注項目最多,共13項。而在這 13項中,有5項與中國相關,這是因為中國自2001年入世后,首次在2002以成員國的身份參加SPS例會,中國作為重要的食品進出口大國,其實施的SPS措施,受到了主要貿易伙伴的關注。同年日本對食品衛生法的修訂,亦引起了許多國家的關注。
2. 成員國構成的多元化趨勢明顯,中國成為被關注最多的發展中國家。數據顯示,在1995至2013年3月底,發達成員國對62項與食品安全相關的措施提出了“特別貿易關注”,發展中成員國對72項措施提出了關注,發達成員國和發展中成員提出的關注比例為0.86:1,其中有些措施是發達成員國和發展中成員國共同關注的。發達成員國對60項措施表示了支持,發展中成員國對149項措施表示了支持。各成員國對發達國家維持的82項措施及發展中國家維持的47項措施提出了關注。特別需要強調的是,美國和歐盟仍是提出特別貿易關注最多的國家。而中國后來居上,排在成員國前5位,成為被關注最多的國家,這與我國作為消費大國市場的地位密不可分。endprint
二、 WTO/SPS“特別貿易關注”對我國食品安全標準的影響
(一)有助于整合我國的食品安全標準化不一的體系
按照我國《食品安全法》的規定,食品安全標準的宗旨以保證公眾身體健康為主,以做到科學合理、安全可靠為目的,并且是強制執行的標準,除此以外,不得制定其他的食品強制性標準。比照TBT協定,強制執行的食品安全標準屬于“技術法規”的范疇。由于我國科技水平的發展與國際發達國家的差距比較大,其國家食品安全標準制定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和消費者的需求已是不爭的事實,且在食品安全標準的執行中又有國家食品安全標準和地方食品安全標準兩套,盡管地方食品安全標準要參照執行國家食品安全標準,但在實踐中出于區域利益的驅動和企業遵從成本的原理,往往有些企業會選擇容易達標的地方食品安全標準,由此導致了食品安全標準化的濫用、強調國內標準和地方標準實際情況多,采用國際先進標準水平較少的情況。各國所通報的《SPS措施》對我國食品安全標準的完善,無疑形成了強大的外驅推力。政府行政部門的整合和對現有標準不一的食品衛生標準、食品質量標準、農產品質量標準的整合,使得國家食品標準體系的完善更趨國際化的趨勢,食品安全標準取代原來食品的強制性標準,成為唯一的食品強制性標準。
(二) 有助于強化政府對食品安全規制的規范性管理
食品安全規制是針對食品生產鏈條全程管控所采取的條例政策工具的總稱。食品安全標準作為糾正市場失靈,基于政府干預的依據起著關鍵性的作用。我國食品安全規制制度采用的是由政府主導的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政府在治理食品安全事件中扮演著主導角色。當市場不能有效提供社會期望的食品安全產品時,政府可以使用經濟政策或行政手段干預市場產品質量安全狀況。如政府可以通過制定更為嚴格的法規和標準、食品安全補貼、設立檢驗和監督系統等制度安排來滿足食品的質量安全要求和動植物的健康要求,促使私人邊際成本接近或等于社會邊際成本。而采用 SPS 等技術標準和措施干預市場失靈是政府的首選。SPS 等技術標準法規的使用不僅受到WTO 條約的許可,更為重要的是 SPS 技術標準和措施多以法律、法規和安全控制為基礎,可以預防風險的發生,可有效抵制不安全產品上市,具有合法、合理和有效的特征。這為我國政府在食品安全規制化的管理提供了決策參考。
(三)有助于推動食品安全從原料到成品鏈節全程管控標準化治理
近年來,從“特別貿易關注”的內容來看,涉及食品安全的方方面面,除農獸藥殘留、污染物、食品添加劑外,標簽、檢驗檢疫,甚至于對包裝材料、設備使用、加工場所都有嚴格的標準規范。歐盟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進口國,其制定的嚴格食品法規標準貫穿了“從農場到餐桌”的食品安全全程控制過程。這對于我國食品安全全程管控是一大挑戰。在我國由于用于耕作的土壤污染所導致的農產品重金屬超標,已成為新的短期內難以治理的現象。如2013年鎘的檢出率為64.4%,超標率為7.3%。鎘超標食品涉及糧食、水果、食用菌、水產品、動物內臟等,說明在一些地區鎘污染情況比較普遍。在比如食品安全的標簽制度在我國并未做到產品的全覆蓋,有些標簽也形同虛設,無法和實際情況相吻合。2012年韓國提出的對器具和包裝材料要適用通用的生產標準,以及泰國提出的“良好生產規范”特別貿易關注SPS措施,使得食品安全標準化的領域逐漸拓寬。從國際的標準化嚴格要求,到國內的現狀,對我國食品鏈節上安全管控的全過程標準化治理,為我國食品安全管控的完善提供了內驅動力。
(四)SPS措施有可能會成為貿易保護主義的更為隱蔽的手段
在經濟復蘇乏力境況下,貿易競爭更趨激烈。這就迫使各國政府在關稅保護程度降低的情況下,尋找更為有效的非關稅壁壘以保護本國市場和產業。其中 SPS 措施的特點使其成為貿易保護主義的首選。因為 SPS 措施具有合理性,符合保護消費者健康和動植物安全的需要;同時 SPS 措施也是合法的,往往以法律、法規/法令、標準的形式出現;加之,SPS 措施的影響非常廣泛,不但最終動植物產品,而且產品的原料與生產過程、加工方法、加工環境等都納入控制范圍;SPS 措施之所以成為有效的貿易保護手段,還在于嚴格而經常變動的市場準入標準,使遵從 SPS 高標準措施的難度加大,遵從成本提高。另外,SPS 措施引發的貿易爭端還具有難以協調性和耗時性。所有這些特征使得處于標準化發展相對滯后的我國,處于相對被動的局面。農產品貿易既面臨發達國家限制,也面臨著許多發展中國家農產品貿易法規和標準的諸多的挑戰。
(五)標準的差異化有可能會導致貿易量下降或貿易禁止
由于不同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安全標準的水平也不同,內容要求也各異。這就決定了在安全標準上具有絕對優勢的發達國家,在貿易上競爭優勢遠高于發展中國家。一種選擇是遵從其標準的要求,這勢必是耗時和增加成本,抑或是耗時短期內也難以改善,于是導致貿易量下降或貿易中止或禁止。另一種選擇是相互認可對方安全標準。在雙邊政府間舉行談判,一方或貿易雙方認可對方的法規標準,接受國際安全標準或接受第三方設立的安全標準。如果國外的生產者認為他們從生產高標準產品中的所得不足以彌補他們的支出,他們將會終止貿易。
(六)食品安全標準的風險評估在標準制定中面臨挑戰
風險評估是制定食品安全標準的基礎。盡管我國已經在制標的過程中應用了風險評估的科學依據,但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用于食品安全污染物檢測的網點未能實現全覆蓋,加之風險評估的專項基礎性研究薄弱,由此導致通過檢測、調查等途徑獲得的危險性評估數據欠缺。這些因素大大影響了我國食品安全標準的科學性依據。因此,當面對其他成員通報本地區的新發布的食品安全SPS措施時,我國往往由于風險評估能力不夠,數據缺乏佐證,而無法提出有針對性的評議意見,進而也就無法充分利用WTO所賦予的權利。
三、應對策略的選擇endprint
(一)全面構建與國際標準規范接軌的食品安全標準體系
我國是SPS國際標準制定的三個國際公約(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CAC、國際動物流行病辦公室OIE、國際植物保護公約IPPC)的成員國之一,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和SPS國際標準、指南和建議的修訂,既維護我國的利益,也有利于在交流中學習,促進SPS措施的國際協調、增加一致性和協調性。鑒于我國在食品安全標準上還存在很多的差距,因此,我國食品安全標準的制定首先要參照國際標準,以國際標準為藍本,建立符合國際食品法典原則的食品安全標準體系。一方面,要清理和整合現有的《農產品質量安全標準》、《食品質量標準》、《產品衛生標準》以及行業性和地方性標準,統一整合為《食品安全標準》,以確保企業按照統一的標準生產和銷售,也便于監管部門按照統一的標準進行監管。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食品安全檢測檢驗體系。檢測的依據、方法和標準要參照其他成員國的SPS措施和方法,以規范食品安全檢測的統一性、法制性、規范性。
(二)盡快構建全覆蓋的食品安全檢測和評估制度
國家食品安全標準的制定,應當建立在食品安全檢測和風險評估的基礎上。根據中國現實的國情,以及國際標準的要求,首先要建立健全全覆蓋的食品檢驗檢測機構,逐步增設食品和食用農產品風險監測網點,擴大監測范圍、監測指標和樣本量,使風險監測逐步從省、市、縣延伸到社區、鄉村,覆蓋從農田到餐桌全過程。其次,強化專業化的人員隊伍建設,提升對食品安全檢測水平的能力和風險評估的水平,在食品安全檢測方面要采用多樣化的檢測方法,提升檢測的快捷性和準確性;在風險評估方面,積極學習并借鑒國際標準規范的風險評估技術,建立相關的風險評估模型和數據庫,提高風險評估的科學性。最后,強化食品安全檢測的科技支撐能力建設,通過增加研發的投入和實驗室建設,逐步擴大食品安全檢測的范圍,提升食品安全檢測的鏈環節的風險控制點。
(三)積極應對和預防超標準的SPS措施所致的貿易壁壘
由于發展中國家技術水平低,管理薄弱,食品安全的標準水平難以達到超標準的國家要求,由此導致產品難以進入發達國家市場,形成貿易壁壘。對此我們要積極應對。其一是對于超高 SPS 貿易標準,且這類超高標準在提出國國內都未全部執行,而是專門用來限制別國出口貿易,保護本國市場和企業的行為,對于這種歧視性的貿易壁壘我們則需要運用WTO所賦予的權利,和特別貿易關注這一平臺予以解決。其二是對于標準的設立國來說,并非主觀上的壁壘,而是由于我們的檢測設備和水平,或經濟發展相對還處于低端化發展模式,難以達到進口國的要求,這就需要我們充分運用SPS協定所賦予的對其他成員通報的SPS措施進行評議和磋商的權利,認真研究并提出我國的評議意見,積極進行雙邊磋商,爭取將壁壘消除在萌芽狀態,或使有關成員最終出臺的SPS措施對我國的出口貿易的影響降到最低程度。
總之從SPS“特別貿易關注”所具有的特征和近年來的發展情況看,“特別貿易關注”對我國食品安全標準體系的構建具有著兩種不同效應的影響。因此,積極參與并時刻關注各成員國“特別貿易關注”的動態,整合現有的食品安全標準不一的條例條規,構建與國際標準相一致的食品安全標準體系,建立科學化的、規范化的、快捷化的、法制化的食品安全檢測和風險評估制度,則是讓“舌尖上的中國”以綠色、安全聞名、溢滿全球的關鍵所在。
參考文獻:
[1]李海清,陳向前,等. WTO/SPS特別貿易關注磋商機制研究 [J].中國獸醫學報,2012,5(32):798- 803.
[2]田靜,李曉瑜,等. 1995-2010年SPS委員會與食品安全相關特別貿易關注的研究 [J].中國食品衛生雜志,2012,24(6):569-589.
[3]李援.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釋義及實用指南[M].北京:中國民主法治出版社,1998.
[4]曾蓓,崔煥金.食品安全規制政策與階段性特征:1978-2011 [J]. 宏觀經濟,2012,(4):23-28.
[5]董銀果.SPS措施對豬肉貿易的影響及中國的遵從方略研究 [D].西北農林科技大學,2005,(4):23-28.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