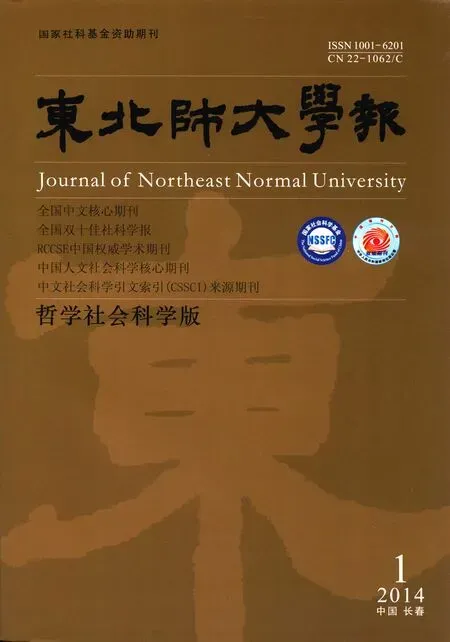論多恩詩歌《出神》的雙重詩意
朱黎航
(1.華中師范大學(xué) 文學(xué)院,湖北 武漢 430079;2.浙江工商大學(xué) 比較文學(xué)與文化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18)
崇高還是荒謬?嚴(yán)肅抑或輕浮?細(xì)讀17世紀(jì)英國玄學(xué)派詩人約翰·多恩的名作《出神》,一種虛幻迷離、難以把握之感始終無法排遣。在這首充滿靈魂和肉體神秘關(guān)系的玄學(xué)詩中,多恩以出人意料的冷靜口吻闡釋了自己的愛情玄學(xué)。他在詩中莊嚴(yán)地宣布:“愛情的秘密確實在靈魂中成長,/然而肉體卻是它的書籍。”詩人以靈魂和肉體的相互依存為理論根據(jù),證明了性愛是獲得理想愛情的必由之路,靈肉相契的愛情才是真正完美的理想愛情。赫伯特·格瑞厄森認(rèn)為此詩是“多恩闡釋愛情玄學(xué),闡釋肉體和靈魂的相互聯(lián)系和相互依賴關(guān)系的最重要的抒情詩之一。”[1]41對于這樣的經(jīng)典評判,西方學(xué)術(shù)界一直存有爭議,甚至出現(xiàn)了一些完全另類的解讀。有人認(rèn)為該詩描繪的是一對情人的第一次性體驗,有人認(rèn)為這是青年多恩對自己的放蕩生活所作的辯護(hù),更有人斷言這是多恩極具迷惑性的又一首色情誘惑詩。評論界對《出神》的多元化解讀正說明了此詩的復(fù)雜多義。本文試圖融會西方學(xué)術(shù)界看似水火不容的觀點,對《出神》進(jìn)行理性層面與感性層面的雙重解讀。
一
西方學(xué)術(shù)界對于《出神》一詩的另類解讀始于皮埃爾·萊構(gòu)斯(Pierre Legouis),他在1928年出版的著作《匠人多恩:論〈歌與十四行詩〉的結(jié)構(gòu)》中提出了與以格瑞厄森為代表的正統(tǒng)觀點截然對立的看法:此詩不過是“學(xué)者唐璜”對肉欲之愛的詳細(xì)闡述[2]。皮埃爾·萊構(gòu)斯用“學(xué)者唐璜”來戲稱青年浪子多恩,其用意不可謂不深刻。“學(xué)者”點明了多恩學(xué)問詩人的特點。多恩確實學(xué)識淵博,且好以各類新奇的知識入詩,而“唐璜”則道出了青年多恩縱情聲色的本性,因為在西方文化中,“唐璜”差不多就是好色之徒的代名詞。青年時代的多恩放蕩不羈,熱衷于追逐女性,好寫艷詩,浪子行徑確實與唐璜無異。萊構(gòu)斯認(rèn)為,《出神》詩中那位道貌岸然的說話人表面高尚的言論只是為了引誘女主角,達(dá)到自己性欲的滿足。因此,萊構(gòu)斯斷定《出神》乃是多恩的又一首誘惑詩,只是手段更巧妙,方法更隱蔽。萊構(gòu)斯直言詩中的男性發(fā)言人就是一個狡猾而偽善的色情騙子,他用莊嚴(yán)的語詞將世俗的肉體之歡提升到了精神之愛的高度,而詩中的女性則是一個誠摯天真的新柏拉圖主義式的情人。要說服這樣的誘惑對象,男主角自然要戴上哲學(xué)情圣的面具。至于詩中男性發(fā)言人莊重嚴(yán)肅的論辯口吻只是多恩采用的更為聰明、更具迷惑性的誘騙手段。
萊構(gòu)斯的驚人之語很容易令人將《出神》與多恩那兩首著名的色情誘惑詩《跳蚤》、《上床》(哀歌第19首)聯(lián)系起來。細(xì)讀這三首詩歌,不難發(fā)現(xiàn)其中的相似之處。在這三首詩中多恩均使出了他擅長的邏輯論辯,雖然三首詩中的男性發(fā)言者論辯的態(tài)度各不相同,一個莊重、一個戲謔、一個粗暴,但三人論辯指向的終極目標(biāo)卻顯然一致。
萊構(gòu)斯的斷言完全顛覆了學(xué)術(shù)界對《出神》的傳統(tǒng)解讀。自萊構(gòu)斯以后,詩中的各種意象、奇喻、暗示都成為批評家們仔細(xì)追蹤的對象。評論界從各個角度對《出神》加以研究,探索詩人的思想來源以及和其他文學(xué)作品的互文性關(guān)系,以至于當(dāng)代多恩研究專家約翰·R·羅伯茨下了這樣的斷語:“沒有任何一首多恩詩歌像《出神》這樣持續(xù)不斷地經(jīng)受著批評界形形色色的批判性和學(xué)術(shù)性的細(xì)篩,然而盡管批評家們竭盡所能,卻完全無法使這首詩歌適應(yīng)于他們設(shè)置的任何一種解讀模式。”[3]65詩歌文本意義的唯一性和終極性被徹底消解。
萊構(gòu)斯譏諷以格瑞厄森為首的傳統(tǒng)派把《出神》一詩看得過于認(rèn)真,他的偏激觀點雖然和者不多,但反響極大。任何人再讀《出神》,都無法漠視萊構(gòu)斯的觀點。確實,雖然多恩在詩中以凝重冷靜的莊嚴(yán)筆觸宣揚靈與肉的結(jié)合及其神圣性,但詩中多處明顯的性暗示又使讀者懷疑詩人的真誠,會有一種恐被愚弄的擔(dān)心。想想多恩在他的諸多哀歌中潑灑的游戲人生的浪子筆墨,這種擔(dān)心顯然不無道理。他當(dāng)真是在探尋理想愛情的真諦,還是在對自己的輕薄行徑進(jìn)行堂而皇之的辯護(hù)?抑或只是一次更為巧妙的文字色情游戲?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有必要對此詩進(jìn)行更深層次的解讀。
二
本詩英文題為The Extasie,這個題目涵義極為豐富。“extasie”源自古希臘語“ekstasis”,原義為“放在外面”、“置于自身之外”,意謂靈魂超越自身的狀態(tài)與超常實在溝通,與柏拉圖所稱的迷狂(mania)所指同一。“ekstasis”后來成為新柏拉圖主義的著名術(shù)語,指人的靈魂脫離身體,在一種超然物外的迷狂狀態(tài)中達(dá)到與神的合一。到了中世紀(jì),基督教神秘主義哲學(xué)又糅合了基督教教義和新柏拉圖主義的觀點,認(rèn)為要達(dá)到人神合一的境界,靈魂必須擺脫自己所依附的感性肉體的羈絆,凈化自己,才能在一種無物無我的迷狂狀態(tài)中與上帝合而為一。需要指出的是,在16、17世紀(jì),“extasie”常常只是用來指靈魂從肉體中分離出來。多恩的這首詩也是如此,逸出肉體的靈魂并不是去和上帝溝通,而是去和情人的靈魂對話。這就使這首詩具有了哲學(xué)、宗教以及性愛等多重內(nèi)涵。遺憾的是,中文譯名很難兼顧這么多的涵義。國內(nèi)的譯名以筆者所見有5種,它們分別是《出神》、《恍惚》、《靈魂出竅》、《狂喜》和《心醉神迷》。前三個譯名側(cè)重以哲學(xué)、宗教的涵義解讀,后兩個則側(cè)重肉體性愛的暗示。本文借用的影響較大的譯名《出神》雖保留了新柏拉圖主義的神秘哲學(xué)內(nèi)涵,但意義卻是單一的,原題擁有的性暗示被遮蔽了。
如詩題所示,詩歌描繪了一對戀人的靈魂在熱戀中升華,逸出軀體,最后又回歸軀體的過程。多恩以涵義豐富的“The Extasie”為題,并以此來構(gòu)思全詩,顯然有使詩歌涵義多元化的企圖。細(xì)察詩歌文本,各種意象、奇喻、場景的暗示及聯(lián)想意義非常豐富,營造了一個充滿肉體欲望的感性隱喻世界,與詩歌莊重嚴(yán)肅的理性敘述基調(diào)形成明顯沖突,從而給讀者帶來了種種矛盾對立的閱讀體驗。上世紀(jì)20年代以來影響最大的兩種矛盾對立的解讀就是上文提到的以格瑞厄森為代表的“愛情玄學(xué)說”和萊構(gòu)斯首開先河的“色情誘惑說”。其實,他們對此詩性質(zhì)截然不同的界定正反映了此詩所具有的鮮明的雙重性。愛情玄學(xué)是《出神》的主題毋庸置疑,而萊構(gòu)斯讀出的色情與誘惑同樣是詩中真實的存在。只有把這兩種南轅北轍的解讀結(jié)合起來,才能更準(zhǔn)確地把握此詩的真意。
多恩憑借《出神》一詩道出了自己對愛情的理解,這是我們從詩歌語義表層即可輕易獲得的信息。《出神》的復(fù)雜在于其詩歌文本具有明顯的表里雙重意識,這種雙重意識傳達(dá)與營造的是精神性與感覺性截然對立的意義與氛圍,它們在詩歌主題強有力的統(tǒng)攝下既相輔相成,又排斥沖突,從而形成詩歌明顯的張力。
《出神》的主題是宣揚靈肉合一的愛情觀,這一主題思想的推演隨著詩中男性言說者的論辯層層深入,邏輯嚴(yán)密,具有濃厚的理性思辨色彩。可以說在詩歌的語義表層,凸顯的是兩個靈魂的交融與對話,使人倍感愛的神圣。但如果對詩歌進(jìn)行深層的語義分析,進(jìn)入多恩用各類意象、奇喻、暗示構(gòu)筑的隱喻世界,得到的感受則大不相同:詩歌表面寧靜神圣的理性之光下掩蓋的是濃濃的情色肉欲。這潛伏著的肉欲氣息是如此濃郁,以至于它不時地溢出詩歌語義表層,與詩歌的理性之光混雜在一起,形成了一種悖論,造成了極具反諷意味的藝術(shù)效果,從而給讀者帶來了困惑迷離的閱讀感受。
三
T·S·艾略特曾夸獎多恩的詩做到了思想與感覺的結(jié)合[4],《出神》就是多恩詩歌中理性與感性和諧統(tǒng)一的典范。本詩一開篇,詩人就通過密集的意象構(gòu)建了一個既具精神性又具感覺性的雙重隱喻世界。
本詩的敘事場景是一個盛開著紫羅蘭的河岸,紫羅蘭在基督教文化中代表著忠貞和謙卑。多恩出身天主教家庭,從小深受基督教文化的熏陶,紫羅蘭意象無疑代表了精神上的高雅圣潔;但“床上的枕頭”、“懷孕的堤岸”……這些曖昧的字眼所構(gòu)筑的意象卻又直指情欲彌漫的床榻,令人浮想聯(lián)翩。詩人在第一小節(jié)就使詩歌表層浮現(xiàn)的圣潔和深層潛伏的色情相互映襯,造成了一種強烈而獨特的精神性與感覺性的聯(lián)合。這種奇特的聯(lián)合看似矛盾沖突,卻與詩人要闡釋的靈肉合一的愛情觀完美統(tǒng)一。
這種對立沖突的雙重詩意在第二、三小節(jié)繼續(xù)延續(xù)。交織的目光、緊粘的手掌……這是一種如膠似漆、水乳交融的默契與激情。戀人雙方手掌的緊合是肉體的接觸,象征著肉體之愛;而眼睛的交流則象征著精神之愛,因為眼睛是靈魂之窗。詩歌開篇三個詩節(jié)塑造的這對有情人正是詩人要表達(dá)的靈肉合一的愛情玄學(xué)的感性顯現(xiàn)。
也許會有人質(zhì)疑二人手掌相合的肉體性愛象征,因為這一詩行中把二人雙手粘合在一起的“香膏”(balm)是一個極富基督教神圣色彩的詞匯。在《舊約》中它是以色列王的圣物,而據(jù)《新約·馬太福音》(26章6-13節(jié))記載,在耶穌被捕前夕,一個女人曾將一玉瓶極貴的香膏澆在耶穌身上,獲得了耶穌的稱許。耶穌甚至說這一行為是為他的安葬而做,值得人們永遠(yuǎn)傳頌。“香膏”一詞果真渲染的只是多恩愛情玄學(xué)的神圣?事實也許不盡如此,伽斯塔夫·克洛斯(K.Gustav Cross)就對這一詩節(jié)中“香膏”做出了完全出人意料的解讀。他將《出神》的第2詩節(jié)和莎士比亞的敘事詩《維納斯與阿多尼斯》的第5詩節(jié)作了比較,提出了一個驚人的發(fā)現(xiàn),這就是“香膏”的秘密[5]。
多恩曾在哀歌第8首《比較》中清楚地將汗液喻為“香膏”(balm):“好像早晨東方萬能的香膏,/這就是我情人胸前的汗珠。”因此我們有理由確信《出神》第2小節(jié)中的“香膏”與《維納斯與阿多尼斯》第5小節(jié)中的“香膏”所指同一,都是汗液的婉稱或美稱。《維納斯與阿多尼斯》出版于1593年4月,后來又多次再版,風(fēng)行一時,而且摹仿之作頗多,可謂影響巨大。這是一首奧維德式的神話艷情詩,講述女神維納斯(即此詩節(jié)中的“她”)對美少年阿多尼斯(即此詩節(jié)中的“他”)的狂熱愛情。在莎士比亞筆下,維納斯與其說是個女神,不如說是個欲火中燒的世間女子或者民間傳說中的狐媚女妖,她百般引誘美少年阿多尼斯與她做愛,言語行為有如蕩婦。伽斯塔夫·克洛斯認(rèn)為,“維納斯的香膏”很可能是當(dāng)時文學(xué)圈中流行的一個笑話。多恩作為身處那個時代的思想前衛(wèi)的時尚青年,很可能讀過此詩,也一定深諳“維納斯的香膏”的色情意義。倘若真如伽斯塔夫·克洛斯所言,《出神》與《維納斯與阿多尼斯》就存在了一種互文關(guān)系,那《出神》一詩的神圣性就要大打問號了。細(xì)讀兩詩,我們還會發(fā)現(xiàn)不少細(xì)節(jié)上的相似之處,比如《維納斯與阿多尼斯》中也描繪了維納斯與阿多尼斯四目相交的情景,還有壓在他們身下的紫羅蘭,而《出神》中也多次出現(xiàn)紫羅蘭的意象。這些究竟是巧合還是詩人有意為之,不同的答案將導(dǎo)致對《出神》的完全不同的解讀。其實進(jìn)一步查考“紫羅蘭”這一意象,可以發(fā)現(xiàn)“紫羅蘭”意象與“香膏”意象一樣也同樣具有神圣和世俗、靈與肉的雙重意味。前文曾指出“紫羅蘭”意象在基督教文化中的高雅圣潔的象征意義,在此還需指出的是,在古希臘神話中,相傳紫羅蘭是愛與美之神阿佛洛狄忒為情人遠(yuǎn)行落淚滴土而生,人們頭戴紫羅蘭花冠來表達(dá)對阿佛洛狄忒這位性感女神的崇拜,而維納斯正是阿佛洛狄忒的羅馬名字。由此可見,《維納斯與阿多尼斯》中“紫羅蘭”意象的出現(xiàn)并非是莎士比亞的隨意書寫,它是維納斯對阿多尼斯赤裸裸的情愛的象征。所以,我們完全有理由懷疑多恩《出神》一詩中的“紫羅蘭”意象同樣具有色情隱喻意義。這一意象和“香膏”意象一樣為《出神》營造出了神圣和世俗交織、精神性和感覺性并存的雙重氛圍。
其實,在詩歌中大膽地描繪性愛在文藝復(fù)興時期并不稀奇,相反這正是時代風(fēng)尚。莎士比亞、馬洛均是這方面的高手。莎士比亞的《維納斯與阿多尼斯》、馬洛的《希洛和里安德》就是這類詩歌的代表。重視和贊美人性、崇尚肉體之愛正是文藝復(fù)興的時代精神[6]。多恩在這首詩中隱含的色情意味完全適合當(dāng)時多恩詩歌閱讀對象的口味。多恩生前只發(fā)表了兩首愛情詩,他的詩歌皆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在他的朋友圈中流傳,他的愛情詩絕非面向大眾,是寫給自己及圈內(nèi)人看的,并無發(fā)表的打算。考慮到多恩的愛情詩多創(chuàng)作于他恣情縱欲的青年時代,因此他詩歌的閱讀對象必是和他教育背景、情趣愛好接近的時尚青年。這些人對多恩詩中的各種暗示和妙語必能心領(lǐng)神會。這也使他的愛情詩少了圣潔的成分,多了游戲的因子,而這正是多恩要的效果。詩歌寫作在多恩那里顯然是一種個人性的主觀智力游戲。作為一名巧智博學(xué)的玄學(xué)大師,他的詩風(fēng)決不是質(zhì)樸簡單,他感興趣的是智力游戲的效果和自娛。因此他在詩歌中巧設(shè)謎團,賣弄詩藝,使詩歌完全可以作截然不同的雙重乃至多重解讀。只有將距離最遠(yuǎn)、矛盾對立的兩種解讀融為一體,才能真正接近多恩創(chuàng)作此詩的主旨。
結(jié) 語
雖然筆者相信《出神》一詩中的種種色情暗示絕對是詩人有意為之,但并不同意將此詩簡單地判定為色情誘惑詩。這是一首經(jīng)過詩人精心構(gòu)思、具有靈肉雙重意味的詩歌,與詩歌所要表達(dá)的主題并行不悖。詩歌表層探討的愛情玄學(xué)和其深層隱喻的性愛世界與詩人所要表達(dá)的靈肉合一的愛情觀是完全諧調(diào)的。正因為這種雙重性,使詩歌既富有靈魂的圣潔,又彌漫著肉欲的氣息,從而形成了一種精神層面和感覺層面的復(fù)雜張力,而這種張力又在靈肉相融的愛情主題的統(tǒng)攝下達(dá)到和諧統(tǒng)一。如果只關(guān)注于此詩莊重的表層語義,就夸大了此詩精神層面的涵義,將其神圣化了;但若只著眼于詩中的性隱喻世界,又將此詩簡單地色情化了。精神之愛與肉體的結(jié)合并舉,才是多恩的真意;精神性(崇高神圣)與感覺性(肉體欲望)的混雜交融才是此詩精心營造,力圖帶給讀者的復(fù)雜感受,多恩想做也確實做到了這一點。
[1]H.J.C.Grierson.ed.The Poems of John Donne[M].Vol.2.Oxford:Clarendon Press,1912.
[2]Pierre Legouis.Donne the Craftsman:An Essay upon the Structure of the Songs and Sonnets[M].Paris:Henri Didier,1928:61-69.
[3]John R.Roberts.John Donne's Poetry:An Assessment of Modern Criticism[J].John Donne Journal,1982,1(1-2):55-68.
[4]T·S·艾略特.玄學(xué)派詩人:艾略特文學(xué)論文集.[M].李賦寧,譯注.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4:12-27.
[5]Cross,K.Gustav.“Balm”in Donne and Shakespeare:Ironic Intention in The Extasie[J].Modern Language Notes,1956,71(7):480-482.
[6]王向峰.亦幻亦真的游走敘事[J].遼寧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