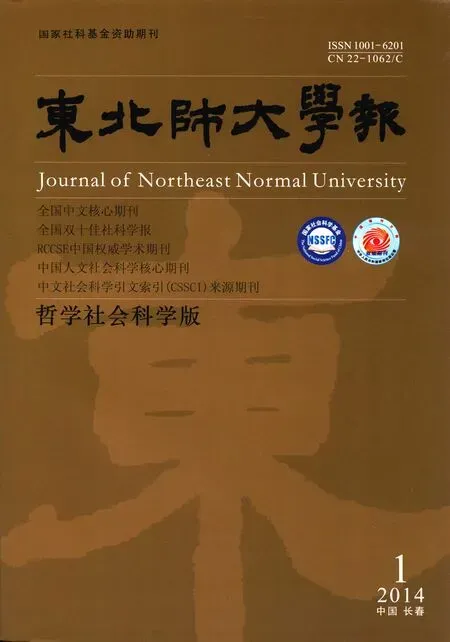梁祝文藝母題的傳說形態考論
匡秋爽,王確
梁祝文藝母題的傳說形態考論
匡秋爽,王確
在中國古代傳說中,梁祝傳說的母題意義和文化價值堪稱典范。從文藝發生學的視角來看,梁祝文藝的發生、發展、繁榮和轉型具有極高的樣本意義和研究價值。通過對史志和文人筆記中關于梁祝傳說的不同記載進行研究,既可以窺見梁祝故事從萌芽、成型到成熟的大致脈跡,同時亦可印證斯蒂·湯普森關于文學母題與民間文學關系的經典論斷。
梁祝傳說;文人筆記;文學母題;民間文學
在我國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梁祝傳說被列在民間文學類別里。傳說是對民間長期流傳下來的故事的記述及評價,有些是以特定歷史事件為基礎,有些則純屬幻想,這些故事的傳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民群眾的要求和愿望。在古代詩歌、民歌和民間故事里有許多傳說的記載。中國以其地大物博的自然資源和歷史悠久的文化積淀在民族土壤中蘊藏著極為豐富的民族文化遺產,在我國數以千計的民間傳說中,《牛郎織女》、《孟姜女》、《梁山伯與祝英臺》和《白蛇傳》以廣泛的流傳性和普遍的認同感贏得了中國四大民間傳說之美譽。這四大民間傳說與其他眾多民間傳說構成了中國民間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成為民間文學的重要載體,對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和審美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梁祝傳說從產生至今歷經一千六百多年,以其獨特的魅力在全世界廣為流傳,被譽為愛情絕唱。梁祝傳說在許多地區和國家留下了深深的印記,追尋其源頭,我們還要從古籍記載的文字說起。
一
梁祝傳說產生于東晉時期,這是幾十年來眾多權威專家和學者們通過對該傳說進行全方位考證所達成的共識。最早提出這一論斷的是近代小說家蔣瑞藻先生,他所依據的是北宋李茂誠的《義忠王廟記》[1]。到了1930年,錢南揚在《關于收集祝英臺故事材料的報告和征求》與《祝英臺故事敘論》中談到梁祝傳說的最早記載,一個來自宋代張津在《四明圖經》中引出唐代梁載言的《十道四蕃志》,另一個來自清代翟灝在《通俗編》中引出唐代張讀的《宣室志》。后來的路工、羅永麟等人經過對梁祝傳說典籍記載的考據研究所得到的結論與錢南揚的說法基本一致。
由此判斷,初唐梁載言的《十道四蕃志》是現今我國最早一部有關于梁祝傳說文字記載的史志。另外,在藏于寧波天一閣的地方志《四明圖經》里可以看到這樣的記載:“義婦冢,即梁山伯、祝英臺同葬之地也。在(鄞)縣西十里接待院之后,有廟存焉。舊記謂二人少嘗同學,比及三年,而山伯初不知英臺之為女也。其樸質如此。”按《十道四蕃志》云“義婦祝英臺與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2]。從其中的“舊記”又可以推斷出,在此之前仍有其他記載,只是沒有保存下來。在南宋乾道五年張津編纂的《四明圖經》中尚且如此記載,足以說明這個故事在民間流傳會更早。明代徐樹丕的《識小錄》中有這樣一句話:“按梁祝事異矣,《金樓子》及《會稽異聞》皆載之。”《金樓子》是梁元帝蕭繹所作,《會稽異聞》已經無從考證。在《四明圖經》這部分記載中,梁祝傳說的祝英臺女扮男裝求學、梁祝同窗三載、合葬這幾個主要故事情節已經清晰,并記載有梁山伯廟的存在,梁山伯樸實憨厚、祝英臺機敏聰慧的人物形象也隱約可見。《十道四蕃志》是以雜記的形式記述梁祝傳說,一直到晚唐,張讀在《宣室志》中用敘事性手法對梁祝傳說加以記述:“英臺,上虞祝氏女,偽為男裝游學,與會稽梁山伯者同肄業,山伯,字處仁。祝先歸,二年,山伯訪之,方知其為女子,悵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馬氏子矣。山伯后為鄮令,病死,葬鄮城西。祝適馬氏,舟過墓所,風濤不能進。問知山伯墓,祝登號慟,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晉丞相謝安表其墓曰‘義婦冢’。”這里明確指出了祝英臺是浙江上虞人,梁山伯是浙江會稽人,梁祝墓位于“鄮城西”,鄮城則是今天的寧波。由此可見,梁祝傳說最早應發源于浙江一帶。《宣世志》中除了交代“化裝求學”、“三載同窗”、“合葬”這幾個情節,還增加了“祝莊訪友”、“求婚遇阻”、梁山伯為縣令、祝馬兩家婚約等故事情節。可以說,此時的梁祝傳說已經基本成型[3]。
二
北宋大觀年間明州知府李茂誠在《義忠王廟記》中則更為詳盡地記述了梁祝傳說,故事情節沒有太大改變,只添加了一些細節。首次出現梁祝二人在求學途中相遇,結拜為兄弟的情節,但是沒有交代結拜的地點。補充了梁祝讀書處為“錢塘”,也就是現在的杭州。寧波天一閣的清代聞性道的《鄞縣志》以文人的寫作筆法,在敘述中加入了不少神化的內容,例如:梁山伯是其母夢見太陽入肚而生;英臺祭墳慟哭,感天動地,墳墓自行裂開將其埋入;梁山伯廟靈驗非常,有求必應等等。唐代的記載中講述的只是一個普通的故事,到了宋代卻將梁祝神化了,極度夸張,這期間或許是李茂誠本人的一己之念,或許是在民間的流傳中發生了變化,百姓賦予了梁祝二人神的色彩,神的力量。梁祝故事經過長期的口頭流傳必定發生細微的變化,而這種變化卻映射出某一時期民俗心理所關注的焦點。根據《義忠王廟記》所記載,梁山伯是位真實的歷史人物,此人在鄮縣任過縣令,百姓為紀念他而建造梁山伯廟,由此產生了《廟記》,這里關于梁山伯的很多信息都是有史可查的,比如梁山伯的生卒年、籍貫、政績等。李茂誠的這篇廟記將梁山伯的人物形象塑造得既樸實賢能又不失氣節,既有歷史真實存在又有傳說故事內容,從而形成了至今為止最早將歷史與傳說巧妙結合的、故事內容最完整的文字記載。民間傳說經常附著于歷史史實,就像歷史中的人物也常被冠以神話傳奇的色彩一樣。這恰恰印證了母題在民間文學作品里是以最小的單位出現,它在作品內容敘述的人物中可分為以下幾種:神話的、歷史人物的、民俗傳說的和小說中的,而這之間并不一定判然分之,往往是雜糅交錯著的。
從寧波地方志《四明圖經》到《宣世志》中明確的祝英臺與梁山伯的籍貫是上虞和會稽兩地,到北宋李茂誠為明州知府(明州即今天的寧波),以及《義忠王廟記》中說讀書處在杭州、墓葬處在寧波,馬文才是鄮西馬家人、梁山伯廟建于公元397年的寧波,這一系列的記載可以認定梁祝傳說的發源地就在浙江東部地區,而且以寧波的可能性為最大。寧波就是古代的鄮城,在寧波的地方志里記錄著歷代縣令,其中赫然寫著梁山伯為東晉鄞縣縣令,今天的鄞州高橋的梁祝墓保存完好,梁山伯廟香火不斷。錢南揚先生于1925年對梁祝墓和梁山伯廟進行了實地考察,寫下了《寧波梁祝廟墓現狀》的田野調查報告,為后來對于梁祝傳說發源的研究提供了珍貴的線索和資料。
三
由于年代久遠,唐宋時期留存的梁祝傳說資料極為有限,從這些文字中我們能看到這個傳說的來龍去脈。那時的梁祝傳說只是一個流傳在民間的故事而已,沒有其他的文藝形式來表現,只有文人將其進行了文學性的修飾,使之讀起來更有趣味。當然,梁祝傳說從最初在百姓之間的口口相傳到引起文人的注意,并將其以文字記錄,再到內容的逐漸豐滿,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故事本身也慢慢的受到民風民俗的間接影響,加上人民群眾在口傳中不斷演繹,將自己的喜好和愿望賦予在這個傳說上,最后在公元1107年《義忠王廟記》的碑記中所呈現的便可稱得上是一個十分完整而又豐滿的梁祝傳說了,至此,梁祝傳說的產生脈絡已逐漸清晰。
到了明清兩代,關于梁祝故事的文本逐漸增多,有黃潤玉的《寧波府簡要志》、張時徹的《嘉靖寧波府志》和《宜興縣志》、馮夢龍《情史類略》中的《祝英臺》和他的《古今小說·李秀卿義結黃貞女》、聞性道的《康熙鄞縣志》、徐時棟的《光緒鄞縣志》、吳景墻的《光緒宜興荊溪縣新志》和《清水縣志》、吳騫的《桃溪客語》和《仙蹤記略》等文獻記載。其中,馮夢龍的《古今小說·李秀卿義結黃貞女》首次將梁祝傳說寫入了擬話本小說,通過小說的寫作手法豐富了故事內容,使其更具可讀性和通俗性,在民眾間的流傳更為廣泛。
作家的文學作品一旦被人民群眾所接受并口耳相傳,就會附上民間文學集體創作的特點,每傳播到一處便會隨著當地的風俗習慣而進行眾人添柴似的創作和改編,使原本的故事越來越豐滿甚至滋生出全新的內容。反過來看,民間文學又對人們的心理、人格等方面起著重要作用[4]。母題常常被作為古代小說與宗教逸聞趣事和民俗故事傳說在歷史文獻上的樞紐環節,正是由于母題與主題相反,主題重在“異”,而母題重在“同”。在《歌德談話錄》中有這樣一段關于詩歌母題的論述:世界總是永遠一樣的,一些情境經常重現,這個民族和那個民族一樣過生活,講戀愛,動感情。可見,母題傳說并不完全是依靠自然力量而保持其生命活力,它更需要在不同時期不同文本和不同形式上有新的組合變化,以滿足人們的趣味喜好和精神需求。在這個漫長的流傳過程中,母題被不斷的重復而顯得越來越有活力和新鮮感。正如西席爾·夏波所說,民間故事能夠反映出整個社會整個民族的審美趣味和情感歸屬,在民眾間的流傳中隨時能夠溶解,又永遠保持著創造精神。民間故事的這種特有屬性愈發推動了梁祝傳說的傳播與發展[5]。
四
衡量某個傳說故事是否具有活力的標準是它在某一地區和某一族群中流傳的范圍與程度,如果這個故事代代相傳,經久不息,說明它具備了某種不同尋常和感人至深的力量;相反,如果我們查閱不到與之相關連續性的史志和文獻,那就意味著這個傳說已逐漸被遺忘,或者說它不具備讓民眾喜愛并傳承下去的特質。也就是說,傳說故事是在廣義的母題系統中被認同接受的,共時性的文化意義需要在歷時性的動態模式中展現凝練。我們現在所熟知的梁祝傳說只是眾多故事版本中的一個基礎版本,或者說是認同度最高的一個版本。由于我國地域遼闊,各地民俗差異較大,所以存在著許多不同的梁祝傳說。據中國民俗協會統計,目前我國大約有十余個版本的梁祝傳說。在浙江寧波的鄞州現存有梁祝墓和梁祝故居,這里相傳祝英臺是明代上虞的一位俠女,梁山伯是金代鄞州的清官縣令,二人均是被權貴所殺害,百姓為了紀念他們,把兩人合葬,結為陰婚。鄞州流傳這樣一句話:“若要夫婦同到老,梁山伯廟到一到。”可見人們對梁祝的尊敬和信奉。在江蘇宜興記述梁祝傳說的《善權寺記》(齊建元二年,公元480年)中說梁祝二人自幼一起讀書,后來到齊魯等地游學而日久生情。宜興有梁家莊和祝家莊,有雙井、九里亭、觀音堂等遺址,還有每年農歷三月二十八的“觀蝶節”,并以梁山伯和祝英臺為蝴蝶命名。梁祝傳說的化蝶情節最初產生在宜興的說法已經得到國內學術界的認可。另外,杭州版本的梁祝傳說講的是祝英臺女扮男裝前往杭州求學,途中遇到梁山伯,結拜為兄弟,并在同一書院共讀三載。明末清初著名的戲曲家李漁正是在杭州居住時創作了《同窗記》,他把書院、草橋、長亭等具有鮮明杭州地域特色的景致寫進故事里,這個書院就是現在位于杭州西湖東南萬松嶺上的萬松書院,當地百姓稱它為梁祝書院,該書院是明弘治十一年在報恩寺舊址上修建的,崇禎年間不幸被毀,直至清康熙五十五年改名為敷文書院。
在各種關于梁祝傳說版本的古籍中,把祝英臺記載為上虞人的約占到百分之八十以上,最早記載梁祝傳說的《宣室志》和《義忠王廟記》中明確指出祝英臺為上虞人。甚至在《辭源》(1915年·商務印書館)和《漢語大詞典》(1986—1993年·漢語大辭典出版社)中所收錄的“祝英臺”詞條也將祝英臺歸為上虞人氏,后來的許多梁祝文藝作品也都無一例外地將祝英臺默認為浙江上虞人。
民間傳說是文藝創作的寶貴素材,自元代起,梁祝傳說便開始了它的變身表演,尤其是在民間,關于梁祝的歌謠和地方戲曲如雨后春筍般層出不窮。元雜劇《祝英臺》又名為《祝英臺死嫁梁山伯》,是元雜劇四大家之一的白樸所作,明寧獻王權《太和正音譜》題作“祝英臺”[6],這部作品比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要早三百多年。元雜劇《祝英臺》的創作問世,成為梁祝戲曲產生與繁榮的奠基石。
[1]蔣瑞藻.小說考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17
[2]周靜書,施孝峰.梁祝文化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23.
[3]王寧邦.梁祝傳說起源時間考[J].藝術百家,2012(6):189
[4]鐘敬文.鐘敬文民間文學論集[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25-29.
[5]朱自強.民間文學:兒童文學的源流[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5):108.
[6]顧頡剛,錢南揚.關于祝英臺故事的戲曲[J].民俗,1930(93):26.
(作者單位:東北師范大學文學院)
[責任編輯:王亞范]
I207
A
1001-6201(2014)01-0223-03
2013-09-12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攻關項目(12JZD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