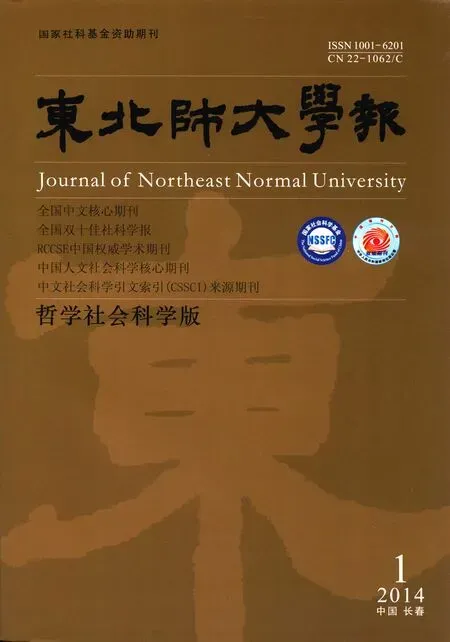中國設計教育中的文化自覺
馬 丹,王鐵軍
改革開放之后的中國設計,與西方世界相比,巨大的差距使“借鑒”與“拿來”成為最快縮短差距的捷徑。渴望發展的迫切心理且有現成的經驗可以使用,在積極行動之余,人及文化的主體意識暫時性地缺失是追趕式發展必須付出的代價。幾十年的積極進取,設計教育的改革已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先行的西方現代化道路上出現的問題在我們的“借鑒”中也隨之出現,相對于現代性的負面效應也隨之產生。改善與自然的關系,重尋精神家園,找回走失的文化自尊成為新時代設計教育的集體聲音和共同訴求。
一、文化自覺概念的提出
1997年,在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舉辦的第二屆社會文化人類學高級研討班上,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首次提出了文化自覺這一概念。所謂文化自覺,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歷史圈子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對其發展歷程和未來有充分的認識,也就是文化的自我覺醒、自我反省、自我創建。費先生說:“文化自覺是一個艱巨的過程,只有在認識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觸到多種文化的基礎上,才有條件在這個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確定自己的位置,然后經過自主的適應,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長補短,共同建立一個有共同認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種文化都能和平共處、各有所長、連續發展的共同原則。”費先生在其80歲生日時說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可以說是其“文化自覺”思想的核心之所在。
二、文化自覺與早期的設計教育
文化自覺反映在設計教育中,即在尊重科學規律的基礎上,建立符合中國的文化特征和審美習俗的中國設計教育體系。用文化自覺的眼光去審視中國建國以來的設計教育發展途徑,對于一些問題可以產生新的認識。在建國初期的設計教育中。以1956年成立的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為例,像德國一樣,以“設計興國”的主旨思想去抬升國家的整體實力,可現實的狀況又令人無奈至極。德國的包豪斯(Bauhaus)是先進的德國工業文明的曙光在設計教育中折射之結果,而當時農耕生產方式是中國社會的生存基礎,農業文明是手工文化的搖籃。以手工文化承載工業文明的設計思想是體用分離的集中表現。加之東方文化的固有特征,以當時的社會現實實現現代設計的教育思想是一個難圓的夢想。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積累了豐富的傳統手工藝資源,從瓷器到印染,從石刻到家具,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傳統手工藝人才,早期設計教育以重裝飾的傳統手工藝教育為主體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而談及文化自覺,則是傳統手工文化在多年的戰亂與破壞之后本能的自覺,對于新設計文化的排斥是一種客觀條件之下的自然之舉。沒有工業社會的土壤,現代設計教育之樹也自無立根之處。手工藝文化與科學技術的分離狀況使得我國早期的設計教育成科學教育的補充,強調裝飾圖案科的學習,滿足衣、食、住、行需要與社會生活的美化是學習內容的主體。用一句話概括,在建國之后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對于傳統手工文化資源的保護性發展以及適度呈現工業文明的早期特征是當時設計教育的基本面貌。
三、當代設計中的傳統文化裝飾元素回歸
隨著社會發展與生產方式的轉變,制造業逐漸成為社會產業鏈條的主體,使得現代設計模式進入中國的設計教育成為可能。在西方世界,自韋伯之后,對于理性主義的重新建構是一個研究問題。以哈貝馬斯為核心的社會批判理論,以交往行為理論來捍衛啟蒙的現代性立場,指出合理性不是傳達和表達的合理性,而是行為的合理性。他承認多元性,“生活世界和系統二元論已成為他(指哈貝馬斯)社會理論的基本框架,現代化可以理解為生活世界和系統的合理化,不同的現代化模式可以根據生活世界和系統的相互關系來分析。”[1]20世紀70年代,西方設計界對現代主義的反思逐漸高漲。幾十年之后,中國人的文化自覺論開始成為學術界的所想。設計教育上的文化自覺同文丘里所倡導的“不傳統地應用傳統”,究其思想內涵基本上如出一轍。正如西方的理論家所說的那樣:“令人可喜的是,由于現代主義建筑理論的失效,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一些理論家,又像19世紀那樣熱衷于討論裝飾問題,于是幾乎消失的傳統術語又回到了當代的藝術語匯之中。”[2]對于先前人類原有的文化土壤的懷念成為現代性洗禮之后設計家們的共同情感訴求。愛美之心是人類各民族的共同意識,“沒有哪個社會不會說話或不會算術;同理,也沒有哪個社會不從事裝飾、美化、圖案設計等活動。或許是歷史記錄的原因,還沒有人在死去時是赤身裸露的,即使裹尸的只是一個腳鐲或身上涂彩。”[3]在21世紀的中國,國際形象的成功展示無一不是民族元素符號的成功使用,從奧運的漢字標識,宣傳畫作品到火炬的中國紅、祥云裝飾,到世博會中國館的設計,對于中國傳統裝飾文化的挖掘、整理越來越為設計師及設計教育者所重視。對于中國傳統裝飾符號的現代性演進是設計教育創新的重要內容,傳統裝飾的回歸是事物發展到極端向相反方向轉化的必然。在整合他人經驗的基礎上,對于在設計道路上還處于初級階段的中國設計教育來說,有以下幾個方面值得注意。
四、對設計教育中文化自覺的若干思考
(一)設計教育中傳統文化的“泛化”問題
在設計教育中提倡文化自覺帶來了對自身文化回歸的思考,有利于設計教育的健康發展,但不要為了文化而將裝飾活動泛化。美國著名建筑師理論家詹克斯曾說過:“后現代主義就是現代主義加上一些什么別的。”[4]由此可以看出,設計教育的出發點還是要以設計為人類服務的產品為重點,而不是為文化而文化,要兼顧現代之合理性。西方社會有一句話同樣適用于設計教育,即:“哲學家不同于哲學教授。”設計教育也不同于設計師的創造。同關注價值理性相比設計師更加關注工具理性,而設計教育既要鼓勵創造還要傳授設計道德。現代主義的缺陷已有目共睹,但其歷史作用也不低估,我們通過裝飾教育來彌補現代主義設計缺乏人類感情的一面,但是除去包含在現代主義設計之中的科學精神,以提倡民族性為理由片面地添加民族裝飾也是不可取的。應當在吸收現代科技的基礎上,創造符合未來社會需求的優良作品才是設計教育的根本。
汕頭大學長江藝術設計學院院長,世界華人杰出設計師,國際平面設計聯盟AGI會員靳埭強先生可以說是將現代平面設計與中華文化的結合推向極致的優秀設計師的典范。作為一個香港人,為了生計,靳先生曾做過10年的裁縫,而后在香港中文大學攻讀了設計課程。在他的設計觀念中,設計如同做裁縫一樣,為他人度身定做是設計服務之本。在他的《漢字》系列海報設計中,山、水、風、云等系列作品以中國水墨畫為創作媒介,在東方意境的“似與不似之間”表達出了東方人特有的藝術觀。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的“和睦和諧”、道家的“師法自然”思想以及中國民俗文化中的剪紙、刺繡、木雕中的視覺元素均成為其創作作品的靈感來源。他的海報設計中,毛筆,尺子,紙扇,玉器造型等以畫面構成要素的形式出現在作品中,成為獨立于西方文化之外的、具有中國文化特征的藝術作品。中國傳統裝飾紋樣及表達方式對于靳先生的創作帶來了豐厚的文化土壤,他的藝術是東方的。可是,我們還發現,他的作品中所涌現出的是東方元素,但畫面組織結構是具有現代主義特征的,是以東方文化及裝飾符號為主導的現代設計作品。在他的作品中,現代依然沒有退去,他的作品是為現代人呈現出具有東方特質的現代藝術品,是西方簡約主義形式美法則之下的東方藝術的再創造,是裝飾與功能的完美統一,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在靳先生的創作道路中,也經歷過20 世紀60年代的全盤西化和70年代的思想覺醒以及80年代的民族化大發展等階段,因此,在他的設計教育中對于設計中的現代化和民族化都深有體驗,成為傳統文化與現代設計觀念結合得最好的實踐者的典范。貢迪南德·莫森在談及中國文化的象征性時這樣說道:“中國人的象征語言,以一種語言的第二形式貫穿于中國人的信息交流中。由于它是第二層的交流,所以它比一般語言有更深入的效果。表達意義的細微差別以及隱含的東西更豐富。”[5]這種中國傳統思想的圖像化、語言的符號化特征與當代設計認識相結合,會產生豐富的設計內涵和深刻的創造想象。
(二)設計教育中的文化復古現象
提倡設計教育中的文化自覺不能因為設計上的文化需求,而走進設計上的文化復古主義中去。文化是動態的,而非固定不變的,文化同樣需要創新。文丘里在他的著作中對于傳統文化在當代設計中的價值,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為建筑師,他提出用“歷史主義”和“民間藝術”兩個方面的裝飾因素來豐富現代建筑設計的語言。針對現代主義設計強烈批判傳統遺產的初衷和立場,他主張用“古代”和“大眾”兩條途徑來使現代建筑具有豐富的審美性和娛樂性。在對待傳統的態度上,他強調現代設計一味地追求革新而忽視了自己是“保持傳統的專家”,而對于當代設計師來說:“利用傳統部件和適當引進新的部件組成獨特的總體,通過非傳統的方法組合傳統部件能在總體產生新的意義。”即后現代設計思想中的“不傳統地應用傳統。”給平淡的要素以不平常的意義,使看似很舊的東西在新的環境中產生“既舊又新,既平庸又生動而豐富的意義。”文丘里主張設計要走裝飾化道路,但不是古典風格的復興,而是以輕松的、折中、戲謔的手法去面對傳統,從“二元論”的角度去解構現代建筑設計的排他性特征。在北京首都博物館的設計中,法國設計師杜地陽對中國文化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將設計理念定位為:“過去與未來,歷史與現代,藝術與自然和諧統一。”設計元素中,清代的丹陛、明代的牌樓、石質的城墻、建筑挑檐、青銅造型及紋飾等中國傳統文化符號與鋼結構棚頂、玻璃幕墻等現代科技有機融合,成為北京長安街上的一個文化景點,從西方社會的角度為我們的設計教育提供了一個成功范例。
這種歷史主義的折中手法在西方后現代設計中已形成了一股時尚潮流,除文丘里外,格雷夫斯、斯特林等一批后現代設計師為當代設計的發展提供了一系列的現成作品,為設計教學提供了示例和理論支持。“現代的藝術家和設計師無法完全使自己脫離習俗。他不能僅因決定脫離習俗而突然聲稱為新史前派。”[6]在今天的中國設計教育中,一批有著深厚東方文化內涵的設計師同樣成為年輕一代的榜樣。對待傳統我們要有清晰的認識,從唯物主義歷史觀來看,儒家、道家抑或佛家文化,均產生在自然經濟基礎之上,是傳統的農耕文明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在文化上的體現[7]。我們在繼承傳統之余更要做到傳統文化的更新,如果中國的設計教育否認現代設計經驗的合理一面去片面追求傳統效應,拿農耕文明去對抗西方的工業文化則是對傳統虛無主義的矯枉過正。中國的設計教育要提倡“文藝復興”,讓幾千年的傳統文化資源服務于當代社會,而非文化復古。我們回望14至16世紀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所復興的是古希臘合乎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思想文化,以文化創新和藝術開拓意識來求得人的心靈解放與精神自由。同時又是對中世紀經院哲學家的思想革命,以傳統文化的精華來武裝人的頭腦,從而促進了西方社會的進步與發展。
(三)文化自覺與設計教育的可持續發展
我們要在總結歷史的基礎上,在設計教育中用理性思維去促進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裝飾文化在現代設計發展的歷程中,從英國工藝美術運動、歐洲新藝術運動、歐美的裝飾運動開始,其存在與否一直是設計界爭論的焦點。現代主義的徹底剝除,后現代時期的復歸在設計者的意識中產生了諸多的思想波折,也就是所有的從事設計活動的人所要必須面對的“形式與功能,傳統與現代”的兩對矛盾的關系問題。設計教育既要對人負責,也要對社會負責。近些年來,公眾質疑的過度包裝問題便是文化情結過度后產生的設計道德問題。月餅盒的包裝過分裝飾,從視覺上讓人感覺到中華傳統節日的愉悅之情,感受到中華文化的獨特魅力和人民生活的日益改善,經濟上也達到促進銷售的直接目的。可是,從設計道德上講則是浪費了紙質資源,加速了環境的退化,增添了地球的負擔,對于國家的經濟建設起到了破壞作用。裝飾讓我們找到了傳統文化關懷,但不切實際的亂用則是成全了“面子”而丟了“里子”的不良行為。因此,合理地利用傳統文化資源,用優秀的傳統文化資源與現代設計的合理化原則相結合去打造符合中國社會消費與審美習俗的設計教育體系,用設計道德標準去規范設計行為是設計教育的核心內容。可持續發展是一個長期的無爭議的論題,設計既要滿足當代人需求,也要有利于未來人類發展。裝飾的回歸帶動了文化自覺思想的發展,合理地整合科技與文化的關系可以使設計更好地服務于人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這也是當代設計教育的重心和出發點。
[1]汪行福.走出時代的困境——哈貝馬斯對現代性的反思[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236.
[2]Isabelle Frank,(ed.),The Theory of Decorative Art:An Anthology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Writings,1750-1940,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14.
[3][英]大衛·布萊特.裝飾新思維——視覺藝術中的愉悅和意識形態[M].張惠,田麗娟,王春辰譯.杭州: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美術出版社,2006:8.
[4]王受之.世界現代設計史[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4:319.
[5]尋勝蘭.源與流:傳統文化與現代設計[M].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07:18.
[6][法]德盧西奧-邁耶.視覺美學[M].李瑋,等譯.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0:138.
[7]楊春時,肖建華.伽達默爾:在歷史主義到審美主義之間[J].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