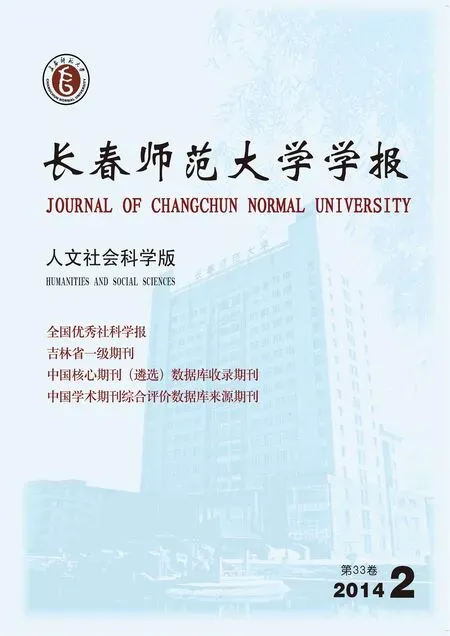認知圖式理論視角下的翻譯人才培養
王 嘉
(東北師范大學 外語學院,吉林 長春 130024)
認知圖式理論視角下的翻譯人才培養
王 嘉
(東北師范大學 外語學院,吉林 長春 130024)
隨著認知語言學的發展與成熟,認知圖式理論被廣泛運用于言語交際。翻譯作為一種雙語互動交際行為,其實質是基于目標語對源語言進行解碼和編碼過程。從認知角度而言,認知圖式是源語和目標語之間解碼的心智工具。因此,本文擬基于認知圖式理論闡釋翻譯構建模式,并進一步提出高校翻譯教學和人才培養的建議與方法。
認知;圖式理論;翻譯教學;人才培養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認知語言學開始興起。認知語言學以體驗哲學為綱,主張語言是人類體驗的產物,將其基本觀點概括為“客觀世界-認知-語言”這一體系[1]。該體系將語言與客觀世界緊密結合,為言語交際活動的解碼帶來認知理據。翻譯作為典型的雙語互動交際,是譯者根據已有源語和目標語的認知對源語言進行解碼和編碼的過程。本文以認知語言學的圖式理論為基礎,提出翻譯的認知圖式模式。
一、認知圖式理論
圖式概念最早是由德國哲學家康德提出的。伴隨著認知科學和認知語言學的不斷發展,圖式論再次受到認知心理學、認知語言學的關注。皮亞杰、巴萊特等認為,圖式是存在于主體內部的一種動態認知結構。人類在認識過程中,只有將不斷接收到的新事物、新訊息通過圖式與表征舊知識相聯系,內部認知結構才能被激活,進而對其進一步理解和記憶[2]。20世紀末,魯姆海德繼承和發展了前人的圖式理論,創造性地將圖式視為“長時記憶中,通過一定等級層次儲存在人腦中的各種相互聯系的知識結構的體系,該體系是人類構建和提高認知能力的基礎”[3]。例如,人們聽到某種動物或看到某一動物圖片,就會在腦中出現該動物的一系列相聯系的集合,包括它的性情特征、生長環境以及其相對的象征形象等。
認知圖式理論具有以下三大特征:第一,認知圖式是以具象知識經驗為基礎的抽象認知結構;第二,認知圖式是通過一定認知規律由某一主體各個部分構成的有機整體;第三,認知圖式是通過“同化“與“順應”作用積極地將新信息與圖式表征的舊知識、經驗加以聯系的互動過程。
二、認知圖式視角下的翻譯模式
基于以上闡釋,我們發現,翻譯與圖式理論類似,是源語和目標語之間解碼和編碼的互動交際過程。在該過程中,源語的理解是解碼之核心,而目標語的表達則是編碼之精髓。因此,我們將其運用于翻譯構建過程中,主張翻譯是譯者將源語文本圖式通過理解轉換成目標語文本圖式的選擇構建過程,即“源語圖式—譯者—目標語圖式”。本文將翻譯活動視為4個基本過程:源語文本的理解,源語圖式的搜索,源語圖式和目標語圖式的隱射,目標文本的生成。
源語文本的理解是翻譯的基礎,其需要譯者掌握足夠的源語言認知體系,包括豐富的源語語料、源語文本背景、源語語言文化等。例如,在翻譯《圣經》時,譯者首先需要了解西方文化,包括西方宗教文化、傳統價值觀、歷史發展與變遷等。找尋源語圖式是翻譯中的重要步驟。在源語理解基礎上,譯者根據源語文本,通過已有認知,在大腦中找尋與之一致的源語圖式。源語圖式的找尋與構建是人腦中對源語言文本認知的產物。例如,在翻譯有關中國長城的篇章時,譯者腦海中往往會呈現與之相聯系的歷史背景、地理風貌、文化價值等認知結構組成源語圖式。源語圖式與目標語圖式的隱射是認知視角下翻譯過程的核心。該過程中,譯者需要在已有的認知圖式中,將源語圖式與目標語圖式相匹配,構成映射。例如,在翻譯“黑馬”時,譯者在生成漢語“黑馬”圖式的基礎上,找尋英語中與之最匹配的圖式。根據英漢對于“黑”這一詞的不同認知,我們可以清晰認識到,英語文化下“dark”是漢語中“黑暗”、“黑夜”的圖式。因此,“黑馬”一詞自然就隱射至“dark horse”。在認知圖式模式下,翻譯的最后步驟是目標語文本的生成。基于源語圖式與目標語圖式最佳匹配,并通過隱射過程,目標語文本意義即可生成。例如,漢語中“紅茶”圖式隱射至英語中“black tea”圖式,因此,我們將紅茶譯成“black tea”,而并非“red tea”。
三、認知圖式視角下的翻譯人才培養
與傳統翻譯觀念不同,認知圖式視角下的翻譯模式將翻譯視為源語文本圖式映射至目標語文本的動態過程。因此,它為高校翻譯教學帶來全新啟發。
(一)培養學生的認知圖式意識
在高校翻譯教學過程中,教師需要培養學生的認知圖式意識。具有良好的認知圖式意識是翻譯教學的首要目標。教師應主動將認知圖式理論傳授給學生,并將該理論與翻譯動態模式相聯系。一方面,在實踐翻譯教學中,教師要通過啟發引導學生,使其不斷掌握和積累豐富的認知圖式,使其能順利地將文本內容轉換為圖式。另一方面,為積累大量認知圖式,教師應鼓勵、指導學生擴展語言知識體系。通過閱讀、觀察、體驗生活等一系列活動,增強學生的文化背景知識,特別是風俗習慣、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價值觀等差異。
(二)教會學生理解認知圖式文本
翻譯的認知文本,簡言之,就是翻譯的系統化結果[4]。教會學生理解認知圖式文本是認知圖式翻譯的核心。在這個過程中,“積木”構建法為提高學生的翻譯認知圖式提供新的視角。“積木”構建法通過將句子按照若干事件或若干詞類進行組合,為各個事物的圖式生成提供參照。教師可將該觀點運用于實踐翻譯教學,引導學生建立以事物為中心的“積木”結構,并運用該結構理解認知圖式文本[4]。例如,在詩句“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中,教師可指導學生構建以“人”和“月”為中心的兩個事件,并分別生成認知圖式。基于對“月亮”呈現的不同形狀的認知和對無法預測的 “人生”的體驗與認知,將漢語中“月亮”與“人”圖示映射至英語“moon”and “men”圖式,其翻譯即可一氣呵成“The moon does wax, the moon does wane, And so men meet and say goodbye”(摘自林語堂先生譯文)。
(三)指導學生進行實踐訓練
在此基礎上,指導學生進行實踐訓練是翻譯教學實踐環節。一方面,教師應盡可能選取不同題材、體材以及年代的代表文本作為學生翻譯練習的材料,使學生掌握不同風格作品的圖式生成,通過實踐習得大量母語和目標語之間的差異,為源語圖式和目標語圖式的隱射提供可能。另一方面,教師需要對學生的翻譯作品進行不斷的修改、評判。通過組織學生自評、小組討論、教師評價等方法全方位地評估學生的作品。這樣,學生在不斷修改、討論中會對翻譯文本有更高層次的理解和認知,從而掌握翻譯圖式轉換,進一步提高翻譯能力。
四、結語
綜上所述,本文以認知圖式理論為基礎,闡述該理論指導下的翻譯構建模式,即源語文本的理解、源語圖式的搜索、源語圖式和目標語圖式的隱射、目標文本的生成四位一體的動態構建過程。在該機制下,筆者進一步提出了翻譯教學啟示和翻譯人才培養建議,為翻譯人才的培養帶來新的理念和教學啟示。
[1] Lakoff,G. & Turner, M.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M].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2]Barlett,F.C. Remembering[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2. 122-124.
[3]Rumelhart, D. E. Schemata: The Building Blocks of Cognition[M]∥R. J. Spiro, B. C. Bruce and W. F. Brewer (Eds. ).Theoretical Issues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Hillsdale, N. 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80.
[4]熊力游. 英譯教學的圖示及其應用[J].中國科技翻譯,2009(4).
2013-12-11
王 嘉(1988- ),女,吉林長春人,東北師范大學外語學院碩士研究生,從事英語筆譯研究。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7602(2014)02-014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