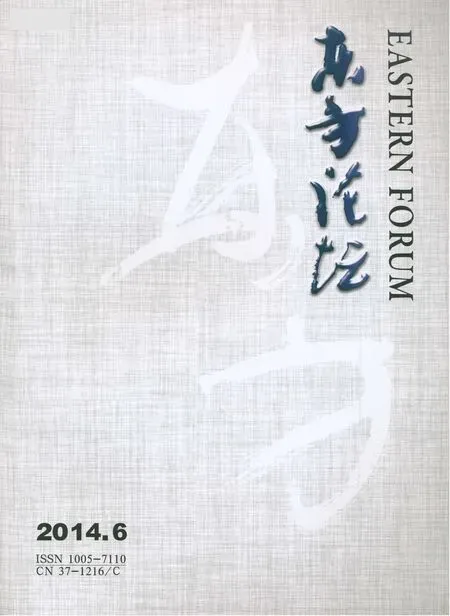試論民族意識對現代白話發展方向的整合
劉 泉
(青島大學 漢語言學院,山東 青島 266071)
試論民族意識對現代白話發展方向的整合
劉 泉
(青島大學 漢語言學院,山東 青島 266071)
在“民族形式”的論爭中,通過“民族意識”的建構,“統一性”與“獨立性”成為了現代白話的內在標準。這種“民族”語言觀念的確立,在發展方向與現實問題兩重層面上,都對現代白話的發展方向產生著重要的整合作用,從而使現代白話被日益定型成為一種“群體化”的公用型書面語言,并使白話的“現代性”與“民族性”之間形成了某種同構關系。
民族意識;白話;整合;毛澤東
20世紀40年代有關“民族形式”的論爭,既是文藝“大眾化”觀念在民族革命戰爭時期的進一步推進,是對新文學自形成起就奠定的民族國家建設宗旨的進一步貫徹;同時又是對時代需求的現實回應,是日趨激化的民族矛盾的必然產物。因此,學界對這場論爭的關注,往往集中在它的意識形態性質,注重梳理論爭中各家各派的政治意識及其先進性等方面。而隨著“民族形式”論爭作為一場歷史事件的塵埃落定,當今的學術界也自然淡化了對這場論爭的研究熱情。
但在筆者看來,有關“民族形式”論爭的研究依然具有價值,尤其其中對于語言問題的諸種論述,都體現出豐富的文化蘊涵與先進的意識觀念。正如汪暉所言,在“民族形式”的討論中,地方形式、方言土語與民族主義運動取得了直接的聯系,并構成了對現代白話文運動的挑戰。[1](P1494)可見,語言作為文學文化革新的必需的載體,在有關“民族形式”的論爭中又一次扮演了重要角色,語言的文化屬性、本體屬性,在“民族意識”的形成中,又一次發揮了重要作用;而民族意識的崛起,又對現代白話的發展,發揮著重要的塑形和規范作用,最終使白話作為華夏民族的現代書面語言形式,得到了最終的確認。就此而言,“民族形式”論爭對現代白話的推進,可謂功不可沒。
一、“民族形式”的語言觀念
“民族形式”論爭中體現出的語言觀念,一方面可視為由“五四”開啟,至20世紀30年代逐步強化的對語言“大眾化”的一致追求;另一方面,則顯示出在現代民族意識與國家觀念的統攝下,語言觀念的核心已經由原有的階級思想內核,轉變為適應于建設民族共同體及現代獨立國家的新型需求。因此,從民族獨立角度而言,語言形式的一致就成為現代中國社會的必然要求。
近代以降,隨著國勢頹敗、領土淪喪,語言文字在凝聚國民意志、提升民族信心方面的特定功用已經為人所關注。當時的國粹主義者鄧實曾經倡言:
合一種族而成一大群,合一群而奠居一處,領有其土地山川,演而為風俗民質,以成一社會。一社會之內,必有其一種之語言文字焉,以為其社會之元質,而為其人民精神之所寄,以自立一國。一國既立,則必自尊其國語國文,以自翹異而為標致。故一國有一國之語言文字,其語文亡者,則其國亡;其語文存者,則其國存。語言文字者,國界種界之鴻溝,而保國保種之金城湯池也。[2](P145)
鄧實將語言看作國家民族存亡的標志,可以說是較早地認識到了語言對民族確立的重要作用。近代小學大家章太炎,對語言文字與國家獨立之間的關系更具有明確的認識。他認為“小學”一門,“這愛國保種的力量,不由你不偉大。”[3](P74)在他看來,,語言文字首先是人內心思想觀念的直接反映,“文字者,語言之符。語言者,心思之幟。遂天然語言,亦非寧宙間素有此物,其發端尚在人為,故大體以人事為準。人事有不齊,故語言文字亦不可齊。”[4](P123)因此,經億萬人共同使用的語言工具,就具有為國家定位民族身份的重要意義,也即“文字政教既一,其始異者,其終且醇化……所謂歷史民族然矣。”[5](P172)同時,語言文字本身,又是作為“立國之元氣”的民族文化中的重要構成,“國家之所以能成立于世界,不僅武力,有立國之元氣也。元氣維何?曰文化。……然吾國自比年以來,文化之落,一日千丈,是則所望于國民力繼絕任,以培吾國者耳。”[6](P267)可見,語言文字的內在價值之一,就在于要匯聚民心、積蓄文化,從而培養國家獨立富強的精神“元氣”。
20世紀30年代前后,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機,使國人的民族主義熱情再次激發并空前高漲起來,國人對語言文字與民族獨立之間的內在關系也形成了更充分的認識與更實際的感受。胡適早在1926年就坦陳:“當然我們希望將來我們能做到全國的人都能認識一種公同的音標文字,但在我們的國家疆土被分割侵占的時候……我們必須充分利用‘國語、漢字、國語文這三樣東西’來做聯絡整個民族的感情思想的工具。這三件其實只是‘用漢字寫國語的國語文’一件東西。這確是今日聯絡全國南北東西和海內海外的中國民族的唯一工具。”[7](P310)胡適所提倡的“用漢字寫國語的國語文”主張,體現出現代知識分子對“民族語言”在凝聚群眾力量、培養民族自信方面的重視,以及對現代白話之統一性、獨立性的現代要求。1938年4月,胡繼存、謝德風在其所著《民族自決問題》一書中,更從學術角度闡釋了語言與民族之間的內在關系:首先,從“共同語言文字與民族意識的發展”來考察,“相同的語言文字往往代表共同經驗和共同情緒,所以語言文字的相同可以證明文化的遺產是相同的,因此可以使彼此感情融洽,同心協力,努力全體幸福的發展。語言文字的確是團結民族精神的金鏈,喚醒民族意識的洪鐘”;其次,從“國語文學”與民族國家統一的關系來看,“語言文字相同的,容易團結起來;反之,語言文字不同,容易發生誤會,結果引起許多無謂的紛爭”,所以若要喚起“四萬萬人民的民族意識”,就必須率先展開統一的國語運動;第三,從語言變更對民族性的影響來看,“語言也和血統及其他文化因素一樣,可以因時因地而變更,國民性也隨之受其影響”,“以武力強迫他族的語言文字改變,使與己的民族性相合的。這是近代帝國主義者常常施行弱小民族的手段,是民族自決運動者所極力反對的。”[8](P12-14)可見,語言的統一與獨立,是一個民族得到統一獨立的精神保障,而語言的變更則會影響到國民主體性格的演變,這就決定了“民族語言”的兩個基本屬性:同一性與獨立性。英國學者埃里·凱杜里對于語言、民族之間特定關系的闡述,也證明了這一點。他認為,“第一,操有一種原有的語言的人們便是民族,第二、作為民族必須操有一種原有的語言。操有一種原有的語言便是忠實于其特性,保持其身份。……再者,事實上,因為一個民族必須講一種原有的語言,因此,其語言必須清除外來的增加物和借用物,因為語言越純潔,它就越自然,這個民族認識它自身和提高其自由度就越容易。……因此,一個民族能否被承認存在的檢驗標準是語言的標準。一個操有同一種語言的群體不僅可以要求保護其語言的權利;確切而言,這種作為一個民族的群體如果不構成一個國家的話,便不稱其為民族。”[9](P61-62)一個民族是否具有統一的獨立的語言,無疑已經內化成為對這個民族是否具有獨立性與完整性的認同標準。
二、“民族”的語言觀對現代白話的整合作用
以統一性與獨立性為標準,“民族”語言觀念的確立,在發展方向與現實問題兩重層面上,都對現代白話的發展方向產生著重要的整合作用。
首先,以“民族語言”為參照,現代白話確立了新型發展方向,即“民族化”與“普遍化”的統一。“民族化”即必須重視屬于漢民族優秀表達傳統的、仍具有現實生命力的語言因素,將其整合進入新文學的用語體系,從而顯示漢語的獨特價值,達到以語言工具凝聚華夏子民、增強民族榮譽感的實際目的;“普遍化”則意味著現代白話在整體上必須進一步完成“五四”新文學革命所倡導的“國語”使命,以統一的語言形式,成為方便廣大人民共同使用的書面語工具,從而更好地服務于救亡大業。
其次,“民族化”“普遍化”的語言觀念,對現代白話語言形式的發展,進行了相應的調整與規劃,從而使“五四”文白轉換后一直存在的某些語言問題,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決:
第一,由于“五四”文白轉換的進程過于快捷,導致漢語傳統因素在現代白話中的缺失,使得知識分子出于豐富表達的需要,不得不向西方語言取經,以至于造成了過度“歐化”的不良現象。在“民族化”的推動下,20世紀40年代文學白話的語言資源,開始明確地傾向于對傳統漢語的自覺吸收,以民族語言的“獨立性”為標準,知識分子有意識有目的地將眼光投向民間文藝語言與方言土語等語言資源,開始注重發掘屬于自己民族的語言特征與表達風格,也即開始追求具有“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的語言形式。“民族形式”論爭中對民間文藝語言資源、及大眾日常用語的探討,就顯示出這一傾向。需要指出的是,現代白話在20世紀40年代雖然關注到了對于漢語傳統的繼承,但其繼承的對象,卻并非古代精英化的文言傳統,而是多見于通俗講唱話本中的民間文藝用語,其原因,除了二者在語言形式上的接近之外,恐怕仍舊難以排除知識分子的“現代性”立場因素。
第二,民族語言的“統一性”要求,還促使20世紀40年代的白話發展,必須整肅自身的駁雜隨意,潛抑之前對個人化表達的重視,轉而追求工整嚴明、表意明確,便于受眾讀解領會的統一范式。這就使現代白話進一步放棄了古代詩文傳統中含蓄蘊藉、“意在言外”的表達風格,更著力于語言的“及物性”,追求能指與所指的同一性、一體性,強調語言對意義的直接傳達,重視如實描寫,略無繪飾。
第三,以“及物性”為指向,現代白話“言文一致”的既定宗旨再次得以強調。從歷次語言論爭的發展來看,“言文一致”始終是貫徹其中的追求與主張。雖然在各個時期,主張“言文一致”的動機各不相同。比如“五四”新文學革命倡導“言文一致”,主要針對文言文“手口相離”,難以即時傳達現代人的觀念意識、生存體驗;而20世紀30年代“大眾語”時期,則針對勞苦大眾低水平文化層次的需要而主張“言文一致”,以促進群眾對新文學作品的接受;20世紀40年代在“民族形式”的論爭中,除強調以“言文一致”的文學作品推動群眾的抗日激情之外,還力求通過“言文一致”的要求,形成普遍的通俗的書面語言,樹立民族統一的凝聚力與自信心,以抵御外來侵略,實現國家自強。
第四,受“言文一致”觀念的統攝,現代白話與“民族語言”之間的內在關系也得以顯現。作為現代知識分子構造現代國民意識的關鍵途徑,現代白話的確立首先體現為對書面表達科學化、條理化的倡導,講求建立統一的語法規則與明確的詞匯語義系統。自近代起,黃遵憲就在其《雜感》詩中寫道,“我手寫吾口,古豈能拘牽?”,至“五四”白話文運動時期,“現代文學運動及其推動者明顯地把這場運動理解為日益口語化的語言運動,這種口語化運動包括了口語的語法結構、詞匯和語音。”[1](P1509)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以“言文一致”為內在宗旨的現代白話文,與日本、韓國現代書面語言體系的生成方式又有顯著不同,后兩者主要追求在語言上擺脫漢語的束縛,并以自己國家的口語系統為中心重新建立書面語言體系與標準語音模式。但中國的現代白話文運動,中國現代語言的建設,并不存在對上述“語音中心主義”的遵循,也并不需要承擔重新創制書面語系統的任務,其中心職能,就在于要“在貧民/貴族、俗/雅的對峙關系中”,確立自身的表達標準與表達體系。可見,“白話文運動的所謂‘口語化’針對的是古典詩詞的格律和古代書面語的雕琢和陳腐,并不是真正的‘口語化’。在與傳統語言的對比中,白話文被賦予了大眾化、民族化的特性,具有了充當民族共同語言的身份與資格。現代白話的主要源泉是古代的白話書面語,再加上部分的口語詞匯、句法和西方語言及其語法和標點。在中國的書面語系統中,已經存在著文言與白話的對峙,這種對峙不能簡單地被理解為文言與口語的對峙。以白話書面語為主要來源的現代白話的基本取向不僅是反對文言,而且也是超越方言,創造出普遍語言。其后來的結果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制定‘普通話’方案,即創造以方言為基礎又超越方言的普遍口語。”[1](P1512)實際上,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的語言大眾化討論中,就已經出現了對“現代中國普通話”的提倡與探討。可見,現代白話文取得與“民族語言”一致性的關鍵,就在于它向廣大民眾的開放,在于它的全民性、大眾性,在于它實際為全民共用的書面語言體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綜上所述,在“民族意識”的調整下,現代白話被日益定型成為一種“群體化”的公用型書面語言。其特征在于:其一,現代白話在資源層面表現出對“大眾群言”[10]的空前重視,以及對既有文人表述傳統的極力否定與輕視;其二,現代白話日趨關注民眾的接受能力,一切語言手段的運用,都以方便群眾讀解欣賞為前提,而表達者在其中個性的滲透與傳達則遭到了潛在的排擠與壓制;其三,現代白話表意的“及物性”得到了強調,從而去除了語義障礙存在的可能性,為它的公用化、普遍化創造了條件;同時,又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個性化與詩意化的表意空間的狹仄。可見,以對“文人傳統”以及“個性”與“詩性”的缺失為代價,現代白話被成功地塑型成為統一化的民族統一語言。就此而言,白話的“現代性”品格,實際就蘊含于語言“民族性”“統一性”的獲得中,白話的“現代性”與“民族性”“統一性”之間形成了某種同構性的關系。
三、“民族性”與“現代性”同構的語言實踐
語言之“民族性”與“現代性”的同構,成為現代白話的基本特征,而毛澤東的語言風格,則是這種語言意識的成功實踐。
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就開始強烈關注“整頓文風”的問題,在《反對黨八股》《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重要文章中,都專門涉及文學的語言問題,顯示出他作為政黨領袖,對于語言與人思維方式間內在關系的敏感與重視。《反對黨八股》是毛澤東語言觀念的鮮明體現。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羅列了八條“八股”,其中前五條“空話連篇,言之無物”“甲乙丙丁,開中藥鋪”等等,都極力推崇語言對思想的真實反映、直接傳達,不主張在語言中蘊涵個人的氣質個性與深層意蘊。而后三條“不負責任,到處害人”“流毒全黨,妨害革命”“傳播出去,禍國殃民”,則更將語言問題上升到了是否有利于社會文化建設與革命形勢發展等政治高度,使語言表達是否“及物”成為衡量政治覺悟水平高低的潛在標準。
毛澤東的語言風格,正是上述“及物”化語言觀的成功體現。在毛澤東的文章中,表意準確精當、語言規范純正、暢達明快,少有歐化痕跡。由于現代白話的形成最初是以西方語言為學習對象,因此一直存在著“歐化”傾向,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眾語”討論及20世紀40年代“民族形式”論爭中,這也成為新白話一直遭受詬病之處。過度“歐化”的白話,往往過分注重專業詞匯的運用以及句子成分的層累,不容易為文化水平較低的讀者接受。這一點,即使在當時提倡“俗語文學革命”的瞿秋白筆下也是非常明顯的,更不用說茅盾、胡風等人。而毛澤東的文章則基本消除了“歐化語”的痕跡,從20世紀20年代起便做到了暢達、規范。如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開篇即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斗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11](P3)開門見山地提出問題,并以明朗的語氣直接進行分析,思路清晰,表現出一種游刃有余的語言運用能力。在講求規范簡明的同時,毛澤東語言還能夠深入生活,從為人熟知的現實世界中擷取能夠傳達內心思想意識的形象載體,較容易引發讀者的共鳴。如《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一文,在談到小資產階級時,說他們“發財觀念極重,對趙公元帥禮拜最勤,他們看見那些受人尊重的小財東,往往垂著一尺長的涎水”,窮形盡相地描摹出對象的可鄙嘴臉。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他形容農民運動:“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逼真地再現了農民運動的熱情與力量。而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毛澤東形容中國革命的高潮時說:“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的一個嬰兒”。以生活化的詩的語句,抒發著自己對于行將到來的革命高潮的熱忱與期盼。毛澤東還善于從古代歷史、文學中,從群眾生活中吸收大量的成語、典故、熟語和格言警句,并加以提煉改造,賦予新的內涵。如“愚公移山”“實事求是”“重于泰山”“輕于鴻毛”“即以其人之道,還制其人之身”“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誡;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放下包袱,開動機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欽差大臣滿天飛”“東風壓倒西風”“懶婆娘的裹腳,又臭又長”“眼睛向下”“紙老虎”“小腳女人”等等。這就使古語與民間用語紛紛獲得了新的生命,走進了現代國人的語言視野,充實了他們的現代漢語資源。另外,毛澤東還注重向西方語言學習,盡力使自身的語言表達體現出論證的邏輯性、思維的縝密性、概念的準確性和句子成分的豐富性。如《改造我們的學習》:“如果我們回想一下,我黨在幼年時期,我們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和對于中國革命的認識是何等膚淺,何等貧乏,則現在我們對于這些的認識是深刻得多,豐富得多了”。以假設句式,成功構建起不同時期不同認識狀況的比較,做到了邏輯清晰、層次分明、語意精到、規范整齊。
毛澤東語言的成功,在于能夠以清晰思想,統領語言手段,使各種詞語與句法成分,恰當地匯聚為一個有效的表達工具,充分發揮語言的傳達功能,且不失生動形象,格外具有說服力。同時,毛澤東的語言實踐,還為現代白話確立了“民族性”與“現代性”同構的典范,推動著當時的眾多知識分子,日漸意識到自身語言身份的獲得與實現,惟有通過統一的簡明白話,驅除表達中種種資產階級的、封建意識的語言質素,以通用型的語言形式,實現群眾對自身表達的普遍接受,才能真正以文學創作匯入現代中國的文化建設,才能通過語言表達,獲得自身文化地位的確認。在這里,能否實現創作中“民族語言”的運用,已經被當時的眾多知識分子視為能否在即將到來的新型社會中得以立足的必備手段。因此,盡管當時多數知識分子在運用“及物”性語言實踐時感到極為吃力,但作家們仍然堅定地扭轉姿態,全心全意去接受群眾語言、包括一向為自己所疏遠的鄉言土語的沖擊與改造。正如李陀所言,在毛澤東語言形式的號召下,“知識分子的寫作已經不再是簡單地寫小說詩歌,寫新聞報導,寫歷史著作,或是寫學術文章,它獲得了另外一種意義,即經過一個語言的(文體的)訓練和習得過程,來建立寫作人在革命中的主體性。在這個過程中,千千萬萬個知識分子正是通過‘寫作’,完成了從地主階級、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立場向工農兵立場的痛苦的轉化,投身入一場轟轟烈烈的革命,在其中體驗做一個‘革命人’的喜悅,也感受‘被改造’的痛苦;在這個過程中,也正是‘寫作’使他們進入到創造一個新社會和新文化的各種實踐活動,在其中享受‘理論聯系實際’的樂趣,也飽嘗意識形態領域中嚴峻的階級斗爭的磨難。”[12]也許正是這種表里一致的語言表達,才使得知識分子在傳統語言詩性傳達模式消泯后,能夠借助于語言傳達實效功能的體現,重新確認自己在現代文化進程中的積極作用及特定地位。綜觀丁玲、老舍、趙樹理、肖乾、馮至、何其芳等,在20世紀40年代至解放后十七年的語言演變軌跡,幾乎都反映出了上述“及物”性的語言表達追求。
[1] 汪暉.地方形式、方言土語與抗日戰爭時期“民族形式”的論爭[A].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下卷:第二部[M].北京:三聯書店,2004.
[2] 鄧實.雞鳴風雨樓獨立書·語言文字獨立[J].政藝通報,1903,(23),轉引自羅志田.國家與學術:清末季初關于國學的思想論爭[M].北京:三聯書店,2003.
[3] 章太炎.我的生平與辦事方法[A].章太炎的白話文[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
[4] 章太炎.規《新世紀》[A].轉引自姚奠中、董國炎.章太炎學術年譜[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
[5]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卷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 章太炎.尚賢堂茶話會諸名流之演說[A].轉引自姚奠中,董國炎.章太炎學術年譜[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
[7] 胡適.國語運動與文學[A].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語言文字研究[M].北京:中華書局,1993.
[8] 胡繼存,謝德風編.民族自決問題[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8.
[9] 埃里·凱杜里.民族主義[M].張明明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
[10] 王一川.近五十年文學語言研究札記[J].文學評論,1999,(4). [11] 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A].毛澤東選集(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2] 李陀.汪曾祺與現代漢語寫作——兼談毛文體[J].花城,1998,(5).
責任編輯:馮濟平
The Integration of the Modern Vernacular Development by National Consciousness
LIU Quan
(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
In the debate of "national forms", "unity" and "independence" have become an internal standard of modern vernacular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This "nationalization" of the language concepts established on levels of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practical issue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dir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vernacular, and finally established it as a public written language for the masses. Mao Zedong's writing style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successful practice of this vernacular concept.
national consciousness; vernacular Chinese; integration; Mao Zedong
I206.6
A
1005-7110(2014)06-0014-05
2014-09-28
劉泉(1974-),女,山東青島人,青島大學漢語言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