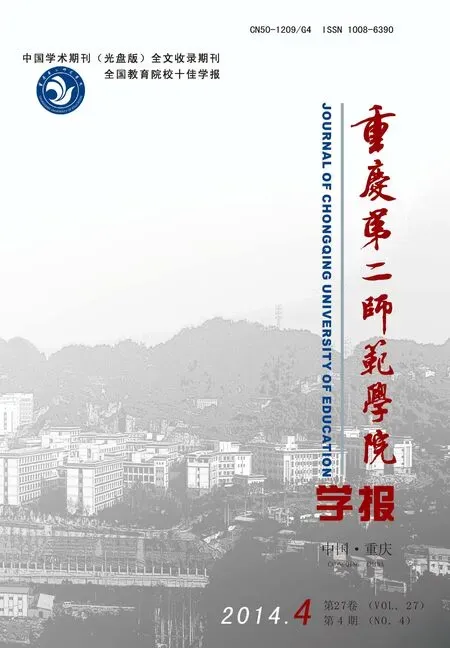不能承受的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歷史書寫之輕
孫景鵬
(福建師范大學(xué) 文學(xué)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戴燕教授曾在《文學(xué)史的權(quán)力》一書中指出:“一旦進入對中國文學(xué)史的思考,便會有問題隨之產(chǎn)生。”[1]27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在中國文學(xué)史上的書寫,就是一個值得研究、亟待解決的問題。比如,洪子誠的《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史》、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史教程》、丁帆和朱曉進主編的《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等,都沒有專章專節(jié)書寫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朱棟霖主編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史》,對臺灣文學(xué)和香港文學(xué)作了專章論述,但沒有對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專章專節(jié)的書寫;目前僅有山東大學(xué)、福建師范大學(xué)等22所院校編寫的《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史》和王慶生主編的《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史》等,在個別章節(jié)如“少數(shù)民族小說”,對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進行了書寫。因此,重新重視對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的書寫,勢在必行。筆者擬從“認同與歸屬”、“劣勢和習(xí)慣”、“歧視與反思”等幾個方面探討這一問題,以期拋磚引玉。
一、認同與歸屬
認同問題非常重要。著名心理學(xué)家弗洛伊德曾將其視為個人與他人、群體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趨同的過程;著名學(xué)者黃平也指出,認同就是“群體中的成員在認知與評價上,產(chǎn)生了一致的看法及其感情”[2]133;查爾斯·泰勒則從文化的層面指出,認同問題關(guān)涉?zhèn)€體或族群安身立命的根本。因此,我們首先要解決認同問題。
20世紀(jì)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由中央民族學(xué)院教師發(fā)起,在報刊上展開了對“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這一概念的討論,包括是否存在“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它的定義是什么,它包括哪些范圍,它有何特點,等等。但最終也還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并沒有對以上問題達成一致的認同。然而,人們要研究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就無法回避這些根本性的問題。
有學(xué)者指出:“嚴(yán)格地說,只有同時具備少數(shù)民族身份和民族認同①的作家,才能稱為少數(shù)民族作家,其創(chuàng)作的作品才能歸入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范疇。”[3]117而由中國作家協(xié)會和國家民族事務(wù)委員會聯(lián)合主辦的、我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的最高獎項——“駿馬獎”,也明確規(guī)定其評獎范圍只限于“少數(shù)民族作者用漢文或少數(shù)民族文字出版的文學(xué)作品”[4]。此外,趙志忠教授也認為:“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的界定只需一個條件,即‘民族出身決定論’。只要你是少數(shù)民族出身,無論你寫什么題材的作品,你和你的作品都應(yīng)該納入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范圍。”[5]5
相對而言,前者的標(biāo)準(zhǔn)非常嚴(yán)格,后兩者的標(biāo)準(zhǔn),則寬松得多,也就是說,只要擁有少數(shù)民族作家的身份,其創(chuàng)作的文學(xué)作品都視為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但是,即便政策如此寬松,也排除了許多優(yōu)秀之作,比如:不具有少數(shù)民族身份的作家所創(chuàng)作的反映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人們生產(chǎn)生活的作品。
那么,究竟什么是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怎樣劃分某一作品是否可以歸屬為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呢?要清楚地回答這個問題,還是相當(dāng)困難的,至今,文學(xué)界仍沒有達成統(tǒng)一的標(biāo)準(zhǔn)。少數(shù)民族作家描寫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人物或生活的文學(xué)作品,人們普遍認為是“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但是,漢族作家描寫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人物或生活的文學(xué)作品呢?少數(shù)民族作家以少數(shù)民族特有的視角和理念,描寫漢族地區(qū)人物或生活的文學(xué)作品呢?比如,藏族著名作家阿來,他的曾獲矛盾文學(xué)獎的長篇小說《塵埃落定》,文學(xué)界公認其屬于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但是,像王朔這類“京味小說家”,像姜戎的《狼圖騰》這類描寫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人物生活和風(fēng)土人情的文學(xué)作品,在我們當(dāng)前的文學(xué)史中,都沒有歸屬到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的行列。而像沈從文、蕭乾、端木蕻良、舒群、李準(zhǔn)、霍達、張承志、阿來等少數(shù)民族作家的作品,在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史上,也沒有作為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來進行專章專節(jié)的書寫。這種對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的書寫,其實是非常不妥的;這種對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輕視的現(xiàn)狀,也是令人極其不安的。
因此,我們必須改正在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認識上長期存在著的重大偏差——只有用少數(shù)民族文字書寫的、反映少數(shù)民族生活題材的作品,才算是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這種錯誤的觀點一直霸占著文學(xué)的話語權(quán),其觀點“根本無視我國各民族人民雜居相處、各民族文化融會交流的歷史特點,不符合許多少數(shù)民族作家使用漢文創(chuàng)作,反映各民族生活的客觀事實,把相當(dāng)一部分重要作家排斥在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之外。”[6]2事實上,凡作家所創(chuàng)作的文學(xué)作品,只要反映了某一特定少數(shù)民族的生活,不管其作者是否擁有該民族的身份,都理應(yīng)歸屬為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
綜上所述,首先,我們要對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有一個普遍的認同;其次,我們要重新界定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的概念,把一些目前還沒有歸在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中、但事實上又屬于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的作家和作品,重新歸屬到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之中;最后,也是最要的,我們在中國文學(xué)史的書寫過程中,要開辟專章專節(jié),著重講述在中國文學(xué)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
二、劣勢和習(xí)慣
縱觀中國文學(xué)史,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長期以來都處于劣勢,一直沒有得到應(yīng)有的重視。首先,少數(shù)民族一般處于偏遠地區(qū),人口數(shù)量少,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滯后。雖然我國少數(shù)民族聚集區(qū)面積很大,但那些地方往往地廣人稀、自然條件比較惡劣,供電供水、交通運輸?shù)雀黜椈A(chǔ)設(shè)施不夠完善,新聞出版、文化傳媒等各項公共服務(wù)比較落后,所有這些原因共同導(dǎo)致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難以得到較好發(fā)展和廣泛傳播。
其次,中國漢族人口的比例雖然總體呈下降趨勢②,但依然占據(jù)總?cè)丝诘?1.51%[7]15;顯而易見,少數(shù)民族在人口上也同樣處于劣勢地位。更重要的是,少數(shù)民族人民并沒有繼續(xù)保持自己民族的特色,并且,由于雜居于漢族之間,基本上都失去了本民族富有特色的活動和互相獨立的地位,之后,逐步被漢民族所同化。雖然這種同化并不是漢民族有意為之,而是歷史向前發(fā)展的不自覺的規(guī)律使然;但是,如果不采取一定措施,少數(shù)民族逐步被漢民族同化的趨勢是不可阻擋的。事實上,不僅漢民族不夠重視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被同化了的少數(shù)民族也不重視自己民族的文學(xué)。
再次,在舊中國③的歷史條件下,除了像老舍、沈從文、蕭乾、端木蕻良、舒群、李準(zhǔn)等這種眾所周知的作家外,少數(shù)民族作家基本上都沒有能力出版?zhèn)€人文集。他們的作品大多散見于各種報刊、雜志之中,久而久之,便淹沒于各種舊的綜合性報刊和小雜志之中了。因此,后代乃至同時代的作家就很少有人去搜集,更不用說去系統(tǒng)地整理了。既然不被重視、沒有文集,也就很少能流傳下來;不能流傳,自然就不能傳播、不能被世人學(xué)習(xí),因此,“欣賞”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這種狀況一直持續(xù)到20世紀(jì)80年代,可以說是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一個非常大的劣勢,是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發(fā)展中一個致命的弱點。
有學(xué)者指出:“長期的無償幫助已經(jīng)使受助者形成了對政府的嚴(yán)重依賴心理,認為脫貧和發(fā)展全然是政府的責(zé)任,與自己無關(guān)。這種扶持模式以及由此導(dǎo)致的受扶持民族主體意識的缺失,使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發(fā)展更為艱難:不僅傳統(tǒng)扶持模式難以為繼,扶持方苦不堪言,少數(shù)民族本身對自己的發(fā)展也倍感茫然、缺乏自信。”[8]111經(jīng)濟如此,文化亦然。大多數(shù)人,乃至很多主體意識缺失的少數(shù)民族人民,面對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史對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書寫之輕這一現(xiàn)狀,不思考、不質(zhì)疑,甚至不管不問,已經(jīng)習(xí)慣了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史對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極其輕視的書寫現(xiàn)狀;形成習(xí)慣后,他們大多再也不會想著改變這種書寫之輕的現(xiàn)狀,更不用說為此付出努力了。
于永正說過:“小時候,人是習(xí)慣的主人,而成人之后是習(xí)慣的奴隸。”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習(xí)慣具有非常強大的力量。科學(xué)研究表明,“改變”是一件難度最大的事情,人們往往習(xí)慣于接受自己目前的狀態(tài),也就是說,“安于現(xiàn)狀”是大多數(shù)人的生活習(xí)慣。事實上,人們對中國文學(xué)史的書寫也同樣受“安于現(xiàn)狀”這一習(xí)慣所支配。縱觀中國文學(xué)史,各種權(quán)威的、常見的版本,都很少書寫到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盡管如此,人們依舊被“安于現(xiàn)狀”這一習(xí)慣所影響,如溫水中的青蛙,逐漸習(xí)慣了這種書寫之輕的狀態(tài),逐步接受了當(dāng)今文學(xué)史的書寫現(xiàn)狀,并且從未嘗試著去改變。
鑒于以上情況,我們必須更加重視對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的書寫,加強對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的研究。要從政策上加強對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的扶持力度,放寬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作家進入作協(xié)的條件;從經(jīng)濟上對少數(shù)民族作家的生活和創(chuàng)作、對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作品的發(fā)表和出版等給予大力支持。不過,最主要的,其實還是少數(shù)民族作家自身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創(chuàng)作出更加優(yōu)秀的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作品。這是一個“適者生存,不適者被淘汰”的社會,改變依賴和安于現(xiàn)狀的不良習(xí)慣、增強本民族文學(xué)實力和民族自信才是最根本的,扶持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三、歧視與反思
有學(xué)者指出:“在一個相當(dāng)長的時間里,由于政治的原因——主要是民族歧視的殘余影響,一些重要的少數(shù)民族作家有意或無意地隱匿了自己的民族成分。”[6]1拿大家耳熟能詳?shù)纳驈奈膩碚f,他曾談到苗族的遭遇:在舊社會,苗族女人生的孩子是不能參加科舉考試的,而“苗雜種”的侮辱稱謂也常常跟著苗族人民,這些可能是沈從文直到1976年才把自己的民族由“漢族”改為“苗族”的重要原因。“對少數(shù)民族作家的歧視”這一情況在滿族作家身上表現(xiàn)得更加明顯,“排滿”現(xiàn)象在舊中國更是異常普遍。辛亥革命后,滿族在中國的地位一落千丈,歧視便隨之而至。更有甚者,出于對滿族人的痛恨,把滿人視為糞土,連乞丐都不如。人們對滿族的歧視與仇恨,使得滿族作家也不能幸免。事實上,苗族和滿族只是被歧視的少數(shù)民族的代表;既然少數(shù)民族如此被歧視,那就更談不上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了。
此外,我們對“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還有另一種更為隱性的歧視。著名學(xué)者梁庭望先生曾明確指出:“在一般人的意識中,存在著漢文學(xué)對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影響的單向思維,很少意識到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也同樣對漢文學(xué)產(chǎn)生影響,這與中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關(guān)系是不相符的。”[5]3其實,這種歧視才是最大的歧視。憑什么就不做調(diào)查分析、不實事求是、武斷地認為從來都是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受漢文學(xué)的影響呢?
就拿對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產(chǎn)生重大影響的六大家“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來說,被譽為“人民藝術(shù)家”、“語言大師”和“京味小說大家”的老舍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六大家之一的漢文學(xué)大家郭沫若曾贊賞老舍的作品“寸楷含幽默,片言振聵聾”[9]203;六大家之一的劇作家曹禺也曾盛贊老舍說:“他運用北京話的本領(lǐng),更叫我佩服得五體投地。”[10]席揚教授也曾指出,老舍小說的成就甚至超過了魯迅。事實上,“老舍是京味小說的集大成者,他的一系列京味小說,最徹底地繼承了曹雪芹、文康的藝術(shù)風(fēng)格,使京味小說的題材更加廣泛,語言更加精練,幽默更加成熟,并且使京味文學(xué)最終成為中國文壇上的一個流派——京派。”[5]89
像老舍一樣,少數(shù)民族作家及其作品蘊藏著獨特的民族文化、民族意識和民族信仰。席揚教授曾指出:“審美自覺地把自己的運動擺入整個民族文明建構(gòu)的歷史,從而使自身獲取永恒,也就成為藝術(shù)創(chuàng)造主體的自覺的理性認識。在這一自覺里,民族意識將在導(dǎo)向世界、導(dǎo)向未來的宏觀格局中獲取自己的審美魅力。”[11]733拿回族作家張承志來說,他在《黑駿馬》中表達的對草原的依戀之情,他在《金牧場》中表現(xiàn)的理想主義的神力,他在《北方的河》中隱喻的對祖國深深的熱愛之情,他在《心靈史》中帶給人們的對于民族信仰、民族歷史和民族文化的啟示,都因為他是一個少數(shù)民族作家,他的內(nèi)心深處有著本民族所特有的意識與信仰。他的民族意識與信仰使他的作品在導(dǎo)向世界、導(dǎo)向未來的宏觀格局中獲取了獨特的、永恒的審美魅力。
中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如此優(yōu)秀,以至于趙志忠教授曾自豪地指出:“中國少數(shù)民族民間文學(xué)尤為突出。那絢麗多姿的少數(shù)民族神話,那令世界震驚的少數(shù)民族英雄史詩,那多姿多彩的少數(shù)民族敘事長詩等等,都是不可多得的藝術(shù)珍品,在中國乃至世界文學(xué)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5]6”
由此觀之,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對漢文學(xué)貢獻巨大。但是,由于對少數(shù)民族乃至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的歧視,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一直未能名正言順、光明正大地進入中國文學(xué)史,更談不上掌握文學(xué)史書寫的話語權(quán)了。
事實上,我們不僅要認識到這種歧視,還要對其進行反思:中國文學(xué),是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文學(xué)。多民族文學(xué)的價值如何體現(xiàn)?特別是“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它的價值如何體現(xiàn)并得到人們的認可呢?這是一個必須高度重視和認真思考的問題。
有學(xué)者指出:“世界各民族的文學(xué),無一例外的均包含著兩個有機的組成部分,即民間的口頭文學(xué)和書面的作家文學(xué)。”[12]1進入21世紀(jì)以來,中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fā)展,“書面文學(xué)如雨后春筍,蓬勃發(fā)展,各民族都出現(xiàn)了自己相對穩(wěn)定的創(chuàng)作隊伍,更為可喜的是很多民族的作家都出版了作品集、作品選以及專集等。”[13]49但是,飛速發(fā)展的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背后,是不是入選標(biāo)準(zhǔn)和出版標(biāo)準(zhǔn)的降低?是不是和突飛猛進的經(jīng)濟發(fā)展一樣,同時也產(chǎn)生了很多文學(xué)泡沫?還有,這種繁榮的背后,是不是一種虛假繁榮呢?
隨著近年來,國家把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作為二級學(xué)科單列出來,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國家對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的重視。但是,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和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本是水乳交融、血肉相連的,如果把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單列出一個學(xué)科,看起來是不是有些割裂了其與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的關(guān)系?
正如學(xué)者李云忠所言,“中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是整個中國文學(xué)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雖有其自身的特點和相對的獨立性,但同大于異”[14]1,那么,如果把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像“臺灣文學(xué)”和“香港文學(xué)”一樣單列出來,整部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史分為四個或五個部分④來書寫,是否是一種新的歧視呢?難道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就不可以和漢民族文學(xué)一起放在主要部分來書寫,以此體現(xiàn)漢民族和少數(shù)民族血脈相通、水乳交融的特點嗎?還有,這種“拼盤式”的書寫是否是一種權(quán)宜之舉?是否只是為了給目前一小部分反對“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歷史書寫之輕”的人一個交代呢?
此外,如果單獨把少數(shù)民族作家列出來,和魯迅、曹禺、王蒙、莫言等這些作家一視同仁,進行專章專節(jié)的書寫;是不是從整體上來看,書寫的標(biāo)準(zhǔn)會不太統(tǒng)一?少數(shù)民族作家的入室標(biāo)準(zhǔn)是不是在無形中被降低了?這種“融入式”的書寫是不是也不夠科學(xué)?
以上這些疑問,在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發(fā)展愈來愈快、地位愈來愈重要的今天,仍然值得我們深思。21世紀(jì)將是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作家不斷涌現(xiàn)、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大放異彩的世紀(jì),如何改變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史對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的書寫之輕這一現(xiàn)狀,就顯得愈來愈重要。
綜上所述,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是在各民族的合作與斗爭中發(fā)展、融合而成的,“中國文學(xué)史,也浸透了各民族文化的墨跡,是各個民族人民共同寫成的,每個民族都程度不同地為發(fā)展我國豐富多彩的文學(xué)貢獻了自己的智慧和勞動”[15]12,我們理應(yīng)給予其公正、合理的評價,并在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史的書寫中,以更加公正、更加合理的形式書寫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
注釋:
①民族認同:指個體對自己所擁有的民族身份的主觀承認,具體表現(xiàn)為對本民族價值觀念、行為規(guī)范、文化傳統(tǒng)的歸屬感,有強烈的文化色彩。
②1953年,漢族人口占總?cè)丝诘?3.94%;1964年,漢族人口占總?cè)丝诘?4.24%;1982年,漢族人口占總?cè)丝诘?3.32%;1990年,漢族人口占總?cè)丝诘?1.96%;2000年,漢族人口占總?cè)丝诘?1.59%;2010年,漢族人口占總?cè)丝诘?1.51%。此數(shù)據(jù)根據(jù)國家統(tǒng)計局人口和就業(yè)統(tǒng)計司編寫的《中國人口和就業(yè)統(tǒng)計年鑒》,北京:中國統(tǒng)計出版社,2013年,第15頁。
③此處的“舊中國”一般指“通過改革開放,經(jīng)濟取得飛速發(fā)展”之前的中國。
④四個部分,即漢民族文學(xué),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臺灣文學(xué),香港文學(xué);五個部分,即漢民族文學(xué),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臺灣文學(xué),香港文學(xué),澳門文學(xué)。
參考文獻:
[1]戴燕.文學(xué)史的權(quán)力[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2.
[2]黃平.當(dāng)代西方社會學(xué)·人類學(xué)新詞典[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3]張永剛,唐桃.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民族認同與創(chuàng)作價值問題[J].文藝?yán)碚撆c批評,2010,(1).
[4]全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創(chuàng)作"駿馬獎"評獎試行條例(2008年2月14日修訂)[N].文藝報.2008-02-28.
[5]趙志忠.民族文學(xué)論稿[M].沈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5.
[6]吳重陽.中國現(xiàn)代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概論[M].北京:中央民族學(xué)院出版社,1992.
[7]國家統(tǒng)計局人口和就業(yè)統(tǒng)計司.中國人口和就業(yè)統(tǒng)計年鑒[M].北京:中國統(tǒng)計出版社,2013.
[8]李成武.探尋人口較少民族的發(fā)展之路——讀《人口較少民族實施分類發(fā)展指導(dǎo)政策研究》[J].當(dāng)代中國史研究,2012,(6).
[9]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學(xué)編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2.
[10]曹禺.我們尊敬的老舍先生——紀(jì)念老舍先生八十誕辰[N].人民日報.1979-02-09.
[11]席揚.選擇與重構(gòu):新時期文學(xué)價值論[M].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89.
[12]陶立璠.民族民間文學(xué)理論基礎(chǔ)[M].北京:中央民族學(xué)院出版社,1990.
[13]鐘進文.中國人口較少民族書面文學(xué)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
[14]李云忠.中國少數(shù)民族現(xiàn)代當(dāng)代文學(xué)概論[M].沈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6.
[15]中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學(xué)會編.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論集(二)[C].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5.